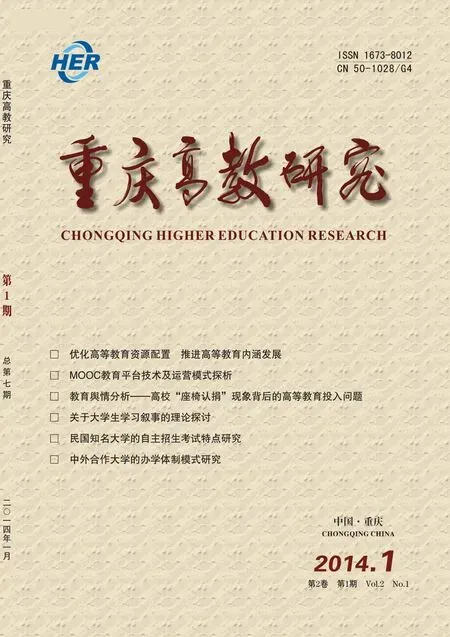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探析
吴 薇, 马 杰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潘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界的学术泰斗,亦是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于潘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过深入探析。但是,关于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系统探讨至今仍然鲜有涉及。事实上,潘先生虽然没有对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以任何论文或专著的形式进行过专门系统的阐释,但他一直以来非常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并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这一思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愈加遭遇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文化困境。如何正确处理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文拟从潘先生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方面梳理归纳其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思想内涵与特点,以期为我国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工作者提供几点启示。
一、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内涵
潘先生虽然没有围绕“什么是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程度如何”“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如何国际化”这几个基本问题进行过专门系统的阐释,但是潘先生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思想渗透于他的国际比较等各种研究与实践中。笔者通过梳理潘先生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发现其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思想包含“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
(一)引进来
“引进来”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和“从哪引”。是依附地引进还是借鉴地引进?是只从发达国家引进还是兼从发展中国家引进?“如何引”和“从哪引”最终取决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文化自觉度与国际视野阈。潘先生在“如何引”和“从哪引”这两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广阔的研究视阈。
在“引进来”的过程中,“如何引”是我们首要把握的原则。清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引进带有一定的依附性,但是潘先生创立的高等教育学科却是“土生土长”,带有浓厚的本土气息。“‘土生土长’的缺点就是‘土里土气’,视野不宽。”[1]高等教育学科要持续发展,必然要有所引进。早在1988年,潘先生就在《十年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进展》一文中谈到,西方合理的、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不应当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提倡而轻率地否定。其次,即使是一些在西方可行、值得借鉴的东西,也还有个可行性的问题,即是不是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问题[2]。 可见,潘先生在引进他国高等教育先进理论成果时,是本着“有没有借鉴之处”与“可不可以借鉴”的原则,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以他国为镜,而不是盲目地生搬硬套。此外,在可借鉴的条件下,潘先生更强调批判性地吸收与创造性地发展。以马丁·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发展阶段论的引进为例,潘先生认为,马丁·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是在研究美国和战后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并非具有放之四海皆准的解释效力。高等教育研究者必须用历史与发展的眼光看待马丁·特罗教授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立足本土、立足国情,构建适合本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理论框架。潘先生在马丁·特罗教授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过渡阶段论”,充分论证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阶段所存在的局部质变推动总体量变的特征[3]。 可见,自高等教育学科建立伊始,潘先生从未故步自封,而是放眼全球,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以积极包容的姿态应对全球化大趋势,立足本土,有目的、有选择地吸收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
“从哪引”是“引进来”的另一核心要素。当中国的学者埋首于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时,潘先生的研究视野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而是凭借其敏锐的学术嗅觉,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拓展到发展中国家。潘先生认为,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固然重要,但是,并不是只有发达国家的经验才值得学习借鉴。1978年,潘先生先后访问了泰国、尼泊尔和科威特三个国家,深刻体会到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他在《泰国、尼泊尔、科威特三国的高等教育》一文中谈到:“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固然可以得到学习某些先进东西的好处,而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了解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的情况问题,也同样有可资借鉴之处,在某些方面尤能发人深省。”[4]作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不仅需要引进先进的理论,需要学习成功的经验,更需要了解与自己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潘先生利用厦门大学的地缘优势,开展了针对东南亚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如1983年《菲律宾的高等教育》、1986年《泰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通过考察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政策、专业结构、投资及师资等方面为同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提供了诸多宝贵经验与值得警醒的教训。
(二)走出去
潘先生不仅始终立足本土,以开放的姿态、谦虚的态度,主动借鉴地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切先进成果,他还身体力行,大力推广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潘先生认为,国际化的题中之意还在于中国研究者参与世界高等教育事务的话语权。通过平等对话、沟通理解,不仅介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就、问题,而且探讨世界高等教育的规律与趋势[5]。可见,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是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潘先生先后到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英国、新加坡、尼泊尔、科威特、美国、俄罗斯、荷兰、挪威、立陶宛等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成果积极向境外推广,促进高等教育的学术交流。他特别注重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开展合作,并与人合作编了一些英文高等教育著作,如《Legislation: The Guarantee of Development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NESCO, PROAP Bamkok, 1996)、《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y in China》(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1997)、《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Prospect,Chance-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Sydney: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Publishing House, 2002)等[6]。 这些英文著作在沟通中外高等教育学术理解、推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助力作用。此外,潘先生还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应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课题研究,促进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交流和学术的普及[7]。
正是由于潘先生不断践行着其“走出去”的国际化理念,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潘先生及其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如加拿大的许美德、美国的白杰瑞、挪威的阿里·谢沃。其中,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先生的著作《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Pan Maoyuan:A Founding Father of Chinese High Education Research)于2005年7月在挪威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正式出版,该书集中介绍了潘懋元先生创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历程并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的发展和研究趋势。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理念走向世界意义重大[8]。2007年,国际权威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收录的、在美国出版的国际著名学术刊物《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在第3期发表了潘懋元先生7篇学术论文。这7篇论文构成一个专辑,题为“潘懋元和中国高等教育”,涵盖了潘先生创建高等教育学科和各个时期关于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最主要的学术思想。该专辑的内容主要有“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走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关于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等。据悉,以专辑的形式在《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上出版个人系列论文还是史无前例的。潘先生系列论文的国际发表,表明了世界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高度认可,对进一步扩大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研究的世界影响意义深远[9]。
二、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特点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重要倡导者与践行者,潘先生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如何实现”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本土意识、广阔的国际视阈以及高度的责任担当,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际化道路。
(一)强烈的本土意识,主动借鉴而非被动依附
“如何引”是“引进来”的关键所在。在引进高等教育先进理论成果时,潘先生是“主动借鉴”地引进而非“被动依附”地引进。选择借鉴与选择依附,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借鉴是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以他国为镜,对照自己,吸取有益的经验;而依附是不顾本国具体国情,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照单全收、盲目套用现成模式。可见,借鉴的立足点是“本我”,而依附的立足点是“他者”。不少研究者不顾具体国情,迷失于“与国际化接轨”的口号,认为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法就是正确的、科学的,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西方高等教育的研究理论,导致研究成果缺乏原创性与创新性,结果出现“越‘国际化’‘现代化’也越‘边缘化’的情形”[10]。潘先生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特色、国际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客观的认识与理性的评价,始终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秉承“有没有借鉴之处”与“可不可以借鉴”的原则,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有没有借鉴之处”解决的是国外研究成果先进与否的问题;而“可不可以借鉴”处理的是与具体国情适合与否的问题。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都受其文化传统、历史条件、价值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高等教育的理论成果在当时当地或许具有成功的解释效力,但应用于别国别时则可能出现理论误导实践的情况。因此,“拿来主义”“生搬硬套”不可能是真正地“引进来”,只能是陷入“某国化”的被动依附与寄生局面。
(二)广阔的国际视阈,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
“从哪引”和“走向哪”反映了高等教育研究者国际视阈的广度,同时也影响着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发展深度。潘先生不仅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成果,更关注发展中国家,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地“引进来”,同时也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地“走出去”。从整体上讲,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无论在研究成果还是办学实践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优越感。美国著名学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就曾指出,美国高等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的范例[11]。 换言之,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与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这种论断难免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视阈产生误导——盲目排斥对非美国或非发达国家的研究。但是,潘先生并不迷信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圣经”,其研究视野没有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研究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他充分打开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不仅从发展中国家“引进”,主动学习借鉴,同时还“走向”发展中国家,将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推而广之、互通有无。可见,潘先生跳出了“发展中到发达”的单线学习借鉴,变为“发展中到发达”“发展中到发展中”的多线学习交流,由“单向引进”向“双向交流”发展。
(三)高度的责任担当,自信力与使命感兼具
“走出去”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并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能否走出”以及“走出去的程度”与高等教育研究者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力与使命感密切相关。信心缺失,难以“走出去”,即使勉强“走出去”,也难以“走远”。当“学科取向”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遭遇“领域取向”的西方高等教育研究时,部分研究者自觉本国高等教育理论成果“土气”,缺乏“走出去”的信心与勇气,不敢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同行一较高下,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化进程。潘先生不仅怀揣着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坚定信心,同时还秉承着将其推而广之的使命意识,通过编著高等教育英文著作,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等形式,身体力行地积极“走出”,力图突破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语言文化隔阂,扩大交流途径,沟通学术理解,将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更大的贡献。种种践行,体现了潘先生“大社会”的责任观: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分享不应局限于国内,而应走出国门,实现国内外同行的互通与共享。
三、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启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愈加遭遇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文化困境。如何正确处理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重要倡导者与践行者,潘先生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如何实现”这一问题上,以强烈的本土意识、广阔的研究视阈以及高度的责任担当为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笔者认为,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后生晚辈,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进程中,应注重提升文化自觉、拓展国际视阈以及树立“走出”信心,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更大的贡献。
无论是“主动借鉴地引进来”,还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地进出交流”,国际化的出发点与归宿均在本土。为了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同时避免迷失于“与国际化接轨”的口号,高等教育研究者应注重提升文化自觉。因为只有理性认识本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来龙去脉与演变趋势,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可度与自豪感,才能摆脱心理依附,防范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畸形发展。其次,研究视野切勿狭隘。“从哪引”“走向哪”不应局限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只有拓宽研究视野,挖掘高等教育研究的区域盲点,推陈出新,才能进一步丰富高等教育国际研究成果,充分实现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如浙江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受潘先生“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思想的影响,长期关注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借鉴引进,发展自身,同时还积极走出,推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先进成果[12]。笔者认为,限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浩如烟海的情况,不同研究机构根据自身的条件发展自己的特色区域研究对丰富高等教育国际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整体上引进多,走出少,这种“交流逆差”挫伤了高等教育研究者“走出去”的信心与勇气。但是,不迈出第一步就永远无法走向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者应树立起“走出去”的信心与勇气,以服务“大社会”的责任为使命,积极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切磋、互通有无,在吸收国外先进成果的同时,推介我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实现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交流与共享。
参考文献:
[1] 潘懋元.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与未来[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6(5):1-6.
[2] 潘懋元, 林叶枫. 十年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进展[J]. 中国高教研究, 1988 (Z1):12-23.
[3] 潘懋元,谢作栩. 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J]. 高等教育研究,2001 (2):1-6.
[4] 潘懋元. 潘懋元文集(卷四)[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03.
[5] 潘懋元. 国际论坛与国际话语[J]. 中国高教研究,2011(9):3-4.
[6] 冯用军. 试论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基于《潘懋元传》的考察[J]. 高等理科教育,2010(5):14-18.
[7] 潘懋元. 大学应当研究自己——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与特征[J]. 大学教育科学, 2003(1):1-4.
[8] 赖铮, 高晓杰. 让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始人》(英文版)评介[J]. 教育研究,2006(1):88-89.
[9] 刘志平. 潘懋元教授7篇论文在美国SSCI刊物《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发表[EB/OL].(2007-09-17) [2011-01-10]. http://che.xmu.edu.cn/news/hqjj/2007917150155.htm.
[10] 陈兴德, 潘懋元. “依附发展”与“借鉴-超越”——高等教育两种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2009(7):10-16.
[11] 阿特巴赫. 比较高等教育[M]. 符娟明, 陈树清,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 1985:34.
[12] 季诚钧. 潘懋元的比较高等教育思想[J].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2011(Z1):381-384.
——记我与潘懋元先生交往的点滴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