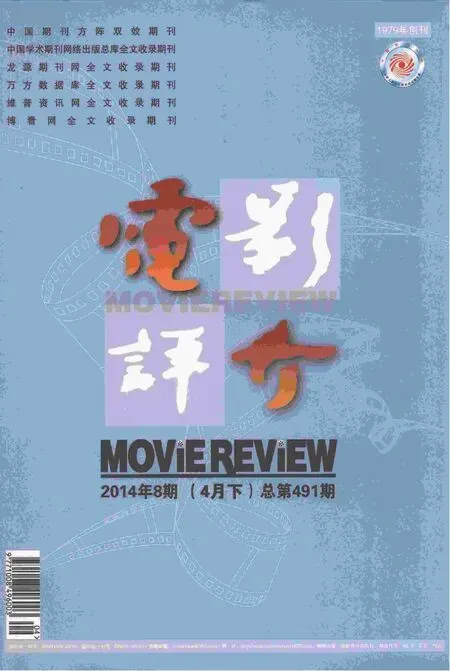王小帅影片中“边缘人”的行为符号特写
□文/罗 娜,广东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讲师

电影《我11》剧照
一
一定的封闭空间承载着人物的行为,当行为具有某种重复反复性时,此时的行为已上升到符号的特性,具有表意和象征的意蕴。电影中的每个画面分割下来都将代表一个典型空间里的场景,按照巴特的符号观点,画面是被分为三成意义的,即信息层、象征层和意指过程层。同样,麦茨认为影片表达应是内涵和外延的叠加。分析王小帅的影片场景或者说人物的各种行为,他们有着表现相似的行为趋向,比如人物对某件事情的一种极度的执着、父辈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对立反抗等,因此,从如此的信息层面,我们不难挖掘信息的背后实质是导演在有意贯穿一种超越时代的连续稳定的生活方式。第一个贯穿的行为符号为罪恶。王小帅在多部影片中让罪恶的行为曝露于观众视野中,《扁担·姑娘》(1998)里的“卖淫”、“杀人”;《二弟》(2003)里的“偷渡”;《青红》(2005)中的“强奸”;《日照重庆》(2009)中的“杀人”和“劫持人质”;在影片《我11》(2012)中更是进行了“强奸”、“杀人”和“纵火”的多重呈现。如上所述的罪恶上升到犯罪的程度,便必然受到法律的惩罚,比如《青红》中的小根和《我11》中的谢觉强被枪毙。除开法律上的犯罪,道德上的隐性罪恶意识更为浓厚。《极度寒冷》中多人的行为艺术以及齐雷最后的“自杀”行为,自杀是一种个人的自我选择,但齐雷最初的动机来自于对社会人性的考量,是一次欺骗大众的行为,站在大众的道德体系来说,这是对道德的反叛。西方历来有“原罪”的概念,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人类生而有罪,而“原罪”也是人类思想和行为上各种罪恶滋生的根源。“死亡与淫欲,是理解原罪的两把钥匙。”[1]“自杀”作为死亡的一种方式,可以当作“原罪”来理解。西方宗教认为自杀是对造物主的亵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恶。此外,对于“淫欲”,王小帅也并未避讳。同样,情欲是人类生理的本能,但在健全的道德风俗体系之内,王小帅表现情欲时显然是更为随性的个人激情表达,且往往处在不合时宜的年代或者生活环境。“比商业片深刻的文艺片陷入了举步维艰的状态,乐于沉思的爱情要么被哲学性思辨彻底解构,虚无化,要么在道德的平庸中磨砺了众多的敏感而多变的情感褶皱,不堪思想的荷重重回到平实的道德大地上,使多少渴望边缘想象的心灵惘然若失。”[2]《冬春的日子》中的冬和春,《扁担·姑娘》中的高平和阮红,《二弟》中的二弟和小女,《青红》和《我11》中的强奸犯,甚至包括《左右》(2007)中的玫竹和肖路——尽管玫竹是以爱的名义,但终究超越了道德和伦理。另外,“淫欲冲动”也视为潜在的罪恶意识:《扁担·姑娘》中的东子,《十七岁的单车》里的小贵,《我11》里的王憨。《四福音书》当中有“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东子、小贵和王憨实际并无“本罪”,更多的是生而有之的“原罪”。
二
王小帅的第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为《冬春的日子》,似人生独白,探问画家内心和灵魂,是一部真正散发出画家气息和专业素养的电影。第一部电影,王小帅便引出了关于艺术的行为方式。此后,在各部影片中,导演都会有意识添加关于人群的一种艺术追求。《极度寒冷》的艺术表达是一群在大学中学习画画的人制造的行为艺术,应该说这是第一次以电影的视角去关注这群人。《我11》中开篇的镜头就是王憨画画,时不时还穿插着王憨父亲对于艺术的见解。《扁担·姑娘》中阮红最初的梦想:做一名歌手,出自己的磁带。无可厚非,《青红》中青红和那群女孩子追寻的高跟鞋与漂亮的裙子都是平凡生活中对于不可触摸的艺术的象征。而《左右》中母亲的行为更是一场疯狂的“艺术”行为。王小帅对艺术行为的凝聚深刻展示了左手是生活,右手是艺术的矛盾冲突。
王小帅对死亡的描述伴随着犯罪与艺术的选择。“人类有史以来无数的经验晓喻这样一个无须用语言陈述的知识命题和逻辑判断:死亡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有限时间的必然归宿,它的生命的终极。”[3]王小帅乃至和他同时代的导演群体集体性地有对死亡的表达无意识。如《月蚀》、《苏州河》、《安阳婴儿》、《非常夏日》、《惊蛰》、《日日夜夜》、《紫蝴蝶》、《世界》等。王小帅中的直面死亡且追问死亡的电影来自《极度寒冷》,主人公的死亡经历了两次,一次是肉体的短暂性休克,一次是肉体永久的掩埋。《青红》的结尾是死亡、《我11》中的死亡是其叙述线且让人感到异常神秘甚至恐惧、《日照重庆》中的死亡一直是活着的人寻找的动机,死亡引导着活着的人走向目标、《左右》中的左右摆动来自于死亡对生命的威胁。除此之外,死亡不仅代表生命的真正消逝,两个关联事物之间的突然断裂也预示着某种死亡的诞生。《冬春的日子》里的冬和春的生活中的与世隔绝、淡漠和无情,最后春还是离开了冬,冬精神分裂,比之前的淡漠更为淡漠。旁白说:在我后来见到他的许多日子里,他一直这么坐着。很少见他拿起画笔画画,他说,他整个春天就是这么过来的。关于他和小春的事儿提的也很少。他说他们是最平常的一对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回忆的。这是生活中主导意识的“死亡”,心灵或者灵魂上真正对生活的一种无视。王小帅真正撇开了曾经死亡的厚重和宏大,今天人类的死亡体验总而言之是“个人化的,破碎的,日常的”[4],诸如疾病与车祸、自杀等意外事件和个人必然抉择等。导演对于死亡镜头的拍摄无疑不是在追溯平凡人的命运,形而上的对生存的问询与思考,镜头中的情绪无比的冷静和无言。
三
王小帅在行为中趋向于罪恶、艺术与死亡,并且让这些行为成为特有的标志性符号,呈现某种现代性和先锋精神。第一个现代性的表征体现为异化。个人的有别于大众思维的选择来源于社会的异化。《我11》中隐含的“文革”年代以及因特殊的年代而产生的小心翼翼的艺术、犯罪与死亡无疑不昭示着社会体制寄予人的个性扭曲和践踏。有评论者指出:《青红》称得上是为一代人的精神成长立传表达的,是一个“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又到哪里去”、“谁曾经是我”的命题。影片非常细致传神地表现了年轻人期望冲破命运,以及以他们的父母亲为代表的成人社会对他们的控制和限定的种种无望努力,于是陷入到一场在当时的体制背景下永远无法取胜的痛苦和挣扎之中,就像王小帅自述的那样,“在那个时候,人的自我意识和时代环境的冲突,以及人的求生意志是非常戏剧化:朦胧的自我意识已经产生,却不能掌控自己,大的环境是不确定的,自己也是不确定的。”
第二个现代的表征体系为游戏。从康德到席勒,他们在艺术的观念上提出“游戏”说,意指为自由、单纯、和娱乐,且提倡人的主体性。在体制性的社会里,王小帅关注的边缘人群集中在先锋艺术青年、忙碌于生计的城市底层人民以及生活在农村的“城市人”三类,他们在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的不和谐中始终保持对个体的意识和对自由的探寻,而在对自由的创造中,却把自由的游戏精神趋向了一种偶尔荒诞的人生体验。在城市化的经济大潮中东子躲在自己的小屋中冥思苦想,抽烟解愁。这种“躲”和“与世隔绝”的状态看似自由,却是被动与消极的人生状态。齐雷真正把人生当做实验和游戏来设计,而这部电影也被认为是“一个充满自恋和自虐的双重象征含义的重要的第六代电影文本,”[5]一方面反映了艺术家或者导演本身对所有的艺术表达媒介的某种“遮蔽性”的反抗选择,艺术家自身和导演再现了多种仪式性的场面,这实质就是一种自恋的戏谑和反讽,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出整个行为的本身就是一场对所有人开的玩笑甚至是宣泄。游戏的最后,看客没有如他所期待的的那样,但自己的身体却陷入了游戏的精神中不可自拔,以致真正走向死亡。游戏精神的结局即是身体死亡的宿命。东子和齐雷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文化守望人”,“这群守望人中有两种,一种是自我放逐;一种是坚守故园,过着清贫的日子,把文化当做一种宗教来恪守。”[6]而“在欲望化的狂欢中,他们都是现代性精神家园的迷路人,一群迷茫世界的精神漂泊者和梦游者。这种精神上的无家感和无根感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演化成了强烈的荒诞感”。[7]《十七岁的单车》里,单车是其核心,“偷”单车的背后引出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但“偷”的动机只是为了炫技和炫耀,包含着青春期小男孩的欲望和游戏的冲动,后来的走向也俨然验证了单车必然是游戏的道具。骑车换车的画面在镜头里飞速调换,你追我赶的一场似爱情的幼稚游戏以男孩之间的暴力结束。而我们重新观看在游戏追逐时小巷街道中旁人的表情,他们并无为这场追逐显得特别担忧和恐惧,相反,他们仅仅也只是认为这是一场闹剧,包括父母也缺席的闹剧。“偷”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但渴求的是一场艺术爱情的较量,最后却不得不以失败和离开的“死亡”结束。王小帅的潜意识表达中,这三种行为方式一直以不同的视觉或者叙事形式存在人的命运之中,而这一系列的贯穿和衔接就是一场游戏的开始、高潮和结尾。
第三个现代性表征体系为寻找。李泽厚曾提出“群体主体性”的概念,从这个意义出发,第五代导演正符合,王小帅一代的导演却已经从群体挖掘到个人的主体,但从群体中抽离出来的个人携带着内心的迷茫与焦虑,在应对强大的社会体制时,常常会如东子、齐雷以及小贵等一样,表现出异常的敏感、多疑甚至精神分裂。齐雷用自己的身体自残来获取认同与关注,《左右》中的母亲用身体来验证自己的爱和付出,《青红》和《我11》中女性身体的被强奸印证的是“一段随风而逝的青春,一种难以自主的宿命。”“身体”在王小帅的镜头中反复被隐喻和象征。身体是身份的象征,“身份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8]所有的人在异化的秩序中历经和反叛寻找身份,使其为真正的个体主体化。“与其相应的是第六代电影中常见的属于现代主义范畴的“寻找”和“流浪”的母题。很多影片充满了真诚执拗而苦涩的寻觅,展现了一种“在路上”的流浪的生存状态。”[9]《日照重庆》是典型的寻找文本。现实中的父亲寻找已经被枪决的儿子的身影,在寻找的路途中,儿子的形象得以重新被展现,而父亲的形象也得以完整建构。曾经的隔膜通过两个空间的不同节奏得以契合。这恰是站在导演的角度,他对边缘人寻找的最好诠释。
[1]吴飞.“对树的罪”和“对女人的罪”——奥古斯丁原罪观中的两个概念[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28-29.
[2]陈林侠.文化视阈中的影像叙事[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80.
[3]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87.
[4]李正光.第六代电影中死亡叙事的特异性分析[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7(4):62.
[5]陈旭光.精神的独语:黄建新、王小帅、张元、路学长[C].电影文化之维,2007:244.
[6]尹国均.先锋实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2.
[7]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30.
[8](美)赛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0.
[9]陈旭光.“影像的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比较论[J].文化研究,2006(1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