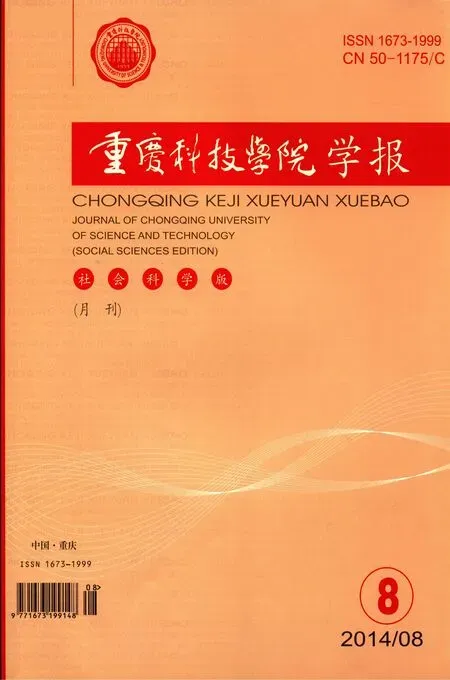中西哲学精神述要——兼论中国哲学的特质
耿芳朝
世人常论,哲学是关于终究至极的最普遍、最本质的学问,是各门科学的根源和基础,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和意义。若具体而论,则可谓见仁见智。马克思认为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冯友兰则认为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反思的思想。基于对该论题的不同认识,中西哲学精神的比较或许是彰显中西方文化根本差异的一个重要视角,从而也有利于在另一个侧面上透显中国哲学的特质。
一、“逐物之学”与“修己之学”
亚里士多德历来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看来,哲学起源于“惊异”,起源于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人们追求知识实是为了求知,其中展现的是为了知识和智慧而不断追求的探索精神。亚里士多德广泛研究众多领域的学问,涉及政治、经济、历史、自然科学等9个科学门类。早在他之前,针对自然论哲学家众说纷纭和智者学派莫衷一是意见的泛滥,苏格拉底深感希腊文明渐渐褪色,就开始反复与人追问“是什么”的问题,追问事物之为该事物之“德性”。他的学生柏拉图更是亲自建立了以传授知识和研究哲学为目的的学园,并与其老师一样,为衰落的希腊文明开出“药方”。因而,亚里士多德求知的精神和卓有的研究成就便不是偶然,它为西方哲学定下了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基调。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就确立了一种学以致知的观念,它以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作为追求的目标[1]198。这是向外探索的逐物求知的精神。古希腊自然哲学早期,西方哲学的始祖泰勒斯一开始就追问宇宙世界的本源。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元素论哲学家。苏格拉底努力“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也未能割断与自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向外探索的精神取向。在张志伟先生看来,希腊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的探索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西方哲学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基本倾向和科学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2]132。
然而,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从一开始就与西方传统哲学迥然相异。中国哲学最具源头意义的当属儒家和道家哲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讨论最多的是人生学说,即君子圣贤人格及其达成方法。曾子则将上述学说系统化为“三纲八目”的大人之学。孟子专注为“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般浩然之气的“内圣”修养。道家学派的老子极力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和“绝圣去智”,庄子醉心于“心斋”、“坐忘”和“超然物外”的修习,以此通达“逍遥游”和“泰山崩于前而安之若素”之境。在此过程中,他们所为并不为探索自然奥秘,也不为求索些关于事事物物的知识,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修为提高自己的修养,最终达到超乎言相的绝妙境界。传统中国哲学虽然并非全是如此,但在宏观上考量大多数都是这样,其所求所究虽有向外的“逐物之学”,但主要还是“反求诸己”的“修己之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子塑造的理想人格,已然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3]43。 并且这个传统是一贯而明显的,怠至张载、程子等人依旧如此。就是倡导“格致、居敬、穷理”之学的朱熹,其最终指向也还是心性涵养。这是明显与西方“逐物之学”相区别的“修己之学”。
这是就中西传统哲学精神源头而言的,西方传统哲学有“逐物求知”的倾向,中国传统哲学有“修己达志”的渊源。基于“逐物之学”与“修己之学”的分野,中西传统哲学走向了认知实践与伦理实践两种截然相异的途程。
二、认知实践与伦理实践
建立在“逐物之学”基础上的西方认知实践论,不但发达而且历史悠久,催生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从学科分类到洛克的人类知识的范围,再到培根的归纳法,目的都在于探讨科学认识、总结归纳知识,力图涵盖人类认知领域,指导人类现实实践。最典型的代表当数建立在大量严密系统科学知识和实验基础上的牛顿经典物理学,其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由此奠定了之后近三个世纪物理学的科学观,影响极其深远。此外,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哲学,颇具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而且广范涉及伦理学、美学、辩证法等众多学科的学问,宏观地探讨了人类思想、宗教、艺术、科学、经济、制度等领域的问题。人们不禁要问,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何有这样鲜明的知识“体系化”的倾向?究其渊源,不难发现:求知爱智的希腊哲人在对宇宙奥秘的探究中已经坚定地塑造了一种渴求智慧真理、推崇理性知识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逐物之学”和认知实践精神为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现代科学主义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这种知识论的实践主张在求取自然真知和探索宇宙奥秘精神的鼓舞下,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向未知领域勇往直前、对外部世界主宰和控制的力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去努力探索、学习,丰富科学知识,进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飞跃,最终依靠知识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建立起日益繁荣的物质文明。相较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传统哲学无“知行关系”的探讨、科学实践较多。那么,由其一以贯之的“逐物之学”和实践精神来看,西方近代科技的发达实是理所当然。
对比而言,中国传统哲学奠基在“修己之学”的基础之上,较为注重心灵的修养和人格的提升。对“知行关系”的探讨此起彼伏,实际上谈及的通常都是伦理道德践履而非科学实验,并且其旨归依然是修己、成人。它力图通过不断的修己功夫,寻求最终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即集道德与功业并隆而“内圣外王”。这种特定实践论的杰出代表当数集“真三不朽”于一身的心学大师王阳明,他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而且身居高位,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有平定叛乱的军功,终封侯爵。当然,在古代中国也有不少科学实践,据说墨子传人鲁班创造了可以在天上飞三天的载人木鸢;三国孔明也曾发明“木牛流马”机械化运输,但这些终因被嗤之为奇技淫巧而淡出传统中国的历史舞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若将人类认识与实践所求看作为“知”,所为视作为“行”的话,那么,在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中,前者所求的是伦理规范、修身养性和经世治国之“知”,与之相应的是修己成人、建功立业之“行”;后者所求则为自然现象、事物规律和宇宙奥秘之“知”,与之相应的则是系统的自然探索、科学实验之“行”。
三、宗教文化与诗史文化
谈到哲学和文化精神,总避不开宗教问题。因为哲学和宗教都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只不过它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前者诉诸认知理性,后者诉诸精神信仰。众多中西学者都曾谈论哲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我们且不谈神秘的宗教神迹和宗教体验,但是我们依然相信纵使科技再发达,宗教信仰依旧为人们所追求。因为它更多承载的是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超越人类自身有限性而抵达无限性的集中表达。
宗教信仰是西方民族五彩斑斓文化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底色”。问题是一向高举理性主义的西方文明为何“迷恋”于宗教文化而“不能自拔”,这要从西方文化的发源谈起。在传统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西方文化称为“两希”文化(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产物。如果说希腊文化孕育了西方文化中理性精神的话,那么希伯来的基督文化则浸染了西方宗教传统。同时,这两个文化传统又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以理性方式探究宇宙本体获取自然真知的希腊哲学中蕴含了宗教神学因素,古希腊哲学势必被基督教神学所取代;以信仰方式无限崇敬上帝获取道德良知的基督教神学中渗透了理性科学因素,理性化的托马斯神学势必成为正统的经院哲学[4]。就这样,理性传统与宗教文化并存便理所当然了。在西方现实中的主流社会,一个人若不去教堂、无宗教信仰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对其是毫无信任感可言的。西方社会,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著名的哲学家就是宗教信徒。在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中世纪,无论是教父哲学家还是经院哲学家,往往都特别重视基督信仰问题。经过长期宗教思想的沐浴和洗礼,宗教情结对西方人而言自然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佛教传入和道教建立之前,传统中国是一个重视“诗教”和史官文化的古老国度。前者即是孔子所强调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之类,其具体纲目则是有关待人接物、洒扫应对之学,是中国古代官学和私学的必修课。然而仅仅就这一点也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它至少可以溯源至周公“制礼作乐”的初衷。后者即为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美誉的史官文化,其突出的特色之一便是史学家秉笔直书的坚定、“春秋笔法”的褒贬和盖棺定论的评判。
在传统中国,庞大的社会结构建立在宗法姻亲基础之上,“国”只不过是放大了数倍的“家”,“君君臣臣”只不过是放大了的“父父子子”[5]37;因而“家”是“国”的一个缩影。官方有专门的史官负责修史,每个家族亦会修家族族谱。因而,在上位者一旦结党营私,必会见诸官方史书;为非作歹的普罗大众也会因其恶言恶行使族人蒙羞而见恶于家族成员,并且还会在族谱上被“记下一笔”。于是,违法乱纪、破坏伦常者将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由此形成了从官方修史到家族族谱著录的严密网络体系,其中的个人有默默无闻者,有流芳百世者,也有遗臭万年者。因此,在希冀流芳百世的信念中,众人砥砺而行、以礼行事。最终,在家族族谱的网络中,在与先祖和“后来者”的纵贯沟通中,以及祭祀与享祭的文化活动中,他们突破人生在世的有限性,达至生命的无限性。这是不同于西方宗教信仰的传统中国人的信仰。
四、追求真理与提升境界
探索指向和文化传统熏染的不同必然导致追求的不同,西方文化以追求真理为最上,中国文化则以提升境界为旨归。作为西方文化摇篮、哲学起点的希腊哲学在对宇宙本源的探究中体现了一种渴求理性真理的精神。这种对真理的渴望,不仅体现在泰勒斯冲破神话思维而求取宇宙真知的探索上,而且表现于毕达哥拉斯“数是万物始基”的理性系统中;既蕴含在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观念中,也包藏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研究中。因而,探求真理性的科学知识、解决科学知识何以可能和何以为真,便成为无止境的探索。
此外,我们知道在西方一直贯穿着追求真理般的希腊悲剧精神——死亡之学和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在哲学精神上即是人们为求真理而不怕牺牲、敢于接受极刑和赴汤蹈火。按照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悲剧震撼人心之处不在于表现了人们的悲惨命运,而在于矛盾双方都没有错,但是最后还是酿成令人痛心的不可挽回的后果,苏格拉底之死便是如此。“苏格拉底自比牛虻,说雅典这匹马太迟钝了,需要有人时不时地刺激它一下。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唤醒城邦人,挽救日益衰落的雅典。 ”[6]17可见,自比牛虻的苏格拉底固然是为了城邦利益而慨然赴死,而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城邦也是依据城邦法律正义、维护城邦利益。这种摆脱不了的悲剧色彩与坚持真论的传统一直潜伏着,直至持续到近代布鲁诺怀抱真理(太阳中心说)而英勇就义。布鲁诺之死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一次悲剧再现。
当然,在中国也不乏追求真理和进步的前辈,如以谭嗣同为代表而视死如归的戊戌六君子;还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传统中国也不乏为求一真论而“程门立雪”的杨时和游酢,当然他们所求是为了心性意旨。或许可以这样说,传统中国哲学基本上没有仓央嘉措“多情”与“梵行”的纠结与无奈,也没有世间生活与高远追求的冲突与抵牾,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最高的智慧莫过于“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转言之,就是世俗的尘世生活与高明的修己追求相即不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不是二。如儒家学者所言“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和修齐治平,佛家禅宗所言“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就是在这“高明”与“中庸”圆融中达到“参赞天地之化育”和“与天地参”的绝妙佳境,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五、结论
综上所述,建立在科学实践及信仰基础上的西方传统哲学是为求索真理和上帝宇宙之奥秘,而奠基在伦理的知行和诗教史官文化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为了修己成人和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然而,前者追求真理却舍不去希腊悲剧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后者追求境界却放不下人间烟火和家国情怀。相比之下,中国哲学的特质便凸显出来了,那就是重道德修养轻知识积累,重伦理实践轻科学实验,重现世家庭感情轻来世宗教情结,重境界提升轻真理追求。
[1]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雷红霞.西方哲学传统的融通、发展及其意义[J].中州学刊,1997(2).
[5]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6]柏拉图.柏拉图读本[M].王晓朝选编,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