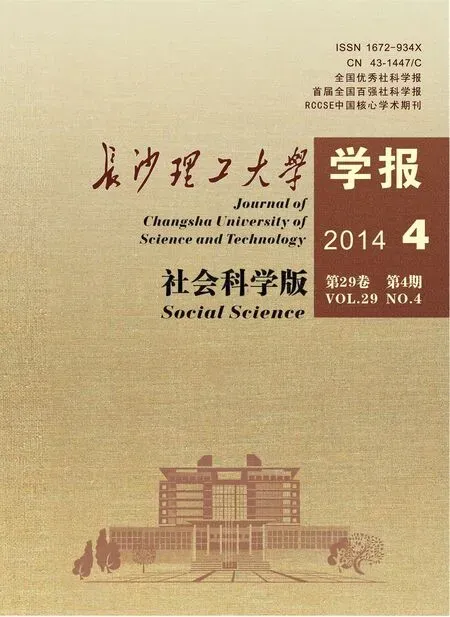解构·颠覆
——从中短篇小说看卡夫卡创作特色
宋玲玲,周丽杰
(烟台职业学院,山东烟台 264003)
解构·颠覆
——从中短篇小说看卡夫卡创作特色
宋玲玲,周丽杰
(烟台职业学院,山东烟台 264003)
作为象征主义集大成者、表现主义先锋及存在主义引航者,卡夫卡“西方现代文学先驱”之誉受之无愧。他不仅丰富和深化了文学形象,而且还解构、颠覆传统叙事美学,创新、重构了文学本质与意义。基于此,文章以其中短篇小说为蓝本,从叙事、人物、主题三方面出发,深入发掘其独树一帜的创作特色。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叙事;人物;主题
弗兰茨·卡夫卡既是奥地利首屈一指的小说家,更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语小说家,还是影响遍及全球的杰出作家。他一生创作颇丰,主要作品包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虽然这些作品有的尚未写完(三篇长篇小说均未完成),且在卡夫卡生前也多未发表,一定程度上致使他的创作没有被充分认识,但并没湮灭其创作的真实价值。若干年后,全世界各地掀起的“卡夫卡热”便是对这种价值的最大佐证。那么卡夫卡创作究竟有何特色与价值呢?笔者将着重从其中短篇小说的叙事、人物、主题三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一、交并·悬置——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
在《悖谬化叙事:卡夫卡的叙事美学论析》中,张沁文曾如是说:“卡夫卡一方面通过沉重、压抑、灰暗的笔调描述荒诞悖谬的人生困境,同时又以滑稽幽默的文字解构这个凝重的终极问题。”[1]由此造就其小说叙事既神秘难解,又富于典型魅力的玄学特质。如此评价,自然不乏深刻独到之处,但还仅仅是从叙事笔调和文字而没有从叙事手法上来彰显和佐证卡夫卡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事实上,较之既着力表现痛苦绝望,又大肆铺设滑稽幽默的二重性悖谬化叙事,交并和悬置更是促成卡夫卡神秘典型叙事的深层动力。
就交并叙事而言,通观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不难发现卡夫卡并不热衷传统的纯客观式再现现实,而是十分酷爱借助现实与幻觉、幻想的交并来表现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于是,读者得以发现无论是《忽然散步》中“我”晚饭后待在家中静坐遐想,还是《乘客》中“我”在电车上凝望姑娘的“满心疑惑”;无论是《大噪音》中“我”面对满屋噪音的绝望狂想,还是《煤桶骑士》中“我”因严寒难耐,骑着煤桶飞往煤贩家的“异想天开”;无论是《商人》中“我”由于公司停业而来的“胡思乱想”,还是《马戏团顶层楼座上》年轻看客观看马术演出期间源源不断的“连篇浮想”;无论是《变形记》中格里高似真似幻的“变形”,还是《梦》中K“难辨真假”的奇幻之梦等,都无一不是以现实为基点,现实与幻觉、幻想交织的艺术之轴。而正是在这种“半真半幻”的艺术之轴上,传统的线性叙事被打破,时间在过去、现在、未来间自由穿梭,叙事时空得以延伸。如此一来,主人公虽尚处此时此地,但是思绪意念却上溯过往,下接未来,丰富真切的主观精神世界也便昭然若揭。以中篇小说《变形记》为例,正是在格里高现实与幻觉的交并中,格里高子还父债的过往、备受老板压迫、身心俱疲之现状、被家人抛弃之未来命运竞相呈现而又相互掩印。
现实与幻觉、幻想的交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线性叙事时间的同时,又带来叙述人称的多维变化与融合。于是,在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中,第一人称单数叙述中出其不意地插入第一人称复数叙述或第二人称叙述的现象随之可见。前者如《跑着的过路人》中开篇以第一人称单数“我”散步见闻叙述,但是在想象中却又不断加入第一人称复数叙述,“我们不会抓住他……我们要是抓住了第一个人……我们不再感到累了……我们再看不见第二个人。”这种第一人称单复数叙述人称变化看似是漫不经心之笔,实则是生花妙笔。一方面它既假借这种转换点表明这些幻想推测是“我”酒醉后之丰富联想,又暗示出同“我”持相见观点者并非少数,而是常态,由此指向存在之真相与本质。后者如《归乡》中“你觉得神秘吗?你有归家的感觉吗?”与《地洞》中“怎么啦?你的家是安全的,是封闭起来的。你生活在一片安宁之中,温暖,吃得好,是主人,支配着无数通道和小窝的唯一主人,但愿你不想牺牲这一切,但却想在一定的程度上放弃,你虽然有信心重新得到它,但你是否要参与一场高额赌博,一场极高额的赌博吗?”表面上看,这些以第二人称展开的“自问自答”不过是孤独绝望之主人公的内心想法,其实不尽然。正是在这种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叙述的交并中,读者与文本的距离被大大拉近,从而更能设身处地理解主人公孤独难安的精神世界。
就悬置叙事而言,只要稍加审慎,就会发现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虽然大都缺少完整统一的故事情节,但是也不乏扣人心弦的动人叙述。以短篇小说《伙夫》为例。文本原本主要讲述卡尔为躲避女仆纠纷与麻烦,前往美国“逃难”的“奇遇”故事。但是文本除了开篇点明卡尔因与女仆“纠纷”前往美国“逃难”外,并未紧接着详述过往“纠纷”始末,而是转入现时卡尔的逃离。而等到卡尔在历经丢伞——找伞——误入伙夫房间——与伙夫闲聊——陪同伙夫“投诉”——舅甥相认后,才再度通过女仆给卡尔舅舅雅各布来信及舅舅之口补叙卡尔与女仆发生关系及生下私生子的具体详情。如此一来,卡尔的故事便在卡尔美国奇遇及伙夫与苏巴尔纠葛故事中被最大限度悬置,并最终形成并列不相交的二重故事,而不是传统“镶嵌”式的故事套故事,更非有着必然因果关系的环环相扣之故事,世界之无理性和存在之荒诞性由此入木三分被显示出来。又如中篇小说《判决》中乔治为满足妻子结识自己朋友的愿望写信给远在彼得堡的好友,但是信写好后文本却没有像平常一样转入乔治寄信的情节,而是将其悬置,插入乔治与父亲的谈话,并最终使其在父子对话中“不了了之”。借此悬置,父子冲突象征而来的个体之压抑与孤独得以最大程度上的深化。
二、异化·悖反——荒诞真切的人物形象
在传统中短篇小说中现实逼真的人物丛林中,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荒诞真切的人物形象可谓“格格不入”。在《荒诞与真实—卡夫卡的〈变形记〉探析》一文中,刘华写道“卡夫卡的创作与众不同,语言平淡透着冷漠,朴实中蕴含深意。荒诞中含有真实,真实中又透着荒诞。做到了荒谬与现实的有机结合。”[2]他们一方面既形貌怪异,有半猫半羊之怪物(《一只杂种》),又有突然变成甲虫的推销员(《变形记》),另一方面又多重属性,有驯化成人之猿猴(《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及会说话亚洲胡狼(《亚洲胡狼与阿拉伯人》),又有富于血肉之躯,感知敏锐的桥(《桥》)。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周围环境与群体所异化,深陷孤独与绝望之中无法自拔。于是,读者发现虽然奇特动物半猫半羊,在世上有无数姻亲,但因为异化却没有一个血亲动物,只能稳抓主人不放以寻求保护;格里高虽然年纪轻轻,但由于被父母、老板等人构建的强大社会压力所迫,终日劳作,最终被异化成身负重压的甲虫;被驯化成人的猿猴虽然因学识“渊博”深为人类“赏识”,但因为异化却失去了自由与本性;亚洲胡狼虽然痛恨人类,但由于异化,却又对人类猎取之物趋之若鹜,成为既与人类敌对又对人类极其依赖的“怪物”;桥虽然渴望被人发现,但一旦面对人类的异化力量,最终不得不毁尸流水。
异化带来孤独绝望,孤独绝望催生幻想与自说自话式悖反。如此一来,悖反便成了卡夫卡笔下人物形象的最大特质。于是,放眼卡夫卡中短篇小说,映入眼帘的尽是看似逻辑推理性强,实则只是以自己的幻觉与想法为核心,对各式各样事物自说自话,且前言不搭后语的“荒诞”形象。前者如《返乡》中对读者与自己说话的“我”;又如《商人》中对电梯说话的“我”;再《伙夫》中伙夫、苏巴尔、卡尔与舅父之间看似言之确凿,实则各怀心思,文不对题,丝毫没有结合谈话情境,不顾忌听话人感受的自话自说,后者如《鸢》中饱受鸢啄之痛,但 “为了脸,宁愿牺牲双脚”,对其采取容忍态度,最后痛之至极,请求路人取枪救援,并以鸢自戗于“我”血泊而感到解脱的“我”;又如《跑着的过路人》中在圆月之夜看到一个跑来的男人,但并没有抓住他,而是陷入各种可能性的想象中的“我”;再如《隔壁》中因哈拉斯租下隔壁空着的小套房,整天疑心他会窃听自己生意往来上的电话,于是想尽各种办法进行预防,但却因此变得抉择没有把握,声音瑟瑟颤抖的“我”。
由此可见,正是借助异化与悖反,卡夫卡赋予人物形象十足的荒诞与异质特质。但荒诞异质并不意味着人物形象“虚假不可信”,相反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形象较之传统人物形象更为真切,他们更关注个人体验和生命感悟,遵从本真感知,故而是人之内在精神更为直观、真实的深层表现。
三、互文·反讽——存在主义的主题表征
正如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所言:“(卡夫卡)作品所揭示的迄今不为人知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种种面貌,是使艺术的演进改变方向的美学方面的创新。”[3]卡夫卡中短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有的甚至只有区区三五百字,如《归乡》、《启程》、《日常困惑》、《陀螺》等篇章),既无完整统一的故事情节,又无丰满具体的人物形象,并呈现出极强的碎片化色彩,但因为对人存在面貌的执着深层表现与思索,从一开始便打上了存在主义的深刻烙印。而这种存在主义式主题表征,在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最集中地通过互文与反讽得以体现。
就互文而言,卡夫卡不遗余力借用古代传说,在丰富创作题材的同时,注入人类存在状态的哲学思索。于是,读者在卡夫卡对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侥幸逃难塞壬的诱惑(《塞壬的沉默》)之调侃性剖析“即使是不完善的、甚至幼稚可笑的方法也能用来救命”中,得以发见世界之荒诞性以及真相与假象永远道不明的关联;在卡夫卡对圣经故事普罗米修斯受罚(《普罗米修斯》)的四种传说举证中,得以领悟基于探究真相的传说难以在解释事物方面的无能为力;在卡夫卡关于巴别塔修造未成功之因(《城徽》)的猜想中,得以窥见人类生存之惰性及无力改变,同时探索到好想法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领悟到想法之精髓,那么原先的好点子就会如同修造巴别塔一样付诸东流之人生真理,更重要的是,借助互文,卡夫卡还打破了小说、神话与宗教艺术的界限(塞壬、普罗米修斯、巴别塔分别是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及圣经中的人物形象),也就打开了小说与其他艺术开放的桥梁。依托这座桥梁,读者得以在卡夫卡小说、神话与宗教艺术中全面获得人类生存境状与意义,并由此开启人生思索。
就反讽而言,卡夫卡似乎有意以这种戏谑调侃的方式来对抗剥夺个体生存自由、使人异化的“现代”社会。为此,他在中短篇小说中浓墨重彩地运用反讽,以此鞭打让人绝望孤独的社会现实。如《日常困惑》中就假借甲明明在大门口巧遇乙,却以急事之名(与乙敲定生意)匆匆离去,最终来回白跑一趟,与生意机会失之交臂的滑稽性情节,讽刺人类常识的误导性及人类沟通之不可行性;又如《往事一页》中依托北方游民入侵,皇宫卫士闭关,工匠商人受苦应对的荒诞不经之事,借“以往那些总是盛气凌人地进出皇宫的卫兵这里却被锁在铁窗之中。于是,我们这些工匠和商人就肩负了拯救祖国的使命,然而这样的使命我们却担负不起。我们也从来没有夸过口,说自己有这般能力。这是一场误会,而我们却要毁于这场误会”调侃之言,嘲讽了统治者耽于享福,让百姓担苦的丑恶现实;再如《夜》通过“必须有要有一个人醒着”之戏谑之语,赋予哨兵守夜深层的反讽意味:这种看似荣光之事之于个人来说,却是“无理蛮横”的生存权剥夺。
综上所述,从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来看,卡夫卡擅长依托现实与幻觉幻想以及叙述人称的交并,叙事情节的悬置来解构和颠覆传统线性叙事,精通借助异化和悖反解构与颠覆传统现实逼真的人物形象,酷爱运用互文和反讽解构和颠覆现实再现,从而使得其创作叙事独具匠心、人物形象荒诞真切、主题表征深刻入微,不愧为西方文学鼻祖。
[1]张沁文.悖谬化叙事:卡夫卡的叙事美学论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33-37.
[2]刘华.荒诞与真实——卡夫卡的《变形记》探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70-72.
[3][捷克]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孟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65.
Deconstruction and Subversion——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afka’s Literary Creation from his Novelettes and Short Stories
SONG Ling-ling,ZHOU Li-jie
(Yantai Vocational College,Yantai,Shandong,264003,China)
As a combination figure of symbolism,forerunner of expressionism,navigator of existentialism,Kafka indeed deserves the title of“pioneer in modern West Literature’.He not only enriches and deepens literary images,but also deconstructs and subverts traditional narrative aesthetics.What’s more,he creates and reconstructs the essence and meaning of modern West literature.Based on this point,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or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Kafka’s literary creation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narration, characterization,and themes of his novelettes and short stories.
Kafka;novelettes and short stories;narration;figures;themes
I106.4
A
1672-934X(2014)04-0100-04
2014-04-23
宋玲玲(1973-),女,山东乳山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周丽杰(1976-),女,山东龙口人,讲师,学士,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