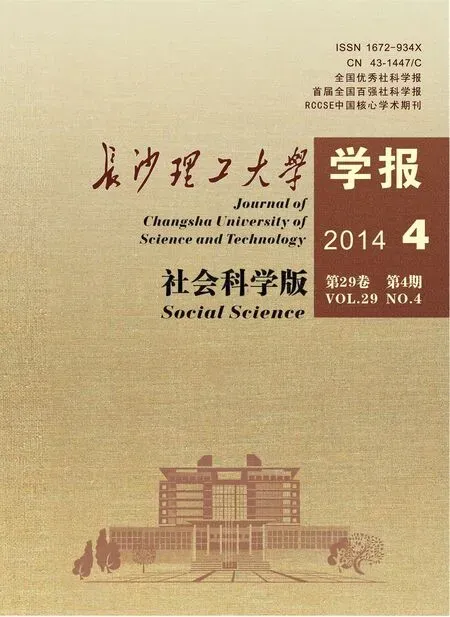解读科学理论的“真”
艾战胜,黄芳萍,王雅蓉
(1.广东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2.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一
长期以来,思想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见解:“真”就是“真理”。虽然,“真”与“真理”有密切的联系,在西方语言中,两者都可用“truth”(英语)和“wahrheit”(德语)来表达,但是,真理并不是孤立的命题,而是由反映事物全体的许多真命题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一个命题的真(即真的)和真理并不是一回事。科学理论的“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是科学理论本身的存在方式及其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真即是对这些是如此的东西的认识”;“真是一个对象与我们的表象相一致……真意味着一个内容与其自身相一致。”[1]因此,科学理论的“真”既是对科学理论存在的肯定,又是对科学理论的功能(即善)和美的肯定评价。概而言之,科学理论的“真”是真、善、美的统一体。
科学理论的“真”首先指其存在上的真,即科学理论存在的客观性。科学理论作为人类思维的产物,它一产生就构成人类整体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存在已具有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性。科学理论的客观性根源于两大因素:一是对象的客观性,科学理论反映的对象是客观物质实在;二是内容的客观性,科学理论反映的不是客观事物的表面的、简单的联系,而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它有客观逻辑的内容。科学理论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但在本质上却要求它必须独立于研究者的主观性而具有客观性。这正如波普尔所说,它“是人造的,同时又明明是超人类的。它超越于它的创造者。”[2](P369)客观性既是科学理论的“真”的体现,又是科学理论区别于非科学理论的根本特征。
“善”是科学理论的“真”的功能要求。列宁认为,“‘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性(2)。”[3]科学理论的“善”必须要满足科学“实践”的要求。在科学活动中,这种“要求”,归根到底归结为科学理论必须满足人的理解的需要。人是喜欢解谜的理性动物,自然世界瞬息万变,奥妙无穷,引发人类对其探究的渴望和好奇。爱因斯坦将这种渴望和好奇被描述为“宗教宇宙感情”,并认为这种有关宇宙的情感恰恰是科学探索的内驱力。科学理论作为宇宙宗教感情引导下的人类理性活动的结果,反过来又满足了人类对宇宙探索的渴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理论具有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解释功能表现在科学理论要能解释科学事实和科学规律。科学理论的预见功能就是科学理论所能解释的客观事实应该多于原来它以之为基础的经验。理论的这种特性不仅是人们非常希望的,而且还是把科学理论与其他概念结构区分开来的特征之一。
“美”是科学理论的“真”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服从于“真”。爱因斯坦认为,“美”的不一定是“真”的,但“真”的一般要求它同时也是“美”的。沙利文亦认为,“由于科学理论的主要宗旨是发现自然中的和谐,所以我们能够立即看到这些理论必定有的美学价值。”[4]但是,我们不能将科学理论的美等同与艺术美来理解和审视。科学理论一般是通过严谨的符号系统呈现出来,这种符号系统并不具备艺术符号那样的特性。严格来说,科学理论的美本质上是思辨美,它体现了舍逻辑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要求。在科学理论的美中,“合逻辑性是前提,合目的性是核心。失去了逻辑性,科学理论的美就会失去其科学的含义,而失去了目的性,科学理论便是盲目的。”[5]
真、善、美三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规定着科学理论的“真”。“真”是科学理论的灵魂与核心,同时也是科学理论的内在要求。失去了“真”,科学理论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据。
二
我们说一个科学理论是“真”的,意味着它已被经验所验证,同时也是对这一理论存在的肯定。但就现实的科学活动来说,科学理论的“真”仍然是相对的。在理论和经验的外部关系上,科学理论的真是与科学理论的可错性相对的。而在科学理论的内在结构上,“真”是与理论基础的虚构性相对的。科学理论的“真”不仅不排斥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虚构性,还必须以之为其为发展的合理形式。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基础的虚构性是“真”变化发展的内在要素。
科学理论的可错性是波普尔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尽管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求确定无误的科学知识,但是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事实上,科学史“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2](P176)科学是试验性的事业,正如犯错误是人的本性一样,可错性是科学理论的本质属性。
科学理论可错性的存在,一方面,它是认识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体现。科学理论的可错性是科学作为人类能动思维活动产物的重要本质内容。科学活动中的可错性不仅不是必须加以排除的消极因素,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科学活动不可缺少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它是科学理论比非科学理论具有生命力的保障。因此,在其证伪主义理论中,波普尔认为,判别一种科学理论是否科学的依据在于它是否可以被证伪或可以被反驳。
科学理论的虚构性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科学理论构建过程中的主观猜想性;二是建构基础具有经验事实的不充分性。众所周知,科学理论的根本组成部分是概念和原理,爱因斯坦认为,这些组成部分虽是人类智慧的自由发明,但并非理性所主宰,它们“具有纯粹虚构的特征”[6](P314)。爱因斯坦因此主张“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自由地创造概念”[6](P309)。爱因斯坦所指的这种虚构性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科学创新行为,它是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对对象的全面认识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而提出试探性理论的一种探索性行为。这种行为既体现了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又强调了在一定基础上的创造性。因而,它与完全虚构和凭空幻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受爱因斯坦的启发,波普尔在其科学哲学中,强化了科学发现中“大胆猜测”方法论的地位。由于主观猜测性成分的存在,科学理论具有不确定性和暂时性。
科学理论的可错性与虚构性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虚构性是可错性的前提。由于构建科学理论时存在虚构性的行为,科学理论中包含可错性成分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可错性是虚构性行为的依据,一切科学理论是可错的,它终被后来的经验所证伪,因此构建科学理论时的虚构性行为就是合法的。
三
尽管科学理论的“真”与可错性、虚构性是对立的,但两者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具体地说,“真”是可错性、虚构性滋生的土壤,可错性、虚构性是“真”变化发展的内在要素,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一)“真”是可错性和虚构性滋生的土壤
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理论基础的虚构性是求“真”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科学理论的求“真”过程归根到底是为了追求科学理论的真、善、美的过程,是求真、求善、求美过程的统一。这个过程最终实现了科学理论的“真”,同时伴随着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虚构性。
首先,科学理论产生过程中所使用的非理性科学方法为科学理论的可错性提供了可能性条件。科学理论虽然应该具有合乎理性的特质,但是,这并不要求在建构科学理论时非得使用理性的科学方法。恰恰相反,多数科学家在构建科学理论时甚至使用灵感、直觉等非理性科学方法。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哲学家就认为,直觉是科学知识具有创造性的根本来源。爱因斯坦也多次公开宣扬和肯定直觉和灵感在科学探索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认为 “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6](P103)实践表明,直觉、灵感等非理性方法由于在构建科学理论时具有不可预估的作用而被广为推崇。科学家们常用它来开启科学理论的大门。但是,直觉、灵感等非理性方法具有较强的逻辑跳跃性,它会导致科学家在理论探索过程中忽略一些必备的经验基础,甚至将一些猜测成分融入理论之中。科学理论因此也具备了可错性的基础。
其次,科学理论求善的过程也是可错性成分融入科学理论的过程。科学理论的求善过程也就是科学理论功能的发挥过程,它的目标是不断增强科学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科学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是由它所包含的信息量来决定的。科学理论包容的信息越多,面临检验的范围就越广,它被证伪的可能性就越大。假如有两个陈述A和B,他们的合取为AB,原则上看,AB所包含的信息要大于或至少等于A或者B。因此可以说,AB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比A或B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强。但是,AB接受检验的范围要远大过A或B,即AB被证伪的概率大过A或B。从次意义上说,科学理论求善的过程即寻求科学理论的高解释力和预测力,也是科学理论被证伪的可能性增大的过程。
再次,科学理论求美的过程是导致科学理论基础不充分的根源之一。历史学家沙利文认为,“对一个科学理论的成功与否的衡量事实就是对它的美学价值的衡量。”[7]因此,科学家往往自觉地运用美的规律来构建科学理论。同时,科学家作为科学理论的美的主要欣赏者,他们在众多的审美原则中往往会优先选择“简单性”原则。爱因斯坦就认为“评价一个理论是不是美,标准正是原理上的简单性”[8],并将“逻辑简单性”作为评价与选择理论的两条标准中的一条(另一条为经验的证实)。为了促成科学理论符合“逻辑简单性”原则,科学家往往会依据尽可能少的假设或公理出发来概括出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科学家因此会可能忽略与此有关的其他经验事实、科学原理,以及经验事实与科学原理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使得科学理论赖以生存基础具有不充分性。
(二)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虚构性是“真”变化发展的内在要素
科学“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已为公众接受的陈述系统,也不是一个向某终极状态稳步前进的系统”[2](P34),“科学中不可能有最终陈述”[2](P43)。因此,作为科学活动的结果的体现——科学理论,它的“真”也不是终极的。它必须体现在科学理论的变化发展之中,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真”是随着时间进程不断地从低到高上升的。
科学理论的“真”的这种逐渐上升的变化状态,归根到底来源于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虚构性。一方面,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和虚构性的合法性从根本上弘扬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它能激发科学劳动者冲破束缚,用另一种更好的或者更合乎要求的理论取而代之。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理论本身固有的可错性和虚构性的特性,它迟早要被经验所证伪,这促使人们重新去探索,用更“真”的科学理论来代替。所以说,可错性和虚构性是“真”变化发展的内驱力。
(三)科学理论的“真”与可错性和虚构性都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科学精神是人类从事科学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体现在科学文化中的精神。由于科学具有历史性,那么体现科学活动的科学精神也是历史的,科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有着不同的科学精神。尽管如此,科学本身固有的特性决定了科学精神应有两个历来就具有的、最本质的内容:一是求实精神;二是自由探索精神。而这两种具体的精神在科学活动结果中的体现形式便是科学理论的“真”和科学理论的可错性、虚构性。换言之,“真”是求实精神的核心体现,可错性和虚构性是探索精神的本质反映。
[1]王路.论“真”与“真理”[J].中国社会科学,1996(6):113-126.
[2]纪树立.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C].北京:三联书店,1987.
[3]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25.
[4][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14.
[5]艾战胜.论科学实验的合理性[J].科技管理研究,2008(4):237-240.
[6]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7][美]钱德拉塞卡.真与美[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74.
[8]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