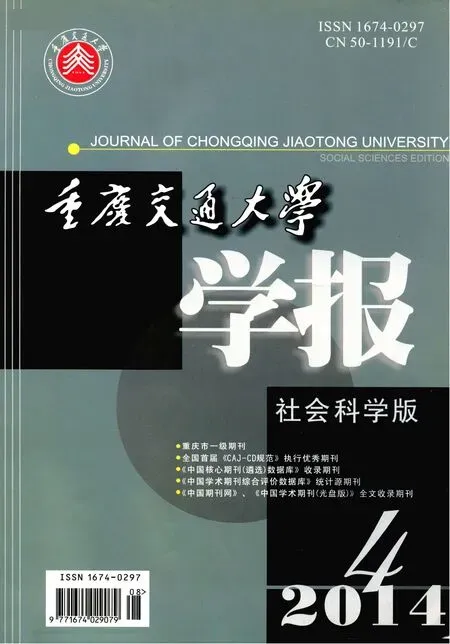省际交界地带发展滞后的因由及路径探讨
王友云, 金子求
(1.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361005;2.铜仁学院,贵州 铜仁554300)
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便于国家在宪法框架下从中央到地方实施统一管理,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主流。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统一是我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这种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造成各省行政区之间因区划的界限而出现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分割的特征很明显,由此造成省际交界地带发展滞后问题,影响了我国均衡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块块“洼地”,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影响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分析省际交界地带的区域特征,寻找滞后的因由,探讨发展的路径,是解决区域发展差异应遵循的基本思路。
一、省际交界地带的区域特征
我国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具有明显的衰竭性,且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面广连片,民族杂居。这种省际边缘连片民族贫困地区成了我国拉大收入差距和扩大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板块”,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短板”。我国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和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圈两相对照形成的“马太效应”和区域上的两级分化现象日益明显,必须下大力气解决我国11个省际交界地带区域的发展问题。纵观全国版图,我国以省际行政区交界地带形成的地理版块几乎成为发展的“真空地带”,远离国家的各层级“经济中心”,发达经济圈辐射带动效应非常微弱,在各自的行政区内相对封闭,冲突不断,矛盾诸多。
我国区域发展的冲突和矛盾在“行政边界地带—地方政府—跨政区协调”主题下交织和渗透,并在行政边界地带被聚焦和放大[1]57。总体分析,我国省际交界地带具有这些基本特征:省际交界地带同属于一个自然区域,因地缘属性形成了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资源相对丰富,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具有区位的边缘性和经济的欠发达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缓慢;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滞后;具有无法替代的生态功能;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区位功能日渐突出;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加强[2]396。我国省际交际地带集老少边穷库于一体,因为省际边界地带敌对势力比较薄弱,在革命战争年代成为党的革命根据地,是党打“游击战”的主要阵地,是党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策源地;进入和平年代,我国发展的战略布局从农村走向城市,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为革命胜利做出巨大牺牲的边界老区发展严重滞后。这些边界地带在历史上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表现出多民族杂居的特点;因远离经济文化中心,被严重边缘化;是典型的民族贫困地区;处于大山和大河的分水岭,有的还是我国的重要库区和重要生态保护区。省际交界地带在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我国跨省行政区边缘地带的地位更显重要,因为这些地带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虽地处边界,却守护“中心”的环境安全,是“中心”的水源地和生态源,还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富集区,区域公共利益日益明显。有学者将这种“行政区边缘经济”定义为:国家经济内由于行政区划、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和“边缘效应”的影响,而在行政区交界地带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具有分割性和边缘性的区域经济[2]399。笔者认为,这一定义涵盖了行政区边缘经济的基本特征,比较科学。
二、省际交界地带发展滞后的因由
(一)行政区划对省际交界地带的制约副作用
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地方行政区划形成省级到乡级的四级或三级层级体制[3],这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国家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便于国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从上到下实行有效分级管理,大大方便了国家管治和治理的需要。我国行政区划更多考虑地理条件、民族分布、人口密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因素,较少顾及经济协作性,建国时行政区划的合理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协作的需要而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有的区划甚至需要调整。有学者曾主张划小行政区划,提升边缘地区行政地位的对策,以缩小中心和边缘的差距,认为行政区划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整合资源、创建富有特色的省域经济[4]。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解决我国省际边缘发展滞后的问题和提升省际边界地区的功能,如海南省和重庆市升格后,其经济发展迅速是我国区划变革的成功典范。但是,我国经济协作中的矛盾绝对不能一味依赖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解决,行政区划同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一一对应,总会存在矛盾,因为行政区划的形成是多因素的结果,经济区的建立主要依赖经济共同性,行政区划的设置要考虑经济、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甚至原居民的情感等方方面面的因素。行政区划是国家管治的必然产物,对国家治理是积极的,却给经济协作带来一定副作用,表现在各行政区划之间必然形成区划壁垒,阻碍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生产要素流动受阻,难以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必然对区域经济横向联系产生刚性约束,阻碍经济合作。随着市场力量的扩大,经济区必然突破行政区划,二者产生矛盾,于是经济协作中必然产生各地方政府的矛盾和冲突。如何突破行政区划对交界地带的制约副作用,成为省际交界地区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及政府协调难以真正实现
省际交界地区因受行政区划的制约而产生诸多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必须靠彼此之间的协调来解决。通过政府协调解决协作中的矛盾,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合作共赢,应成为解决我国行政区划对省际交界地带制约副作用的理性选择。但我国区域协作在发达地区较落后地区容易实现,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合作的经济和人文基础都比落后地区要好。我国很少关注行政区边缘经济的发展,不论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还是在落后的西部,都对行政区边缘经济关注不足,由此造成省际行政区交界地带普遍落后。这种边界差距很难通过省级行政区划属地管理解决,必须通过国家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调整和跨省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来解决。省际边界地带因为行政区划而被人为分割,出现“行政区行政”,行政区划界限成为地区发展的壁垒和屏障,严重阻隔区域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违背市场规律,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突破区域壁垒的重要动力在于实现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和省际行政区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但因为省际边缘地带经济的滞后性、封闭性和观念保守等特性,省际边缘经济协作及其政府协调的难度更大,需要解决制约区域合作的一些长期形成的深层次难题,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合作机制和体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甚至需要中央政府从国家层面进行协调,以解决跨区域公共事务。
(三)文化维系力衰减,区域治理出现“碎片化”
省际边界地带互相封闭,加之处于大山大河的分水岭,集老少边穷于一体,这种地域的自然状况阻碍了文化的交流。省际交界地带交通不发达,生产要素流动的成本偏高,交流受阻,文化共生与包容性发展没有形成。长期落后的经济形式,尤其是自然经济形态在历史上曾一度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会造成人的思维方式单一、眼界不开阔、心胸狭窄、观念落后、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等心理特征[5]。省际边界地带的文化维系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呈现出衰减趋势,而文化和观念的封闭与落后会给人类实践带来深远的负面效应和影响,强化了行政区划对省际交界地带的人为分割,在区域实践中造成治理“碎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各自为政”“行政区行政”和“山寨王”等等治理“碎片化”行为,阻碍了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增强文化维系力,整合区域公共治理的“碎片化”现象,进行省际交界地带文化认同和规范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三、省际交界地带发展的路径策略
(一)树立地缘观念,遵循省际边界地带地缘属性
地缘经济是从地缘政治视角移植用来追求利益的一种方式,是地理位置邻近或毗连的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资源互补、经济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地缘经济区是以地缘为基础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6]。我国省际行政区可以借鉴地缘学理论,解决我国省际边界各政府间的关系问题。省际边界边缘经济具有“地缘经济”属性,因省际边缘交界地带是一个统一的自然地理单元,具有共生性,形成“共生关系”,也是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单元,地缘产生了人缘和业缘,因此,对跨行政区边缘的治理必须遵循地缘这一自然属性,维护“地理环境关系”和必然的区位边际关系。区域协同治理的社会技术是行政区边缘的地缘属性这一自然技术的客观要求,基于地缘的协同治理技术有利于边际间要素的流动和联系,节约了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有利于区域经济协作和走向一体化[7]。省际边界地带面临跨区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等诸多问题,公共利益出现分化;在边界地带更容易产生独立性地方政府利益和利益集团;边界地带计划经济观念更加强烈,行政区划意识明显,利益多元致区际冲突和矛盾不断,集体行动下的“公地悲剧”比较明显,因此,必须树立地缘观念、加强合作。还可以从资源稀缺性和交易成本两个视角分析边界合作的动力来源,资源稀缺性是指当组织和其它组织结成联盟的时候可以获得或者提高在它们的领域内对稀缺资源的控制能力;交易成本视角是指组织通过联盟可以提高在其领域内的交易效率[8]。这两个分析视角告诉我们,组织为有效控制资源和提高交易效率,可以通过组织联盟来实现。由此,边界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基于解决资源稀缺性问题和提高交易效率而获得了联盟与合作的动力,这是联盟与合作的一种内生的动力,不过也需要政府培植。说到底,省际边界地带地缘属性决定了省际边界行政区划之间必须进行区域协作和政府协调。当然,具体的协调路径探讨和协作体制机制构建问题则是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在实践之前树立地缘属性的观念是首要的,是实践和行动的指南。
(二)发挥国家协调力和发展主体间合作关系,实现省际边界区域协作
从本质来看,区域协作在经济层面上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有序、合理流动。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但因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和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很健全,市场在配置跨政区资源时往往显得不足。在省际边界地带配置资源时,如果单靠市场进行跨政区资源配置,会出现失灵,必须辅以政府规制,政府规制在跨政区资源配置时更多体现为政府的协调。突破行政区划界限,进行深层次的区域经济协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区域内地方政府协调必然成为区域经济协作的基本问题。区域间政府协调实质是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关系错综复杂,既有纵向的垂直关系,又有横向的平行关系,是涉及到多元利益重组的具有政治性的问题。具体到区域间更多表现为区域内各政府如何就区域公共问题达成一致,实现共同利益。在公共问题协调方面,学界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涉及网络治理模式、复合行政模式、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探讨等等。行政协调是公共行政的永恒难题,基于省际边界公共问题的复杂性,需更多借鉴各种模式和理论成果,结合实际推进。
省际交界地带跨政区合作和政府跨政区协调问题是解决省际交界地带发展瓶颈的关键环节。省际交界地带跨政区合作和政府协调比任何地区都变得更加复杂,矛盾叠加,更需要发挥政府的协调力,发挥政府协调外力和市场调节内力的作用,使其产生叠加效应,发挥双重合力作用。如Pressman和Wildavsky所说:“没有比对国家的官僚体系‘缺乏协调’更频繁的抱怨了,也没有比‘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协调’更普遍的改革建议了。”[9]因此,经济协作中的政府协调既是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也是区域公共治理问题。区域冲突并不总是带来恶果,冲突一般来说是基于利益的不合理,冲突能带来原有体制机制的改革和突破,发生利益重组。如果能把握冲突在萌芽阶段带来的契机,区域内一定范围的冲突就会“化危为机”,为区域间进行“关系管理”、建立合法的稳定机制提供诉求,最终使区域间的矛盾由“零和博弈”的囚徒困境走向互利共生的多赢局面[1]57,实现区域整体利益的帕累托最优,特别是为建立有效政府协调机制,发挥协调力提供很好的机遇,为打破区域间固化的制度体制机制的路径依赖提供良好时机。正是这种区域间利益的分化与整合的矛盾运动,强烈催生着省际行政区边界地带合法化机制的构建,使区域内各主体从“对话型合作”稳定为“制度型合作”[10],使政府间协调有了稳定的制度,走向法制化和法治化。
我国最典型的政府协调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方式,它是一种科层制的协调,在我国威权体制政治生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行政民主化的潮流,特别是当组织的结构更加松散或者处于要求多个组织的多种信息交换和互动的时候,这种传统方式的效率就大大降低了①。而我国边界地带地方政府和各非政府主体之间以及各主体内部之间的关系具有结构松散的特点,应积极构建各主体间平权型的合作关系,促进各平等主体间的合作。省际边界地带经济落后、封闭保守、矛盾多样等特点决定了单靠边界各政府和各组织间的自发合作和协调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把各主体平等合作和国家层面的协调结合起来,既发挥各主体间横向合作的作用,又纵向发挥中央政府的组织力和协调力,同时辅以现代治理理论倡导的一些新型模式,如复合行政、网络治理、公共产品理论,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俱乐部理论等等。
(三)实施省际边界地带集中扶贫,以集中扶贫整合治理“碎片化”
我国省际交界地带具有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特征,大多是集中连片民族贫困地区,这就更需要充分发挥中央政策倾斜和财政扶持的政策效应,由国家层面主导,建立省际交界地带边缘地区合作的体制机制,建立省际交界地带边缘地区经济协作区,突破以往分散和单独扶贫而效果不佳的藩篱,进行省际边缘地区国家集中连片扶贫开发新模式的深入探讨和实践。可喜的是,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战略下,我国省际边缘地区多省合作建立经济协作区正在深度实践,国家更是把集中连片扶贫开发作为新世纪扶贫开发新模式,目前这一新模式正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区先行先试,这必将为我国省际边界地带发展、经济协作和政府协调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通过集中扶贫模式下的体制、机制建构和制度建设,推进区域一体化,整合区域治理的“碎片化”行为。推进省际边界地带文化共同体建设,积极进行文化的认同和规范建设。区域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文化是根,一切体制、机制建构和制度建设必须借助文化软实力来强化和维系,我国省际交界地带大都是浓厚的民族文化、深厚的红色文化、良好的生态文化聚集地,是中国一条条的“文化沉积带”,必须深入挖掘被沉积了的深厚文化,使原有文化的生命得以延续,这是省际交界地带文化建设的根基。同时,在区域合作中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做到保护和创新相结合,从省际交界地带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中蕴含的共同因子来促使区域文化协调共生共荣[11]。在文化创新建设中,还需积极寻求互利共赢、互惠互补,最终通过文化共同体建设达到整合治理“碎片化”目的。
注释:
①参见 Chisholm D.Coordination Without Hierarch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1]王爱民,马学广,陈树荣.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构建[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7(5).
[2]安树伟.行政区边缘经济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EB/OL].[2013-09-23].http://www.gov.cn/test/2005-06/15/content_18253.htm.
[4]郑亚平.省域边缘地区经济特征及发展对策初探[J].新疆社会科学,2007(1):34.
[5]王友云,杨胜江.“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区域协作中地方政府协调的障碍与破解[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3.
[6]Chen Cai.Regional Economic Geography[M].Beijing:Science Publishing House,2001:267.
[7]冯佺光.地缘经济区视角下的行政区边缘山地经济协同发展——以渝黔湘鄂结合部的武陵山区为例[J].山地学报,2009(2):167-168.
[8]任敏.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协调研究——碎片化理论的视角[D].广州:中山大学,2008:399.
[9]Pressman J L,Wildavsky A.Implementation[M].2nd ed..Berkeley:Universtiy fo California Press,1984:133.
[10]蒋英姿,江溢,成新.太湖流域省际边界地区水资源保护问题与对策[J].水资源保护,2006(3):88-89.
[11]任钢建.“中国-东盟文化共生与包容性发展研讨会”综述[J].琼州学院学报,201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