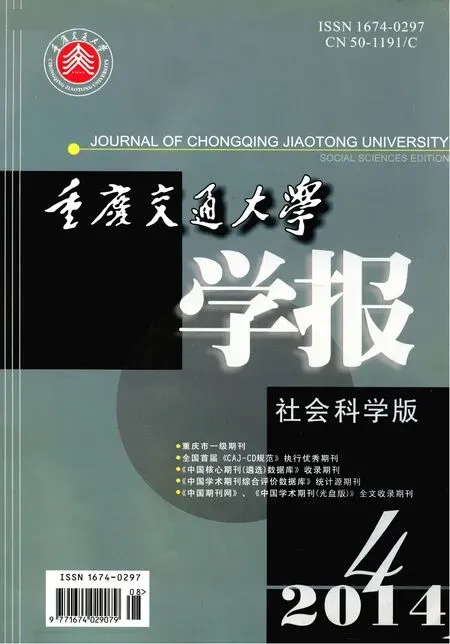朗费罗诗作的寓意解析和译文探讨——以《箭与歌》的理解和翻译为例
罗长斌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外语系,广东佛山 528000)
一、简评朗费罗的诗人道路
朗费罗(Henry W.Longfellow)(1807—1882)是19世纪美国著名、多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于1807年2月27日出生于缅因州波特兰城的一个律师家庭,1822年进入博多因学院,与著名作家霍桑是同班同学。他毕业后去欧洲学习欧洲语言和文学。1836年他开始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讲授欧洲文学长达18年。那是美国的一个诗歌年代,同时代的诗人还有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和惠特曼(1819—1892)等等,所以他同时也致力于诗歌创作,是一个少见的兼具“文学教授”和“诗人”双重身份的人物。
朗费罗于1839年32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夜吟》和浪漫主义派小说《许珀里翁》。他此后的诗作甚多,真是文思泉涌。他不仅在美国备受欣赏和赞扬,在英国也名声鹊起。这个名声推动着他的多产直至晚年。良好的名声也一直持续到晚年,他先后获得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在他1882年辞世之际,全世界都视他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他在英格兰的声誉能与英国诗人丁尼生相媲美,还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英国人将他的半身雕像安放在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在美国作家中,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文人作家。20世纪之后,随着他同时代默默无闻的女诗人狄金森的诗作被发掘问世,她的诗歌价值也被发现和重视。人们从而发现了朗费罗诗作的重要缺点,他的名声于是迅速下降。最后美国人下结论说,他是“著名的小诗人”(Yet Longfellow,though not a major poet,was a notable minor one[1])。
狄金森女士在世时默默创作的诗歌不被编辑看好而未能面世。受诗歌时代的影响,她至少是一个具有极大热情的诗歌创作者。她把出名的机会留给了朗费罗,也可以说是朗费罗的诗歌名声太大而左右了人们的欣赏口味,这样就埋没了狄金森的天才。但是,狄金森在诗中所表达的声音后来成为美国文学的典范。据统计,狄金森为世人留下了1800多首诗。她去世后,亲友曾编选出版了她的部分遗诗,于19世纪末出版了3本诗集。
狄金森女士的短诗在形式上非常富于独创性,大抵应该算是美国自由体诗歌的创始人,且诗作价值很高。尤其是她通过短小的诗歌超前反映了个人的幻想、想象、思考和心理活动,在诗歌形式和内容上的独创性功劳和价值都是很丰富的。而这些诗人真正所应该具备的独创性品质都是朗费罗所缺少的,所以她身后的名声就远远超过了朗费罗。
惠特曼也是同时代的诗人。他也一直在积极地创作他发明的自由体诗。他想满足所有人(reach everybody),在诗歌中描写了所有人,上至总统林肯,下至最穷的穷人。但是,他的自由体(Free Verse)实在是太自由了,诗句很长很长,像是散文句子,这很不讨人喜欢。人们还是继续着传统观念,喜欢押韵的、朗朗上口的格律诗。于是,朗费罗的意思肤浅而押韵的诗作就非常讨众人喜欢。惠特曼也不得不把出名的机会让给朗费罗。由于狄金森的自由体诗没有及时问世,惠特曼独享了自由体诗的发明权,这也就成了惠特曼的文学贡献。可是,朗费罗的文学创新的确是缺乏的。
二、朗费罗的诗作分析
朗费罗的诗作价值比较小,这是指文学贡献方面。他只是做文学教授的材料,有文学理论水平,却缺乏文学写作上的独创性和个性。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个很好的教训。反之,伟大作家最善于创作,可是文学理论水平似乎是欠缺的;然而他们的实践证明,理论又的确是次要的。也只有少数作家,比如爱伦·坡、厄普代克等还可以兼做“文学评论家”和“作家”两个职能。当然,朗费罗的良心还是不错的,这是作家至少应该具备的底线。作家绝对不能是墙头草,那必会作为垃圾被扫走的。

中国人所熟知和盛赞的《生命礼赞》,有人翻译为《人生颂》,共有9个诗段,每段4个诗行,韵式是abab。朗费罗采用了传统格律诗中最常见的四行诗节的形式。他还使用了韵式、脚韵与头韵,于是从总体上形成了这首诗的工整韵律,读起来节奏明快、语气流畅、铿锵有力、优美动听。诗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最后一段。诗中说:苏仲翔先生把整首诗都翻译为仿汉语格律诗的形式,因为原来的诗行只有7~8个音节,所以他每行用5个汉字,像是五言绝句。这真是难能可贵的尝试,这和笔者长期的主张是吻合的。这样翻译的话,译者必然要深入理解原作。苏先生要放弃对于表面意思的直译,并刻苦寻找高水平的汉字。在精雕细刻之后,他确切而灵活地表达了原诗的内涵。他对于这一诗段的译文是:
众生齐奋发,
顺逆不介意;
勤勉而戒躁,
探索又进取[2]259。
在这里,苏先生把any fate译为“顺逆”,把labor译为“进取”,把wait译为“探索”。这难道不对吗?可是如果译为自由体诗的时候,比如李正栓教授就把它翻译为:
那么就让我们起来行动,
准备一个应对一切命运的胸怀,
成就总是有但永处追求中,
学会苦干还要学会等待[3]。
该译文中的用词用语很随便、很表面、很肤浅、很松散。这是因为译者随随便便依照诗作的表面意思来翻译,没有下功夫去钻研其深刻的内涵。更有陈卫安等人撰文《一首永恒的生命赞歌——朗费罗〈生命礼赞〉赏析》,以李正栓的译文为例大加赞扬之[4]。可是都译偏了,意思都变味了,语言随便肤浅,缺乏质量和诗意,有什么可赞扬的呢?
我们就是仔细体会苏先生译文的内涵的话,发现它还是很空洞的口号。但是这不是译者的过错,该诗的品质就是如此,自由体诗的译文就更空洞了。因为译者的责任是译出原作的本意,既不要美化它、拔高它,也不要贬低它、折损它,从而使得读者能够从译文中品出原作的本意和寓意。
仔细体会全诗的话,9个诗段都是空洞的口号。之所以被中国人喜欢,是因为中国有喜欢空洞话语的环境,这样的环境是由大文豪郭沫若等人奠定的。但是,这样的诗必然会被美国人民所搁置,因为美国人民的基本品质就是“诚实”。因此,朗费罗的文学地位绝不像某些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高,但也绝不是垃圾,因为他有道德。
比如在《奴隶之梦》(“The Slave's Dream”)[5]中,他抱着非常大的同情之心描写了一位劳动着的黑人奴隶。他不堪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残忍白人主子的惩罚,干着干着活,就累死了,倒在地上“睡着了”。当很多美国人在歌唱美国梦之时,在黑奴制是合法的情况下,这个黑奴的美国梦是怎么做的呢?他累死了,这样他才能“进入梦乡”,去做他那个“回到非洲家乡”之梦。这是多么残酷的法律,是多么严厉的恶法,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尤其是一半国土在捍卫奴隶制的时候,尤其是在尊重法律的美国人面前的时候,诗人无疑有勇气、有胆量、有正义、有道德去挑战这样的恶法。这是何等勇敢的精神!何等的正义!几人能有?他知道,在法律和正义面前,正义总是第一位的。但这首诗并没有被中国人所热捧,因为国人体会不到或者不欣赏诗中的正义感。综合起来说,对于英美作品的赏析,绝对不能尾随中国的文学评论趣味。
中国还有一首很流行的朗费罗的短诗《箭与歌》(“The Arrow and the Song”),可惜也完全被理解错了,翻译错了。原诗如下:

这首短诗有3个诗段,每段有4个诗行,每行有8~10个音节。音节数是不规则的,因此音步数也就不规则了。多数诗段是4个音步,但有4个诗行有5个音步。其韵式是aabb。每个音步中轻重音节的规律基本上是“轻重格”,但有17处例外。如第一诗段中就有|row in|、|to the|、|air,|、|swiftly|、|follow|、|it in|。第二诗段中就有|into|、|low the|、|flight of|、|song|。第三诗段中就有|after|、|wards,in|、|And the|、|ning to|、|end,|、|in the|、|heart of|。这实在是太多,远远超出了格律诗的容忍度。只能说是不合格的英语格律诗,不过韵味还是比较足的。
诗意还有点意思。第一诗段讲箭射出去找不到了,第二诗段讲歌唱出来之后也找不到了,第三诗段就说箭和歌都找到了。箭扎在坚固的橡树上了,而歌声则存在于朋友的心中了。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箭”和“歌”的象征意义。“象征”是指“用A代表B”。那么“箭”和“歌”如果不能代表别的东西,这首诗就太肤浅,没有意思,所以它一定有所指。搞不清楚这一点,也就不能翻译正确。
三、中译文分析
翻译《箭与歌》这首短诗的译者也不少。杨霖先生的译文被收录在《英美名诗一百首》之中。他的译文如下:
我射一箭直上高空,
待它落下,不见影踪;
因为它飞得如此疾迅,
我的眼力无法追寻。
我歌一曲响遏行云,
待它飘下,无处觅寻;
谁的眼力那么强,
能追随歌声飞扬?
好久、好久后,我见一株橡树,
树上嵌着箭,完好如故;
那首歌,从头至尾,我也发现
在一位友人深深的心田[2]271。
首先这个颇有韵味的短诗在中译文中没有体现出必要的韵味和节奏感,杨先生译成了自由体。这是不应该的。须知格律体就是它的风格之一,译成自由体之后破坏了这个风格。其次,这个译文也只是将原诗的表面意思翻译了出来,还存在有重要的失误:杨先生没有翻译出来“箭”和“歌”的象征意义。这样的错译从译文“树上嵌着箭,完好如故”中就暴露无遗,因为这是最关键的诗句。
原诗的本质内涵是讲述“爱”与“恨”的问题。“对空唱歌”是指无意中对人表达了善意,多年以后却仍被人记着和怀念,这是在歌颂善意、爱心和友谊。而“对空射箭”则是指无意中伤害别人之举,虽然自己没有有目的地伤害别人,但这个动作是危险的伤人动作,而且伤人的力度还很大,就是能够射进坚硬橡树的树身那样大的力度。因为这样严重的冲击,多年以后,被伤害处的疼痛仍然存在。
科学已经证实:在树身上面钉上钉子,仪器能够检测出树在受苦受疼中的呻吟。因此,对于植物的伤害也是伤害,而诗人同时喻指对于人的伤害。显然,这首短诗是在表扬善心善意,同时在警告和批评恶的言行会导致很不好的结果。而这点重要的内涵却被翻译掉了,那是因为译者没有看懂“箭”和“歌”的象征意义。“箭”象征着“恶行”,而“歌”则象征着“善心”。
译者如果理解到了这个道德深度,他的语言和语气都会往这个方向去铺垫,这样才能让读者也能读到、感受到原作的美感和善意的劝告。
四、小结
笔者对于这首短诗的理解也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正如古人所言“读书千遍,其意自现”。笔者不断讲给学生听,讲着讲着,笔者的理解也加深了,就感觉以前讲错了。这时,笔者体会到了诗中的深刻内涵,笔者的译文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笔者现在的译文如下:
我射利箭入长空,
飘落大地无踪影。
迅若疾风瞬息逝,
何人利眼能追寻?
高歌一首对蓝天,
飘落大地无处现。
谁有非凡敏锐眼,
追溯歌声到天边?
数年以后橡树上,
利箭无损伤树身。
轻柔歌声暖意长,
善意仍存朋友心。
笔者翻译时保留了原诗的格律体,并尽力使译文押一点韵。在“利箭无损伤树身”一句中,笔者使用了一个“伤”字表达了“箭”所象征着的“恶行”。在“轻柔歌声暖意长”中使用了一个“暖”;在“善意仍存朋友心”中使用了一个“善”和“存”,就表达了“歌”所象征的“善心”。实际上,笔者花了几年时间,解决好了理解问题之后,重点只是选用了两个字“伤”和“善”,就把该诗的两个深刻内涵表达了出来。
这样,在笔者的译文中,原诗的形式和内涵都得到了全面的、最好的保持和表达。最后,诗作中的善恶自现,诗人的善恶自现,从而由不得读者不赞叹诗人和佩服诗人的道德感和文字表现能力。译者的文化桥梁作用就这样实现了,译文的文化交流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才是翻译工作的最终面目。
[1]Bode Carl.Highligh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M].Wash-ington D.C.: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Division,1987:54.
[2]孙梁.英美名诗一百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3]李正栓,吴晓梅.英美诗歌教程[M].北京:清华大出版社,2004:194.
[4]陈卫安,申玉革.一首永恒的生命赞歌——朗费罗《生命礼赞》赏析[J].名作欣赏,2007(7):101-104.
[5]吴伟仁.美国文学史及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256-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