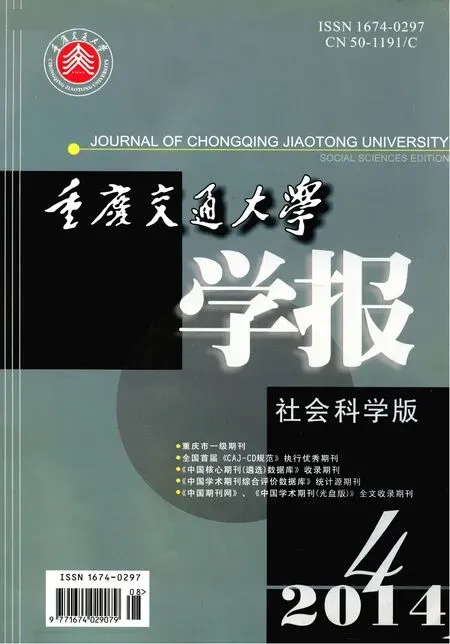藤本惠子文学中团塊者的生存困境
韦 玮
(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1171)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团塊世代是指日本战后出生的第一代,狭义指1947—1949年间日本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群,广义指昭和20年代(1946—1954年)出生的人群。这一代人年轻时候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体制的反对者,其后进入社会,成为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军,支撑着日本的中流社会。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经济低迷不振,日本进入长期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原先处于主流社会的人物开始了从“中流”向“下流”的转变。团塊者一代作为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在中流社会崩溃的背景下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威胁。
女作家藤本惠子本人属于广义上的团塊者一代。她1951年生于日本滋贺县大津市,曾先后获得“作家奖”、文学界新人奖,两次获得芥川奖候补,2001年以《响彻筑地的铜锣》获得开高健奖。藤本惠子文学涉及到团塊者题材、农村题材、边缘人物题材等方面。在其团塊者题材代表作《团塊者》后记中,藤本惠子流露出了对“团塊者在工作、生活当中的矛盾”的兴趣,也揭示了其作品中团塊者一代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团塊者》的岩田章司,《被控医师》中的医师正是经历着各自工作、生活上的困境,面临着“下流化”的危机。他们如何应对自身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实际上也反映了形塑者对团塊者一代报以了何种期待。
二、团塊者们的“下流”化危机
日本在战后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大量白领工作人群出现,迅速成长的社会知识精英和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师、医生、律师、技师等掌握各种专业技能的人群,构成了不是仅仅以财产和收入,而是以职业、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综合特征为标志的中流社会。此后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低迷不振,进入长期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大量中流社会的成员在日本企业的组织变动中失去了原有的社会位置,开始了从中流向下流的转变。“所谓下流,并非单纯指收入低,而是指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积极性、学习积极性、消费热情——总而言之即对待人生的整体热情低下。”[1]这种人生热情上的低下正是下流社会人物的典型特征。
团塊者一代是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主力军,成为社会体制的支撑者,但他们在中流社会崩溃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下流化的危机。《团塊者》中从泰国铩羽而归的岩田、《被控医师》中的医师都是一个个面临着下流化危机的人物形象。
岩田的下流化危机要追溯到他的泰国之行。肩负着到泰国打开农药销路人物的岩田在泰国却有点“不务正业”,尝试在泰国农村恢复炉子、草药治虫的试验。这些实验无疾而终,表面上是因为普恩的刺杀事件使得岩田被公司召回国内,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则是“穿着西服收割”这个岩田首先的身份属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做什么守护泰国农村的事情。岩田在工作上所感受到的困境来源于企业员工属性与个人意愿之间的对立、冲突,铩羽而归的岩田也的确感受到“公司内部也有主流的话,自己是被排除出去了”。可见此时的岩田正面临着被主流社会抛弃、沦为下流化的危机。
作为普通职员的岩田面临着下流化的危机,连精英人物的佐山也摆脱不了同样遭遇。佐山从小家境优越、成绩优秀,从一流的学校毕业,工作也是一流的会社,但是“最让人感到压力的还不是物质上的繁荣和父母的威光,也不是学历这些,而是自己积累的实际成绩起了作用”,这才是更让岩田们感到压力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精英人物在工作上跟人发生打斗,被人打伤,生活上妻子又有了外遇。在这样的境遇下,佐山请岩田给他找一个乡下干农活的地方来“疗伤”。疗伤过后,佐山恢复了回到原先社会的勇气,这也验证了之前在工作、生活双重打击之下,佐山感受着工作、生活热情的低下,面临着下流化的危机。
跟岩田相比,《被控医师》中医师的下流化危机更为戏剧化。倘若不是因为一个掺杂着不伦嫌疑的医疗事故,医师应该是与下流社会无缘的。医生的生活一直没什么波澜,不是传媒的宠儿,也不是医学界活跃人物。“即不是名医,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产科医生。”但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医疗事故,不胜其扰的妻子选择了跟医师离婚,而医师工作的医院原本就是妻子家的,这样一来,医师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工作,只是凭着离婚分得的600万日元租了住的地方,免去无处安身的困扰。医师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但正如作者在这一章节标题“流浪”所揭示的那样,医师正经历着一段流浪的时期。医师在面对流浪者时还有着强烈的抵触,认为自己跟对方不是一类人,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流浪者倒是大方地把医师当成了自己人。
实际上,医生潜意识里已经认可了自己下流社会一员的身份属性。医师重新找工作,考虑到医疗事故的影响,只能隐藏做医生的这段简历,新的简历上自己是一个没什么特长、离婚单身的人。可见,尽管医生本人对下流社会一员的身份属性还有着明显的抵抗,可是这份简历已经把他下流社会的身份属性固定了下来,而医生所找到的工作都是诸如游戏店打扫卫生、面包房打杂一类非主流社会的工作,工作的同事也都是同样被社会抛弃、没什么特长的下层人士。这些无不说明了这段时期的医生正是被主流社会抛弃、沦为下流社会一员的人物形象。
下流社会的典型特征在于人生热情的低下,医师沦落到下流社会,成为社会边缘人物,固然是由于在中流社会失去了立足之地,失去了象征中流社会的“先生”的称谓,根本原因还在于此时的医师正体验着人生的失落。离婚后,医师失去了自己多年来营建的一切,面对未来,医师茫然地发问“我还能东山再起吗”,这个疑问表明了医师精神上的虚弱。同样的虚弱表现在医师在游戏店打工的同事平岩身上。年轻时候有着音乐梦想的平岩曾有机会发行唱片、走上音乐人的道路,但因为社员携款潜逃、签合同碰到火灾等一系列的挫折没能在音乐路上走下去,只能到处打短工。屡次失败的平岩用自己的话说,“老是流产的话,子宫本身会变弱的。”亦即在一系列的挫折面前,平岩失去了工作、生活的热情,体验着一种精神上的“败北感”。要想从下流化的危机中摆脱开来,就必须恢复工作、生活的热情,摆脱虚弱的精神状态。
三、疗伤与介体——摆脱生存困境的关键
面临着下流化危机的团塊者们想重新回到主流社会,关键在于恢复工作、生活的热情。在藤本惠子的文学中,想要把面临下流化危机的主人公们从下流社会拉回到主流社会,疗伤、介体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因为欲望有别于需求,并不能直接作用到客体,因而主体惟有借助介体的存在才能激发真正的行动动机,通过模仿介体对客体的欲望,主体自身的欲望也得到强化,或因此激发出某种潜在的欲望[2]。藤本惠子文学中的这种介体功能早为学者所认同,《新宿分子》中的吴也是这样一个介体形象,“在友礼这一介体的激发下,希一和敏行们潜在的战斗欲获得了燃烧的契机”[3]。
在《团塊者》中对岩田而言,泰国女孩普拉尼和日本做小生意的老人充当着介体刺激的功能。岩田以私人旅游身份来到泰国,碰到了上次来泰国时认识的普拉尼,普拉尼此时在鸡肉加工厂工作,正组织着工厂女工罢工。岩田在鸡肉加工厂看到女孩麻利地杀鸡,想到日本的女孩子连看到鱼眼都说可怕,不由感叹日本的女孩子“明显输了”。所谓的“输”,实际上就输在行动力上,这恰恰是岩田本人所缺乏的。岩田肩负着到泰国拓展农药销路的任务,但自己又热衷于草药防虫的事情,工作也好,出于个人兴趣的试验也罢,这些最终都不了了之,虽说有着来自外界的原因,但总归与岩田本人行动力的缺乏有着莫大的关联。
在罢工问题最终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上,岩田跟普拉尼们再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罢工陷入僵局之际,岩田提出可以把鸡运到工厂内部,以此向资方施压。普拉尼听了以后决定依计行事,此时岩田反倒退缩了,声称这是他随口说的,他自己也不认为这个主意能成功。相比之下,普拉尼们则要果断得多,认定此计可行之后即付诸实行。最终在他们的压力之下,资方很快让步,双方达成了协议。罢工事件的解决离不开岩田献计的功劳,但他就是在行动力上有所欠缺,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普拉尼们,觉得计策可行之后立马付诸实施,充满了行动力。
充当介体作用、富有行动力的不光是普拉尼,岩田在自由市场上碰到的日本老人也具有介体功效。从泰国铩羽而归,感受着工作、人生热情低下的岩田代替妻子去自由市场卖饼干,碰到了卖盆栽的老人。老人尽管已是75岁高龄,但这是他第七次来自由市场,“每次卖的东西都不一样。想想下一次卖什么,这也是乐趣之一”。老人做小买卖是出于“个人爱好”,并不是生活所迫,他住着大房子,家里有着佣人,完全不用为生计烦恼。另一方面,在老人眼里,小生意并非局限在“乐趣”这个阶段。老人在生意上有着多年的经验,战后先是在青空市场卖日用杂货,之后在池袋的市场做生意。在他看来,“买卖双方的能量,成为了其后经济复苏的底力”。原本只是个商贩的老人转身一变,似乎成为了经济学家或者哲学家,将包括小买卖在内的生意上升到了经济复苏的地步。老人跳出了自己作为小生意者的局限地位,站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上来看待自己的生意,把自己的生意跟国家民族的复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此时的岩田正处在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低落中,日本老人这种把个人意愿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充满了人生、工作热情的态度,正是从泰国铩羽而归、感受到被主流社会抛弃的岩田所缺乏的。
《被控医师》中对医师而言,阿婆是一个充当着介体功能的人物。被中流社会抛弃的医生对自己能否东山再起、重新融入主流社会颇为犹豫。这个时候只有原先在医师的医院做打扫工作的阿婆关心医师的生活,鼓励医师重新找工作,尽快融入社会。跟医生的踌躇不安相比,阿婆要积极乐观得多。面对医生的疑问,阿婆充满信心,“当然了,你有医生执照,你的话,总会有人雇佣的”。
相比之下,松尾教授的介体功能更具有戏剧性。松尾教授曾经让医师在大学受尽冷遇,医师想要留在大学做研究的愿望最终因为松尾的反对没能如愿,在这个意义上,松尾先生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医师一生的敌人。医师到了老人之家做打扫卫生的工作,意外地发现松尾先生也在这里,只不过此时的松尾已经是一个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的病人。面对着这个仇人,医师尽管刚开始也有点报复的念头,不过很快就消失了,相反,医师拉上在游戏店打工时的同事平岩一起给包括松尾先生在内的老人们做音乐治疗试验。平岩的音乐会取得了成功,很受老人们的欢迎。医疗试验的效果姑且不论,正如医师所说的那样,被救的“第一是平岩,第二就是我自己了”。这里所谓的被救,指的就是在给松尾先生实施音乐治疗的过程中医师重新恢复了人生的热情,这也是其摆脱下流社会的关键所在。之所以有这个治疗,松尾先生对医师的刺激是必不可少的。
“介体”之外,“疗伤”在藤本惠子文学中起着更直接的把团塊者从下流社会拉回到主流社会的功能。作为精英人物的佐山在工作、生活中受伤之后,请求岩田给他找一个乡下干活的地方来疗伤。在工作上饱受磨难的岩田在生活上也遇到了新问题。女儿要搬出去跟人同居,同居的对象是已经38岁的上司。岩田心理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女婿”,更何况这个人现在还没有离婚,处在跟原配分居的状态。女儿把同居当成是“试着”,“试着”本意是试穿衣服的意思,人生大事当做试穿衣服一样来看待,更让岩田无法接受。原本在农药问题上就跟自己不是同路人的妻子,在女儿同居问题上也跟岩田站在了对立面。这样一来,岩田也需要来一场精神上的康复,跟佐山一起到了岩田乡下的叔叔家里,干着农活来疗伤。
疗伤的结果是把佐山、岩田从下流社会的边缘又拉回到了中流社会。佐山声称已经被治愈了,想回到过去,“以后交给命运”。这里所谓交给命运,并不是任由命运摆布缺乏生活、工作意愿的下流人物的无奈之举,恰恰相反,已经治愈的佐山又恢复了干劲,这里的以后交给命运,正是一种毫不退缩、一往无前、充满干劲的心态。另一方面,岩田也声称被治愈了,体会到当下“说败退还早”“不要示弱”。至此,岩田也恢复了对生活、工作的热情,摆脱了所面临的下流化危机。
《被控医师》中的医师重新回到主流社会,也依赖于疗伤,只不过这里的疗伤具有双重属性。岩田想要给松尾教授来一场音乐疗伤,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医师、平岩也得到了治疗。平岩有着音乐才能,年轻时也有机会走上音乐人的道路,可惜因为一连串的挫折而没能如愿,自己也丧失了工作、生活的热情。用平岩本人的话来说,他陷入了被害妄想,持续着这种萎靡的生活。平岩用子宫老是流产本身会变弱的比方来解释自己在音乐上失败多次以后失去了梦想,感受着生活意欲的低下。下流社会的人要想重新回到主流社会,首先就得燃起工作、生活的热情。实际上,即便是流浪期的医生内心也还有着向上的意愿,这向上的意愿同样存在于平岩的心中。平岩感到“跟木村有同样的东西”,而医师也感到平岩跟流浪者不一样,“虽说脱离轨道了,但是精神面貌上向前生活的火没有熄灭”。对医师、平岩来说,尽管在现实面前他们处在下流社会当中,体会着人生热情的低下,但他们内心没有完全丧失对待人生的热情,这也就是医师所感受到的“向前生活的火没有熄灭”。
来到老人之家做打扫工作的医师碰到了让自己受尽冷遇的“敌人”松尾先生,医师对这个曾经的“敌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拉上平岩一起给老人们做音乐治疗。医生宣称通过这种治疗“第一被救的是平岩,第二就是自己”,正体现了这种治疗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是医师、平岩们通过音乐来治疗这些老人,而这个过程本身对医师、平岩们也是治疗。在老人之家,平岩尽情地发挥着自己的音乐才能,给老人们带来快乐,实际上也给平岩自己带来了快乐,使之有机会实现自身价值,不再是一个作为被社会抛弃的败北者,而是作为一个音乐人立于世上。医师本人在这个过程中涌起的工作、生活意欲,正是把他从下流社会拉回到主流社会不可缺少的力量。医生称自己得救,所指的也正是通过这种为他人的付出,点燃了其“内心向前生活的火”,恢复了工作、生活的热情。
四、小结
在泡沫经济崩溃、中流社会日益下流化的背景下,原先作为社会支撑者的团塊者一代面临着失去原有的社会位置、沦为下流社会一员的危机。下流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在于人生热情低下,想要摆脱下流化危机,人生热情的恢复是必不可少的。
总的来看,藤本惠子着眼于“团塊者在工作、生活当中的矛盾”,而这种所谓的“矛盾”指向的是团塊者一代所面临的下流化危机。岩田、医师们或是心理上感受到被主流社会抛弃,或是直接从下流社会走了一遭。但他们最终通过疗伤、介质的刺激,又能恢复生活、工作的意欲,这也可以看出藤本惠子给予了面临着下流化危机的主人公们一种相对乐观的语境,对他们重新回到主流社会充满了期待。
[1](日)三浦展.下流社会 新たな階層集団の出現[M].東京:光文社,2005:7.
[2](日)作田啓一.個人主義の運命——近代小説と社会学[M].東京:岩波書店,1981:22-23.
[3]王奕红.日本当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新宿分子》中形塑者的“第四种态度”[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5):5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