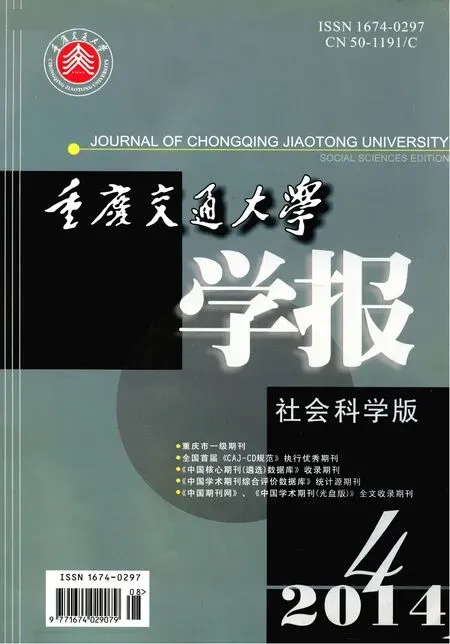从音乐到文学:“雅”之审美内涵与评判标准
吴雪美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雅”是中国文化中不同艺术形式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异于西方文学审美标准的独特气质。“雅”作为中国古代诗学重要的美学范畴,其审美观念从诞生之日起,几乎没有离开过文人的审美视线,许多文人在创作实践中不自觉地向“雅”靠拢,乃至尚“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传统艺术思维。
一、“雅”之训诂与起源
“雅”诞生于先秦文化土壤之中,对“雅”追本溯源,弄清其最初的含义,是探究其审美内涵的重要前提。究竟什么是“雅”?这个问题可以从“雅”字训诂找到答案。
“雅”字无甲骨文记载,最早出现的字形为金文大篆。然而,据古籍记载,“雅”字起初可用为“牙”。《书序》:“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尚书》有《君牙》篇,曰:“呜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1]。郑玄注:“雅,《书序》作牙,假借字也。《君牙》周穆王司徒作,《尚书》篇名也。”可知“雅”通“牙”,“君牙”大概为周穆王时期的大臣,而《君牙》则是周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时发布的策命之辞。“雅”在上古时期可作称谓之用。
许慎《说文解字》:“雅,楚乌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谓之雅。从隹,牙声。”[2]可知,“雅”为形声字。根据汉字构成的特点,形声字是在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基础上,由两个文或字复合成体,由表示意义范畴的意符和表示声音类别的声符组合而成。许慎对“隹”的解释为:“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隹之属,皆从隹。”[2]可判断“雅”字意符为“隹”,声符为“牙”。“隹”在古代泛指短尾鸟,指“鸟头尖锐”之意,“隹”与“牙”组合在一起,可理解为“尖锐的牙齿”。根据牙齿构成的生理特点,前排犬牙非常坚固,被古人视为“基准牙”。如此,“雅”在古代汉语里被引申为基准、标准、规范之义。
《说文》曰:“雅,楚乌也。”徐铉认为“雅”“今俗别作鸦,非是”,《小尔雅》云:“纯黑返哺者谓之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雅”。《说文通训定声》指出:“雅即乌之转声字亦作鸦。”可知,“雅”即“鸦”,先秦时期指一种鸟。而近代学者章太炎考证,他认为“雅是近似馨鼓的一种乐器名,同时又认为是一种发声乌乌的曲调名”;“雅”与“乌”古同声,发“乌”音,“乌乌”则是秦地一种特殊的声音。《周礼·春官·笙师》曰:“掌教龡竽、笙、埙、籥、箫、篪、笛、管、舂牍、应、雅,以教祴乐。”[3]郑玄注引郑司农曰:“雅,状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纽疏画。”这大概就是上古时期“雅”乐器的形状。可知,“雅”亦可指一种命名为“雅”的乐器,这是后世“雅乐”之称谓来源的一个依据。
“雅”在文学领域的运用最早应始于《诗经》。“雅”在先秦时期指《诗经》六义之一。《诗序》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为《诗经》作品不同题材、风格的分类,主要针对篇章体制而言。而“雅”作为《诗经》的一个组成部分,分为大雅和小雅两个部分。“雅”亦可指周代的万舞。《诗经·小雅·鼓钟》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郑玄笺:“雅,万舞也。万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进退之旅也。周乐尚武,故谓万舞为雅。雅,正也。”
此外,“雅”通“夏”,指中国,今中原地区。《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最后,“雅”亦可指“雅言”,官方的标准用语。《论语·述而》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训诂与起源的角度来分析,“雅”在先秦时期有着丰富的含义,不管是用来形容《诗经》六义之一,还是形容语言、地名、乐器,都与“正”相关联,“雅”之原始审美内涵与正确、规范存在密切联系。
二、“雅”与上古音乐之关系
在中国文论中,文学与音乐关系密切,二者的审美原则存在许多相似共通之处。“雅”与音乐的渊源可以从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以及《诗经》诗歌入乐与分类之说进行说明。
诗乐舞三位一体是中国文化早期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礼记·檀弓下》曰:“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也”,较早论述了诗、乐、舞之间的关系。《毛诗序》以“诗言志”为基础,进一步解释了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关系。然而,从文学与音乐关系探讨“雅”在文学领域审美内涵的形成,需要注意诗、乐、舞这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的产生存在先后之别。有学者认为“乐一,舞二,诗三”[4]即认为音乐先于诗歌和舞蹈存在,这一说法得到学界认可,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文学理论起源于音乐理论”的观点。由此可知,在上古时期诗歌、音乐、舞蹈三者之审美内涵存在相似之处,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上古音乐的审美标准为文学审美所吸收借鉴。那么,“雅”作为中国诗序美学范畴,其审美内涵是如何从音乐中孕育而出的,“雅”与音乐的关系如何形成?这个问题可以从《诗经》与音乐的关系进行说明。
《诗经》是先秦时期文学与音乐结合最鲜明、有力的证据,历代典籍的相关记载与后世文人的考证已让《诗经》诗歌入乐之说成为公认的事实。
关于“《诗经》风、雅、颂的分类之说,最早见于《荀子·儒效》,这是古今最被认可的分类方法”[5]。《诗经》风、雅、颂根据音乐的不同进行分类。此外,宋代朱熹认为《小雅》为“宴飨之乐”,《大雅》为“朝会之乐”,两者“词气不同,音节亦异”。唐孔颖达则认为:“诗人歌其大事,制为大体;述其小事,制为小体,体有大小,故分为二焉。……诗体既殊,乐音亦殊。”[6]可知,大、小雅亦是根据音乐性质的不同进行划分。由此可知,《诗经》中《雅》诗部分的音乐性质与美学标准应是构成“雅”审美内涵的重要来源。
从“雅”之训诂与起源、上古诗乐舞三位一体、《诗经》入乐与分类之说可推断,“雅”最初应是用来描述音乐的,与上古音乐曲调、风格、演奏方式等有关。“雅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雅乐与乐的最初域义接近,不仅指音乐,还应该包括乐舞之乐的原始艺术形态。”[7]根据《礼记·名堂位》的记载,上古时期的“雅乐”主要指在郊社、宗庙、宫廷礼典、乡射和军事等各种重大礼仪祭祀场合表演的乐舞、乐曲、乐歌。这一部分的“雅乐”也包含《诗经》中《雅》诗部分的音乐。
“雅”之概念与音乐密切相关,而“雅”亦可指周代的万舞,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有舞必有乐,如此,“雅”从音乐描述过渡到文学审美领域,则不可避免地继承了“雅乐”的审美原则。
三、“雅乐”之性质与艺术构成
“雅乐”的性质与特点主要由“正”“和”与教化功用三部分内容构成。首先是“雅乐”之“正”。上古时期“雅”与“夏”通,“雅声”即为“正声”,而“夏”指中原地区,“正声”应为西周王畿的雅正之乐。可知“雅乐”指朝廷正乐。上古时期“雅乐”为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飨时所用的音乐,内容庄重、严肃,演奏过程规范、严格,音调“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代表规范与正统。由此,“雅乐”之“正”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朝廷大型典礼、仪式演奏的正乐;二是正确、规范。“雅”审美内涵起源于“雅乐”,而“雅正之乐”是儒家文艺批评的重要标准,“正”的内涵也就成为后世“雅文学”的评判标准。
其次是“雅乐”之“和”。“雅乐”的核心美学精神是“和”。“雅乐”之“和”包括内在之“和”与外在之“和”两个层面的意义。内在之“和”指上古音乐自身的一种属性;外在之“和”则是“雅乐”演奏所要达到的目的,使听者得到审美愉悦,以实现内心的和谐,维护社会和谐。《尚书·尧典》日:“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8]1“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说明了音乐本身“和”的重要性。《礼记·乐记》认为“雅乐”“其声和以柔”。《诗经·商颂·烈祖》亦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顾霞无言,时靡有争。”意思是说纯正平和的音乐可以让人心平德和、气定神闲。《国语·周语下》:“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乐和,律以平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9]《淮南子·天文训》曰:“宫生徵,徵生商,商羽角,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应生钟,比于正音故为和。”[10]东汉高诱注:“应钟十月也,与正音比,故谓和。”这里“和”表示校正音高,使之协调于音高标准,有指调、谐和之意。“雅乐”外在之“和”指“雅乐”教化功能,通过音乐对人情感的陶冶,使人感受到愉悦,净化人的心灵,使人的内心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通过实现人自我的和谐而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雅乐”之“和”涉及到人的主观情感体验,与审美挂钩,是“雅”审美内涵形成的一个启蒙。
最后是“雅乐”之教化意义。《礼记·乐记》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周礼·春官·大司乐》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袛、庸、孝、友。”说明了上古时期音乐用于教化的社会功用性质。古人认为“乐”能善化人心,移风易俗,使尊卑、贵贱、上下之间相亲相爱、和谐共处,用以维护社会的和谐。孔子主张以“乐治国”,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音乐“美刺”“教化”的社会功能。此外,《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善矣,又尽美矣。谓《武》,尽美矣,为尽善也。”[8]7在孔子看来,音乐的审美价值不仅在于其外在的曲调,其内在意蕴更为重要。
归纳起来,“雅乐”之“正”“雅乐”之“和”、“雅乐”之教化功能构成了“雅乐”的审美内涵与评判标准,而“雅”在文学领域的审美内涵也吸收了“雅乐”“正”“和”与教化作用的基本内涵。然而“雅”从音乐过渡到文学审美,仍是一个需要外部因素助推的过程。
四、从音乐描述到文学审美
“雅”从音乐描述逐渐过渡到文学审美,吸收和延续上古时期“雅乐”的审美内涵与文化意义,中国古典文学审美意识的觉醒、《诗经》文化传承、文人审美与创作倾向、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文学审美意识的觉醒。“雅”形成丰富审美内涵的过程,实际上可以说是文学审美自觉的一个过程。中国文学在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文学泛指一切文章,审美意识淡薄。中国古代无“审美”一词,先秦时期有“观”“赏”“览”“品”“味”等概念,中国文人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审美的特征,有“乐水乐山”说、“心物感应”说等,但这只是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一个初级阶段,尚处于朦胧当中。上古时期文人虽然没有系统的审美理论,但对“雅”的审美倾向却是明显的。如先秦《楚辞·大招》曰:“容则秀雅,犀朱颜只。”王逸注:“言美女仪容娴雅,动有法则,秀异于人。”这里的“雅”谓之高雅不俗,优美。在楚辞创作中,“雅”已经开始成为一种审美观念。到了汉代,“雅”在文人的著作中多次提及,含义也逐渐丰富起来。贾谊《新书·道术》曰:“辞令就得谓之雅,发雅为陋。”倡导文学创作的语言要“雅”。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从车骑,雍容娴雅甚都”,指雍容娴雅状态之美。王充《论衡·四讳》提出“雅俗异材,举措殊操”,雅与俗成为对立的审美概念。《汉书·王嘉传》:“谭坡知雅文。”可知,在两汉时期,“雅”之观念已经深入文人审美与创作意识,“雅”之观念也具备了规范与标准。中国古典文学审美意识的萌芽与觉醒是“雅”之审美内涵与“雅文学”评判标准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到了魏晋之时,随着文学创作与审美的自觉,文学的审美理论才逐步形成比较系统、完善的理论。
其次是《诗经》文化的传承。根据文化延续性的特征,一种文化诞生和发展,延续性是其存在的现实依据与发展的前提。《诗经》的篇章体制是后世文学创作的典范,《诗经》的文化传承“雅”是从音乐描述过渡到文学审美与评判领域的关键性因素。《诗经》的文化传统继承与延续是“雅”审美内涵与文化品格生成的重要原因。《诗经》中“风雅”精神所表现出的关心现实、情志充实深刻、艺术表现明朗真朴的优良传统,在后世文学中得到继承与延续,也是“雅”审美标准的一部分内容,是构成“雅”之审美内涵与文化品格的重要因素。《诗经》所具有的美刺讽谕精神及其批判现实的文化精神,更是成为“雅”文学评判的主流。此外,《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都被后人当作典范,成为文学创作的楷模。
最后是“雅乐”审美内涵的延续。前面第二、三部分已经论述了“雅”与音乐的关系,以及“雅乐”的性质与艺术构成。“雅乐”亦指《诗经》中《雅》诗部分的音乐,“雅”吸收了“雅乐”中“正”与“和”的文化内涵与美学基本原则,形成其自身的文化品格。再加上儒家推崇“雅乐”,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和”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为诗歌定下“和”的基调。由此,“和”在音乐领域的审美原则被“雅文学”所吸收和借鉴。
“雅”的审美内涵在先秦时期就已萌芽,文人已经具备“雅”之审美观念,但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的含义;“雅”审美内涵的丰富是后世文人审美倾向与创作实践的结果。到魏晋之时,“雅”成为内涵丰富的审美范畴,并就“雅文学”之品评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品评标准。
五、后世“雅文学”评判标准
“雅”发展到魏晋之时,具备清晰审美概念与评判标准。刘勰对一百多位作家及相关作品进行评判,他在《文心雕龙·征圣》中说“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雅”即一种雅正的内容,“丽”即华,指华丽的言辞和形式。可知刘勰把“雅”视为一种文学理想状态。至此,“雅文学”具备了一套理论完善的评判标准,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儒家经典范式的文体风格。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曰:“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鬼儒门者也……”刘勰对不同文体风格进行概括,这里所说的典雅就是要取法经典,继承儒家的经典范式。
刘勰从文章体式和风格对“雅”之文学进行评判,他在《宗经》一文中围绕文章内容与语言表达的问题,将“雅”概括为六个方面:“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11]28。刘勰认为写文章应根据“五经”的体式去写作,吸取“五经”“雅正”的言辞以丰富表达,效法“五经”创作。所谓儒家的典范式文体风格有以下要求:感情深挚而不诡谲,符合《诗经》所倡导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即情感中正和谐的要求;文风清新而不驳杂,即文章内容要规范,表现事实与情感专一,不杂乱;叙事真实而不荒诞,即叙事要有现实主义精神,与《诗经》反映显示的创作要求挂钩;义理正确而不歪曲,即文章要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符合正统,实事求是;文体精约而不繁芜,达到语约义丰的表达效果;最后做到文辞华丽而不过分。自此,“雅”之审美观念与评判标准形成系统的理论范畴。刘勰提出的这些要求成为后世对“雅文学”进行评判的主要依据。
二是“雅文学”要具有讽谏、教化意义。后世被称为“雅”的文学在内容和思想上除了达到纯正的要求,更要具备教化功用,符合儒家所倡导的文学教化功能。如西汉杨雄对汉大赋特征的描述是“曲终雅奏”,即“劝百讽一”;这里“劝”是鼓励、提倡之意,“讽”是“讽谏”“劝谏”之意。“劝百讽一”就是说“劝”与“讽”二者在汉大赋中的比例悬殊。汉大赋的主要特点是铺张夸饰、辞藻华丽,用极大的篇幅和过量的辞藻铺叙奢侈享乐生活,却在结尾处出现讽喻之意,实现了一个“曲终雅奏”的效果。杨雄把这几句讽谏之语比喻为“雅奏”,认为它符合文学的教化意义,符合道德的规范作用,因而称之为“雅”。
三是创作主体精神品格高尚。“雅”作为中国诗学的美学范畴,体现着以朝廷与士大夫审美情趣为正统的,以恪守现实文化秩序和规范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士人意识及其独立道德人格完善为基准的美学精神导向。正如王谦先所说:“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谓之雅。”刘勰亦指出“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11]331,认为感情受到触动而形成语言,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转化成为文辞,而文章的内容是借助形式表现出来;人的才智有平庸、俊秀之分,气质有刚强和柔弱的不同,学识有浅薄的、高深的,洗染有雅正的、淫靡的,这都取决于创作主体的文化修养情况。王国维提出“古雅”的美学范畴,其核心观念就是“雅”。他认为艺术中古雅之部分,“苟其人格诚高,学问诚博,则虽无艺术上之天才者,其制作亦不失为古雅”。“雅”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首先要“正”,具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
六、结语
魏晋之后,“雅文学”的创作呈现繁荣的趋势,许多文学样式都经历过一个“雅化”的过程,“雅”与“俗”存在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而“崇雅抑俗”始终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传统艺术思维。“雅俗”之分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的文学现象,许多文学样式经历过一个雅化的状态。如苏轼认为“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则提出“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形成了江西诗派“点铁成金”“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独特创作理论。随着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雅”与“俗”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不能成为衡量文学优劣的标准,被称之为“俗文学”的文学样式同样有许多经典的作品,这也是文学发展的进步之一。
[1]顾迁.尚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273.
[2](汉)许慎撰.说文解字[M].(宋)徐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63:76.
[3]吕友仁,李正辉.周礼[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218.
[4]门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汇典:上[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1129-1131.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9.
[6](汉)郑玄.十三经注疏[M]//毛诗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272.
[7]李天道.“雅乐”之美学意义原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1):105-107.
[8]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罗家湘.国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97.
[10](汉)刘文.淮南鸿烈集解[M].冯逸,乔华,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113.
[11](魏晋)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