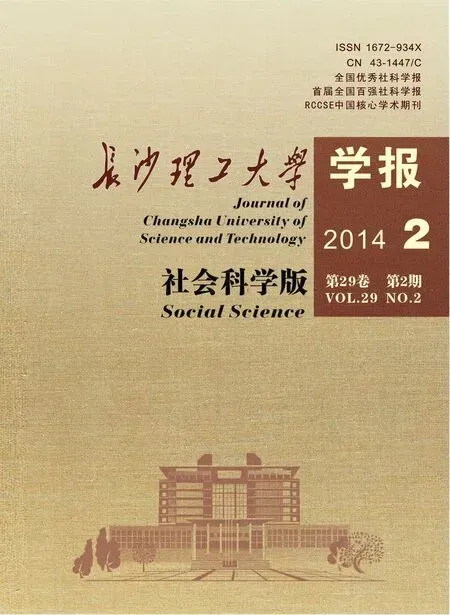文化身份的消解、重建与回归
——以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为例
唐丽伟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文化身份的消解、重建与回归
——以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为例
唐丽伟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讲述了主人公丽贝卡在美国隐藏犹太身份、追寻美国身份、回归犹太身份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犹太移民终其一生在反犹环境下寻求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本文从文化身份的视角,探讨了导致丽贝卡身份变迁的主要原因:第一,丽贝卡从隐藏犹太身份到追寻美国身份并不是美国文化简单地消解、同化犹太文化的结果,而是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历史汇合;第二,丽贝卡回归犹太身份也不意味着犹太移民对美国文化的否定,而是其在理解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的自我抉择,即犹太文化始终以各种方式制约、规范和影响着美国犹太移民。
文化身份;犹太移民;犹太身份;《掘墓人的女儿》;欧茨
文化身份和认同问题(cultural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人在文化上的归属感,是对一个文化基本价值取向的态度,是与家园认同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问题。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涉及到角色定位、自我认同和他人的承认等几个方面。对于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与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与权力的不断‘嬉戏’。”[1]我们认为文化身份认同主要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面临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时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思想震荡与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这是因为:文化身份认同一方面是为了现实生存对迁入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潜意识中对本民族文化的记忆和保留、对迁入地文化的抗拒等,甚至始终处于二者相互矛盾的“中间状态”。身份确认是个体内在的行为要求,一般而言,居于主流地位的、强势的团体及其个体在文化认同问题、文化身份确认问题上是不存在困惑的,因为他们生活在稳定、自足的民族和家园中,他们的身份有着安全、可靠的保障,所以不必怀疑和质问自己的文化身份。只有居于弱势地位的团体及其个体才会不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求证。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小说《掘墓人的女儿》以主人公丽贝卡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以心理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个被边缘化的德国犹太后裔在美国隐藏犹太身份、追寻美国身份、回归犹太身份的心路历程,揭露了美国社会自二战以来对犹太移民的偏见与歧视。我们试图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阐述美国犹太移民是如何在与异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思考自己的文化归属和进行身份选择;在犹太移民成功融入美国社会之后,犹太传统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是以怎样的方式制约、规范和影响着他们并最终导致其回归犹太文化身份等问题。
一、文化身份的消解:隐藏犹太身份
对于美国犹太移民而言,身份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化变迁的一种核心标识,也许正因为如此,欧茨对《掘墓人的女儿》中主人公的犹太身份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和表现。就像托马斯·索威尔所说,“种族身份的重要性,在各个种族内部是有巨大差异的。对某些人来说,种族身份是一种足以在世人面前加以炫耀的自豪标志。对别的一些人来说,种族身份是一种值得珍惜的个人生活方式,虽然无需公开张扬。另外还有一些人,对他们来说,种族身份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令人好奇的东西——或是一种尽量予以忘却、回避或逃脱的污点。”[2]作为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丽贝卡一家在踏上美国领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只有对犹太身份“尽量予以忘却、回避或逃脱”才可能在反犹主义大行其道的美国得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
为了隐藏犹太身份,雅各布不许家人讲德语,他“要让孩子们学英语,要让他们把英语说的跟真正的美国人一样”[3](P83),这就意味着一家人为了隐藏身份,不得不放弃母语。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来看,语言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克拉姆契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谈到:“一个社会群体成员所使用的语言与该群体的文化身份有一种天然的联系。”[4]正如海德格尔的那句著名论断,“语言是存在之家”,把人的最高本质归结为语言的存在,“任何存在者的存在都居于词语之中”[5]。因此,作为思想现实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身份,一种文化的存在。移民到美国之后,丽贝卡一家身处的语言环境和社会背景都发生了变化,语言隔膜、失语症或是语言混杂等问题自然而然凸显出来。由于语言文化差异所隐含的冲突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安娜学习英语特别吃力,直到临死她讲这门后学的语言都缺乏自信。在一次单词拼写比赛中,丽贝卡通过努力获了奖并得到一本字典作为奖励,两个哥哥也认为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但父亲对于此事却极度鄙视。对于中年的安娜而言,移民美国后的失语不只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同时还来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误解。她学习英语的痛苦和自卑反映了移民能否在异国扎根取决于他们对该国语言文化的接受和转换,取决于在应付自谋出路的艰难和文化失语症中的坚韧。因此,失语往往意味着身份的遮蔽。
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仍然强调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从来就不信任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可能真正成为欧洲主流社会的一部分。正如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平斯克所言,“对于活着的人,犹太人是死去的人;对于当地人,他们是异己和流浪者;对于有资产的人,他们是乞丐;对于穷人,他们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对于社会各阶层的人,他们是令人厌恶的竞争者。”[6]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第一次反犹主义高潮时期,犹太人是“美国经济的攫取者”、“破坏美国人血统的贱民”、“国家的颠覆性的因素”等观念甚嚣尘上,犹太人在美国遭到强烈的攻击。基督教反犹主义的传统经过美国第一次反犹主义高潮的大肆渲染和强化,成为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再度爆发的反犹主义高潮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20世纪30、40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难民潮的发生,以及美国本土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美国又爆发了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犹太人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全社会的攻击。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反犹偏见大行其道。“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偏见之中,很少有基督徒不曾轻视过亚伯拉罕的子孙。传教士从来没有停止过强行要求犹太人改宗,以拯救他们的灵魂,同时灭绝犹太教。”[7]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几乎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反犹主义,反犹主义也成了与犹太人俱在的一种生存外因。丽贝卡一家是这段不幸历史的亲身经历者:万圣节时,墓园的所有设施被当地人破坏得一塌糊涂,房子外到处刻上纳粹的标志符号。在学校里,三个孩子也受尽了排斥和欺凌。丽贝卡在学校饱受歧视欺辱,可是无人替她撑腰,最终她没等到十六岁生日就退学了。“在中学里,别人老是骚扰她。老师们和校长也都知道这事,可就是听之任之,从不出面干预……丽贝卡被摔倒在地,众人都伸出脚来,一脚接一脚朝她的身上踢去。此时,走廊里的人,个个欢欣鼓舞的样子,好像在观看一场野火似的。”[3](P215)因为是犹太后裔,丽贝卡时常感觉父亲做的事情就像一道光晕,始终罩着她。她走到哪儿,那光晕就跟到哪儿。“这道光晕她本人看不见,但旁人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光晕还散发着一种气味,这气味和镇垃圾场里闷烧着的废弃轮胎发出的气味无异。”[3](P217)大哥赫彻尔因反抗他人羞辱而打伤对方后为躲避警察的抓捕而亡命天涯,紧接着,不堪忍受父亲暴力的二哥也离家出走。最终,父亲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枪杀母亲后自杀,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在自我的内心煎熬和反犹主义的外部打击中消亡。在饱尝歧视、兄长离散、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初婚被骗并遭受家庭暴力的种种心酸经历中,丽贝卡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她身上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承载者犹太文化传统,处在夹缝中的丽贝卡在美国主流文化社会中被彻底边缘化,丧失了文化身份。她困惑着自己到底是谁,犹太人?美国人?她不知道自己归属何在。
二、文化身份的重建:追寻美国身份
对于处在文化边缘地位的美国犹太移民来说,其文化身份危机感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感、无根感尤为深切,正如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中痛楚的叩问,“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什么——对于流浪者而言是很难维持。”[8]也许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这样深层的渴望:清楚自己的身份,是做什么的,并永远坚守这样的知识,生活在难以动摇的信念的幸福状态中。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人生的每一步都必须摧毁原有的身份,如果身份的变化只能是旧身份的瓦解,所以人不得不无数次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那就真是人生境遇的一大不幸,令人不安了[9]。文化身份建构的过程包括自我认同与外部认同两个过程。前者是指一个文化群体自我认可并表现给他人的形象。后者指他人赋予某个文化群体的形象。这两个过程共同作用才能构成群体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的建构依附于众多因素,主要包括语言、外表形式特征、心理结构等等。为了使自己和儿子能在美国生存并不再受人排斥,丽贝卡也选择了摧毁原有的犹太身份,重新建构美国身份。
在带着儿子成功逃离提格诺之后,为了彻底与犹太身份决裂,丽贝卡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更改名字。她为儿子从《圣经》里取了一个名字,扎卡奈亚斯,给自己取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化名字“黑兹尔·琼斯”。众所周知,名字蕴涵着历史和文化,是身份的象征,因而每个民族都赋予其非常重要的内涵。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名字是其人格的重要成分,甚至是其灵魂的一部分。人的名字是其身份的昭示,丽贝卡意识到,重新取名是建构新身份的一个重要手段,新的名字标志着自我的新生。除此之外,在外型方面,丽贝卡也极力向美国人靠拢。因为觉得自己的样子像印第安人,她对自己的长发都心生厌恶,“这油腻发臭的味道折磨着她的灵魂”,于是将长发剪成清爽的短发,看上去就是一个貌美的美国女孩。在与加拉格尔交往过程中,丽贝卡无论在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上,都丝毫不敢懈怠,“她会用浅色乳液和粉底液来掩盖自己的深色油性皮肤……她还会藏好自己发际处淡淡疤痕,以免被加拉格尔看到……她的发色是栗色的,其中挑染了几处深红色,这很适合她黑兹尔·琼斯的身份。”[3](P455)为了彻底与犹太身份割裂,在丽贝卡偶遇哥哥古斯时,她极力掩饰,否认自己认识他。她和孩子一路逃亡,从未回过头。她努力从事流亡中的每一份工作,维持母子的生计。在马头镇拿到威利帮自己和儿子开的身份证明时,她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停下来了,扎克。我们可以跟别人一样,证明我们是谁了”[3](P387)。丽贝卡与加拉格尔的相识,是其成功建构美国文化身份的关键因素。小说中,丽贝卡一直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即使成为黑兹尔之后的她依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什么工作都干过:餐馆服务生,清洁工,酒店清洁员,卖过票,当过电影院引座员,商店女店员。还要时刻带着“美国甜妞式的经典微笑”,跪下来给穿长袜的男人试鞋……对于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单身母亲来说,任凭自己如何努力也难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加拉格尔的出现就改变了“黑兹尔”的命运,通过与加拉格尔的联姻,她不但为自己和儿子获得了经济上的依靠,而且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主人,一个未来钢琴家的母亲。她不用再担心周围人的歧视,甚至还深受大家的喜爱。至此,她真正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成功的将犹太身份隐退,转换成了美国身份,成了地道的美国人!她所拥有的不但是美国名字,美国女人的外表,更重要的是通过跻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而融入了美国文化。
丽贝卡犹太身份转换的意义首先在于,她以犹太移民个体的身份变化,揭示了犹太文化在与美国文化的接触、碰撞中所发生的历史变化。文化个体比较一种文化的整体而言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有着更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丽贝卡犹太身份的消解与美国身份的重建也表明了在现代美国生活情境下,犹太人业已走出传统的犹太圈子,他们不仅逐步汇入到大美国的统一生活潮流中,也在更多的生存问题上与美国社会达成了新的契合和一致。对拥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欧茨来说,她笔下的丽贝卡及其所代表的犹太移民所发生的每一种心理变异、身份困惑,都以小见大的揭示了整个犹太移民群体在美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他们渴望早日同化于美国,希望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往往很少。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正地美国化,他们既不能同化于美国,又无法回归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失去了旧的身份,又难觅新的身份,成了美国社会中“没有身份的美国公民”。
三、文化身份的回归:寻根犹太身份
文化身份的追寻是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作为少数族裔的丽贝卡在经历了诸多生活磨难和精神上的痛苦与挣扎后,开始意识到舍弃族裔传统只会令自己陷入身份混乱和分裂状态中。在加拉格尔带她到格林斯顿岛上那次,“黑兹尔很早就醒了……她的心脏在胸膛中猛烈的跳动着,耳边有一个放肆大笑的声音说,你这个犹太姑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3](P453)在拒认哥哥古斯之后,她好几次偷偷跑去公园,但没能再见到哥哥。“沮丧的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她多希望可以再和他不经意的相遇”,“那个男人的声音刺穿了她的心!他提起了她的名字,她好久都没被别人这么叫过了。”[3](P527)婚后给儿子办好领养手续后,她觉得“心里藏着这么多秘密”,常常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喜欢独处,“一个人呆着真开心!……不当黑兹尔·琼斯的感觉真好。”[3](P543)虽然她已经成功实现了身份转换,也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但她自己明白:丈夫所尊重所爱的是“黑泽尔·琼斯”,而非“丽贝卡·施瓦特”。在旧金山观看儿子钢琴比赛时,她的思绪回到了童年,内心却听到了自己和母亲的对话。夜晚睡在丈夫的身边辗转反侧,心神不安,她觉得自己到现在还无法表达对丈夫的爱,只因“她被剥夺了说母语的权利,而其他任何语言都表达不了她的心声”[3](P549)。处于极度挣扎和痛苦中的“黑兹尔”心里想着“我要叫醒他,告诉他我是谁。我要告诉他我的人生充满了谎言和讽刺。根本没有什么黑兹尔·琼斯。在我的故土,谁都不在了”[3](P518)。然而,最终她也没有告诉丈夫这个秘密,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玩着犹太人才玩的纸牌游戏,悄悄地给犹太表妹写信。在她的内心,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形成了身份选择所产生的强烈的思想震荡及巨大的精神磨难。
为了让主人公得以解脱,作者在小说“跋”的部分终于为读者展示了犹太移民后裔不再为获得主流文化的接纳而疏离甚至抛弃传统和族裔性,而是加以肯定和接受,最终走出文化身份的迷失和分裂状态。从1998年9月到1999年10月,丽贝卡和表姐摩根斯腾共有二十九封书信往来,这些信件的主题从内容上看是丽贝卡的“寻亲”,实际上是她对自身犹太身份的认同和回归。丽贝卡本人并非大屠杀的亲历者,但是她和她的家人却一直生活在大屠杀的阴影下。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阅读了摩根斯腾教授的《起死回生:我的少女时代》,从摩根斯腾教授关于犹太种族大屠杀的亲身经历的叙述中,丽贝卡推断对方正是自己素未谋面却一度朝思暮想的失散于二战期间的表姐,于是便不断地写信给对方追忆往事,并且执着地希望“认亲”。她沿着回忆录中的线索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在自身记忆的对照下不厌其烦地核实着相关的年代、人名、地点、事件等基本史料,甚至试图更正摩根斯腾记忆中的难民船名称,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她与回忆录作者的“表姐妹”身份[10]。丽贝卡的“认亲”过程是一个从被拒绝到互动到被接受的过程。她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给摩根斯腾连续发出七封信,其间她收到了一封拒绝所有认亲请求的公函和两封言辞冷漠的简短拒绝信。然而,丽贝卡锲而不舍,用精心挑选的明信片打动对方,摩根斯腾开始与她进行思想的交流。在摩根斯腾收到丽贝卡1999年1月30日的简短回信之后,接下来两个月不再有丽贝卡的消息。这时候,双方的通信状况发生了逆转:摩根斯腾在信中开始表达对“表妹”的想念、关心和收不到回信的焦虑、懊恼等,言辞也由之前的冷漠变得饱含温情;丽贝卡的信却变得简短到最后完全失去联系。从两人之间的二十九封往来信件可知,丽贝卡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通过回忆完成了犹太身份的回归。
四、结语
《掘墓人的女儿》中丽贝卡犹太身份的消解、美国身份的重建和犹太身份的回归昭示了犹太移民在对美国生活的汇入中业已生成的新的身份特征,即既作为犹太人又作为美国人,以及既不同于纯粹的犹太人、又不同于纯粹的美国人的新的文化特征。丽贝卡犹太身份的演变是以文学的形式从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角度对犹太文化和美国文化历史汇合及其结果的一种写照。但值得指出的是: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汇合并不意味着犹太文化业已丧失其内涵,更不意味着犹太移民必然要被美国文化所同化。因为作为一种文化流变,美国犹太移民在融入美国社会生活时,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不会消失,这不仅是其文化传统强大的生命力使然,也是由诸多外部条件所决定的,特别是那些令犹太人不能忘怀的历史,更促使犹太移民在汇入美国生活时,绝不会抛弃传统、抛弃其民族文化。即使在战后的美国,犹太移民也许不会再有二战期间德国犹太人的类似遭遇,但历史作为犹太人的一种“遗产”和传统,也必定会在犹太移民的文化操作中发挥其深刻的内在效用。现代以色列的建国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冲突,也从一个独特的方面吸引着世界各地犹太人对“犹太问题”的关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决定了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对居住地文化的汇入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整合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变迁的文化自律运动。
[1][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9 -223.
[2]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3-97.
[3][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掘墓人的女儿[M].汪洪章,付垚,沈菲,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4]Claire Kramsch.Language and Cultu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65-126.
[5][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 1065.
[6]Walter Laqueur.A History of Zionism[M].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2:72.
[7][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M].杨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18.
[8]Edward Said.After the Last Sky[M].New York:Pantheon, 1986:16.
[9][荷]塞姆·德累斯顿.迫害、灭绝与文学[M].何道宽,译.广州:广东花城出版社,2012:76.
[10]林斌.大屠杀叙事与犹太身份认同——欧茨书信体小说《表姐妹》的犹太寻根主题及叙事策略分析[J].外国文学.2007(05): 3-10.
The Destruction,Reconstruction and Return of Cultur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Joyce Carol Oates'The Gravedigger's Daughter
TANG Li-w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The Gravedigger's Daughter,written by Joyce Carol Oates mainly talks about a Jewish immigrant who had suffered a lot in the process of hiding her Jewish identity,pursuing American identity and eventually returning to Jewish identity.It reveals the soul journey of Rebecca,living in the anti-Semitism America,in pursuit of"herself".In view of cultural identity,we discuss the reasons that lead to the change of Rebecca's identity:On the one hand,the"change"is the confluence of Jewish culture and American culture rather than a simple decomposition or assimilation.On the other hand,the return of Jewish identity doesn't mean her denying of American culture,but actually a decision made by herself on the basis of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her history and reality.Jewish culture will always influence,specify and restrain the life of A-merican Jewish immigrants in various ways no matter whether with an American identity or not.
Key words:cultural identity;Jewish immigrants;Jewish identity;The Gravedigger's Daughter;Oates
I106.4
A
1672-934X(2014)02-0107-05
2014-01-30
唐丽伟(1980-),女,湖南株洲人,讲师,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翻译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