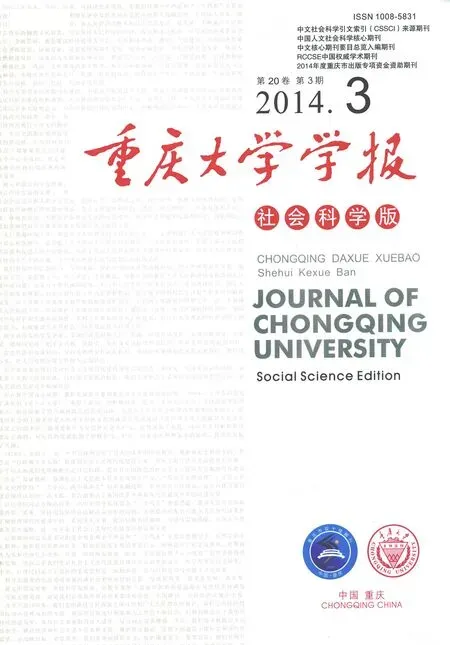论工具理性下智慧重建的一种可能路径
张礼建,向礼晖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论工具理性下智慧重建的一种可能路径
张礼建,向礼晖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以分科之特征反映世界,形成了不同的学科,并拓展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把握,但这种理解与把握随着技术的侵入与成功从一个方面加强了这种知识的权威性,从而使得工具理性下对自然的理解与利用得到张扬,但另一个方面也折射出在工具理性下对自然统一性分割下认识的片面性,而这与人对自然整体性观照有冲突之忧;如何在工具理性下智慧重建是科技哲学必须直面的问题。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在对事实割裂下的智慧重建的可能诉求。
工具理性;事实割裂;智慧重建路径
科学通过技术的中介而产生的社会效应要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以智慧作为一个平台。智慧是包括价值、信念、理性、知识、习俗等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是在整体下对事实的一种观照与把握,以整体性与终极关怀为核心处理人类社会行为与实践活动的一种态度。在哲学上,一般把形而上学定义为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它追问的是“存在为什么存在”,追问的是根本和基础。从而认为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而这种智慧是在整体性上才能显现与产生。而以分科为特征的各门具体自然科学门类,如物理学等则研究某一特殊领域的“存在”,也就是“存在者”,是对整体的一种分解性认识与把握。西方自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以对世界的事实收集与割裂为途径,建立起对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利用与控制自然方面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时代下人们的头脑中往往把自然科学研究事物的途径与方法,即对事实的收集与整理、概括,看成绝对的东西,忽视了智慧对科学与技术的观照。如任其发展,我们认为可能造成科学技术发展目的的模糊。科学是一列飞驰的火车,而智慧观照下产生的人类价值观体系却是这列火车上的刹车系统与方向控制系统,只有此系统运行正常,科学技术才能和谐发展,为人类服务。
一、自然科学对世界的把握以对整体事实的分割为切入口,而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专业化和研究内容不断精深,使这种情况更加突出
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对寻求知识的途径与手段作了比较,他认为感官知识是个别的、零碎的,经验使个别知识关联起来,因此经验高于感官知识;而技术是在个别知识基础上所达到的普遍性的判断,并且掌握了事物的原因,它既高于感官知识,也高于经验。但这些也仍然不是对待世界最高明的层次,要得出“事物背后的一般”才是高明的状态。在《形而上学》第4卷中,亚氏将哲学与科学大致区别,指出哲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ing)、本体的性质、变化的原理和终极原因的,而科学只是割取了“存在”的一部分。开始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根据或语境就是牢固地扎在经验的泥土中,虽然他仅把技术归结为寻求事物背后的一般规定为高明的状态值得怀疑,但他确实得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1]。在他的理解中,智慧属于有关事物的普遍性的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并认为那种最高原因和最普遍的知识也就是最高的智慧。
近代以来,各门具体的科学建立起来,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这种应付自然与环境的知识与工业的结合,显示出巨大的力量。科学的进步从历史上看,它经历着对前人对自然的看法的研究和“人类心灵机制的类比”,从而走到努力回到客观事实上来,这确实是一个飞跃。“它的主要任务成了在系统检验这些现象的基础上,修正和重建日常经验中形成的观念,以便能更好地认识到特殊性只是普遍规则的实例”[2]。哈耶克说:“这场斗争所获得的动力使科学走过了头,造成一种相反的危险处境,即唯科学主义的支配地位阻碍着理解社会方面的进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2]自然知识产生于对自然的一种操作,近代以来的科学形成了一种对自然有规则程序的操作,即形成了一种对自然的操作方法,其形成的知识在实践过程中又非常有效,特别是在工业活动中。工业活动中对物的改造效率增高,加上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愿望,以及同时形成的对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作用,科学技术显然成为了一种值得充分信赖的认识方式和操作方式。
我们认为,这种知识是在对整体的割裂下而建立的。它一方面对我们利用这种知识改造自然为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凸显了工具理性,并在技术与工业的结合中取得现实的生产力功能。另一方面,在利用这种知识的深入过程中现成的观念与方法成为主流的观念与方法,忽视了其它人文的因素与方法,这影响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持续性。当然,我们要看到自然科学是在无限的宇宙内的有限范围内起作用,是在理性可及的界限内。它“关心的是展示自然界的内在理性,并不在乎这些理性能否终极性的自我说明,也不追问隐藏在各种知识领域背后的终极理性基础。这些科学在本质上就是要排除这些问题,且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其探究并理解自然现象的任务”[3]。这确实是对自然科学的合理的界限及其作用的公正的说明。提醒我们,科学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局限性。就学科的历史沿革来讲,科学原来是“分科之学”之意,是“作为各部门的知识者”[4]。而学科的分立,容易使研究画地为牢,孤陋寡闻。这既不利于全面、联系地看问题,也经常容易导致夜郎自大式的判断。因此,对自然事实的整体观照和理解并形成应对的智慧,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自然自身的和谐,要在较高的智慧下对科技的运用才能实现,是一种对事物整体的观照。否则,科技水平越高,如果智识不能同步,则破坏的可能性就越大。现实情况下,“我们的学科建设存在着专门化的问题,科学的发展要求我们考虑人文精神与科学的关系,因为纯粹发展科学的观念可能导致现代的野蛮,甚至使人原始化”[5]。人们也可能会想起C.P斯诺在备受争议的著作《Science and Government》中,曾指出了某些科学家总是偏执地坚持某一片面的断定或者满意于某一小范围的研究原因。即他们的成功总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或者是使用某一特定仪器完成的。由此,反思以对事实割裂为研究出发点而建立的自然科学,并明白它的局限性,从而用人类的智慧因素弥补纯技术的、部分的分析与把握,从而开启在智慧的视域下对科学及技术的观照就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如果仅建立在概念、语言的基础上,可能对事实整体产生分割的认识与理解,智慧则是在对事物整体观照基础上,而产生于“全面”领悟和体验之上
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认为,人的语言和概念习惯于进行抽象,把具体事物分割开来把握。但一经分割就有了界限,那就不是整体的道。所以,他提出“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齐物论》)。同时,他认为静止的概念不能把握动态的变化的事物,有限的概念不能把握无限的事物。这些思想值得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们反思,不能把对某一个阶段的成果看成对事物的绝对把握,不能把技术的一时成功当成“技术决定论”的依据。科学认识与理解的世界必须要用智慧来观照,对事物具体而阶段性的把握必须用整体的直观予以辅助。
逻辑与实验是自然科学的最大特征。中国哲学家冯友兰认为,逻辑是哲学的入门,但要达到哲学的最高境界却不能依赖逻辑分析方法,并反复地强调哲学所追求的这种境界即是人自觉到与宇宙为一,超越了理智,达到了一种形而上的境界。同样,中国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也认为哲学上不应过分地看重逻辑分析或论证。当然,他是针对分析哲学的发展来谈的,但也可以理解为,追求智慧与追求知识是迥然不同的。反映在逻辑分析与实验研究中事物的本质中介,客观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本质,它与客观事物有着较大的差异,因为客观的自然界、社会生活是无穷无尽而极其复杂的,其中的每一事物都处在和其他事物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以逻辑分析与实验研究为主的自然科学为了达到对某一对象某一方面的认识,就必须要淡化甚至要排除认识对象和其他事物的联系。这就是认识上的离散性、排它性,其结果使认识客体在一定程度上变了形。自然科学研究中要讲究对概念、命题、推理的分析与论证,这种研究路向决定了永远无法完整地描述和说明这个无限的对象世界。
诚然,自然科学形成的对自然的认识与理解对于智慧的产生有必要关系,但决不是充分关系。智慧的产生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其中哲学的思辨至少是不能少的。
具体的实证科学对自然的把握是对世界整体的割裂下的一种认识与把握,是对整体事实的分割,而对事物整体的理解与把握不是部门科学所能达到的,这需要主体的悟性与智慧力量。智慧是产生对事物整体的、系统的把握上的,是对自然的整体观照,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在此可能无能为力。对事实的割裂与对事实的整体观照,我们认为是具体知识与智慧的最大区别所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末,智慧却是本和根。在现代社会中,对追求“末”的知识方式的推崇是人们实用与功利欲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展现。可以说这种展现方式在今天已到了一种“惟一”获取知识的地步,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与这种推崇有着关联。
康德曾认为,我们的智慧不是从自然中寻找出它的规律,而是把自己的规律强加给自然。康德持有的这种思想甚至被后来有些哲学家认为是哲学上类似于科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第4卷中将哲学与科学大致划分出来,指出哲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Bing as Bing)”、本体的性质、变化的原理和终极原因的,而科学割取了“存在”,使之成为一个个的部分,从中来探询自然、运动的原因与原理。部门科学,经世致用尚可取,但终极观照不可行。在当今日益复杂、危机共存的人与世界,重建智慧来关照人类对自然的“实证”研究的后果显得尤为必要。
三、在“工具理性”背景下对智慧重建的一种可能途径
如何形成智慧呢?人与物不同在于劳动,按卡西尔在《人论》中的观念来讲是“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围。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6]。这些组成部分并不是松散的,而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纽带不是一种实体的纽带,如在经院哲学中所想象和形容的那样,而是一种功能的纽带”[6],我们认为这根纽带是在文化根基上形成的智慧。在根本上讲,智慧是精神的自觉,是思想对思想的认识,是一种对无限和超越的境界。胡塞尔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评价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到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造成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7]。如何从机制上使“事实”分割研究进行智慧重建呢?我们认为应从如下方面建立一种重建的机制。
其一,提倡“回到事物本身”的哲学追问,并使这种理念渗透到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不同学科中。
“回到事物本身”是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的导言中提出的,胡塞尔又重提此口号。从表面上讲,胡塞尔只是为了要人们把对于事物的一切成见和定见悬置起来,在原初意向中直接接受把握事物。但我们更应从本体论角度理解“事物本身”。事物本身只是一个无穷大的意义源泉,这样一个无穷大又时时反衬出人的有限性,时时提醒人们勿把有限当无限,囿于一已之见,而忘了事物本身具有与时消长的无穷意义。
“事物本身”从整体上看就是希腊哲人说的Physics。这个“自然”不是事物的“本性”,而是事物的“本然”。前者是固定的东西,因而是有限的,而后者却是在永恒生成,因而是无限的。当代哲学人类学家阿诺德·盖伦说,人天生是文化的动物。文化规定了人的世界以及人在此世界中的地位。但文化必然以某种确定的模式出现。这样,人们往往把某一文化模式或某一文化时代的定见误以为是事物的本然,而把自己封闭在自己造成的偏见之中。“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还完全不同于卢梭的“回到自然去”的口号,而是要从根本上突破近代思维的固定模式,从而看到从前看不到的许多东西。
其二,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者与人文学者的携手和对话交流是一种重要的途径。科学并不是唯一的价值源泉,在社会的价值形成过程中,人文知识与宗教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信仰在价值的过程中确实不能忽视,但我们要认识到自近代以来,克服社会中人们的轻信是思想解放的一股潮流,而轻信的解毒剂是对“事实的真理”的热爱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价值确实重要,而科学则是价值的保护人。
其三,目前更需要对“专门的、实证的事实”成果进行通盘和整体思考与哲思的大家,需要有自然科学素养的人文学者和有人文素养的自然科学研究学者即“哲人科学家”。正如汉伯里·布朗在其《科学的智慧》一书所说:“如果我们要明智地利用这些知识的话,我们必须学会把科学作为我们文化的一个宝贵组成部分来看待,而不仅仅把它视为物质进步的动因。”[8]同时,要对目前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进行反思,我们坚持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智慧。智慧就是关于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因此,形而上学就是最高的智慧。……如果我们不能求诸神学,我们就必须转向形而上学。要是没有神学或者形而上学,大学就不能存在”[9]。
其四,自然科学研究者应在研究自已的专门领域过程中,时时跳出来,浏览一下其他领域,更需要对其进行哲学思考,同时要注重“跨学科性科学研究”[10]。文化交融是不同学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当代的社会发展需要哲人科学家的产生。但目前不能否认,我们的学科建设存在着专门化的问题,科学的发展要求我们考虑人文精神与科学的关系,因为纯粹发展科学的观念可能导致现代的野蛮,甚至使人原始化,科学虽然能够战胜自然界,但是却不能面对社会对其的否认,如何应用科学的问题却需要人文精神予以调节①郑祥福在其《科学的精神》(三联书店,2001年,P4)中有较为深刻的分析与梳理。其中也提到“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只存在着一个各门具体科学所面对的世界。各种世界体系常常只属于知识的某个特定范围,但是,它们往往错误地被绝对化和普遍化了。不同的科学观念只是提供了各种特殊的看法。因此,每个世界体系都是取自于这个世界的一部份。世界自身是不会变成一个体系的。一切‘科学的宇宙论’都是虚构的,它们都建立在科学的方法和少许神话残余之上”。确实值得深思。但对有些过激的态度我们持保留态度。。
[1]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M].苖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
[2]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9.
[3]托马斯·陶伦斯.上帝与理性[M].北京:中英编译出版社,2004:85.
[4]熊十力﹒新唯识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5:248.
[5]郑祥福.科学的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2001:4.
[6]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87.
[7]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
[8]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M].李醒民,译.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8.
[9]菲利普·弗克兰.科学的哲学[M].许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
[10]刘啸霆.当代跨学科性研究的“式”与“法”[N].光明日报.2006-03-28.
On the Restoration of Wisdom under the Severed“Truth”
ZHANG Lijian,XIANG Lihui
(School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P.R.China)
Since the 15th century, science has been reflecting the worl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ubjects.Science develops human's grasp of the world with deeper research,but this kind of grasp is got by dividing the world into several parts.The introduction and success of technology strengthe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knowledge on one hand;Meanwhile, the concentration on the whole world, philosophy and metaphysics all have a trend to be a fringe issue,and this trend is strengthen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sm,it also influences the standard of training the persons with ability.Calling for scientists with a philosophical mind is just against this kind of training standard;furthermore, it call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wisdom under the situation of severing the truth.
science;dividing the world into several parts;the restoration of wisdom
(责任编辑 彭建国)
N031
A
1008-5831(2014)03-0158-04
10.11835/j.issn.1008-5831.2014.03.022
2014-01-09
张礼建(1963-),男,四川达州市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向礼晖(1988-)男,贵州贵阳市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