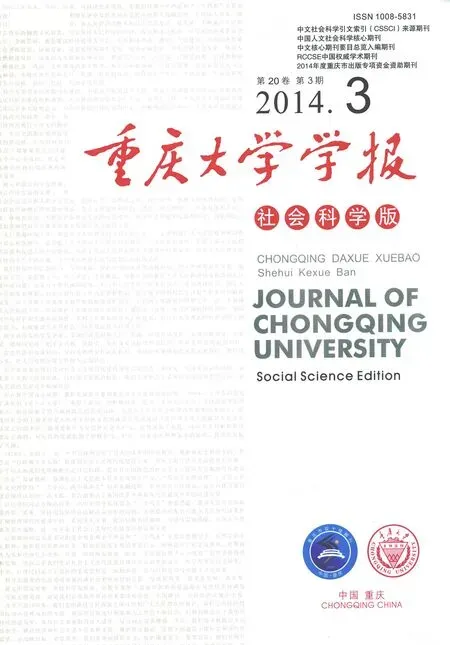公开盗窃理论构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质评
高国其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44)
公开盗窃理论构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质评
高国其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44)
公开盗窃学说在理论前提的认识上,置盗窃的秘密性于无关紧要的地位,这种学说以现实存在公开盗窃作为立论依据采取循环思维想当然地借鉴国外刑法学说,主观地解读处罚上的空隙,因而该学说在理论构建的必要性上存在认识论上的偏差。同时,公开盗窃说在理论证成上不恰当地使用了文理解释、历史解释和比较解释的方法,在确立盗窃罪的边界以及建立盗窃罪和抢夺罪等其他侵犯财产罪的区分标准上均不完满,由此,公开盗窃理论在构建方法上也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在盗窃罪学说上应当进行理论辨正,维护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罪质内涵。
公开盗窃;秘密;认识论;方法论;质评
在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上,当前刑法理论有秘密窃取说与公开盗窃说之争。中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盗窃罪是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的本质特征是对他人财物的‘秘密窃取’”[1-2],[3]164。近年来,所谓公开盗窃理论为不少著名学者所提倡,他们认为,“盗窃行为既可以具有秘密性,也可以具有公开性”[4]。“‘盗窃’主要是指秘密窃取,但是不限于秘密窃取,也可以是抢劫、抢夺、聚众哄抢等强制方法之外的公开盗取行为”[5]370。“只要是以平和而非暴力的手段,违反占有人的意思而取得财物,就是盗窃罪中的窃取,而不以实施隐秘方法为必要条件”[6]97。公开盗窃理论被写入诸多版本的刑法教科书,已经在理论界成为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学说[6]97,[7]877,[8-11]。
公开盗窃说的主张,把中国刑法理论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秘密盗窃的观点进行了颠覆性改造,从而扩张了盗窃罪的罪质内涵和适用范围。但是,公开盗窃理论构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仍然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笔者拟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公开盗窃说进行分析、质疑和评价,以求为盗窃罪理论提供一个辨正的方向。
一、秘密与公开是否真的不重要
对于盗窃罪而言,传统刑法理论坚持其行为方式的秘密窃取性,认为“秘密窃取,是盗窃罪区别于抢劫、诈骗、抢夺罪的主要之点”[12]。“盗窃罪和其他侵犯财产犯罪的主要区别就在其犯罪手段,即取财行为具有秘密性”[13]。司法实践也形成了以秘密窃取为客观要件的盗窃罪行为模式①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8]。但是,坚持公开盗窃说的学者,认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除了秘密窃取外,也包括公开取得,从而彻底放弃了以秘密与否作为盗窃罪的认定标准。如有学者认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占有人的意思,以平和手段将财物转给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的行为”[4]96。有的学者尽管仍然把盗窃罪的行为表述为“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但把“窃取”界定为“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7]877。在盗窃罪的行为描述上已经不再出现“秘密”的字样。学者在界定盗窃和其他侵犯财产犯罪的界限上,也抛弃了秘密与公开的标准而尝试创设新的标准②如有学者明确提出区分盗窃和抢夺罪的标准:“对象是否属于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行为是否构成对物暴力。”参见张明楷《盗窃与抢夺的界限》(《法学家》2006年第2期119-131页)。。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对盗窃进行秘密或是公开的论证时更明确指出,行为的秘密还是被发现仅是与法益侵害无关的偶然事实,不应当成为左右构成要件该当与否的因素③“以窃取为要件,那么公车上或公园里的扒手是否构成盗窃罪,就要视客观上被害人或第三人有无发现此等事而定。让这些与法意侵害无关的偶然事实来左右构成要件的该当与否,不合理处不言而喻”。参见蔡圣伟《财产犯罪:第二讲:盗窃罪之客观构成要件(下)》(《月旦法学教室》2009年第75期57页)。;行为是公然还是秘密,和财产的保护没有关系④“……从保护被害人的财产的角度来看,只要行为人未经本人同意或是违背本人意思而取走其持有物,即属不法而应罚,至于行为系公然为之或隐秘为之,和财产的保护就没有关系了……”参见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45页)。。总之,持公开盗窃说的学者在构建盗窃罪相关理论时,可以随意突破传统刑法理论关于盗窃罪仅限于秘密窃取的界限,盗窃罪的行为方式是秘密还是公开,在他们那里已经显得一点都不重要了。
事实上,经过理论自身的演进和司法实践的反哺,把盗窃罪的秘密性作为本罪的本质特征,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秘密和公开对于盗窃罪的行为方式而言,绝对不是可有可无、可以随意抛弃的偶然因素。
(一)罪刑法定的意义
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要求刑法规定的各种犯罪具有个别化、类型化的区别性特征。“犯罪作为刑法特有的法律要件,要求有其明确的概念规定,并严密地将其种类、范围特定化”[14]。中国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规定了不同类型的侵犯财产行为,传统刑法把盗窃罪的秘密性作为本罪的基本特征,以区别于其他侵财犯罪类型。应当说只有维护盗窃罪的秘密性,才能保持侵犯财产罪一章各种犯罪类型之间具有相互区别性和体系协调性。强调盗窃罪的秘密性,有利于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维护刑法规范的确定性,实现对秘密窃取他人财物行为的类型化规制。
(二)反映法益侵害(犯罪客体)的不同程度
一般认为,盗窃罪和以公然夺取为特征的抢夺罪的犯罪客体相同,都是单一客体即公私财产的合法所有权[3]223-224。但是法益侵害(犯罪客体)的类型相同,并不意味着侵害程度也完全相同。在秘密窃取的情况下,对于被害人而言,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遭受了财产损失,其心理上的冲击相对较小。但是,如果是在直面行为人的场合,被害人目击财物被强取的过程,由此对其产生的心理冲击要比无意识的遭受财产损失强烈得多;同时行为人肆无忌惮的公然强取财物,也会加重被害人对整个社会秩序和安全的不信任感。盗窃罪的秘密窃取与抢夺罪的公然夺取,决定了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程度轻重有别。严格区分行为的秘密与公开,能够从被害人的角度,折射出法益侵害程度的差别,在犯罪学上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三)行为人主观归责的需要
选择采用秘密的方式窃取财物,避免和被害人的直接冲突,说明行为人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还存有一定的顾及,比较在意侵财行为的社会评价,因此主观方面的可责性相对较小。而采取无所顾及的公然方式强取他人之物,说明行为人不但具有贪图他人财物的不良意识,而且毫不在意其目的实现的方式,说明行为人主观方面对公共伦理规则、法律秩序和社会善良风俗的藐视,其主观可责性明显大于前者。由此可见,强调行为方式秘密还是公开,有利于根据行为人主观可责性的大小追究行为人相应的刑事责任,有利于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做到罪刑相适应。
(四)司法实践的意义
根据刑法规定,普通盗窃罪和抢夺罪的成立都需要“数额较大”的法定情节。但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在确定盗窃罪和抢夺罪数额较大、成立犯罪的标准上通常存在差别。例如广东省确定一类地区认定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为2 000元,而抢夺罪是500元⑤参见粤高法发[1998]11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确定盗窃案件数额标准问题的通知》;粤高法发[2006]3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办理抢劫、抢夺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浙江省的标准是盗窃罪2 000元,抢夺罪1 000元⑥参见浙公通字[2009]22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关于修改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通知》;浙高法[2006]30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关于修改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通知》。。可见,在作为认定犯罪成立的“数额较大”标准问题上,司法实践中抢夺罪的起点要远低于盗窃罪,这体现了盗窃和抢夺两种行为司法评价上的差别。通常的认识是抢夺罪的危害性要高于盗窃罪,而二者之所以能够有所差别,只能从其行为方式的不同上寻找原因:一个是秘密取得,另一个是公然强取,从而决定了后者的社会危害性要比前者大得多。由此可见,在侵财行为方式上,秘密与公开的区别具有深厚的司法实践基础,如果无视这一区别就有可能引起观念上的混乱,会使刑法的司法适用无所适从。
综上所述,秘密还是公开对于认识盗窃罪的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如果置盗窃罪秘密性的本质特征于不顾,在认识上视秘密与否为无关紧要、可有可无,那么不但会危机到盗窃罪类型应有的存在价值,而且在犯罪学意义上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也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侵犯财产罪的认定和处罚。
二、公开盗窃理论的构建是否必要
知为行者先,欲采取行动实现一定的目的,须首先对事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利于提供一个相对正确的行动方向。如果对一事物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即使有再高的立意、再精妙的方法也不可能走上正途,只能是离正确的方向渐行渐远。在刑法理论上也是一样,不论如何解读和建构盗窃罪的行为方式,首先应当对盗窃罪有关的罪质特征、理论背景、立法体系和司法适用等因素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然后再去探讨理论构建的必要性。公开盗窃说在理论构建的必要性认识上存在诸多问题。
(一)公开盗窃是否在现实中存在
主张公开盗窃说的学者,往往以现实存在作为理论构建的事实依据。例如,有学者在批评传统的秘密窃取说而主张成立公开盗窃时,列举的理由之一是“公开盗窃的情形大量存在”。“既然如此,刑法理论就必须面对现实,承认公开窃取行为构成盗窃罪”[7]878。还有学者一方面认为“……将盗窃罪中的窃取概念缩限为‘秘密窃取’这样的解释一般来说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说“但是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下,行为并非秘密窃取,仍然成立盗窃罪,例如在公共汽车上、集贸市场明知有他人(包括被害人)看着自己的一举一动而‘公然’实施扒窃的”,因此得出结论“只要是以平和而非暴力的手段,违反占有人的意思而取得财物,就是盗窃罪中的窃取,而不以实施隐秘方法为必要条件”[6]96-97。
上述学者试图通过列举日常生活中的实例,来说明盗窃罪的行为也包括公开取得。就论者的认识逻辑而言,属于典型的循环思维:这些行为是盗窃——这些行为是公开取得——所以盗窃罪包括公开取得。论者先入为主地已经在意识中嵌入了公开盗窃的观念,以公开盗窃的存在作为前提,对一些行为现象进行评价,自然可以得出这些行为是公开盗窃的结论。以公开盗窃在现实社会存在作为事实,认为盗窃应当包含公开取得的主张,很难说具有说服力。
另外,上述学者的认识过程采取的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思维。这一由“公开盗窃的情形大量存在”到“盗窃罪包括公开盗窃”的归纳思维至少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作为前提的“公开盗窃”是已经附加了论者主观评价的现象,相对于传统“盗窃”(限于秘密取得)存在归纳前提的歧义。第二,由此得出作为结论的“盗窃”,其内涵已经跨越了应当作为认识前提的“盗窃”概念应有的界限,在逻辑上违背了同一律。第三,采取从案件事实出发找规范的归纳法,是立法者典型的思维方式[15]。上述归纳思维的认识过程,采取了立法者的立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在既定立法之下认识和评价一事物,正确的思维方向应当是从概念到现象,依据已有的规范通过演绎的方式推演到现实中的各种具体事实。对上述实例中的行为进行刑法上的评价,其认识过程应当是:盗窃罪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这些事例都是公开取得而不符合秘密窃取的行为方式——这些行为不是盗窃罪。
(二)国外学说是不是改造中国刑法理论的当然理由
主张公开盗窃说的学者,在讨论问题时,往往依据国外关于公开盗窃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作为立论的一个支撑。如有学者在所著教科书中称“国外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均不要求秘密窃取……本书也认为,盗窃行为并不限于秘密窃取”[7]877。论者的论证逻辑大致采用了这样的三段论:大前提——德日等国外刑法中的盗窃不限于秘密窃取而包括公开盗窃,小前提——中国刑法中的盗窃仅限于秘密窃取,结论——应当改造中国刑法中的盗窃罪,使之包含公开盗窃。这种论证逻辑把德日刑法作为讨论问题的大前提,而不是把中国刑法的既有传统作为背景,得出的结论自然就需要对既有理论进行改造。
以国外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制度为中心,采用逻辑演绎的方式研究中国问题的范式,在认识论上可能会存在问题。似乎当然的逻辑是:外国刑法多是如此,中国也应该如此。对于采用这种演绎方法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对于持公开盗窃说的学者自己也曾经对其不足提出质疑,指出“演绎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本身就包含在其前提之中”[16]。正像有的学者批评的那样,这种研究模式往往“忽略了对中国问题的独立思考,不考虑中国问题的独立性和独特性”[17]。面对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不典型的犯罪类型,在如何适用刑法上正确的作法应当是,以中国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为大前提,把实际问题作为小前提,从而得出符合中国刑法背景的结论。
(三)是否确实存在处罚上的空隙
在现实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不典型的侵犯他人财产的犯罪行为。例如,乘被害人摔倒无力控制财物之机,当着被害人的面把被害人甩出去的钱包强行拿走逃离的行为。对于这种违背被害人意志,以不存在人身暴力的方式强行取走他人财物的行为,在如何适用中国现行刑法进行规制的问题上,主张公开盗窃说的学者认为,“如果将盗窃限定为秘密窃取,则必然存在处罚上的空隙,造成不公正的现象”[7]877。
刑法上问题的讨论,必须立足于中国现行刑法的实际规定,并且考虑国内刑法理论对于此类犯罪研究的理论基础。由于德日等国的刑法没有规定,以非人身暴力方式公然侵财行为为要件的诸如抢夺罪的犯罪类型,对于上述不典型的侵财行为造成处罚上的空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以中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为大前提,则问题会大有不同。因为根据中国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规定,除了以秘密窃取为特征的盗窃罪、以人身强制为特征的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外,还规定了以公然夺取为特征的抢夺罪、聚众哄抢罪和以公然强占为特征的侵占罪等非人身强制的公然型侵财犯罪类型。刑法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对各种侵犯财产行为确立了严密的规制体系,为新出现的侵犯财产犯罪行为提供了广阔的刑法评价空间。上述认为存在处罚空隙的学者,一般是以德日等国的刑事立法为前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中国讨论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应当立足于国内的立法和相关理论。
如此看来,所谓处罚上的空隙有可能不是立法本身存在的,而是论者自己解释出来的。针对上述不典型的侵财行为,应当首先考虑现行刑法的既有规定,在已有侵犯财产犯罪类型之下讨论法条选择适用的可能性,而不是急于得出存在处罚上空隙而需要对盗窃罪传统理论进行重构的结论。
三、公开盗窃理论的构建是否合理
方法是知后践行的工具,方法正确方能指导实践,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为了主观目的,牵强地使用一些方法仍然不能获得论证的说服力,在其基础上构建的理论也需要进一步的推敲。公开盗窃说在方法论上主要通过法律解释的途径,试图论证盗窃行为包括公开取得的合理性,但其在方法运用和解释的体系性效果上均不尽如人意。
(一)文理解释的方法是否适当
主张公开盗窃成立者,首先通过文理解释的方法解释盗窃行为不限于秘密窃取,还包括公开取得。不过,不同的学者在通过文义解释达到其目的的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却有不同。
有学者认为“从文理解释的角度看,认为盗窃包括秘密盗窃与公开盗窃,也不存在疑问……窃并非用于修饰盗,而是与盗具有等同意义的概念……在现代汉语中,‘盗取’、‘窃取’、‘盗窃’的含义完全相同”[4]。进而认为现行刑法的盗窃不限于秘密窃取。从汉语语法和词义学的角度看,论者对盗窃这个词语在词义的解读上存在问题。对于现代汉语中“盗窃”一词,“盗”是“窃”的属,二者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如果要设定一个和“窃”构成并列关系的词,应当是和“窃”同义或者反义的字,至少二者具有同一“种”的关系,例如和“偷”连用可以构成“偷窃”。所以,对于“盗窃”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只能认定为偏正词组,“盗”修饰“窃”,含义重心在于“窃”而非“盗”。“盗窃”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18],“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占为己有的行为”[19]。如此看来,把盗窃罪的行为解读为秘密窃取,是当然的文理解释,不应存在任何分歧和疑问。所以说,在现代汉语中,“盗窃”的含义并不当然等同于“盗取”、“窃取”。如果认为现代的“盗窃”和“盗取”、“窃取”的含义完全相同,只能说是论者在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对于汉语词汇赋予了自己主观的想象。
有学者一方面承认“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盗窃’一词是‘盗’与‘窃’连文而成,中心词是‘窃’字,因此,其日常用语含义仅仅是指秘密偷窃”,另一方面又主张“在汉语言文字系统中,‘窃’是指偷窃,‘盗’包括偷窃和强盗……盗窃的刑法规范含义必须作不同于日常用语但是合乎汉语言文字本意的解释,既包括秘密窃取,也包括公开盗取”[20]。论者把盗窃一词日常用语的含义和汉语言文字的本意对立了起来。其实,词汇日常用语的含义和其当下的本义应当是一致的,现实的情况不可能是说汉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非汉语言的本义。论者这里的所谓“汉语言文字本义”,是通过采用解构词语的方式,挖掘词组语素的本义而赋予了整个词组超出基本含义的其他意思。立法者在法律文本中为司法者规定的解释规则性框架,是由法律文本可能的口语化词义加以标定的[21]。盗窃一词随着语言沿革已经形成了其概念化的口语含义,通过语素解构的方式赋予其刑法规范的另外含义,不具备语言习惯的现实基础。从另一个角度看,学者是在规范意义上通过解构语素的方式,对刑法上的词语作超越日常用语含义的解读;应当说这种解释具有词义渊源上的技术支撑和规范意义上的可行性。但是,规范的建构不可避免会存在主观评价的成份,如果仅从规范的角度对盗窃一词进行解释,就会随解释者立场的不同而解释出不同的结论。持公开盗窃说的学者可以从挖掘盗窃“语言文字本意”的角度赋予盗窃包括公开盗取的规范含义;同样,在规范上维护盗窃一词秘密窃取含义的学者,也可以立足于盗窃一词现在的日常用语含义,坚持盗窃行为在规范意义上仅限于秘密窃取。如果尽可能抛开解释者价值判断的影响,对刑法规范上的盗窃用语作通常意义上的理解,其与日常生活中含义的距离要比论者所称“语言文字本意”的距离近便得多。
通过文理解释赋予盗窃罪公开取得的内容,还会造成刑法语言表述的混乱。论者一方面把盗窃罪的行为仍然表述为“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另一方面在“窃取”之下装入其公开取得的行为内容⑦“窃取是指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77页);“窃取,是指违反占有者的意思,排除其占有,由自己或者第三者对财物进行占有”。参见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如果说把“盗窃”解读为包括“秘密窃取”和“公开盗取”的方式还可以从语言学和沿革意义上找到注脚的话,那么把“窃取”解释出所谓包括秘密取得和公开取得,则是彻底违背了汉语言的本义,完全改造了“窃取”这一词语语言学上的内涵。刑法规范的解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和日常用语不一致,但是解释的限度和规范的伸缩度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对刑法概念进行过度的解释乃至重构,不但直接造成犯罪类型的模糊化、破坏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而且会给刑法的司法适用带来困难,更有甚者可能使公众面临司法者不着边际的法律解释,丧失在法律面前应有的安全感。
(二)历史解释的方向是否正确
持公开盗窃论者,从历史解释的角度论证公开盗窃成立的合理性。有学者认为:“古代刑法的‘盗’包含秘密窃取与公然取得他人财物。后来将秘密窃取行为从‘盗罪’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窃盗’概念……现行刑法使用了‘盗窃’概念,而非‘窃盗’……在现代汉语中,‘盗取’、‘窃取’、‘盗窃’的含义完全相同。”[4]作者通过历史解释的途径把现代刑法中的盗窃罪等同于古代刑法中的盗罪,从而得出盗窃并不限于秘密窃取,还包括公开盗取的结论。
从盗窃罪立法的历史看,古代刑法初始采用大的盗罪罪名,不细分非法侵财的具体行为方式[22]。后来立法逐渐出现细化的趋势,唐律《贼盗律》有“诸盗,公取、窃取皆为盗”的规定,盗罪有窃盗、强盗等具体类型。唐律影响至深,盗的概念被后来宋、明、清立法所承继,直到民国时期,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仍然沿袭了窃盗和强盗等侵财类型的划分。从中国解放后的立法资料看,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沿用了旧刑法的规定,“侵害私有财产罪”一章有“窃盗”和“强盗”的划分。以后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一直到196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33稿),“窃盗”一词一直用“偷窃”来替代。到文革以后1978年重新启动刑法典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稿)》(34稿),第一次把“偷窃”改为“盗窃”的用语,并且一直沿用到1979年刑法的通过[23]。从这一法律起草的过程来看,在盗窃罪上经历了“窃盗―偷窃―盗窃”的表述变化;可以推知,刑法使用的“盗窃”一词,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盗”的全部,而是“盗”中“窃盗”的部分。现行刑法的盗窃罪承袭的是古代刑法中的窃盗,二者具有行为类型上的一致性[24]。“盗窃行为之秘密窃取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定型化了犯罪行为”[25]。1979年刑法第152条把“盗窃”单独列出,明显印证了盗窃罪意在“窃”而非“盗”上。
另外,如果把现代刑法中的盗窃和古代的盗罪作对应的解释,赋予盗窃过多的内容,则无法在现行刑法体系内解释盗窃和抢夺及抢劫的关系,因为抢劫和抢夺也大致包括在古代的盗罪之中。如果认为现行刑法中的盗窃包含了“公取”的内容,那么又把刑法中的抢夺和抢劫置于何地?如此看来,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必须对现行刑法中的盗窃进行限制性解释,即仅是指“窃取”,以区别于刑法中抢夺罪和抢劫罪等公然取得的财产犯罪类型。
进行刑法的历史解释,意在阐明现行刑法规范的合理含义,为刑法规定适用于社会现实提供注脚,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而不能仅作刑法史意义上的溯源和考据。对于盗窃罪进行历史解释,必须结合其立法发展的脉络探求刑法规定发展至今的现实意义,把解释的落脚点定位在现实而非过去。从历史的角度把现代刑法规定的“盗窃罪”和古代“盗罪”作对应性解释,扩张了盗窃罪的内容,而忽视了刑法语言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刑事立法的历史沿革,也违背了当前刑法中侵犯财产罪立法结构的体系性要求。
(三)比较解释的路径是否可取
比较解释在法律解释学上,一般指参照外国立法或学说以阐明现行法律规定的含义。采取比较解释的方式,引入国外较为成熟的理论为本国刑法实践所用,可以说是一种便捷的方法选择。但“在刑事法上,由于采取罪刑法定主义,以此解释方法,较属罕见”[26]。如果确有必要采取中外比较的方法为解释中国刑法提供参照,首先需要考虑二者之间的可比性,尤其要关注二者之间是否具有较为一致或者类同的立法前提。公开盗窃论者,在构建其理论时通常采取比较解释的方法,参照德日等国外的刑法学说,说明盗窃罪包括公开取得行为的合理性[4]。但在盗窃罪理论上采取比较解释的构建路径是否可取,需要进一步探讨。
作为一种传统的自然犯类型,盗窃罪在不同法域之间具有较大的相通性,但是基于不同国度之间财产犯罪体系的差别,为了满足现实中不同犯罪行为规制的需要,其在罪质内涵上会有所差异。在对盗窃罪进行比较解释时“不可忽视中外刑法在实质、内容、体例上的差异,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与犯罪的名称,而应注重规定某种犯罪的条文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了解相同用语在不同国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27]。德日等国外侵犯财产犯罪类型上,通常根据是否存在人身强制而规定有盗窃罪和抢劫(强盗)罪,在二者之外少有规定尽管具有公然性但无直接人身强制的抢夺罪类型。基于此种立法背景的不同,针对现实中出现的违背被害人意志、以非人身强制方式公然取得他人财产的不典型侵财行为,德日刑法在理论上通常选择距离相对近便的盗窃罪进行规制,通过扩充盗窃罪的内涵而把所谓公开取得的行为涵摄其中⑧“窃取,本来是指秘密取得之意,但即便公然实施也可构成本罪”。参见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所谓窃取,是指单纯的盗取……虽然使用着‘窃’取一语,但是,并不需要暗地取得,也可以是公然的侵害占有”。参见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但是在中国刑事立法背景之下,存在德日等国刑法所没有的以公然夺取为特征的抢夺罪类型;对于现实中不典型的以非人身强制方式公然取财行为,选择抢夺罪进行类型化的规制是一种有说服力而且易于被公众接受的理论[28-30]。
选择比较解释的路径时,还应当用解释的效果去衡量采用国外理论学说的合理性。盗窃罪在中国刑法侵犯财产犯罪体系中,因其行为的隐密性特征而具有独特的地位;在中国现行刑法规定之下,试图通过打破盗窃罪秘密性的界限实现对某些公开取得行为的规制,要比选择现有的公开型犯罪类型进行规制徒增太多成本。秘密与公开绝不是仅有一步之遥可以随意跨越的一小段模糊距离,而是存有天壤之别的一道鸿沟;如果非要对现实中这些非典型的侵犯财产行为做出一个选择,那么要么走向公开的犯罪类型那边,要么先把以秘密为特征的盗窃扩充出公开再对此进行选择,二者孰远孰近,不言自明。
比较解释的合理实现需要特定的条件,只有与本国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相协调的比较解释结论才具有可取性。国外理论学说的方向不是构建中国相关理论的当然方向,只有符合中国实在法规定和理论基础的结论才更具有本土的适用性。
四、公开盗窃的边界能否确定
尽管主张公开盗窃论的学者在扩充盗窃罪的罪质范围与主张成立公开盗窃这一点相同,但在具体认定一些事例的性质时得出的结论却有不同。例如对于下述案例就存在明显分歧:犯罪嫌疑人吕某伙同另一嫌疑人来到某市中山路肯德基餐厅内。其同伙从背后拍拍正在用餐的被害人钟某的肩膀,让她看一则广告。吕某乘钟某扭头看广告之际,乘机拿走钟某放于餐桌上的一部价值人民币1 300元“三星”型手机后逃走。对于上述案例,举例的学者认为应成立盗窃罪[4]。而另外有学者把“创造他人不注意的机会,例如欺骗他人转移注意力,然后将财物取走”作为抢夺的方式之一[6]91,据此上述案例应认定为抢夺罪。可见,在坚持公开盗窃的学者中,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盗窃罪和抢夺罪等财产犯罪的划分标准,另一方面又难以在具体应用上达成统一的结论,因此使得盗窃罪和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让人觉得难以捉摸。主张成立公开盗窃的学者,由于不再把秘密与公开作为判断盗窃罪成立与否的依据,因此在盗窃罪的边界问题上面临新的课题,不得不寻求盗窃罪和其他财产犯罪尤其和抢夺罪之间新的区分标准。
有学者在盗窃罪和抢夺罪的界限上认为,抢夺罪中的“夺”决定了行为必须要使用不法有形力,而不可能以平和方式实施,这是区分抢夺罪和盗窃罪的关键[6]91。即以“不法有形力”和“平和方式”来界分抢夺与盗窃。尽管该学者提出了区分抢夺和盗窃的标准,但在理论表述的协调性和实际应用上却显得前后矛盾、徘徊不定:论者一方面认为“只要以平和而非暴力手段,违反占有人的意思而取得财物,就是盗窃罪中的窃取,而不以实施隐秘方法为必要条件”[6]97。另一方面又在抢夺罪部分把“明知他人密切关注某一事项或财物,但仍然在他人注目下将财物突然取走”列举为抢夺方式之一,并举例指出行为人“在选购金银首饰时,接过售货员递过的财物即转身逃走”的行为属于抢夺罪[31]。如果依照论者对盗窃罪公开窃取的描述,上述行为人违背占有人的意思,以平和手段取得对项链的占有后再逃走以取得该财物,应该属于公开盗窃,但论者却在抢夺罪下举例说明其应认定为抢夺罪,显然前后矛盾。也许论者后来发现了其理论的自相矛盾以及与事例相背离的情况,在稍后该学者出版的另外一本教材中彻底转换了立场:“明知他人密切关注某一事项或财物,但仍然在他人注目下将财物突然取走,例如,选购金银首饰时,接过售货员递过的财物即转身逃走……有的人认为应当定抢夺罪,但我认为,以定盗窃罪为宜。”[6]91可见,在坚持公开盗窃的情况下,依据论者提出的标准,有些行为是认定公开盗窃还是认定为公开夺取出现两可的局面。如果以论者自身提出的标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都无法准确区分行为的性质,又如何能够为司法者和普通民众提供一个明确的判断依据?
有学者明确提出了划分盗窃罪和抢夺罪新的标准,主张从两个方面区别抢夺和盗窃:一是对象是否属于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二是行为是否构成对物暴力[4]。但事实上这一标准不具备理论清晰性和现实操作性。
首先,论者所称“紧密占有的财物”在很多情况下很难作出区分。例如:被害人将财物放在自行车前面篮筐中骑车行走时,行为人突然使用强力夺取财物。对于此种情形,学者认为所夺取的财物属于被害人紧密占有之物,因此成立抢夺罪。而论者接着又举例,行为人在被害人摔倒后,捡拾其甩落于身体3米远处的钱包,因为钱包并非被害人紧密占有之物,故认为行为人不成立抢夺,只能认定为盗窃[4]。论者把距离被害人3米远的钱包认定为非紧密占有,而把同样离开被害人身体的车筐内的财物界定为紧密占有,二者界限如何划定并非易事。假如钱包甩出去并没有3米远而是刚好就在被害人手边,但即便是毫厘之差也使其不能触摸得到而被行为人拿走,从距离上看这要比骑车人和车筐中财物之间的距离近得多,还能不能认定为紧密占有?再如,被害人带一只价值连城的名狗出去散步,小狗在主人旁边左右跟随。如果当面强行抱走该狗,按照论者的标准,当小狗离被害人3米的时候抱走,小狗不是主人紧密占有之物,抱走行为是盗窃;而当小狗跑到被害人脚边的时候抱走,小狗就成了被害人紧密占有之物,强行抱走构成对物的暴力因此成为抢夺,这样的定性恐怕难以为公众所接受。可见,以侵害的财物是否和被害人紧密占有作为区分抢夺和盗窃的界限,实践中很难操作。
其次,学者主张区分盗窃和抢夺的第二个标准是,是否实施了对物的有形力,即物的暴力。论者试图从抢夺罪的立法沿革上寻找注脚,认为历史上对抢夺罪多规定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结果加重犯,进而推论抢夺行为通常可能致人伤亡,因此,抢夺行为应当是具有致人伤亡可能的物的暴力行为[4]。固然,立法上结果加重犯的规定说明抢夺行为可能存在对物的暴力的情形,但是据此不能直接推出致人伤亡是抢夺行为的通常结果,即便是通常结果也不能排除有其他情形的存在。就像刑法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此条第二款规定了非法拘禁罪致人重伤和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但据此不能得出非法拘禁行为通常由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人身强制方式实施,以间接方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仍然成立非法拘禁罪。不能因为刑法规定了可能使人重伤或死亡的直接人身强制方式,就说非法拘禁罪的行为方式仅限于此一种。同样,即使从前的刑法规定了抢夺罪的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结果加重犯,仍然不能据此得出抢夺罪的行为表现为对被害人贴身物的夺取。况且,现行刑法已不再规定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结果加重犯。认为抢夺行为都存在对物的暴力行为,显然是为了扩大所谓公开盗窃的含义而强行限缩了抢夺行为的范围。
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尽管论者为了明确公开盗窃的边界,明确提出区分盗窃和抢夺的标准,但事实上适用的效果并不理想,提出的方案很难说是成功和可行的。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所谓的公开盗窃很难和抢夺在本质上区分开来。如果主张公开盗窃的成立,排除盗窃罪的秘密性,相应的就要对抢夺罪的施行行为进行范围的限缩。如此以来,无论如何界定盗窃和抢夺的界限,都很难在理论上找到一个清晰的可操作标准。
由此可见,在公开盗窃理论之下,处理盗窃罪的边界以及相应的和其他犯罪类型的界分问题上,存在方法论上难以解决的难题。把盗窃行为扩充到公开取得,只会使盗窃和抢夺的界限更加模糊,使司法实践中两罪的区分在操作上更加困难。在盗窃罪和其他侵犯财产犯罪的界分上,传统学说坚持盗窃罪的秘密窃取性,从而和其他公然性犯罪相区别,边界清晰、经纬分明,易于司法认定。传统学说的这一基本立场如能得以维护,不但有利于盗窃罪等侵财犯罪的司法适用,也符合社会的一般观念和公众的心理认同。
五、盗窃罪行为方式的方向选择
通过以上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开盗窃论者对秘密性在盗窃罪中的地位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主张公开盗窃成立的理由难以充分说明,在理论构建的方法上也存在是否合理和可行的问题。总的来说,公开盗窃理论的构建在中国刑法背景下很难说是成功的。对于现实中新生的不典型侵犯财产犯罪的行为方式,不是必须通过扩张盗窃罪内涵、构建公开盗窃理论才能实现,可以考虑通过发展相关财产犯罪的理论,实现体系性刑法规制。在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上,应当维护秘密窃取的盗窃行为模式。在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之下,只有维护传统盗窃罪的罪质内涵,才可能在理论上处理好以下诸项关系。
第一,中外刑法理论的关系。中国刑法中的盗窃罪,是具有悠远历史的犯罪类型,具有固有法的本性。经过立法沿革、理论发展和实践运用,在中国已经形成具有本土特点的盗窃罪学说,具有一定的理论自足性,这一既有的秘密盗窃理论应当得以尊重。如果立足于有着不同立法背景的国外刑法理论,经过过度解释的途径扩大中国盗窃罪的内涵以构建公开盗窃理论,则会在观念上对中国传统盗窃罪类型予以根本性颠覆,造成司法适用的混乱,由此获得的理论改造可能得不偿失。
第二,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法律是一种规范的存在,具有抽象性和一般性。法律规范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适用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行为样态。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具有类型化的规范特征,每一种规范都具有特定的涵摄范围。在规范适用过程中,如果现实中的某一具体事实超出了规范的涵摄范围,则直接效果应当是排除此规范的适用而寻找其他规范以求解决。如果基于一定目的牵强地通过类型化的扩充实现对某些事实的规制,其规范改造的代价巨大。对于现实中出现的不典型公开取财方式,同样面临规范的选择问题。这些行为在公开性上已经超出了盗窃罪的类型特征,应当首先考虑选择公开型的侵犯财产类型,而不能由事实推论出规范,为了规范的适用而扩大盗窃罪到公开取得。
第三,个罪与体系的关系。中国刑法分则根据法益侵害的种类和程度等因素规定个罪,形成了完整的犯罪类型体系。对于盗窃罪这一侵犯财产罪类型,中国传统理论立足于盗窃罪的秘密性特征,以维护盗窃罪的既定边界并区别于其他犯罪类型。如果突破盗窃罪秘密窃取的范围,主张公开盗窃的成立,势必会影响到整个财产犯罪类型的清晰性,由此带来一系列体系性问题。因此,对于盗窃罪理论的改造,涉及的不仅是盗窃罪一个罪名问题,还会影响到整个财产犯罪体系,必须慎重。
第四,刑法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关系。刑法理论的构建不能脱离现行汉语的标准含义和人们的语言习惯。刑法的专业语言要尽可能与通常的语义相一致,一般不应与生活语言的通常含义相背离。就盗窃一词而言,随着语义演变和语言习惯的形成,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基准含义已经仅限于以秘密方式取得财物;司法适用和民众认识中的盗窃罪,也仅限于秘密的方式窃得他人财物的犯罪类型。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必须建立在民众认同的基础之上[32]。试图采取文义、历史或者比较等方法在当下解读出盗窃罪包括公开取得的结论,违背了基本的语言习惯,很难得到民众的内心认同。理论的构建不应脱离基本的社会生活常识和人们的语言表达习惯,在盗窃罪理论上,应当尊重盗窃一词的基本含义,顾及社会基本认知和国民的接受程度,维护盗窃罪限于秘密取得的传统含义。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66.
[2]马克昌.刑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69.
[3]赵秉志.侵犯财产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64.
[4]张明楷.盗窃与抢夺的界限[J].法学家,2006(2):119-131.
[5]曲新久.刑法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70.
[6]周光权.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7.
[7]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77.
[8]曲新久.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9:423.
[9]黎宏.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743.
[10]孙国祥.刑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523.
[11]阮齐林.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537.
[12]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1.
[13]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1090.
[14]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1.
[15]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90.
[16]张明楷.刑法学研究中的十关系论[J].政法论坛,2006(2):12.
[17]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0.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80.
[19]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K].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2042.
[20]曲新久.从“身份”到行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一个解释问题[J].人民检察,2011(17):6.
[21]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85.
[22]陆惠芹.盗窃罪小考[J].河北法学,1984(3)38-40.
[23]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153-391.
[24]刘柱彬.中国古代盗窃罪概念的演进及形态[J].法学评论,1993(6):47.
[25]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97.
[26]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5.
[27]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1.
[28]赵秉志.略论抢夺罪的几个问题[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2):15-18.
[29]吴林生.平和窃取说之批判——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J].法学,2010(1):30-48.
[30]董玉庭.盗窃与抢夺的新界分说质疑——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J].人民检察,2010(15):20-25.
[31]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18-119.
[32]陈忠林.刑法散得集(Ⅱ)[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24.
Assessment on Open-theft Theory in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GAO Guoqi
(School of Law,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P.R.China)
In the premise of cognition,open-theft theory makes no importance of the secrecy.This theory takes existing truth as a premise to adopt circular thinking, takes the foreign theory for granted to be assumed, and interprets penalty gap subjectively.So, in epistemology, there is deficient for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the theory.In the arguments of the theory, it inappropriately uses literal interpretatio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It is not perfect in establishing the boundary of theft crime and distinction with robbery and other crimes of property.Therefore,it is questionable for the rationality and feasibility to construct open-theft theory in methodology.The theft theory should be reassessed,so as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secret-theft.
open theft;secret;epistemology;methodology;assessment
CF792.7
A
1008-5831(2014)03-0120-09
10.11835/j.issn.1008-5831.2014.03.016
2013-10-1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CDJXS12 08 11 05)
高国其(1974-),男,河北邢台人,重庆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