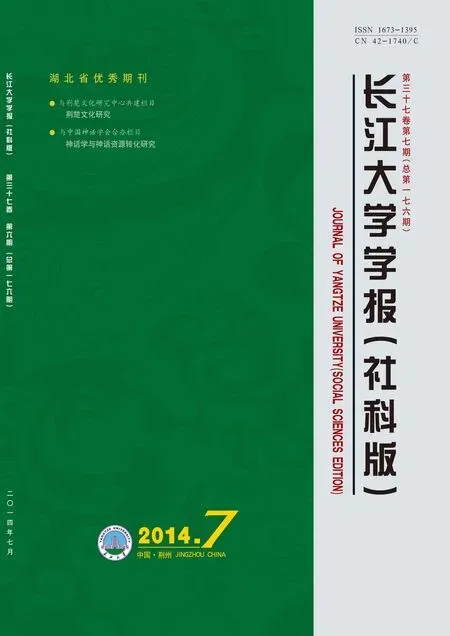教育场域中的权力:基于学校仪式活动的分析与启示
张银霞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人类学仪式研究经历了研究对象的转变,由起初集中关注神圣的、宗教的、神秘的仪式活动,到逐渐将现代社会中具体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日常仪式纳入研究范围。早期剑桥学派的研究,便主要集中在神话和宗教范畴,并形成了神话—仪式人类学范式。以迪尔凯姆和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家,考察带有明确宗教意义和喻指的仪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作用和地位,形成了结构—功能范式。随着仪式理论的发展,现代仪式学研究开始走下宗教神坛,呈现泛仪式化倾向。现代仪式学研究者认为,并非所有仪式性行为都是宗教性的,超出宗教之外,仪式化行为存在于社会文化生活中。[1]美国社会学家贝格森是泛仪式化取向的支持者。他把仪式划分为微型、中型、大型三个层次。微型仪式指的是人类群体的语言符码,即经过规范后的仪式化用语,如见面时说“你好”。中型仪式指的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群体内部的行为规范,如旧式英国绅士遵循的女士先行规则。大型仪式便是与日常生活区别开来的集体庆典仪式。[2]
权力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指的是某一社会实体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和意愿行动的能力和可能性。权力越大,左右他人的能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瓦解着社会整体性的宏大叙事,个体化、日常化、生活化的微观层面事物受研究者关注。受其影响,权力研究也发生转向,由关注宏观和中观权力的运作,走向探析日常生活化的微观权力运作。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法国两位著名的社会学大家福柯和布迪厄身上。他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知识权力、话语权力、符号权力等微观权力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作,并最终得以合法化的。可见,权力研究和仪式研究在研究取向上具有耦合性,它们都将研究着眼于日常生活,仪式背后隐含的权力喻指,使得权力和仪式两者成为天然同盟,而探索微观层面仪式化行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则是权力研究和仪式研究的契合点。
一、教育场域中的学校仪式活动
仪式研究视角也发生了转变,由早先关注仪式的社会定位、功能,到关注仪式的社会运作机制。早期仪式研究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注重仪式功能探讨,如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仪式功能在于以象征和隐喻的方式创造权威和权力。现代仪式学研究者更注重对仪式进行象征性分析,试图阐明仪式的内在逻辑,分析仪式如何存在并为人们理解接受,如何发挥社会认同和社会动员功能。研究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取向与探究仪式运作机制的取向相结合,使得现代仪式研究呈现出日常化、生活化、微观化、精致化等特点,而日常仪式行为背后的权力关系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域。仪式化行为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备受研究者关注。他们既将仪式理解为一套约定俗成的生存技术,又视其为一套由国家意识形态运用的权力技术。[3]
仪式概念的内涵具有复杂性。[4]试图探究学校仪式活动中的权力,需先界定学校仪式活动。仪式对应英文中的Ritual,指的是以同样方式重复的习惯性行为、典礼或者程序,具有表演性、象征性、情境性等特点。表演性指的是仪式参与者有各自角色,并以各自固定的行为规范展现角色内涵;象征性指的是仪式不仅是仪式本身,而且是一种隐含深层意义的象征性符号;情境性指的是仪式依赖于特定情境才能展现其内涵和意义所指。[5]日常仪式化行为在人与人的互动交往过程中形成,是日常生活中重复进行的,具有不同发生频率的一种行为或一组行为,具有日常性、例行性、程式化、象征性、社会情境性等特点。[5]作为一种日常仪式化行为,学校仪式活动指的是在学校教育环境中以一定频率发生的社会行为,由学校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等教育活动参与主体,按照既定方式、次序和规范,在学校日常教育生活中重复进行。这种行为受社会文化环境制约,具有象征意义。
学校仪式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性和时代性。本文主要关注当下我国中小学校中内部仪式活动中的权力及其运作机制,而不将学校与外部他者或他组织间的仪式列入探讨范围(如教育实验培训基地挂牌仪式)。具体而言,学校仪式活动包括:阶段性仪式,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学位授予典礼;节假日庆典,如儿童节、国庆节、校庆、院庆、五一劳动节等;比赛及颁奖仪式,如奥赛、作文比赛、演讲比赛、运动会等;政治仪式,如升降旗仪式,入队、入团、入党的程序以及宣誓仪式等;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礼仪,如见到老师主动打招呼、进老师办公室先敲门、穿校服、佩戴红领巾(胸章、校徽)等;会议仪式,如全校大会、年级会议、班会、教师大会、选举大会、学校工作会议等;课堂教学仪式,如上下课喊口令、起立,提问先举手,站着回答问题,上课坐姿体态、课堂讲授、考试等。
二、学校仪式活动中的权力运作逻辑
(一)仪式活动中的国家权力意志
仪式具有维护建立秩序规则和社会整合的作用。在本质上,仪式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相结合,其通过论证与维护国家权力的符号秩序,将某种合法性依据嵌入人们的价值标准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权力的实践工具。学校是国家培养未来公民的场所,通过学校传达的意识观念,需要与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吻合。学校仪式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国家意志。美国学者伊万·伊利奇认为,美国学校教育是仪式实施场所,甚至学校教育本身便是一个维护既定社会秩序,传递既定意识形态的昂贵仪式。[6]伊利奇的观点因偏激性而受到批判,然而他也为我们指明了一种思考方向,即学校教育仪式中所传递和维护的国家权力意志。
学校仪式活动传递国家权力意志的功能,在政权特殊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奉行愚民政策,其教育目的在于将青年人培养成身体健壮而残忍狂野的野兽,忽视甚至鄙视智育活动,青年学生在课堂上随意起哄捣乱,将教师拽下讲台,甚至随意诬告和打骂。类似情况也存在于二战时期的日本学校教育中。受军国主义影响,日本小学的一二年级教材中充斥着有关武力和扩张的神话故事,打仗游戏,军事作战基本技能成为其主要课程。在非常态的国家权力意志影响下,学校仪式活动脱离了正轨,处于极端失控失序的疯狂状态。
依赖于学校仪式中的人、物、语言、行为等多种要素,国家权力意志得以集中而强烈地表现和维护。国旗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象征,象征着民族团结和烈士功勋。在我国,升国旗仪式是国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主要方式。自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颁布实施以来,每周举行一次升旗仪式,已经成为全日制中小学校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升旗仪式参与者有不同角色,且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要求。升旗队员以及国旗下讲话时的学生代表,是学生中的佼佼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和学校身份的代表,在升旗仪式中发挥着榜样作用。升旗仪式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一般有出旗、升旗并奏唱国歌、国旗下讲话等步骤。升旗过程中,参与者穿着统一校服,面向国旗肃立致敬,行注目礼。国歌营造了仪式严肃,振奋人心的气氛。国旗下讲话是升旗仪式的重要环节,以爱国主义、先进人物事迹、思想教育为主要内容,强化了升旗仪式的教育功能。通过角色扮演、行为规范、严格程序、气氛渲染和情感烘托等方式,升旗仪式有效地传递了国家权力意志,达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除了升旗仪式,学校中的入队、入团、入党等仪式也具有象征意义,也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体现,并通过这些仪式传达给年轻一代正确的政治价值观。
(二)仪式活动中的规训权力
规训被福柯用以概括近代以来的一种新型管理权力。它是一种持久的运作机制,通过对人体的解剖、分配、组合与编排,达到对人体位置、姿势、形态及行为方式的精心操纵,以此造就“驯服的肉体”。规训权力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为了控制和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在福柯看来,现代学校是一个典型的规训机构,通过行使制度化和规训化的管理权力,学校创造出新型的、顺从的、训练有素的“听话的身体”。
课堂成为规训场所,规训权力集中体现在一系列课堂仪式化行为中。教师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课堂仪式行为,如“上课专心听讲,独立思考,不讲小话,发言一律举手;坐姿端正,左手背臂向下,右手臂搭在左手背上,右手臂向下,双臂平放在课桌边;做好课前准备,摆放好课堂学习用品,文具盒放在桌子正中央,课本放在文具盒下边,工具书和作业本放在桌子右上方”[7]。除课堂仪式外,规训权力还渗透到了日常学校仪式活动的方方面面,如服装、发型、自行车码放、出操站队、就餐、休息等方面都有统一的要求和严格的规定。一些学校要求学生午间必须在教室趴着休息,不许抬头,不许看书,更不许说话,睡不着也得趴着;中午在学校就餐,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吃完,不能剩饭,不能倒掉,饭后洗刷餐具要用指定的水龙头,将餐具放在指定位置。[8]学校仪式活动中的规训权力通过上述纪律化和制度化行为,规范型塑学生的身体和行为,年级越低,身体控制越直接,年级越高,言语性控制则越显著。言语性控制直接指向对学生心理和精神的影响,试图通过言语引导,将外在控制逐步转向学生的自我控制。[9]言语性的规训权力无疑更具隐蔽性,它将外在的强制性转变为被控制者的理解和认同,获得了规训权力实施的合法性,通过仪式活动的不断再现,以实现对学生的精神规训。
在学校仪式活动中,由学校行政管理者权力、教师权力和学生干部权力构成的权力金字塔,对型塑学生的身体和行动产生规训影响。规训权力拥有者通过制定具体的行为细则,对各种教育活动情境中的学生进行身体和行动规训,以形成严明的纪律、操守、仪规和礼节。在学校仪式活动的规训权力实践中,学校行政管理者是仪式行为规范的制定者和检查者。他们的规训权力对教师和学生具有强大威慑力。他们对不穿校服,不带校徽等违反纪律的行为严惩不贷,并通过一系列会议强化其管理规训权力。教师作为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规训权力的执行者,按照要求“修剪”和“建构”学生的身体和行为。学生个性化的与规训不符的言行被修剪掉,符合要求的得到保留和赞扬。在学校仪式活动中,教师处于优势地位,学生处于劣势地位。双方处在一种紧张的控制与反控制对抗中。当学校行政管理者和教师缺席学校仪式活动时,这种规训权力往往下移到被管理者和教师所认可的“守规矩”的学生干部手中。他们成为暂时的规训权力拥有者,代替管理者和教师行使规训权力,检查和监督其他学生的行为表现。
(三)仪式活动中的知识权力
在福柯看来,任何社会的知识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纯粹的,知识是权力化的知识,知识在诞生之时就与权力紧紧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是一种共生互生关系;知识来源于权力,谁拥有知识,谁便拥有控制和影响别人的权力。[10]知识通过语言表述而达成一种意义、价值和规范的建构,进而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形成一种话语权力,对他人有着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11]学校课堂讲授仪式中的知识传递和生产过程并非客观或纯粹,它暗含着由知识权力化而来的教师权力,而教师权力的背后,则隐藏着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要求。
课程标准、课程计划的制定以及教科书内容的选择,集中反映了主导阶层的权力意志和利益。通过主导阶层的确认和授权,这些知识成为课堂讲授仪式中的法定知识。课堂讲授仪式必须以课程知识为基础,课程知识法则就是课堂讲授仪式所要遵循的法则。课程知识是知识和国家权力结合的结果,是一种权力化的知识。国家权力借由课程知识权力支配课堂讲授仪式中的人和物。[12]在国家权力、课程知识权力和教师权力的传递过程中,课程知识隐含着国家权力,发挥着中介作用,教师则是权力的执行者,在具体的课堂讲授仪式中,影响和规范学生的知识构建和价值观念。换言之,国家权力经由课程知识权力过渡到教师手中,教师代表学校和国家实施对学生的教化,使其接受具有特殊价值的知识体系。这种教化具有强制性。
较之强制力的权力控制形式,意义操控是更间接的权力运作方式。意义化和合法化这两个权力运作基础,被支配者不假思索地接受和践行,并为其赋予理由和意义。课堂讲授仪式得以开展的前提,便是人们对学校教育合法性地位和讲授方式的普遍的内在的认同。因而,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人们往往只看到知识和教育,而潜藏于其中的权力则被掩盖起来,且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学生则不知不觉地臣服在教师的知识权威下。知识背后的权力以知识系统为工具,不但控制学生的身体,并藉由知识进行价值观、信念、行动等方面的控制。
三、结语与启示
权力作为控制他人行动自由的能力,需要通过某种途径证明其合法性,并获得被控制者的认同,以便于长久维持权力拥有者的地位和既定的控制规则。现代学校教育具有高度制度化的特点,是权力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最佳场所,成为各种权力竞相争夺的场域。布迪厄指出,教育是有史以来掩藏得最好的权力传递方式,在其表面的中立态度下,掩盖着再生产阶级关系的本质。学校仪式活动是学校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正式、半正式或非正式权力发挥其控制力量的实践方式。换言之,仪式承担着传递和建构学校日常生活权力秩序的职责。学校仪式活动中所蕴含的国家权力,是人们熟知与认同的正式权力。此外,学校对学生形成一种貌似具有合法性的规训权力,某种程度上控制着学生的身体和行动。这种规训权力为人们普遍认同,并以学校行政管理者权力、教师权力、班干部权力的权力金字塔形式呈现。再者,教师是实现学校教育目的和功能的中介。教师权力一方面源自国家和学校认可的正式权力,另一方面则基于教师(相较于学生)的知识文化资本优势的知识话语权力。教师权力集中体现在课堂知识传授过程中。
权力可谓无处不在,渗透在学校仪式活动的各方面。如何看待仪式中的权力运作?其一,学校仪式活动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在仪式中的权力秩序与国家权力具有同构性,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个体的要求,有助于学校教育完成促进个体社会化的功能。其二,学校仪式活动中的权力运作可能导致既定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从积极方面看,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消极方面看,这可能扼杀社会发展变迁的可能性,并再生产社会不公。其三,权力藉由仪式全面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方面,对学校教育的独立性、教师与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诚然,人们对权力的理解,通常具有某种负面性,认为它意味着违背他人意志,强迫他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抑或阻碍或蒙蔽他人对自身真正利益的表达或追求。如福柯所言,权力并非恶魔,中小学校按照国家需要培养人才,教师悉心传授知识和技能,这些活动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当学校和教师的要求与学生自身的发展需求之间,存在差异甚至冲突时,当学校或教师按照统一的所谓“好学生”的标准,强迫学生改变个人意志,并湮没学生个人需要和感受时,便出现了遭人诟病的负面权力。支配和自由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并行的一对张力,负面权力可能导致抵制的产生。因此,当权力藉由仪式活动试图支配中小学校、教师及学生时,需预留一定的自主选择、意义协商和个体表达的空间,以此强化学校教育的独立性以及教师与学生的主体性。绝对的强制力并非权力运行的唯一机制,如何赋予权力底层合法性基础,进而避免抵制的产生,则是更为关键的。
参考文献:
[1]杨民康.信仰、仪式与仪式音乐——宗教学、仪式学与仪式音乐民族志方法论的比较研究[J].艺术探索,2003(3).
[2]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J].江西社会科学,2007(1).
[3]耿敬.民间仪式与国家悬置[J].社会,2003(7).
[4]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J].民族研究,2002(2).
[5]吴艳红,J·David Knottnerus.日常仪式化行为:以知青为例的研究[J].社会,2005(6).
[6]钱民辉.论美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实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7]张文学.从一则常规看课堂的管理[J].中小学管理,2003(3).
[8]田国秀.学校规训教育与人的物化[J].当代教育科学,2007(18).
[9]谢妮.学校日常生活中的身体[J].教育学报,2006(6).
[10]傅春晖,彭金定.话语权力关系的社会学诠释[J].求索,2007(5).
[11]李松林,金志远.教育场域:权力的运作与学生的境遇[J].当代教育科学,20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