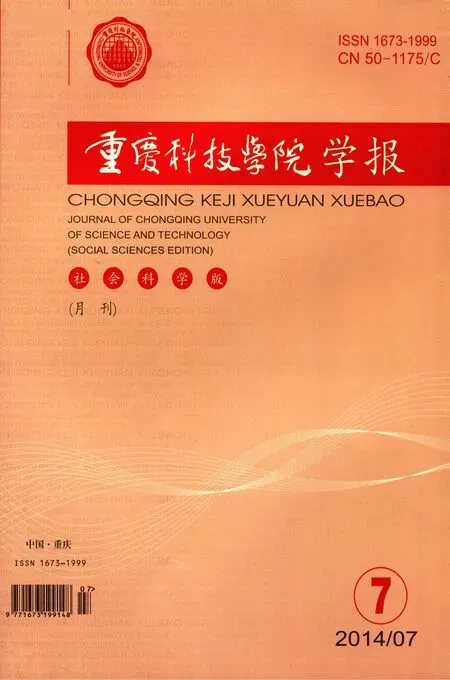从神话原型看《小鲍庄》的“寻根”内涵
孙 晖
1985年,作家王安忆在《中国作家》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作的《小鲍庄》。在这篇小说中,王安忆对现实和象征的完美融合让已熟悉其早期创作风格的读者和研究者眼前一亮。习惯于细腻地抒发感情的上海作家王安忆竟然写出了如此“土气十足”的作品,而这样的“土气”似乎也契合了当时刚刚崛起的“文化寻根”意识,加之这篇小说叙事模式的独特,以致近年来对于《小鲍庄》的研究多集中于 “寻传统之根”“叙事特点”“民族生存”等视角。但是,在近3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小鲍庄》,却可以发现其内部隐藏着的种种神秘的因素,而王安忆创作《小鲍庄》的目的似乎也并不是“寻找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仁义’之根”那么简单。正如陈思和所说:“……为什么这样一部描写平平常常的农村生活的故事会吸引那么多批评家。……《小鲍庄》没有那种外在弥合的痕迹,它似乎只有一个世界:现实世界。但就在这个世界的背后,隐藏了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它似乎不出现于文学表象之中,需要读者的体验与领悟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我姑且把这隐隐约约形而上的世界,称之为‘神话模式’。”[1]《小鲍庄》中的这种“隐隐约约的神秘”究竟与“寻根”有着什么样的关联?而王安忆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其对民族精神之根的探寻?本文将利用 “神话—原型”批评来解读《小鲍庄》,通过作品中对神话原型的几次移位,分析以“仁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精神内核在当代中国的现状和处境,同时解读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神话—原型”批评是20世纪流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的批评流派,被誉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三足鼎立的文学批评流派。“神话—原型”批评旨在发掘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塑造类型、叙事模式以及各种典型意象,并且找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原型,而对于这些原型的追根溯源往往会追溯到远古先民们的神话之中,故被称为“神话—原型”批评。它的出现对于探索文学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神话—原型”批评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是加拿大学者诺斯罗普·弗莱,他将“原型”这一原属于心理学范畴的概念加以新的解释并创造性地纳入文学评论,并且在当时西方文学界“回归神话”倾向和荣格的原型理论以及“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影响下,给出了自己对于“原型”的定义:“它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指一种象征,它把一首诗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2]99可见,“原型”在弗莱的定义下,成为一种可以独立进行交流的文学单位。而“从文学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植根于原始文化,最初的文学模式必然要追溯到远古的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去。”[3]19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文学中所有的“原型”出现在神话之中。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原型不可能永远只将其照搬至作品中而不加任何创造和改变,故而要对原型进行“移位”和“置换变形”。有了这种处理,文学作品才可能在基于某些同样原型的基础上变得多姿多彩,生发出不同的魅力,这也是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所在。可以说,利用“神话—原型”理论可以对《小鲍庄》中那些近乎魔幻的书写作出极为合理的分析和解释。而通过对文本中“原型”的追溯,我们可以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象征,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王安忆对于“仁义”之根的理解和态度。
一、“根”的确立:对洪水神话的移位
《小鲍庄》表面上看来是一篇描写江淮地区农民抵抗洪水灾难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但是,王安忆却在篇首加上了两个极具神话传说色彩的引子,就使这个贫穷小庄子的故事带上了传奇色彩。第一个引子描写了小鲍庄经历的那场滔天的洪水,这是对上古洪水神话的一次置换变形。
“七天七夜的雨,天都下黑了。洪水从鲍山顶上轰轰然地直泻下来,一时间,天地又白了。
鲍山底的小鲍庄的人,眼见得山那边,白茫茫地来了一排雾气,拔腿便跑。七天的雨早把地下暄了,一脚下去,直陷到腿肚子,跑不赢了。那白茫茫排山倒海般地过来了,一堵墙似的,墙头溅着水花。
茅顶泥底的房子趴了,根深叶茂的大树倒了,玩意儿似的。
孩子不哭了,娘们不叫了,鸡不飞,狗不跳,天不黑,地不白,全没声了。
天没了,地没了。鸦雀无声。
不晓得过了多久,象是一眨眼那么短,又象是一世纪那么长,一根树浮出来,划开了天和地。树横飘在水面上,盘着一条长虫。”[4]284
这样雄浑壮阔的场景让人瞬间想起上古神话中关于洪水的描写,可以说这个引子就是洪水神话移位后的再生原型。洪水在世界各种文明的神话中都有出现并占有重要地位,如中国的《山海经》《尚书》中就有关于洪水的记载,《圣经·创世纪》中有对于毁灭世界的大洪水的描述,印度的《摩奴法典》中也有记载洪水的篇幅。洪水可以说是人类再生的源头,这场灾难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王安忆以滔天的大洪水作为《小鲍庄》的开篇,直接将小鲍庄的历史追溯到了人类文明产生之初,可以说,小鲍庄的文明代表着人类的文明。
王安忆在“引子”之后的“还是引子”里进一步阐述了小鲍庄的来源。传说小鲍庄的祖上是大禹的后代,也是个治水的官,因治水不力而被龙廷罢黜,但是龙廷念他往日的辛勤,免了他的死罪。官儿深感愧对百姓,为了赎罪,于是携家带口在鲍家坝最洼的一处安了家,从此繁衍开来,形成了小鲍庄这个有着几百口人的小庄子。王安忆所描写的小鲍庄的起源显然是对“鲧禹治水”的一个置换变形。《山海经》中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王安忆借“鲧禹治水”的神话原型给小鲍庄安排了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起源,同时也道出了这个小庄子自诞生起便以“仁义”为根。小鲍庄的祖上便是鲧这个形象从神话向传奇的移位,鲧代表了心系黎民、为天下奉献生命的仁义精神,而作为鲧的移位,治水的官也继承了鲧的仁义精神,在鲍家坝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他也将这种精神深深植入这个村庄的人的意识。如果说小鲍庄代表了华夏文明的话,那么,小鲍庄人所一直信奉恪守的“仁义”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内核。因此,可以说王安忆在《小鲍庄》中的文化寻根之旅寻到了一个切实的落脚点。
那场大洪水作为小鲍庄的起源,在给小鲍庄植下了仁义之根的同时也给那里的人们带来了原罪。“原罪”是来自于基督教的宗教术语,在《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告诫,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上帝判为有罪,将他们驱逐出伊甸园。来到人间后的亚当和夏娃开始繁衍人类,于是他们繁衍出的人类生来便带有罪过,人的一生就是赎罪的一生。小鲍庄里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并不作恶,并且都恪守着仁义的准则,但是没有一个人生活得如意。建设子老大不小了还娶不上媳妇;文化子和小翠想爱而不敢爱;文疯子追求文学理想,非但为世人所不理解还到处碰壁;鲍秉德无可奈何地守着一个疯老婆……小鲍庄人的这些苦难都不是他们自作自受或者因果报应,也很难从社会历史上找原因,这只能归结于他们与生俱来便背负的原罪。他们的祖上治水不力,所以洪水给小鲍庄带来仁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贫穷和封闭,鲍家坝变成一片洼地,高高的鲍家坝也将小鲍庄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当年祖上的治水不力造成了世代困扰小鲍庄的灾难,而这一切也只能由小鲍庄人自己承担。王安忆将宗教的原罪意识纳入文本创作,不仅是对固步自封地恪守传统仁义道德行为的反思,更是对人类自身的深刻反省。
二、“根”的死亡:对英雄神话的移位
在文学史上的众多文学作品中,但凡生灵涂炭、百姓受苦,总会有英雄出现拯救苍生,为了人类的延续与灾难邪恶抗争,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基督教神话中,耶稣作为上帝之子,为消弭人间的罪恶和灾难来到人间,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教会了人类很多知识,并且冒死为人类盗来火种,人类得到了光明,而他却被宙斯囚禁在高加索山上,每天忍受恶鹰啄肝之苦;在中国神话中,鲧为了治水盗来息壤,触怒了天帝,将其诛杀于羽山,死后的鲧也没有放弃拯救人类的愿望,于是生下了他伟大的继承人禹,父子二人为了挽救人类于灾难可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小鲍庄》里的人们都生活在洪灾和原罪带来的苦难中,这时就需要一个英雄来拯救他们,于是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捞渣的肩上。
《小鲍庄》的正文开篇就是写捞渣的降生,他是伴着洪水而生的,这样的安排似乎隐约昭示着这个孩子的不平凡之处。随着捞渣的成长,他身上的人格光芒为所有人所惊叹。他善良,从小就与孤寡老人鲍五爷亲,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给鲍五爷吃;他快乐,“笑起来的模样好,眼睛弯弯的,小嘴弯弯的,亲热人,恬静人。大人们说他看上去仁义”[4]296;他无私,宁愿自己不上学却把学让给哥哥上;他尊重生命,哪怕只是一只叫天子,他玩过之后便会把它放生;他更有大人都不具有的舍己为人的精神,为了救鲍五爷而自己被洪水淹死。捞渣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形象,他诠释了小鲍庄人所一直坚守的“仁义”的精髓。捞渣是为了解救小鲍庄人的苦难而降生,他用他的生命和纯净的灵魂消弭了小鲍庄的原罪,他带着小鲍庄的苦难和罪恶随着那场洪水被卷走,将希望和改变留给了这片土地。
如何理解捞渣和捞渣的死亡是读懂《小鲍庄》的关键。捞渣的死带走了小鲍庄的灾难和罪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而捞渣死后他坟上出现的那只雪白的小羊羔就是对其的印证。“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认为,动物界的原型中之所以羊很受器重,是因为羊善良温顺的品格使它具备献身精神,所以才有了上古巫术中将濒死的神或者国王当做替罪羊杀死或驱赶的仪式,以带走部落或种族的罪恶和灾难。可以说“替罪羊”都是为人类受难的英雄,而捞渣的死亡则是对这种英雄神话的移位。他用他的生和死净化了小鲍庄人们的灵魂,带走了小鲍庄的灾难和罪恶,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捞渣作为“替罪羊”的作用最显著地表现在小鲍庄人们的生活因为捞渣的死而发生的改变,他们的灾难或者困境得到了逐步的摆脱:鲍仁文的作品终于被刊登发表,这也坚定了他继续文学创作的信心;鲍彦山家终于盖上了梦寐以求的新瓦房;建设子娶上了媳妇也当上了工人;文化子和小翠的爱情终于可以公开和被认同;鲍秉德终于摆脱了疯老婆,娶了一个普通的女人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正常生活;拾来也因为找到捞渣的尸体而收获了他所渴望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认同。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中,弗莱认为悲剧是对牺牲的模仿,尤其是英雄的牺牲,悲剧中英雄的牺牲犹如萧条肃杀的秋季。作为英雄神话的移位,捞渣的死充满了悲壮的气氛。捞渣出殡的那天,“全庄的人都去送他了,连别的庄上,都有人跑来送他。……送葬的队伍,足有二百多人,二百多个大人,送一个孩子上路了。……天阴阴的,要下似的,却没有下。鲍山肃穆地立着,环起了一个哀恸的世界。”[4]359作为移位之后的英雄,捞渣的死亡仪式也充满了肃穆悲壮的气氛。
捞渣的死亡不仅对于改变小鲍庄和小鲍庄人们的命运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昭示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仁义”的衰落。小鲍庄生于洪水,毁于洪水,又在洪水后被重建;洪水在开篇为小鲍庄带来原罪,在结尾又将苦难和罪恶带走;开篇小鲍庄人的祖上在这里落户繁衍是苦难的开始,结尾捞渣去世是苦难的结束。这仿佛一个闭合的圆,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命运,而在这个象征中,捞渣即是仁义的化身,这里他已经脱离作为一个简单个体的存在,而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符号。自小鲍庄诞生,村里的人们一直恪守着“仁义”的准则,将“仁义”视为生命的最高标准。但是,作为“仁义”化身的捞渣的死则显示出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衰落。《小鲍庄》中虽没有明确地指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社会背景,但根据零星的社会背景描写我们可以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定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文革的中后期。这时的小鲍庄虽仍然封闭落后并保留了传统的文化形态,但是,现代化的气息已经飘入了这个贫穷且自闭的小庄子。这一点从捞渣死后小鲍庄的种种改变中可以看出。小鲍庄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闭锁的所在,现代化的种种因素已经渐渐涌入,并且开始改变小鲍庄的面貌,而小鲍庄的人们面对现代文明的涌入不再是被动的、麻木的,而是主动地积极地去接受。小鲍庄送走了将“仁义”席卷而去的滔滔洪水,又迎来了现代化的滚滚大潮,等待他们的将是对新文明、新文化的建构。
三、“根”的重构:对“毁灭—重建”神话的移位
《小鲍庄》篇首的那场洪水创造了小鲍庄,是创世神话的移位;篇中的那场洪水毁灭了小鲍庄,是洪水神话的移位;而对洪水之后小鲍庄人重建精神信仰的描写,则是对“毁灭—重建”神话的移位。几乎所有文明的神话中都曾出现神毁灭世界之后重建世界的记载,在这些记载里,初次创世后人类的种种罪恶为神所不容,于是神引发灾难毁灭人类文明,再让幸存下来的人类在原来的土地上重建一个新的文明。《圣经·创世纪》中耶和华在创造出世界万物之后发现人类世界充满罪恶,对此深感后悔,于是发动了一场滔天的洪水将人类文明全部毁灭。在发动洪水之前,好人诺亚受领神谕,造了一艘方舟而幸免遇难,洪水过后诺亚带领方舟上幸存的人兽在洪水退去的土地上重新开始营造新的人类文明。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也有“毁灭—重建”模式的内容。华夏大地上洪水泛滥,万物毁灭,只有伏羲和女娲两兄妹幸存,二人通过滚石磨的方式决定结为夫妻,开始了大地上继初创世时女娲造人之后的第二次繁衍,华夏文明被重构。诸如此种模式的记载在北欧神话、印度神话、拉丁神话等神话系统中都有出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毁灭和重建不仅仅是指人类作为自然个体的自然性的消失和再生,更重要是指一种制度、文明、价值观念的毁灭和重建。作为将“寻根”内涵寄托在神话原型中的《小鲍庄》,我们自然也可以从中寻觅出“毁灭—重建”神话的移位再现。
大洪水之后的小鲍庄虽然并没有造成大面积的人员伤亡,全庄几百口人只死了三个,但是作为“仁义”化身的捞渣便是其中一个,小鲍庄以“仁义”为精神内核的传统文化随着洪水被卷走,留下了重建现代精神文明的任务给幸存下来的小鲍庄村民们。通过对整个文本的观照,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选择的带领小鲍庄村民重新建构现代文明的人是鲍仁文,这个痴迷于文学创作的文疯子的所作所为,在无意识中一步一步将小鲍庄推离传统,推向现代化。之所以说他“无意识”,是因为他行动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追求自己的文学理想,并没有扩大到要为整个小鲍庄做些什么。捞渣的死带走了“仁义”传统,开启了小鲍庄现代化的大门,为小鲍庄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能;而文疯子的活动却在实际上带领着小鲍庄走向现代化。捞渣的事迹最初只是在小鲍庄和附近几个庄子传颂,但是因为鲍仁文的一篇报告文学,捞渣的事迹先被县里的媒体注意并刊登在地区报纸上,进而省上的媒体也派人下来采访,将捞渣的典型事迹刊登在省报上进行大力宣传,再发展到邀请作家将捞渣编进书里。这样,捞渣和小鲍庄一时间便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最终捞渣被评为“少年英雄”,并在小鲍庄正中的场上为他竖起了一块纪念碑。捞渣成为少年英雄之后,小鲍庄的面貌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庄上的人们开始摆脱原罪和苦难,展现出了新的生存状态。至此,小鲍庄的人们实现了“毁灭”之后的“重建”,这一切固然是因为捞渣之死带来的对原罪的赎罪,更有鲍仁文在无意识状态下对“重建”施加的影响。
小鲍庄是由被毁灭走向被重建的,那么,那场涤荡一切的洪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小鲍庄恪守的“仁义”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品格,是他们的祖上在落户于此的时候便深植于他们的意识和精神之中的,由此传承了几千年,这就是他们的文化和精神之根。这同时也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被深深地镌刻在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但是历经千年,这样的文化和精神之根却没有被添加进更多的注解,一直保持着固步自封的状态。这一点从小鲍庄村民的生存状态中便可以看出:单身汉拾来和守寡的二婶的结合不为族人所容,还被族人以“仁义”之名殴打;鲍秉德守着一个疯老婆苦不堪言,但是为了守住“仁义”,他不敢抛弃他的疯老婆;小翠和文化子真心相爱,但是他们的爱情却为族人所不容,只因为小翠是文化子哥哥的童养媳,名义上是哥哥的媳妇,弟弟抢哥哥的媳妇便是“不仁不义”……这样被他们恪守的“仁义”的某些方面已经变味,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化大潮席卷下的小鲍庄。所以,王安忆通过安排一场大洪水冲刷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部分,打破传统文化和民族性中麻木、愚昧、封闭的陋习,在发现民族文化之根的同时寻找重建民族精神的可能。
四、结语
通过对神话原型的几次移位,王安忆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几乎现实主义的故事,但在这个故事里却存在着种种象征和种种神秘,也正是这样的象征和神秘使这篇小说有了代表王安忆的寻根之旅的意义。通过利用“神话—原型”理论对《小鲍庄》进行解读,我们可以看到王安忆试图通过将民族文化之根追溯到远古神话之中来寻找重建民族精神内核的可能,可以说是在神话原型之中寻根。作者通过小鲍庄的创造—毁灭—重建,向我们昭示了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必须被荡涤的必要性,同时也宣告了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现代文明逐渐兴起的时代的到来。
[1]陈思和.双重迭影·深层象征[J].当代作家评论,1986(1).
[2]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3]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4]王安忆.小鲍庄[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