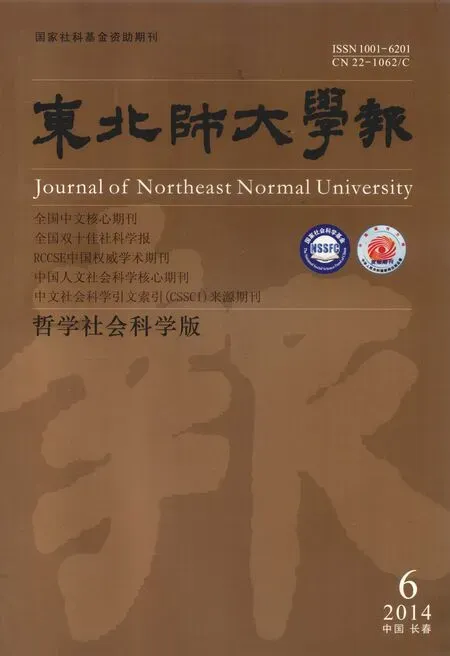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童年故乡印象书写的对比研究
张 国 华
(长春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童年故乡印象书写的对比研究
张 国 华
(长春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虽然大江健三郞和莫言分别为日本作家和中国作家,但在初入文坛时却走过了一条极为相似的道路,两者的童年故乡印象书写是他们的最大共同点。虽然两者处于不同的社会体制内,但是,对于人性的关注,却使两者走到了一起。通常说来,儿童的内心世界尚未被世俗所污染,是相对纯洁的,因而童年印象书写可以使作家不以先入为主的世界观来看待世界,进而在构建儿童乌托邦的理想世界中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大江健三郞与莫言之间的交往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个人之间的往来意义。两者之间的文学交流在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方面,对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具有更为广泛的现实意义。
大江健三郞;莫言;童年;故乡;全球化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虽然大江健三郎和莫言在获奖时间上相差了18年,但两人步入文学创作的道路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大江健三郎“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1]而获奖;莫言则以“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及当代融合为一体”[2]而获奖。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更大层面上体现在他们早期走上文学之路的童年故乡记忆。这一点既可以从两位文学大师的对话中得到印证,又可以从他们的早期作品中得到阐释。
一、故乡的记忆对两者的影响
毋庸置疑,在文学地理的塑造方面,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更加接近[3],但是,就作家文学地理的成因而言,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却直接受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雪国》的影响;而就作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而言,大江健三郎却与莫言走得更近。在谈及两者在这一点上的共同之处时,大江健三郎听完莫言的童年记忆时指出:“听了这些详细的解说,生长于农村的少年莫言能成就现在的文学造诣就比较好理解了。我也再次思考了自己是如何成为小说家这一问题。”[4]215大江健三郎与莫言两人均对故乡怀有深深的爱与恨。两人都不能释怀在故乡度过的童年时代,而这一切都在两人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眷恋之情。莫言“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概念超越了事实上存在的国家疆界概念,“实际上是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验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它是没有围墙甚至没有国界的。”[5]大江健三郎与莫言一样,都是“农村人”。大江健三郎的故乡在日本的四国爱媛县的喜多郡大濑村,莫言的家乡在中国的山东省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共同的农村经历使两位世界级文学大师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到了一起。大江健三郎儿时居住的村庄属于山区,总是有种令人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一样的感觉;莫言在农村度过的童年也为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痛苦回忆。大江健三郎如今的家乡就像是一处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但大江童年时期的故乡并非如此。由于战争的缘故,这个村庄与其他村落相互隔绝,既偏僻又落后。童年时期的“洪水”记忆成为两位作家早期创作的主题之一。大江健三郎回忆道:“我们村子之所以要进行露天火葬,是因为夏季开始前就开始接连不断的梅雨、持续地长时间地接着下,直到引起接连不断的洪水的缘故。从我们的村子通向‘镇’里的近道的吊桥由于山崩一旦被毁,我们小学的分校就会关闭,邮件滞后。而且我们的村里的大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沿着山脊窄小的缓坡而行,才能抵达‘镇’里。将死者运到‘镇’的火葬场根本就不可想象。”[6]286-310更为甚者,当时山村里的人们在镇上经常被镇上人视作肮脏的动物,受到镇上“文明人”的歧视。因此,在大江的记忆中,故乡一直是灰蒙蒙的。大江选择了逃避的道路。但是,从乡村逃离出来之后,大江又感觉到自己与都市文明之间发生冲突而处处碰壁,遂决定再次返回故乡。大江在其作品中经常出现对自己反叛故乡的歉意描写,经常把自己的家乡设计为其小说故事情节的背景,因为故乡对大江的创作而言,尤其是对其初期的文学创作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莫言童年时期的家乡也经常发大水,河水像马头一样冲过来,这种现象被莫言称之为“河头水”。莫言认为:“河水不单为我们提供了食物,而且后来也给我提供了文学灵感。有河水的地方肯定是文明产生的地方,也是文学产生的地方。”[4]217在个人亲身经历的基础上,莫言创作了早期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大江认为,河水又是从异界通往自己生存地方的通道,因而洪水也是大江创作的主题之一,其早期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是此类题材的代表作之一。大江和莫言的这两部小说均把洪水作为引子,描述了早期乡村人在特定历史境况下的生存困境。大江在这部小说中把洪水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从一个故乡的“农村人”视角表达了他对洪水和战争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但大江更加看重莫言对洪水描写的意义,认为莫言把“少年时代的记忆发挥出来,以人民公社为主题,用非常现实主义的手法,创造出甚至超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真实的形象,由此形成了莫言的世界”[4]219。
关于小说的世界,大江回忆道:“回顾我的文学生活,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是以日本列岛其中一个岛、几乎是位于四国中央的、在四国山脉的分水岭北侧的深山老林的小山谷之间的村落作为小的舞台。”[6]286-310大江提及的“很早的时候”指的是他获得芥川奖的中篇小说《饲育》(1958)中所提及的时代。在这部作品中,大江讲述了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军对日本空袭的经历与感受。美军飞机被击落,黑人士兵坠落到环绕着谷间村的森林当中。主人公“我”发现了这个美国黑人士兵并把他带回家像对待自家的牛一样精心饲养着。黑人士兵和“我”之间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原因而结成敌对关系,反倒成了田园牧歌式的亲情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却一直都喜欢这个成为阶下囚的黑人士兵,因为“我”和黑人士兵都是父亲用短矛打败的。大江借这部作品中的描述,阐释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而恰恰就是这种描述将大江的文学创作背景置于黑人士兵降落的谷间村,即大江的故乡。
大江在文学创作初期就与莫言一样,不约而同地将自己故乡的回忆设计成自己的文学舞台背景。至于两者的社会改良思想,却并非是有意识的。莫言基于自己借鉴川端康成的《雪国》为自己的《白狗秋千架》所设定的基调,一反“还乡小说”的传统写法,虽是儿童,却以成人的视角来表现“意外的事故导致了美丽的东西被毁灭。不过莫言并未意识到作家的这个共同点”,这说明写作当中是有潜意识的,要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分析可能还能发现一些东西[4]232。莫言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和大江健三郎在《饲育》中出现的四国“谷间村”及其后来的故乡系列作品中虽然讲述的分别是中国农村和日本农村的故事,但在文学的起点上,两位作家却走到了一起。
首次下意识出现“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白狗秋千架》,但表现莫言童年故乡的却是《透明的红萝卜》。对于莫言而言,故乡是割舍不下的,以至在后来大量的作品中,除《红树林》和《酒国》等少数几部作品以外,莫言都是围绕故乡为背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大江健三郎自称为山里人的话,那么莫言则是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在那“革命的年代”,由于出身中农家庭,再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和前苏联逼债的大背景,所以莫言在故乡的童年生活中充满了苦难和孤独。童年时期的莫言对故乡没有任何留恋,而是抱有深深的怨恨之情。在故乡,莫言每日辛苦劳作,仍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因而莫言厌倦那低矮的农村草房、干涸的或洪水泛滥的河床。莫言和大江一样,也想逃离自己的故土,到外面去寻找自己的生活道路,所以,当莫言“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于是,当他爬上“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当那些与我同车的小伙子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感到我如一只飞出了牢笼的鸟。我觉得那儿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我希望汽车开的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能开到海角天涯。当汽车停在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二百华里的军营,带兵的人说到了目的地时,我感到深深的失望。”[7]153-154与大江健三郎一样,莫言虽然在童年时期一直对故乡采取回避的态度,但是在他的文学世界,故乡的影子却从未从他的脑海中消失过。在他写到大海的波浪、军营生活和连绵不断的域外山脉时,脑海里浮现的却全都是故乡的山川、河流和故乡的人们。成名后,莫言怀着兴奋的心情再次踏上故土。当他看到蓬头垢面的母亲出来迎接儿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时,莫言也禁不住地泪流满面。这时,莫言才真正意识到故乡对于人们的制约。“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回到高密东北乡去,遗憾的是那里的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现实中的故乡与我回忆中的故乡、与我用想象力丰富了许多的故乡已经不是一回事。”[7]170
二、两者的童年印象书写
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早期作品均体现了孩童时代的空想社会改良思想,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对童年时代的印象书写对这一点表达的尤为明显。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均围绕作家童年时代的印象书写展开,是这一主题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两位作家初入文坛时的文学作品,对他们日后的文学发展形成了重大影响。大江健三郎的中篇小说《饲育》1958年发表于《文学界》,使大江获得了芥川文学奖,同时也确立了大江作为新文学旗手的地位。《饲育》虽然采用的是儿童视角的叙述方式,但是,在儿童视角的背后却包含了大江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生的深邃思索。莫言则通过1985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进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
两位文学家虽然年龄相距很大,走上文学道路的时间也不尽相同,但是,两位作家在日本和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上均以中篇小说形式发表的作品及其影响力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位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儿童印象均是处于饥饿和孤独境况下的儿童,《饲育》中的主人公“我”也可以说是《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小子,他们都是在生活中饱受苦难,遭人白眼,在孤独中独自挣扎,试图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的儿童形象。
大江在《饲育》里写道:“当时居住在位于我们村庄中间的公用仓库的二楼、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的狭窄的养蚕的房间。在厚厚的有些腐朽木板的地板上堆放着饭桌和铺盖。父亲横躺在地板上,我和弟弟躺在用于养蚕铺设的门板上。墙壁上粘贴旳纸上还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天棚上裸露的木梁上黏着腐烂桑叶。只不过是原来成群蠕动而行的蚕的旧居住满了人而已。”“我们村子里的人们在‘镇’里经常被当做肮脏的动物一样受到厌恶。”[6]286-310这里的人们除了马铃薯以外,别无可吃的东西,有时甚至连马铃薯也吃不到,就更不用去想象吃什么白面了。
大江将故事的主人公设定在这样悲惨的境遇与大江本人悲惨的幼年经历相关。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的幼年经历有两种类型:经历丰富的类型和经历缺陷的类型。前者指的是人们在幼年时代的生活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完美无缺的;后者则指的是人们在幼年生活中充满了不幸的经历并留下了痛苦的记忆,这类人由于物质匮乏而导致精神上受到伤害和压抑而心理上感到极端郁闷。毫无疑问,大江和莫言都属于缺陷型的人。虽然大江的家庭曾经属于悠闲富裕阶层,但是在大江健三郎6岁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9岁时祖母去世,其兄长们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大江健三郎成为这个家庭中唯一留下来的男性。战争之后,故乡又接连发生水灾,大江也只能在饥饿中度日。经历了这些苦痛之后,大江健三郎变得更加敏感,也更加脆弱。“大江常常因为大人们意识不到的阴暗面而诚惶诚恐。对于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惴惴不安。他经常由于过度地害怕,不知道以后要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法而不停地流泪。大江描写的主人公也是如此,他们常常败给周围的事和环境。”《饲育》中的“我”正是大江自身的写照。在小说中的“我”虽然一直把美国黑人士兵当做牛一样养育,对其施以爱心,但是有那么一天“我”却突然成了这个黑人士兵的囚犯。“黑人士兵的指甲深深地掐进我的喉咙的皮肤里,我痛苦地叫喊着。”[6]286-310然而,当父亲用秤砣击打自己和黑人士兵的手时,“我”的心灵和身躯却同时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当“我”的意识清醒后,“我”感到浑身无力,对成人世界的行为感到特别恶心。“我”在一个空房间里,从开着的窗户俯视着村庄,“带有咸味的泪水常常浸湿皲裂的嘴唇,如同针刺般地疼痛。”[6]286-310大江的悲观情感可以从萨特的存在主义那里得到解释。萨特认为,人们生存在世界上,就无法回避孤独、失望、仇恨和遗弃这些悲观的感觉[6]286-310。为此,主人公的“我”也表现为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抗争,只能选择了一条沉默和逃避、在心中自我抚慰伤口的救赎道路。
莫言在其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描写的那个主人公“黑小子”也是一个既悲惨又孤独的孩子,实际上也是童年时期莫言的自身写照。莫言13岁的时候,也像那个“黑小子”一样,为建桥工程的铁匠拉过风箱。虽然莫言在创作《透明的红萝卜》时取材于他本人的这段经历,但是,作为文艺作品,书中的主人公“黑小子”却并非完全就是作者本人,然而莫言与这个“黑小子”又是息息相通的。莫言以这个“黑小子”的人物形象塑造向读者展示了自己少年时代所经历过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和内心的孤独,并借助这个“黑小子”向读者展示了那个苦难的年代和处于苦难中儿童的最低心理诉求,因此评论界有人认为理解了“黑小子”也就理解了作家莫言。在瑞典颁奖时,莫言就直言道,的确在《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以后,虽然我描写了许多其他的人物,但是像这个孩子这样接近我的心灵的只有这一个。“黑小子”的父亲已经去世,继母却经常虐待“黑小子”,即使在深秋时节他也只能露着脊梁光着脚,身上的衣裳也仅有一件半截短裤。“黑小子”受了伤,继母也仅仅往其伤口上撒些灰土面就算了事。拉风箱时,那个痩小的“黑小子”的每一条肋骨都看得非常清楚,甚至人们都能看到他的心脏像一只可怜的小老鼠一样在跳动。黑小子就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以致于队长看到他时竟吃惊道:“你这家伙还活着呢。”“黑小子”就像路边的野草一样,任凭生活的磨难而顽强地生存下去。这种悲惨的生活境况成为形成莫言儿童乌托邦理想的伏笔。
大江《饲育》中的“我”和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小子”,不论他们究竟是谁,在他们的心中都对大自然抱有一种敬畏感。在大江的童年印象当中,就连森林也是有情感的生灵。实际上,《饲育》中的森林留给人们的敬畏感在日本由来已久。日本人对森林怀有一种崇拜感,他们把森林视为神仙停歇的地方,就连佛像也都是用木头雕刻而成的。因而,日本的宗教认为“神道原本就是森林的宗教”。
与大江相同,在莫言的作品中,自然界中的万物也都是有生命的。例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小子就具有感知自然界的能力,因而,在“黑小子”那个模糊不清的世界中,各种色彩、光线和诡异的图形不断地在“黑小子”面前涌现出来,尤其是在那透明和闪耀着金色光芒的红萝卜里面,“黑小子”却能够看到银色的液体在流动,还能够感觉到在水里面的鱼在亲吻自己的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少年时代的莫言与作品中的“黑小子”非常相似,他也十分孤独,陪伴着他的只有牛,牛成了童年时代莫言的知心朋友,因而莫言也了解牛的表情与情感。莫言还试图要了解鸟儿的叫声,与鸟儿沟通,但鸟儿过于忙碌,根本就没有理睬他,也只好作罢。但这种幻觉世界在后来莫言的作品中一直延续下去,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翱翔》中的女飞人、《丰乳肥臀》中能听懂鸟语的鸟儿韩、《月光斩》中树上那颗诡异的人头、《火烧花篮阁》中的神秘大火、《铁孩》中能够吃铁的孩子、《怀抱鲜花的女人》中那个神秘的女人、《战友重逢》中死去战友的地下世界和《生死疲劳》中人的六道轮回等作品,构成了日后莫言获奖时的“魔幻现实主义”,使莫言把童年乌托邦理想付诸于现实主义批判,构建了属于他的乌托邦王国,而莫言正是那个王国中的国王。
弗洛伊德认为,幸运的人们不抱有幻想,只有感到不满的人们才抱有幻想。愿望不能被满足是产生幻想的原动力。大江健三郎和莫言都是基于不幸的幼年经历,把自己的故乡作为乌托邦的背景,以童年印象开始实施自己的空想社会改良计划。
以童年印象叙事的方式写小说似乎难于有其确定性,但是却有其特殊的优势。儿童的内心世界一般说来尚未被世俗所污染,是相对纯洁的,因而能够不以先入为主的世界观来看待世界。作家对童年印象中的东西,不管是他所喜欢的还是厌恶的,都可以毫无掩饰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因而这样的作品就不会受到世俗利益的束缚,也不会被世俗的偏见所左右。在童年印象中,外界事物与孩子本人是相互融通的。儿童看到的世界中,万物皆有生命,都跳动着生命的音符。他们可以把星星的闪烁看成是星星在向自己眨动眼睛,可以把花儿的随风摆动看作是花儿在对自己招手。正是由于童年印象的世界中充满了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才促使大江健三郎和莫言两位作家在童年印象的感召下走上了文学的成功之路。
大江以“我”的目光来看待成人的世界。“我觉得大人们让我感到恶心、感觉让我恐怖,每当那时都把头扭向窗外。大人们在我睡觉期间,好像完全变成了其他的怪物似的。”[6]286-310在大江健三郎的童年印象中,没有大人的世界是那么美好。清晨,阳光照射到仓库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绚丽多彩的阳光里,孩子们可以静心地沐浴阳光、给睡在身旁的狗捉虱子而显得那么自由自在和悠闲自得。在孩子们内心世界里,童心就像坚硬表皮和厚厚果肉的里面的一颗种子,任何外部事物都不能对其构成侵蚀,即便是战争状态下也是如此。于是,天空中飞过的敌机对孩子们而言,也只是一种罕见的飞鸟而已;他们也不会把美国黑人士兵视作敌人,所以才会像对待自家的牛一样来饲养并与其和睦相处。在这些幼小的心灵中固守的只是那些梦境中清澈而又天真无邪的精灵。大江通过诸如此类的故事叙事,描述了一幅完美无缺的乌托邦社会景象,为读者引起苦难童年时代中尚存的快乐回忆。
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也具有这样的力量。通过“黑小子”的眼睛,莫言向人们展示了他那苦难童年中绚烂多彩的乌托邦社会的美好图景。在莫言的笔下,红萝卜是透明的,闪烁着金光,萝卜里面流动着银色的液体,其轮廓既光滑又优美,在美丽的弧形中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光线有长有短,长的如麦穂的芒尖,短的则如同睫毛。这些美丽的景色对于历经痛苦磨难的“黑小子”来说已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透明的红萝卜属于他,是他的希望,因为只有在透明红萝卜的世界里才充满希望的阳光。
三、全球化因素对两位作家的促进作用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起步较早,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日本国内获奖,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文学起步相比之下则较晚,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步入文坛,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两人在步入文坛的时间段上相差了将近30年,但是,两者进入文学创作高峰期却均处于文学全球化发展的成熟期,因而全球化因素对于两者之间的交流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互动关系。
诺贝尔文学的评奖原则要求把该文学大奖授予“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8]。“最佳理想作品无疑包括人类对理想社会所进行的文学构想与描述,因而有责任感、有作为的作家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其中必然包括对人类历史的反思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展望。”[9]大江健三郞和莫言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文学起步时期,将童年印象作为主要内容,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以儿童视角来看待故乡和描写故乡,表达出两位作家的“乡怨”、“乡情”与“乡恋”这种错综复杂的儿童心理情结,构建了两者的儿童乌托邦文学世界。
在不同的国家体制下,大江健三郞和莫言作为文化使者,为增进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文化互动,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大江健三郎数次访问中国,并对中国一直持有友好的态度,其很多作品已被译成中文,被广大中国读者所接受。大江健三郞从不否定文学家的政治责任,早在其小说《饲育》获得了芥川奖时就对报界明确表示:“我毫不怀疑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选择文学的责任。”[10]大江健三郞对日本“和平宪法”中“永不再战”持肯定态度就可见一斑。此外,大江健三郞一直在关注中国文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一生都在阅读鲁迅。”[11]19作为一位世界级文学大师,大江健三郞一直在思考作家的本质:“所谓作家,就是想象、构筑未来的人性——假设现在是21世纪的开始的话,那么就是想象、构筑21世纪中叶或是21世纪末的人性会是什么样。”[4]247莫言也曾访问过日本,其作品经日本翻译家藤井省三和吉田富夫等人翻译成日文,被广大日本读者所接受。在国内,莫言还多次与大江健三郞会面,交流创作的体会。对此,莫言认为:“此前是各人在自己的所在国写作,现在走到一起,促进了友谊,增进了相互了解,所以说积极作用还是很大的。”[11]21
就童年印象书写而言,大江健三郞和莫言之间也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才相互结缘的。在两人之间的对话中,大江健三郞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共性和他对莫言的赞赏:“小说家把自己童年的记忆加深,再加上自己的记忆和想象力,使得自身能够在童年的自己和成人的自己之间自由移动,这是小说家应有的能力。从这一点上,我看到了莫言先生作为小说家的特点,也看到了我们的共通性。”[4]221这一现象也正说明了文学全球化对于人类精神财富共享的正面意义。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是当今民族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而大江健三郞和莫言的文学之路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1] 兰守亭.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概观[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学林出版社,2006:371.
[2] 梅进. 我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EB/OL]. 科学网,2012-10-11.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 2012/10/270342.shtm.
[3] 胡铁生,夏文静. 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与莫言的自主创新[J]. 求是学刊,2014(1):127.
[4] 大江健三郎,莫言. 寻找红高粱的故乡——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对话[A]. 莫言. 我的高密[C].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5] 莫言.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代前言)[A].曹元勇主编.莫言小说精短系列[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1-12.
[6] 唐月梅. 获日本芥川奖作家作品选 [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7] 莫言. 超越故乡[A]. 莫言. 写给父亲的信:莫言作品精选[C].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8] 贾文丰. 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百影[M].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354.
[9] 胡铁生,周光辉. 论文学在文化强国进程中的软实力作用[J].学习与探索,2013(3):127.
[10] 全国文化资源共享工程网. 大江健三郞[Z/OL]. http://www.library.hn.cn/ztbk/sjdsr/ljds/200911/t20091110_ 2049.htm
[11] 铁凝,大江健三郞,莫言. 中日作家鼎谈[A]. 林建法. 说莫言[C].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张树武]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ldhood-Hometown Writing Between Kenzaburo and Mo Yan
ZHANG Guo-hua
(Foreign Language School,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32,China)
As winners of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both Japanese writer Oe Kenzaburoe and Chinese writer Mo Yan have witnessed the very similar way when they started stepping into the literary circle. The creative writing of their Childhood impression in their hometowns is the most common aspect in the two literary masters’ works. Though living in the quite different systems of society,they have stepped together with their concern of human nature. Generally speaking,the children’s inner world has not been ruined by secularity and is comparably pure,thus writers can observe the world without preconceived viewpoint so that it is more actively significant to create ideal world of children’s utopian.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the exchange between Kenzaburo and Mo Yan is beyond the personal relations. In the aspect of cross-reference and common development,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literary masters is more extensively significant in the practice of developing national and world literatures.
Oe Kenzaburo;Mo Yan;Childhood;Hometown;Globalization
2014-08-12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14B26);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CSC97822032)。
张国华(1958-),男, 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I0-03
A
1001-6201(2014)06-0166-06
——以大江健三郎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