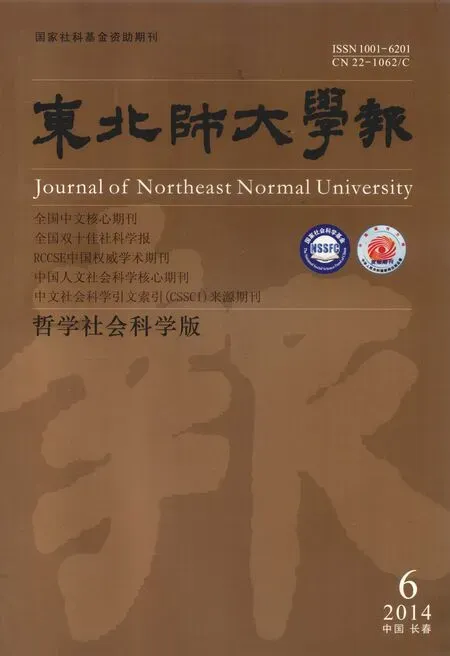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
田 慧 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
田 慧 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的气候治理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面临困境,即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却显著不足;二是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内容的气候治理由于自身特殊性引致的困境,即气候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导致全球气候进程停滞不前,暴露出现有气候治理全球机制的重大缺陷;三是中国自身存在的低碳转型能力和低碳外交困境。破解全球气候治理僵局,中国作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需要站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进行战略布局,平衡各方利益,增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意愿,通过灵活方式推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切实稳步推进中国的国内外经济战略。
全球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低碳经济;南南合作;南北合作
一、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的困境
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气候议程成为近20多年来全球范围内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多边进程之一。全球治理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机制安排,建立起全球性的运行规则,促使各国加强协调与沟通,共同解决全球经济中的负外部性问题。
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特征是“西方治理”,即以G8集团为核心的发达国家主导凭借国际机制或是国际机构(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精英俱乐部”之外,在全球治理中处于“被全球化”的地位。进入本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等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核心特征是从“西方治理”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20国集团“共同治理”转变[1]。G20的出现使新兴市场国家首次以平等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G20的经济总量(GDP)约占世界的88%,人口约占64%,基本覆盖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为南北国家共同应对全球重要经济问题的代表,G20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地位迅速提升,逐步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金融危机也催生了金砖合作机制,使得金砖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从边缘移到中心,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也推动全球治理向平等参与和互利共赢的民主型特征转化。
从经济实力看,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均衡,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人均GDP以及引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能力方面。金融危机虽然给美、欧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破坏美欧的经济基础。美国经济总量仍是全球第一,是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欧元区乃至整个欧洲、日本虽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比美国还大,但经济总量依然庞大,也还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
从贸易联系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基本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发达经济体与其他成员国之间普遍存在较高的贸易互补性,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之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德国和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指数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而新兴经济体内部的贸易互补性相对较低。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受总量上偏向中方的贸易不平衡而导致的对印度的心理影响,是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瓶颈性制约。中非贸易交流日益频繁,但文化价值观认同和理解仍常常引发矛盾冲突。因此,金砖国家间政策协调的有效性,更取决于微型多边机制下双边关系的发展。
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的困境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却显著不足。从微观层面来讲,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正在减缓,同时面临通胀风险、外部环境不利、“中等收入陷阱”逼近、资源和环境约束等种种挑战,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困境在于新兴经济体能否拥有长期增长的潜力。从中观层面来讲,新兴经济体参与的合作机制相对较少且成立的时间较短,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合作效果不太显著,进一步表现为集体身份认同的困境[2]。从宏观层面来讲,“北强南弱”的格局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变化,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表现为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等方面仍然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制于发达国家。
二、全球框架下气候治理的困境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是全球治理困境的典型表现。气候变化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失灵”,通过减少碳排放降低全球变暖的速度,这是全球气候治理努力的基本目标。气候作为一种特殊属性的全球公共物品,要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必须构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治理框架。首先,要明确各国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责任,并就减排目标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其次,构建兼顾历史排放责任和具体国情的减排成本分担和国际合作机制,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三可”的资金、技术及能力建设上获得发达国家的支持。这一过程的实质即是在全球有限的环境容量范围内,合理合法分配全球碳排放空间。
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各国的政策重心纷纷转移到恢复或稳定经济增长上来。美国复苏进展缓慢;欧债危机始终弥漫在欧洲上空;日本经济稳态低增长趋势难改;资源出口国的增长受制于商品景气行情;新兴经济体虽然有较大选择能动性,也面临减速调整。这使得气候问题在全球治理舞台上被暂时边缘化,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局。
自1990年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启动以来,随着各国对国家发展空间和碳排放权的争夺,以及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作为关键的气候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一进程遭遇到极大挑战,几乎陷入停滞,暴露出现有气候治理全球机制的重大缺陷。
一是现行国际规则的约束力难以协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利益冲突和立场分歧,无法满足全球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于1994年3月生效,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大法。现有国际气候治理尽管坚持了这一基本的合作框架,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各缔约国就具体的减排目标达成一致,但到目前为止,各国并未能制定出一份具有牢固约束力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协议。在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上,印度与中国希望延长京都议定书。欧洲希望实现一个自上而下的协定,而美国则希望通过自愿承诺和国内立法实现“自下而上”的治理。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下,欧盟将京都议定书延长至2017年,但加拿大与日本退出。中国和印度一直希望促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给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时间在不威胁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调整强制性减排承诺。而西方国家则希望中国尽快加入到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中,接受国际核查和监督,并以中国现阶段的降低碳密集度40%—45%的减排目标难以从外部监督为由,对中国的承诺不予认同。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上通过《议定书》修正案,从法律上确保了《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及俄罗斯已明确表示不参加《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地抱怨联合国机制的低效。尽管各国都根据国情设定自身相应的低碳发展战略和减排目标,但全球范围内的碳减排成效远低于期望值。联合国环境署(UNEP)2013年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已达到50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20年预计将达到590亿吨,比2012年估算的排放量又高出10亿吨。即使所有国家都兑现其雄心勃勃的承诺,到2020年,排放差距仍将在80至120亿吨(UNEP,2013)。
二是发达国家始终主导气候谈判的话语权,拒绝兑现资金及技术承诺。世界范围内低碳领域的技术和资金合作交流虽然已经展开,在加强气候变化合作、降低环境商品和服务贸易及投资壁垒、促进低碳技术转让和研发合作及官方发展援助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合作范围仍然相当有限。资金和低碳技术是发展中国家气候减缓、适应、损失和损害、技术开发与转让、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行动的基础和前提。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谈判意愿明显不足,并以各种理由逃避资金援助问题上的承诺。受知识产权、转移成本和风险、市场因素等影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技术转让始终无法实质推动[3]。2013年底结束的华沙气候大会再次显示了德班平台、资金和损失损害三大核心议题进展之缓慢。在兑现资金承诺问题上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出资意愿大幅减弱,美国、欧盟等也明显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能效技术及低碳能源技术创新方面拥有绝对领先优势,具有长期主导清洁能源行业的经济潜力[4],页岩油/气的成功大规模开采也大大降低了美国的减排压力,而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必然带来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并且面临低碳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巨大障碍。
三是多边气候合作机制正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当前的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和利益均衡,导致在气候谈判中大国与小国的矛盾凸现,同时并存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加中国”三股制衡力量,以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哥本哈根谈判成为新一轮全球利益分化和力量组合的分水岭。发达国家在策略上企图颠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强调中国、印度、巴西等基础四国的减排责任,并在资金援助对象国方面倾向于将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排除在外,谋求从内部分裂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加中国”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小岛国等由于更敏感于气候变化所致的海平面升高和风暴频繁,也开始对中、印等国家在采取减排和适当气候变化行动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四是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体数量和组织种类都有了极大的增长,但在制度层面,相互之间的协调以及实施非常薄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仍然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但气候治理也在其他平台上得以推进。2011年,OECD部长级会议将《绿色增长战略》定为首要发展战略;2012年墨西哥20国集团峰会把促进绿色增长列为会议的优先事项之一。除公民社会行为体外,跨国行动网络、私营决策机构、政府机构和公私伙伴关系等新型行为体也涌现出来[5]。从国际论坛到各种多边论坛,再经过各国间网络传播,最后连结各国的司法管辖区,如州、县、市。气候治理参与群体壮大,包括民间组织,金融和商业组织,甚至一些有影响力的演员和名人。从纵面来看,应对气候变化在许多国家的决策层面、企业的行动战略和公众的意识日益增强,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低碳绿色发展战略和行动,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但这些努力并不能归功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三、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困境
中国是世界上煤炭储藏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煤将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接近70%。中国经济增长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低效、对环境有害或者非社会公平的,排放量减低必将显著伴随产出的相应减少,要维持每年6%—7%的平均增长,当且仅当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来实现环境友好型增长时才可能实现。所以中国一旦在国际社会中承诺减排,压力将远大于其他国家。2000年至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同比增长120%,二氧化碳排放占比由12.9%提高到约23%。根据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全球碳计划”最新年度数据,中国已经成为2011年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尽管中国的人均排放与美欧日等国还有较大差距[6]。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气候博弈中将必然被赋予极高期望,同时面临更多挑战。
一是身份困境。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也越来越模糊,要求中国承担量化减排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提出雄心勃勃减排目标,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却远低于中国预期。发达国家一直希望中国能加入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中,接受国际核查和监督,而这恐怕在所难免。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一个重要策略是强调温室气体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这一策略正趋于弱化。中国目前年度人均排放量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未来的立场空间越来越小。
二是外交困境。当前中国主张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的立场空间正在缩小。发展中国家内部在碳减排问题上也开始分歧。如果集团分化持续下去,将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也将使中国陷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面夹击中。对中国的减排期待不仅来自于谈判桌上的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来自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中国至今仍缺乏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的经验,无法对国际非政府组织产生有力影响。中国气候外交的被动之处就在于,即缺乏稳固的同盟,又缺少愿意主动帮着中国说话的“朋友”。
三是贸易困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和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2012年5月美国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税率为31.14%—249.96%的反倾销税。随后中国风电设备也遭遇贸易壁垒,美国商务部于2012年7月27日公布要对多家风电企业征收高达20.85%—72.69%的倾销税。贸易政策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措施,却是有效的政治和惩罚手段。贸易壁垒措施小的方面看是为了把中国新能源产品阻挡在美国市场之外,大的方面考虑则是抑制中国在国际市场的拓展。
四是自主创新能力困境。首要挑战就是技术困境。中国低碳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而发达国家往往对低碳技术进行出口管制,并追求技术转让的完全商业化,即使转让成功,技术输出方也会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控制关键技术。以清洁能源为例,2013年3月6日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发布报告称:连美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究竟在哪里,而事实上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导者,美国处于领先地位是清洁能源技术,和美国企业在整体解决方案上的显著优势[4],全世界都在购买美国的技术和产品。中国在核心关键技术方面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能力显著不足且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近年来尽管国际专利的申请数量上升很快,仍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当中国向欧美寻求技术支持时,常被美国以技术多为私营企业所拥有、中方在知识产权方面保护不力、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无偿或低价转让。美国担心核心技术向中国出口会加强中方军事经济实力或出现民用技术军用化等“安全化问题”,也担心中国强大的模仿和自主技术升级能力会在技术转移后,还未从中国这个尚未实现的清洁能源市场获利,就被排挤出去。对于在众多低碳核心技术中,到底需要国际社会转让哪些技术来实现中国的既定减排目标,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技术清单”。
五是资金困境。中国的低碳发展存在巨大的融资瓶颈。仅能效投资需求,根据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的估计,“十二五”期间全社会能效投资需求总规模约为12 358亿元,资金缺口4 134亿元[7]。要实现中国到2020年要把碳浓度从2005年的水平降低40%—45%的国际减排承诺,根据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2013年最新预估,2015年和2020年中国每年气候融资的资金缺口分别高达12 219亿元和14 010亿元[8]。从资金供给面看,融资渠道狭窄。随着国际碳市场的资金来源渠道收紧,国内公共资金在气候融资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各商业银行也是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经济领域发展的主力军。但低碳项目往往存在较高的技术和资金风险,而政府提供的诸如风险补偿和税收减免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不足,加上金融机构对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关注优先于社会效益,使得低碳项目面临着较为严苛和不利的债权融资环境。此外,公共资金引导能力不足,财政担保和保险机制缺乏,难以撬动大规模社会资本的进入。创新型融资模式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金融机构的“碳金融”业务还处于概念和研究阶段,投资者对碳金融产品信心不足,也制约了低碳融资业务的创新。
总之,2012年以后国际气候融资市场的不确定性、国内金融市场法律政策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结构不平衡、金融创新能力受限等,使得我国国内的气候融资还任重而道远。
四、对策与建议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三重困境,一方面给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极大挑战,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重大机遇。对气候变化议题,中国应该站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来进行战略布局,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实现中国自身的低碳转型,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全球气候治理问题能否达成一致行动,有赖于各国是否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和有约束力的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时间不长,长期以来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更多的是处于接受者的角色。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对于外部环境的敏感度增加,中国需要适应时代潮流,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全球治理规则的核心制定者。全球治理既是中国的战略挑战,又是中国的战略资源。中国自身经济治理的成功来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改革。同样在全球治理中,作为南北合作G20平台与南南合作金砖平台的核心参与者,中国要争取从被动参与者成为主动塑造者,从规则接受者成为核心规则制定者,坚持有新兴经济体色彩的全球治理改革,使两个平台相互促进,相互借鉴,为全球经济治理寻找到一条创新型发展道路。
在全球层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不改变联合国谈判主平台基础上,中国可以积极利用多边区域谈判和其他的国际活动配合和补充气候谈判。
首先,G20国家的排放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而“金砖四国在G20中重要性日益上升,如果将重心转移到要为减排负主要责任的少数大国身上,针对内部主要的谈判方,增强共同合作的政治意愿,有助于共识的达成,同时也可以树立中国富有特殊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此,中国需要加强和拓展G20框架内的多种利益共同体。正确处理同美国、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欧洲和日本)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三个层面的关系。在不同GN之间,以及GN和G20之间发挥积极主动发挥中介桥梁作用,增强各国的政治意愿,有效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进展。
第二,中国也可以尝试建立一个包含中美欧在内的气候变化三方磋商机制,增强三方共同合作的政治意愿,缩小潜在的冲突和误解,形成中美、中欧、美欧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气候谈判多年进展缓慢的大背景下,随着双边对话的深入,中欧之间、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识和包容正在逐步增加,存在三方开展合作的空间。尤其中美之间在2013年取得重大突破。在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S&ED)框架下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负责确定双方在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而且在过去几轮对话中都没有突破降低碳排放量议题,在今年的第五轮对话中具体落实到五个重点合作领域,充分表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决心。
第三,在南南合作问题上,加大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力度。特别通过现有渠道或更多方式,在技术转让、项目管理和资金等多方面,给予南方国家更多行动上的支持,并通过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互开放市场,提升南南合作水平。也可以考虑建立南南气候与发展基金,鼓励发展中大国共同出资,给予较不发达国家更多支持,以身作则督促发达国家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承诺,提升中国的外交形象,巩固发展中国家联盟。
第四,创新合作模式,加强在非政府层面和公民社会层面的合作。比如与美欧等国建立规范化的民间对话平台。这个层面较少涉及政治,更多地与科学和专业相关,具有人道主义色彩,是较具合作潜力与可行性的领域。合作主体上,加强与国际、国内NGO的交流合作,建立起固定的NGO与政府交流平台和信息传递通道,让环境非政府组织成为中国气候政策的对外宣传平台,和倒逼国内低碳改革的“第三方”力量。
在国内层面,提升自身能力建设,扶持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从根本上推动国内经济转型。
首先,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扫除企业创新链上的障碍,建立跨境技术流动机制,搭建我国的低碳技术开发与转移平台,最大化低碳技术的溢出效应[9]。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优化国内外生产流程,提供清洁产品和服务,通过母子公司的联系和各种技术转让机制等方式促进绿色增长。
在供给层面,政府可以通过明确政策信号支持特定行业促进经济发展,完善环境立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国家间技术研发和传播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多双边磋商和对话,为气候有益技术的国际合作扫清障碍。在需求层面,企业是最终利润与风险的承担者,政府需要做的是制定保障政策,支持企业的自主发展和创新能力。可以运用公共财政手段,支持国内的基础和长期研究,并为新技术的开发、大规模扩散和推广提供有效激励。
其次,建立多元化的金融创新体系,加大对低碳行业和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国际层面,政府协助企业寻求更多替代性融资来源,尤其是国际发展低碳经济的资金资源,如全球环境基金(GEF)、绿色气候基金(GCF)、CDM等,并加快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等国际机构在低碳领域的合作。“低碳经济”正逐渐成为金融危机之后养老基金投资策略调整的一个新动向,他们正在与发展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密切合作,以确定具体的投资机会。国际风投VE/PE也开始盯住清洁能源行业。对此,需要加强政府官员的能力建设,积极培育中介机构,包括交易平台的培育和完善以及对参与碳金融的咨询、评估、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的培植,鼓励专业性中介机构参与其中,协助企业认知到这些潜在的国际替代性金融商品。
国内层面,一方面要加大对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进行政策性倾斜力度,鼓励商业银行将贷款重点投放于低碳生产、低碳改造、节能减排、循环利用的企业[10]。另一方面,建立“绿色通道”,鼓励和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应用企业进入创业板市场公开发行和上市,或设立减少碳排放的产业基金和面向节能减排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用于低碳企业生产发展的投入资金风险的防御,从而扶持低碳企业进入资本市场[11]。此外,积极支持创新型融资。比如对于一些大的新建项目如风力发电、余热发电等可以开展委托杠杆经营租赁。引导一些投资机构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对一些大型节能项目开展委托杠杆经营租赁业务。
总之,气候变化的步伐不会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受阻而放慢,降低碳排放,走低碳之路,是全球的大方向。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对外部环境高敏感,使得中国已经从全球治理体系的接受者向着体系的改善者甚至改革者变化。作为南北合作,同时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有必要构建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通道,促成稳定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并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原则的前提下,积极主动承担责任,通过灵活方式推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切实稳步推进中国的国内外经济战略。
[1] 黄仁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与金砖国家崛起的新机遇[EB/OL].中国改革论坛2013-10-09,http://www.chinareform.org.cn/open/economy/201310/t20131009_177619.htm.
[2] 王凯.新兴国家与全球治理:一种国际机制变迁的视角[D].山东大学,2012:42-43.
[3] 国际能源署(IEA).能源技术展望2010[R/OL].IEA REPORT,http://www.iea.org/techno/etp/etp10/Chinese_Executive_Summary.pdf.
[4]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 Advantage America: The US-China Clean Energy Trade Relationship in 2011[R].Pew Charitable Trusts Report,2013-03-06.
[5] [英]戴维·赫尔德,安格斯·赫维,谢来辉. 民主、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J].国外理论动态,2012(2):63-68.
[6] 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UK Tyndall Centre). 维持全球升温低于2℃的挑战[R]. 自然·气候变化专刊(Nature Climate Change)201203.
[7]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低碳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5.
[8] 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策略[EB/OL].气候组织,2013年3月,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3-04/01/c_124525232.htm.
[9] 杜国辉,田慧芳.中国低碳转型的困境和思路[J]. 绿叶,2012(12):26-28.
[10] 郭沛,张曙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基于2002—2010年面板数据的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5-49.
[11] 杜晨妍,李秀敏.论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27-30.
[责任编辑:秦卫波]
China’s Triple Dilemma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TIAN Hui-fang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China’s climate governance is facing a triple dilemma: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is deadlocked;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global clirmate governance is experiencing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 due to its particulates;in addition,China is confronting heavily challenges in its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Breaking the dilemma,the Chinese need to stand to new heights,with a broader perspective to re-examinc the issue or climate security strategy,through indirect and creative approaches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nd enhance the major economies’corporation willingness i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and furthermore by increas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to become the core of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of global governance process,thus striving to achieve China’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Global Governance;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Low-carbon Economy;South South Cooperation and North South Cooperation
2014-03-02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重大项目(2014YCXZD008)。
田慧芳(1977-),女,山西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F113.3
A
1001-6201(2014)06-00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