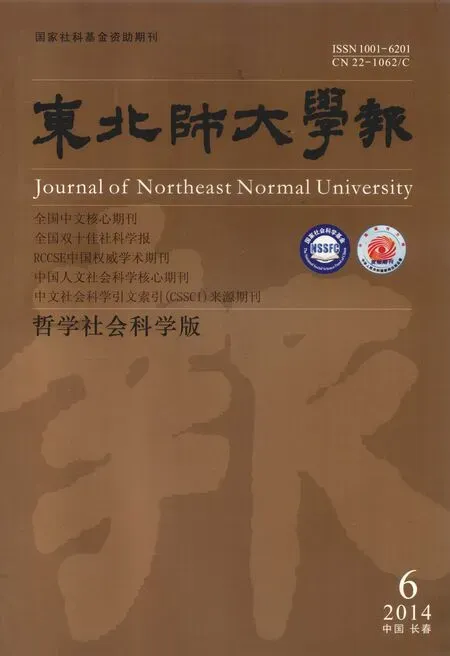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改革的制度选择与发展反思
王 晶,杨小科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2.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改革的制度选择与发展反思
王 晶1,杨小科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2.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基层医疗服务供给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在市场化社会中,基层医疗机构变为逐利性的市场主体,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性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问题。而在当前社会结构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受到行政体制的严重制约,造成基本功能萎缩。在进一步的基层卫生改革中,需要重构政府、市场与供给者的关系,探索有效的激励机制。
总体性社会;市场社会;行政社会;基层医疗服务
一、引 言
基层医疗服务不仅需要从医疗服务体系自身去梳理,更需要从基层医疗服务所嵌入的社会制度中去考察。特定历史背景下,一种社会制度直接主导了基层医疗服务的传递形式,本文对80年代以后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改革路径进行考察,分析基层医疗服务制度的演变逻辑,同时反思医疗卫生制度背后的社会治理问题。
王春光等曾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进行了一个理论上的划分,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改革后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市场社会和21世纪初的行政社会。在总体性社会下,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稀缺的资源和结构性的社会活动空间,而社会、市场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制度性空间[1]3[2]。在市场社会下,市场被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国家将一些公益事业、公共服务交给了市场来解决,放弃应该承担的公共职责和功能。而到了行政社会,政府一方面放权于社会,另一方面不希望丧失行政动员能力,因此,在政策选择上左右摇摆,触角经常伸向社会各个角落,模糊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分工和合作,削弱社会联系的纽带、社会共同体的自主性和自治能力。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对我们分析基层医疗服务制度变迁非常有价值,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基层医疗服务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传输到民众,基层医疗服务的资源如何配置,这样的服务供给和资源配置如何与当时的社会制度扭绞在一起是本文希望挖掘的问题,同时对于当下如火如荼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也有反思价值。
二、“市场社会”下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
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革命性的政治动员机制,保证了合作医疗资金得以有效筹集,同时也保证了基层医疗服务供给可以借由半农半工的赤脚医生实现低成本供给[3]。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始以户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与农产品经营,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制形式均已解体,农村集体经济不复存在。传统的合作医疗制度主要依赖于人民公社集体的动员能力才能实现最大范围的筹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合作医疗制度大范围的土崩瓦解[4]。同时,原有体系下的赤脚医生转化为新体制下的个体开业医生。个体开业医生与原来的赤脚医生在性质上具有本质的差异,赤脚医生的工资来源于集体经济收益,而个体开业医生的收入来源于自负盈亏的经营收益。90年代之后,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乡人口剧烈流动,城市打工人群的收入已经超过了部分乡村医生的收入,乡村医生的数量开始大量降低。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随着人口大量外迁,留守农村的人口越来越稀少,因此不少乡村医生放弃了子承父业的世家经历,成为一名普通的农民工。
而对于留守农村的乡村医生来说,如何维持生存也是一个挑战。传统的赤脚医生与村民之间是处在“熟人关系”的乡土社会之下,人与人之间具有朴素的信任关系,村民与乡村医生之间看病赊账现象很是普遍。到90年代以后,赊账现象也拖垮了一部分乡村诊所。从资金链条上来讲,乡村诊所面对的服务对象少则一个村,多则不过数个村的村民,达不到一定的就医规模。而政府对乡镇卫生院的补贴已经寥寥无几,更不可能覆盖乡村医生一级。在2003年之前,可以生存下来的乡村医生大都是子承父业的中医,在给农民看病的同时也兼卖药勉强为生。2003年以后,情况有所改观。2003年政府开始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实行门诊账户和大病统筹的筹资方式,在基层采取“定点诊所”的管理制度,门诊账户的资金只能在定点诊所进行消费,农民看病费用只有在定点诊所消费才能报销,所以在2003年以后基本实现了一个行政村一个诊所,原来没有诊所的行政村,也聘用了新的乡村医生。2008年笔者在河南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乡村医生为了得到定点诊所的指标,甚至不惜以贿赂的形式获得政府的指定,而实际上部分乡村诊所设立以后,由于医生的诊疗水平和经验不足,也仅仅是起到了卖药的功能。但是无论如何,乡村卫生室从80年代的衰落,到2000年以后的重新恢复,毕竟是一个良性的过程。特别是对边远山区来讲,乡村卫生室的设立,对于农民看小病节省了高昂的交通成本。
除了村卫生室之外,乡镇卫生院是农民就医最常选择的基层医疗机构。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中,乡镇卫生院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一方面乡镇卫生院需要对所覆盖的人口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乡镇卫生院负有对村级卫生机构进行业务指导的责任。在80年代以后的市场化浪潮中,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名义上是公立的事业单位,但实际上已经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主体,政府仅承担部分编制内人员的基本工资,如案例1所示,部分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仅能按照差额支付部分医务人员的基本工资,乡镇卫生院的生存完全靠自身是否能吸引足够的病人,是否能够激励医务人员开大处方、多做检查,最大限度的实现创收,以此来维持乡镇卫生院的正常运转。
案例1:一个乡镇卫生院的两次差额
克什克腾旗SY镇乡镇卫生院位于克什克腾旗高速公路旁,交通较为便利。该乡镇下辖6个村,覆盖的人口为2 000人。当地的财政经费预算只保工人工资,当地财政按卫生预算的80%拨款,卫生院再按70%发工资,工人实际到手的工资只是应发工资的56%,也就是说实际上1 600元的工资,医务人员能领到手的只有900元左右。卫生院集中了的30%工资差额,卫生院利用这笔资金建立了一套内部绩效工资制度,卫生院内部确定的考核指标,其中包括医务人员承担的工作数量、医务人员的工作业绩等等,总的说来,能为医院创收多的员工自然获得了较高水平的绩效工资,相反可能获得很低、甚至得不到30%的绩效工资。这套指标的设立对医务人员的激励机制起到很重要的导向作用,在我们调查的SY镇乡镇卫生院分院*SY镇卫生院目前设立了一个总院,一个分院,总院的位置还在原来的永胜村内,分院设立在乡镇内。分院的经营规模远大于总院,实际的技术骨干都已转制分院。因此虽然挂名总院,实际上已经变为乡镇卫生院的分院。,医务人员一直对80%的70%耿耿于怀,因为分院的业务量少,因此收入水平比总院要低,所以2009年在分院工作的几名员工基本没有获得这部分差额的工资。
实际上,在整个90年代,整个乡镇医疗卫生体系已经从六七十年代的公益性质转变为功利性质的牟利性组织,在农村缺乏完善的医疗保障的背景下,最后承担医疗成本的是最基层的农民。在市场社会时代,资源配置注重效率而非公平,地方政府实际的资源配置方向扶强不扶弱,越是能够适应市场发展的组织,地方政府越有动力去扶持其成长,而越是在市场机制下发展不足的组织,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自生自灭的一种态度,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这是造成基层卫生机构发展先天不足的根本因素[5]。在这种背景下,乡镇医疗机构能力发展不足,导致居民无论大病小病,都倾向于向大型医疗机构就诊,大型医疗机构人满为患,而乡镇卫生机构门可罗雀。随着大型医疗机构的膨胀,越发有充分的理由向地方政府要求更高的财政补助额度,由此在医疗服务市场内部,大型医疗机构与政府财政投入之间造成了一种捆绑式的螺旋上升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速度远远被甩在专业医疗机构之后,这个问题是造成新医改中基层卫生改革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
三、“行政社会”下的基层医疗服务
历经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2013年,中国GDP达到了9万亿美元,跃居世界排名第二位;城市化率达到53.73%[6]。从经济指标上来看,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快速的经济发展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是同样剧烈的,2013年,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7[7],已经濒临警戒线的水平。2009年课题组在贵州进行调查发现,虽然一些县平均下来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是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仍然堪忧,教育和医疗是农民最大的两项支出,一旦家人患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还是相当突出。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经提出,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可行能力”的贫困,而所谓扶贫,不仅仅要扶持农民摆脱被动贫困,更要构建平等的社会服务设施和社会保障水平,使农民能够获得公平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本文主要关注点在基层的卫生服务,单从卫生投入上看,2000年以后,政府确实在不停地调整政策方向,从2003年构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09年推出医疗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新一届政府正在逐步从原来的市场社会下放任自留的粗放社会治理模式向以民生为中心的柔性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摸索。
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补偿机制是触动基层医疗机构变革的核心动力。在新医改方案中,政府对于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即保障其“公益性”,在手段上政府希望采取“收支两条线”的行政办法,进行严格的预算管制,控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营利性动机[8]。这种维持公益性的做法,体现了政府重新扮演起基层医疗服务筹资和供给的责任。但是从目前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的发展情势看,实际的发展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新医改之前,农村的乡村医生都是游离在正规体制之外,依靠业务收入和药品加成收入维持生存。依据医改的方案,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财政能力给予乡村医生补贴,以贵州省务川县为例,2012年县级财政设定补偿标准,乡村医生财政补贴400元,基本药物补助417元。切断药品加成后,村医每月基本的工资收入为817元,年终公共卫生一次性奖励补贴1 200元,一个村医在农村从事医疗服务的年收入为11 000元,这一收入水平远低于未实行医改之前的收入水平,大部分乡村医生的收入降低了一半以上,与城市农民工群体相比,乡村医生的工资并没有优势。对于乡村医生来讲,如果制度环境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有一条“用脚投票”的退出机制。
在行政社会下,地方卫生机构对于乡村医生具有很大的管控权限。首先,在设定合作医疗定点机构时,执行上级任务效率高的乡村医生更有可能获得合作医疗定点的指定,因此乡村医生的业务表现往往成为是否能够获得指定的重要考量;其次,在农村,私人医生没有行医权限。在乡村行医的都是非体制内的乡村医生,他们的业务标准低于职业医师。地方政府每5年会根据地方医疗需求,委托培养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在地人才成为乡村医生,颁发乡村医生资格证。但乡村医生资格不同于职业医师资格,法律上不允许开立私人诊所。乡村医生资格证只允许在所在地从事医疗服务。医改之后,这一规定变得更为严格,部分地区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一个行政村只允许设立一个村卫生室,2—3个乡村医生联合办公,接受合作医疗报销,执行基药政策。不希望受政策约束的乡村医生如果继续行医,则属于非法行医,卫生监管部门有惩处的权力,这是地方卫生部门控制乡村医生执行医改计划的第二道法宝;第三道法宝是资金控制,在贵州某县调查时,乡村医生每年要向政府交保证金,保证金额从5 000—10 000元不等,如果村医在家诊疗*按照地方卫生要求,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之后,村医需要在卫生室进行诊疗,诊疗用药为基药。、不采用基药、没有完成公共卫生工作量,管理部门将从保证金中适度罚款。有了这样的一个自上而下的集权性的控制手段,想要在乡村继续从事农村卫生的乡村医生只能被动的适应体制,这样的制度约束也招致很多乡村医生对现有改革体制的不满。
案例2:道真县某村卫生室
原来村里有6个村医,合并后没资格行医了。后来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通过考试剔除了一部分乡村医生,现在石笋村只有两个正式的村医,能拿补贴,剩下的医生行医都属于非法行医,他们有乡村医生资格证。这些人有的实际上还在偷摸看病,自然村之间距离的比较远,单独靠这几个村医集体办公不可能解决问题。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解决不了。合并之后,看病的人比以前少了。政策规定村级门诊不超过20元,输液不超过40元。来村卫生室看病的主要是小病、中年人。老年人大都出去看病。现在来村卫生室看病的大概就占患病人数的一半,一半在这看,一半去农村个体医生看(非法行医)。一个月大约有100多个病人,40—50个在卫生室这里看病,还有40—50个在个体医生那里看病。
在切断了药品收入之后,要求乡村医生向公共卫生服务转型,必须在支付方式上进行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相比,依赖政府补贴维持生存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两种不同的支付制度对于乡村医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激励,在市场体制下,乡村医生的激励在于多诊断,多卖药,多赚钱;但是在医改的逻辑下,乡村医生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其公共性,而非医疗本身。目前乡村医生的公共卫生经费总体偏低,地方卫生机构对乡村医生给予了相当多的任务,比如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慢性病监测,每月定期回访等等,这些任务如果严格地按照条文上规定执行,成本是相当高的。在贵州这样的山区,服务半径远远超过平原地区,乡村医生的工作量巨大。从目前情况来看,乡村医生建立健康档案、进行慢性病监测已经占据了乡村医生相当多的精力,但是据我们实地了解的情况,即便如此,一个乡村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单单依靠一两个乡村医生目前的工作力量还不足以覆盖全部人口,更何况现在公共补贴力度不足,乡村医生在执行公共卫生任务时还可能有投机取巧的行为,实际公共卫生服务力度远远不足。
案例3:道真县ZX镇卫生院
公立医院改革之后,乡镇卫生院的收入明显下降了,从2009年的170万下降到2010年的110万元。合作医疗的结余资金较多,2010年的结余是80万,2011年的结余是60万元,报销门槛提高,所以报销少了。乡镇卫生院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才缺失。2007年正式医务人员27人,2012年只有12人(其中有一个还是长期生病的,实际是11人)。2011年调到上一级医院的有6人,分进来2人,退休2人。乡镇卫生院现在一共有15个人。正常能看病的中级职称医师只有一个。现在乡镇卫生院又回到了老三件的状态,有设备,没有人才也不能用。B超、心电、血常规都没有人做。比如以前乡镇卫生院可以做下腹部手术,比如阑尾炎在乡镇卫生院做,600—700元,报销后也就200—300元,现在到县医院,总费用3 000多,报销比例降低,个人还是得出2 000多。现在麻醉和影像人员没有,就不能再做了。老百姓也觉得乡镇卫生院技术水平差,有大一点的病就往县上跑。现在乡镇卫生院的主要业务是治疗伤风、感冒等小病。
对于基层乡镇卫生院,医改的主要决策有两点,一是“药品零差价”,二是“收支两条线”。两个决策的一个核心点在于恢复乡镇卫生院的公益性,降低农民看病费用。从我们调查的贵州省两个县的情况来看,医改对于两个县的影响有所不同。A县经济状况在整个市处于较低水平,执行医改政策并不严格,因此在药品零差价和收支两条线管理上都有一定的折扣。一旦实行药品零差价,医院不再能从消费者身上收取15%的零差率,那么政府必须对于乡镇卫生院补齐15%以上的零差价的差率,但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政府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对乡镇卫生院给予补贴,这是问题核心所在。在贵州省的B县,经济条件处于中等水平,卫生部门执行医改的决心较大,在2012年所有乡镇卫生院推行了药品零差价的政策,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收入和支出彻底脱钩,在政策细节上甚至规定了乡镇处方不超过30元,输液不超过50元。执行一年后发现乡镇卫生院出现了功能性衰退,乡镇卫生院一年住院人次和门诊人次下降了36.5%。
综合来看,医改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促进作用有限。影响农村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因素有很多方面。首先,医改之后,政府重新成为基层卫生资源配置的主体,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定了很多行政指标。西部很多县级医疗机构能力薄弱,人力资源匮乏,但是为了完成政治指标,部分县级地方卫生机构采取了杀鸡取卵的办法,从乡镇一级调人才成为不二之选。在我们调查的几个县内,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上级卫生机构倒吸下级卫生机构优秀人才的局面。不仅如此,上一级卫生机构吸纳的人才还经常占用下级医疗卫生机构的编制,影响下级医疗卫生机构招聘新人。乡镇医疗卫生资源本就匮乏,一两个骨干医生通常就是一个乡镇卫生院的支柱,从乡镇卫生院抽取人才无疑对农村基层卫生资源雪上加霜。在一个县医疗卫生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如果改革的重点放在县一级,而非乡镇一级,那么乡镇一级的资源可能就被逐步抽空,这是乡镇医疗机构功能性衰退的外部因素;第二个因素在于支付制度的改革,原来的市场体制,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倾向于按项目收取治疗费用,多开药、多检查就能增加医院利润。“收支两条线”的改革,要求乡镇卫生院必须使用基药,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工资与收入脱钩,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因此乡镇卫生院业务量降低、收入减少与医生的激励机制有密切的关联。三是基层社会信任的缺失,按常理讲,越接近基层的医疗机构,应该越容易与病人达成共识,减少医患纠纷的可能性。但是当下,医患纠纷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少乡镇卫生院因为一个患者的误诊,经常要动用县一级卫生权威机构介入才有可能解决,巨额赔偿也是乡镇卫生机构难以承受的。因此,正如案例中所示,原来可以在乡镇卫生院进行的一些小手术,现在乡镇卫生院也关闭了这样的业务。稍微严重一些的疾病,就建议病人转诊去大的医疗机构,造成县一级医疗机构人满为患。
四、总结与讨论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是关乎百姓安危的准公共产品。西方福利国家中,基层卫生服务始终是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支柱,社区医生充当医疗体系守门人的角色,而政府的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对基层卫生服务进行购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也在不停地进行着调整,比如传统的北欧国家是医疗服务供给最公平的国家,但是医疗服务带来的高成本已经使得整个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80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国家开始大力裁剪社会福利公共组织。但是在福利收缩的浪潮中,福利国家财政投入并没有大幅度缩减,而是投入到了非盈利性的组织,政府从直接公共服务供给者的角色退出,转而扮演公共服务监督者和筹资者责任[9],从而使得医疗服务供给走向一种“福利混合经济”的格局[10]。
中国过去30多年中治理模式经历了数次的变革,8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被推向了市场;2000年以后中央政府提出“社会建设”,把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重新纳入政府财政范畴。通过对基层医疗服务的梳理,基层医疗服务的供给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一切,普通民众可以获得低水平的医疗服务供给,由于政府资源有限,短缺现象普遍存在;到了市场经济社会,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基层医疗机构演变为逐利性的市场主体,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性问题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问题。当下,中央政府希望重新承担起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并在管理模式和资源配置机制上进行创新,比如“收支两条线”的财政体制。政府虽然没有直接地扮演起服务供给者的角色,但是无疑行政性的官僚机构重新成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核心。
那么为何中国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始终不能摆脱“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两端,而走向一种混合福利的模式,使得基层卫生服务提供者能够成为基层卫生服务的真实主体,并在激励机制上朝向公共卫生服务进行转型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始终是中国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没有摆脱的桎梏:一是政府的职能定位。当下,政府虽然有放权于社会的需求,但是传统的制度惯性,使得政府依然在政策选择上左右摇摆,这一点正如王春光[1]3所言,政府自身模糊了与社会和市场的分工和合作,削弱了社会主体自身的主动性,由于政府的强大,社会力量习惯性地成为政府的附庸。在基层医疗服务上也是如此,主要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基层医生希望成为编制内的主体,他们的核心关注点并不在于提供多少基层医疗服务,而在于如何成为制度内的员工,获得稳定的收入。当下的财政激励机制并不是激励社会服务主体自身发挥其基本的潜能,去满足社会成员的医疗需求;而是激励社会服务主体去社会化,向准官方机构转型,获得稳定的财政投入。
除此之外,中国城乡二元的发展模式虽然正在逐步瓦解,但是20多年的发展模式已经使许多服务制度定型化,比如城市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者是社区医生,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就是乡村医生,二者在资格准入、工资福利上截然不同,地方政府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基础设施投入远高于农村地区,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相比城市社区医疗服务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平等问题。当下中央政府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县级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从客观经济水平上难以实现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来讲,政府虽然已经提出了基本的政策目标,必须在财政资源上进行相应的倾斜,才有可能使得这些公共服务项目落地。
最后,医疗保障制度与基层医疗服务紧密相关,医疗保障水平决定了居民利用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居民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面对专业性的医疗服务机构始终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是被动的医疗消费者。发达国家卫生体系改革正在逐步扭转这种局面,以英国的国民保险系统为例,国民保险系统(NHS)是购买服务的身份,相对于医疗机构具有对等的地位,这样对基层医疗机构既能监控其资源利用是否合理,也能确保其为居民提供公平的医疗服务[11]。而我国当前的医疗保险系统还存在着诸多的弊端,首先一点是医疗保险的水平还较低,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合作医疗报销的比例尚不足农民医疗支出的20%;其次,医疗保险机构并没有承担起消费者代理人的角色,对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仅仅是被动埋单,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反倒是政府资源对于基层医疗服务供给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这一点上来讲,在构建基层医疗服务供给机制中,未来不仅要理清政府、市场和服务供给者的关系,同时在组织结构上更要理清政府、保险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供给关系,唯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才有可能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王春光等. 社会现代化:太仓实践(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 孙立平. 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J]. 社会学研究,2011(4):22-32.
[3] 顾昕. 当代中国农村医疗体制的变革与发展趋向[J]. 河北学刊,2009(3):1-6.
[4] 朱玲. 政府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选择[J]. 中国社会科学,2000(4):89-99.
[5] 刘民权,李晓飞,俞建拖. 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及其公平性探讨[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3):23-33.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M/OL].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3/indexch.htm.
[7] 何敏. 统计局: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R/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1-20/5754910.shtml.
[8] 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2009[R/OL],http://www.nhfpc.gov.cn/tigs/s3576/201309.
[9] 顾昕,公共财政转型与政府卫生筹资责任的回归[J].中国社会科学,2012(2):103-120.
[10] [英]鲍威尔. 理解福利混合经济[M].钟晓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14.
[11] Le Grand, J.Competition, Cooperation, or Control? Tales from the 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J].Health Affairs,1999,18(3): 27-39.
[责任编辑:秦卫波]
The Reflect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Choi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Reform in Rural China
WANG Jing1,YANG Xiao-ke2
(1.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2.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China)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rural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 in China, the paper found rural primary care delivery affected by mode of governance. In market society, market mechanism is the crux principl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primary health institutions became profit-driven entities, which generate a seriously inequity problem. While under the current social structure, the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 seriously hampered the capacity of primary health system, which led to basic dysfun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ucture the relationship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upplier, and explores an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Totality Society;Market Society;Bureaucratic Society;Primary Health Care
2014-09-28
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CSH065)。
王晶(1980-),女,吉林四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博士;杨小科(1983-),男,河南济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师,博士。
C913.7
A
1001-6201(2014)06-006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