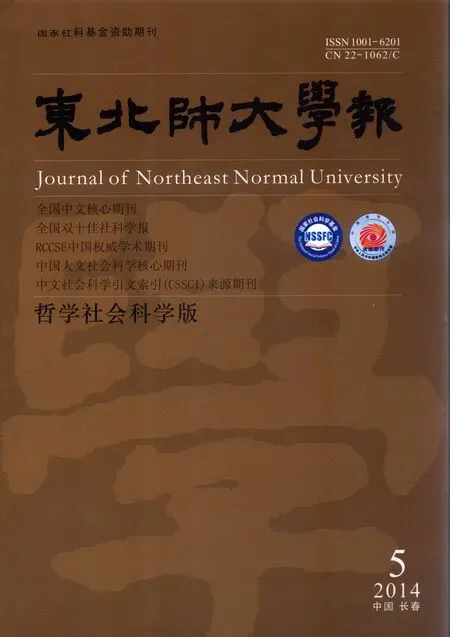美国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政策论析
宋银秋,董小川
美国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政策论析
宋银秋1,董小川2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发动了以“强制性”为主要特征、旨在“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同化教育运动,并出台了强制同化教育政策。强制同化教育政策的本质是文化侵略和文化毁灭,它违反了道义及文化多元的客观规律。其失败说明民族教育应认同各民族文化的自身价值,要兼顾民族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赋予群体传承民族共有精神财富的功能,以实现各民族的持续发展。
印第安人;强制同化;唯英语教育;民族教育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西进运动已近尾声,被赶入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也放弃了反抗,白人得到原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联邦政府思考的新问题是:如何同化这些原住居民。鉴于印第安人难以自愿接受白人文化,只能强制同化他们,将他们早日塑造成具有白人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文明“红”种人。强制同化的第一步,打破印第安部落土地的公有制,依据《道斯法案》将土地按份分给他们经营;第二步,强制同化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因此,强制教育政策本身是与该时期以强制同化印第安人为目标的一系列政府政策相辅相成的。
一、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政策内容
美国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政策是印第安人事务署署长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提出的,以“印第安人教育补充报告”(SupplementReportonIndianEducation)的形式递交美国国会通过[1],其内容概括如下:
印第安适龄儿童和青年(6—16岁)共3.6万人(不包括五大文明部落和纽约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下一代智力水平与白人儿童存在悬殊差距,为文明开化这些野蛮儿童,使他们成为合格美国公民,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教育的责任方是联邦政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强制性措施,推行全体性教育和“唯英语”教育;加大对保留地走读学校、保留地寄宿学校及保留地外寄宿学校的投入,大力兴办保留地外寄宿学校,将校舍确立在远离保留地的白人农耕区,保证学生与白人文明的融合;保障充足的教育经费,以建造和维护校舍,购买办学设施,聘用教师,满足学生的膳宿及其他费用等;统一教学大纲、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材及工业实训体系;教育学生热爱美国国旗,灌输真正的爱国主义,让学生明白美利坚合众国而非不足称道的保留地才是他们的家园,培养学生美利坚公民权利、责任及义务意识。
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必然性。印第安事务专家一直普遍认为,学校是彻底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印第安人事务署试图通过将寄宿学校的学生培养目标由纯知识、智力型,到半知识、半实用型,到最后纯粹实用型的转变,唯英语教育目标由习得英语,既英语的听说读写综合能力的培养,到作为一种职业技能培养的转变实现同化教育目标。印第安人是否能够找到令他们满意的合同条款并不重要,作为蒙昧的人,他们没有能力决定什么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印第安人会接受他们施恩者的智慧。当时的印第安人政策制订委员会对同化教育的作用信心十足:“让印第安人能够充分享有教育的恩惠,并藉此快速走出数世纪的无知。”[2]
二、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政策的失败
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运动始于1877年,止于1928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77到1897年;第二个阶段从1897到1928年。从1877年,美国政府开始为同化印第安人的教育年度拨款,并研究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但成效甚微。1901年,时任印第安人事务署署长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其年度报告上指出[3]:政府在1877—1897年间为强制同化印第安人进行的一切努力和投资均未见成效,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政策是失败的;第二阶段,琼斯报告并未阻止美国政府继续推行政策的脚步,也未促使政府及时审视和研究出现的问题,而是任由事态的发展。直至1928年,政府才组织了梅里亚姆小组调查情况,《梅里亚姆报告》[4]终结了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政策。至此,强制同化教育时期基本结束。
强制同化教育政策的实施主体是保留地外寄宿学校,它展现了美国联邦政府欲彻底重构印第安人思想和个性的决心。这种努力是在印第安儿童离开熟悉的部落生活方式,奔向白人学校陌生世界的那一刻开始的。印第安儿童被保留地事务官和校方以欺骗或行政压制等手段强制带离家乡,到校后他们的文化身份被剪发、换上统一白人服饰、更名、改变饮食习惯、接受时间观念等方式强制剥夺。由于白人社会坚信英语是将印第安人带入文明世界的主要工具,唯英语教育被当作最有效实现印第安同化教育目标的途径。因此,保留地外寄宿学校实行了强制性唯英语教育,严格要求学生在校期间不得使用印第安语言。
当然对印第安人事务专家来说,印第安儿童步入寄宿学校的旅程是走出蒙昧的黑暗世界,走向光明的文明世界的第一步。玛贝尔·纳尔丁(Mabelle Nardin)在“语言是同化印第安人的屏障”一文中声称,“美国社会必须同化印第安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同化印第安人。”[5]但对大多数印第安青年人来说,这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他们离家的时刻、去学校的途中、步入校门之后的生活和学习,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所有事情让他们恐惧、困惑和愤怒,他们甚至强烈反抗。白人给他们的文明教育在白人看来是恩赐,但在他们眼中完全是一种强加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并未给予话语权及选择权。唯英语教育要实现的是通过语言教育的专断将白人的价值体系强加给印第安人,唯英语教育政策本身说明了语言的政治性及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语言的控制是实现政治和文化剥削的重要工具,强制推行唯英语教育势必会削弱土著印第安人独立自主的权利,势必将加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所谓公信力和日常事务的管理力度。以同化为核心的语言政策在剥夺土著人语言权利的同时,破坏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6]。
三、对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政策的批判
强制同化教育政策对印第安儿童的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产生重要影响。在接受同化教育过程中,印第安儿童不自觉地受到白人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并因此获得新态度、价值观、技能、偏见、愿望和行为习惯,这些印第安人儿童成为印第安人文化变迁的原动力及文化同化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上寄宿学校是学生对“印第安人身份”扩大的感知。在卡莱尔和哈斯克尔,苏族学生通常会与科曼奇族和纳瓦霍族学生建立亲密的联系[7]。在谢尔曼,霍皮族学生与卡惠拉族和塞拉诺族学生同吃,同住,同时上课,一同玩耍[8]。在这种同质教育中,印第安人明白了,“伟大的父亲”并不给部落区别留有任何余地。近50年的同化教育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
(一)渐进主义者对政策的批判
早期社会改革家观点激进,认为在白人的监护下,印第安人能够在一代人之内跨越蒙昧与文明之间的差距。而20世纪初期在美国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渐进主义思想则认为,同化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代表人物弗朗西斯·路比(Francis Leupp)指出,“我们总是对印第安人抱有太多的期望。学生的故态重萌说明,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种族性不可能在一天、一年,甚至数年里消除。横跨野蛮和文明的鸿沟需要时间,部分上由于这个民族所具有的原始品质是全人类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共有的特性,部分上也是由于遗传的心理和道德特征。”[9]希洛克寄宿学校校长麦考恩(McCowan)如是说,“印第安人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明白我们的文明。如果不懂,他们就不可能欣赏它,也就不会跟从它。”[10]麦考恩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盛行的渐进主义观点:印第安社会进化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二)白人社会对政策的批判
进入20世纪,白人社会对强制同化教育政策的反对呼声不断高涨,认为它鼓励了依赖性。一位寄宿学校参观者评价道:一大群舍监、厨子、缝纫工细心呵护着这些顽童,他们享受着电灯、冲水马桶、暖气等现代文明产物,享受着体育、音乐和其他各类文明活动。署长琼斯指出,“不需要自己和自己民族的丝毫努力,学生们就享有了这一切。事实上,印第安青年是当代的阿拉丁,只需不断擦拭政府的这盏灯即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11]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们教育结束。对比之下,回到家的他们发现自己的家是那样的污秽,所受的教育让他们再也无法以自己的父母为荣。他们多数仍住在保留地,但他们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为下一代要更多的教育资助,要政府派更多的农民及机修人员上门服务,较比政策实施前,他们向独立的目标迈进了一小步,但与政府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相比,进步甚微。
(三)教育家对政策的批判
通过研究,著名心理学家、儿童教育家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发现,原始社会有许多值得称赞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里,年轻人对自然生长和体力活动的冲动能够得到合法的实现。霍尔认为,对印第安儿童施行的强制同化教育是极其残忍的,是有悖于儿童的天性及认知规律的。霍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将他们培养成良好的印第安人,而硬要他们成为廉价的白人仿制品。”[12]在给国家教育协会印第安教育者的一封信中,霍尔敦促教师们要加强对印第安儿童固有的天性、潜能和成长背景的认识,而不是彻底毁掉它们。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也对印第安教育者们的做法提出质疑,“教育必须始于对儿童的潜质、兴趣和习惯的心理洞察,学校应当设立在儿童早已熟悉的环境中”[13]。这与印第安办公室确立已久的对寄宿学校的依赖是不相容的。
(四)受教育者对政策的批判
持续不断的学生抵抗、归家的学生重返昔日部落生活方式等现象,使得印第安人自己逐渐认清了政府对他们施行的同化教育政策、唯英语教育及寄宿学校制度的本质。曾在印第安寄宿学校上过学的苏族作家格特鲁·德西蒙斯·鲍妮(Zitkala-Sa,Gertrude Simmons Bonnin) 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上发表了三篇半自传体随笔,揭示了以保留地外寄宿学校为主要特征的强制同化教育政策的核心理念:消灭印第安儿童的本族身份。在第一篇文章“印第安童年印记”中,鲍妮描写了自己8岁时被牧师的花言巧语所诱惑,离开扬克顿苏族社区,骑着“铁马”(火车)去一个满是大红苹果的地方(寄宿学校)[14]。在第二篇文章“一个印第安女孩的学校生活”中,她描绘了寄宿学校教师及管理人员如何像待小动物一样粗暴地对待他们,自己如何在痛苦、无奈中服从了学校一系列“钢铁般永不更改的日常生活”的过程[15]。在第三篇文章“印第安人中的印第安教师”中,鲍妮剖析了她长期不快乐的根源:“我就像一棵细嫩的小树,被从母亲、自然和神那里连根拔起,我在不断召唤对家人和朋友的爱的枝杈被修剪了,保护我敏感天性的自然树皮衣被剥光了,我灵魂深处的东西被无情地暴露在族外的陌生人面前。”鲍妮对不断涌到学校、经常在学校的走廊里走来走去、抽查学生作业、窥视教室内正在读书的学生们的白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剖析:“来访的白人一定感到骄傲和自我满足,因为他们看到,野蛮的武士及其后代竟然在如此驯服、如此勤奋刻苦地读书。”但鲍妮认为,“这只是貌似的文明”[16]。
基于对美国强制同化印第安人教育政策本质的认识,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用教育引导而非教育独裁的方式与印第安人讨论他们自己的事情。印第安人教育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教育引导应承认印第安人个体的愿望,那些愿意融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印第安人应当得到帮助,应做好调整,使那些希望作原来的自己、希望依据其旧文化传统生活的印第安人也可以在各方面得到支持。教育引导更应尊重印第安人宗教、道德观念乃至生活习俗。美国社会应当努力帮助印第安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非通过“公民教育”[17]强制同化他们。
[1] Prucha,F.P.ed.DocumentsofUnitedStatesIndianPolicy[M].3rd edi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0:176-178.
[2] Prucha,F.P.ed.AmericanizingtheAmericanIndians:Writingsbythe“FriendsoftheIndian”,1880—1900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196.
[3] Office of Indian Affairs.AnnualReportoftheCommissionerofIndianAffairs[R].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1:3-4.
[4] 宋银秋.唯英语教育——强制同化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印第安教育政策[J].历史教学,2010(22):54-57.
[5] Nardin,M.B.Language as a Barrier to Assimilation of the American Indians[J].Studium,1971(1):175-187.
[6] 范媛媛,宋银秋.美国强制同化时期唯英语教育与20世纪末唯英语运动对印第安语影响的分析[J].现代教育科学,2013(2):111-113.
[7] McGillycuddy,J.B.McGillycuddy,Agent;ABiographyofDr.ValentineT.McGillycuddy[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208-210.
[8] Talayesva,Dan.SunChief:TheAutobiographyofaHopiIndian[M].ed.Leo Simm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2:128.
[9] Leupp,F.E.The Failure of the Educated American Indian[J].Appelton’sMagazine,(May) 1906(7):597.
[10] 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ProceedingsandAddressesofthe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M].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2:861-862,1904:984.
[11] Office of Indian Affairs.AnnualReportoftheCommissionerofIndianAffairs[R].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1:2.
[12] Office of Annual Affairs.AnnualReportoftheCommissionerofIndianAffairs[R].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5:8.
[13] Dewey,J.MyPedagogicCreed[M].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59:22-23.
[14] Zitkala-Sa.Impressions of an Indian Childhood[J].AtlanticMonthly,(January)1900(85):37-47.
[15] Zitkala-Sa.The School Days of an Indian Girl[J].AtlanticMonthly,(February)1900(85):185-193.
[16] Zitkala-Sa.An Indian Teacher Among Indians[J].AtlanticMonthly,(March)1900(85):381-386.
[17] 金昕.美国公民教育的品牌效应、培育路径及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85-189.
2014-03-15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教科合字[2011]第15号)。
K712.54
A
1001-6201(2014)05-0269-03
1.吉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2.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赵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