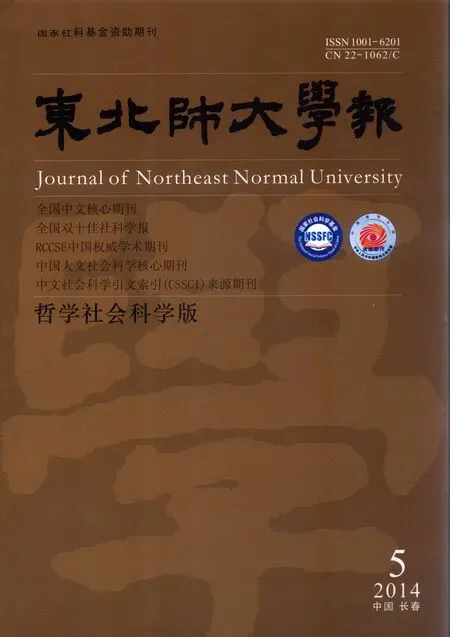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构建的系统化进路
曾文革,肖 峰,黄 艳
(1.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5;2.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5)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保障食品安全即抑制“从农场到餐桌”中的风险因素和行为,“引起人类健康的食源性风险,包括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三个方面的危害因素”[1],不同利益相关人维系于同一食品价值链中,价值诉求的差异决定了经营者、政府和消费者不能自发形成共同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食品对人类的生存保障功能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抵牾,食品安全法治是必然要求。但是,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构必须适应安全风险的存续规律。而我国现行立法价值目标不明、立法系统化严重不足,会在执法时造成诸多困扰,应对其缺陷之处予以检视,提出新的系统化立法进路,以图弥补之策。
一、食品安全风险的分散性特征与防控制度构建的系统化要求
食品在生产、流转、消费中可能产生危害健康的致害因素,现代社会条件下交易规模与日俱增,现代食品工业及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也引发了新的安全隐患,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无法抑制市场主体引致风险,必须立足于安全风险的基本特征,科学制定规制的法律规则。
(一)食品安全风险的分散性特征
人为原因和自然原因都会引发食品安全风险,体现为单个威胁因素或组合并存在于食品价值链始终,是静态和动态风险的结合。
静态上看,安全风险是可能造成食源性损害的所有物质,包括农药、化肥、兽药等残留,环境破坏造成的农产品污染,食品添加剂使用过当,生产、加工、运输、仓储过程中引入的威胁因素等。虽然存在多种静态风险,但如能规范食品链利益相关人生产、传递、消费的行为,使其承担防范自然因素对食品的污染,即能保障流向餐桌食品的安全;在静态风险因素已然存在的基础之上,利益相关人未能通过积极作为防止自然性风险或通过消极不作为抑制自身造成风险的行为,则静态风险因素将通过食品价值链流动。因此,利益相关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主要包括:(1)非法经营者的所有行为;(2)合法经营者的超限行为;(3)合法经营者对防止食品受污染的不作为;(4)监管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因此,食品安全风险是生物、化学和物理性污染物质的客观存续状态和利益相关人社会角色的不充分履行的综合体。
由于食品安全链条中利益关系复杂且风险敞口大,风险量规模大、风险因素间独立,呈现出明显的分散性特征。一方面,引发食品安全风险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非法经营者也包括合法经营者,还包括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另一方面,风险的客观形态与引致行为类型多样,各自构成损害的充分条件而相互间无必然关联,非法经营者未获批准从事经营的行为,合法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自然、意外因素污染食品的不作为与超限行为,监管机构不作为以及错误消费行为,都是独立的安全风险来源。
(二)风险防控制度的系统论指向
虽然安全风险存续呈现分散性规律,但各类风险所依附的食品交易环节却形成环环相扣的经济利益链条,保障食品安全很大程度上要正确处理个人经济利益和风险防范社会利益间的关系。因此,利用交易主体、交易环节间利益联系为保障工具是必然选择,这需要针对风险的分散性采用系统论思想设计防控机制。将风险防控全过程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把握整体与局部对立统一关系,通过顶层设计指导防控系统,关注各防控环节间的互动关系。
“系统的定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2],哲学上讲系统具有整体性、能动性、相关性、涨落性等多项属性[3],将系统论思想寓于风险防控系统应视风险分散性特征而定,根据基本价值指导系统整体与内部因素、内部因素相互间,以及与其他系统间的沟通方式。
首先,防控的价值目标是核心要素,风险引发的食源性损害最终危害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而非经营者经济利益或行政利益,构筑公众健康防护网应是风险防控的基本目的。因此,公众利益处于系统的中心位置,防控手段应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其次,防控系统的作用范围须覆盖整个食品利益链中的所有风险因素,“一个有力的控制体系要求在诸多环节上的有效管理,包括:计划、组织、检测、协调、沟通。为了将这些行为连接起来,必须将其纳入一个稳定的结构中,该结构包括:管辖各种管理行为的机构、能够并愿意正确执行必要任务的个人。食品控制管理可被视为若干机构的集合”[4]15。参与防控的主体类别、防控针对的风险行为等应整体上与风险的动静态表现一致,系统构成要素要具有整体性;再次,根据防控系统价值本位的指引,系统各因素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实现防控目标须各要素间在位阶、效力发挥等方面层次分明,同一层次及各层级间的要素须具备协同效力;最后,食品安全问题的国际化要求防控系统必须向国际社会开放,协调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达成食品安全保障之目的。
(三)系统论指向下防控制度的应然内容
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社会系统进入法律领域,即是系统功能的法律制度化,将防控行为事实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规定权利、义务、责任以及相关实体性、程序性制度,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食品安全。防控制度规制改变自然条件、附着非自然物质、不当加工或保存等引发威胁的行为,关注谁具有作为或不作为之义务,所保护的是依赖公众的基础性利益——公权力和私权益之外的社会性利益。据此,防控制度应坚持社会本位,通过法律建构保障食品安全利益的权利(力)义务结构,在民事私权和行政权之上附加特定义务。世界食品安全法制经验显示:法律须建之于“从农田到餐桌”过程,采取预防性立法并保障消费者、经营者与政府充分参与,核心是对“风险”行为的规制。由于风险在食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和主体控制范围内的异质性,防控法律体系须具备系统性,其应然内容主要表现三个方面:
第一,防控制度是全部风险法律关系的综合体。纵向看,在社会本位指引下,公众食品安全利益是法律体系的中心权益,处于制度顶端并高于监管权和经营权;经营行为是风险主要来源,政府监管部门是风险次生主体,政府和经营者是公众监督的共同义务主体,经营者又是政府监管的义务主体,社会监督、政府监管和经营构成的纵向防控法律关系;横向看,防控制度需保障食品传递过程对风险的闭合性,食品安全问题的国际化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国际合作以利用国内与国际两种法律资源来共同实现制度价值。
第二,不同法律主体在所有环节中权利(力)义务的联动是防控制度功能实现的根本要求。风险在食品传递各环节中表现形态不同,各类法律主体在防控权利与义务上应具有共同价值指引。一方面,防控权利(力)、义务和责任形成的法律关系链共同服从于防控制度的价值指引,法律对各环节的保障力度应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理顺同类型主体内部成员间的法律关系,协调统一的发挥该类主体功能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功能。
第三,信息保障机制是连接所有防控法律关系的纽带。公众、经营者与政府在食品安全法律关系中的互动根本上依赖安全信息的传递,包括食品生产原料、生产过程及生产工艺、运输、仓储等物流信息,也包括监管部门预防风险、制定技术标准及执法的依据、过程等信息。以法律之力保障食品安全信息沿价值链充分传递,确立公众知情权和经营者、监管者信息公开法律义务,通过立法规定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公开内容、程序、透明是根本保障。
食品安全风险的分散性存续规律决定了防控制度的设计必须具有系统性,法律关系建构上将所有利益相关人纳入不同层次权利义务关系中,通过国际合作延伸国内法效力,保障安全信息流动顺畅,以共同价值理念和法律本位协调统合法律主体发挥防控的制度功能。
二、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系统性缺陷
我国对食品的法律规制已从“食品卫生”提升为“食品安全”,形成了以《食品安全法》为基本法,兼有食品市场准入、产品标签与营养标示、流通环节安全保障、安全信息发布等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初步形成中央与地方、综合性与专业性结合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群。但该防控制度体系还存在质和量的残缺,利益相关人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完善,监管主体内部的协同水平不高,生产、经营、监管和消费环节的风险防控手段未良好的协调,权利(力)、义务、责任未反映风险特征及防控根本需要,系统的防控制度体系尚未形成。
(一)风险防控制度的调整对象狭隘
防控制度的调整范围应与食品价值链广度及风险存续规律匹配,“一个成功的立法过程,要求立法的结果以不同的方式造福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5],防控制度体系应当赋予经营者、监管者和消费者相应法律主体地位。“食品的生产者、加工者、管理者、制造商、交易者、零售者和餐饮业经营者,是向消费者提供安全食品的第一责任人”[6]3,风险主要存续于经营环节,衡量食品安全立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否“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生产者、加工者对食品安全和质量承担首要责任”[6]3;食品监管须“存在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存在能就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的有效机构、食品安全职责和责任在不同政府部门间合理分配与协调,分工明确、行为协调一致”[4]15,防控法律关系应科学建构于消费者、监管者和经营者间。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了不同主体的防控地位,确立多部门协调监管、政府监管权处于中心的机制,经营者通过遵守安全标准和经营规范承担防控义务,消费者享有依附于监管的安全信息知情权、违法行为举报权和对监管机构的批评建议权,公权力本位造成了法律调整对象较为狭隘,并影响了公众食品利益在防控制度中的中心法益地位。
公众缺乏法律独立地位和监督经营者、政府部门的法定程序和救济机制。公众监督权应包括:一是风险预防中提供风险信息,通过风险沟通充分发表意见和评价,如欧盟消费者政策战略(2007—2013)规定:“欧盟将消费者政策中置于下一阶段的内部市场核心地位”,“消费者福利是市场良好运作的核心”,并把“将消费者置于欧盟其他政策和规定的核心”作为优先行动之一[7];二是请求经营者依法履行标签、标识注明等经营性防控义务,索取执法过程和依据等监管信息,当监督义务不履行时可以依法救济。但我国将社会监督局限于向监管机构举报、批评建议,客观上使社会监督成为依附于政府的监管启动“申请权”,不具有独立于监管权的法律效力,风险防控的权利义务流向具有典型的单向性,没有充分发挥风险沟通的功能,社会监督权成为“软权利”也使监管权行使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防控制度体系构成要素间的协同度较低
风险防控法律实施的协同性指经营者、监管者和消费者的防控法律行为协调统一,共同服务于公众健康利益,既要体现法益的层次性,又要保障各类主体功能发挥的充分性。
首先,公众的社会监督权与政府监管权间的协调性不高,体现为前文分析的社会监督权法律属性的缺陷。
其次,权力配置模式不科学以及能力建设不足造成监管权内部协同性较低。一方面,监管权配置模式显示出其应急功能强于日常管理能力,国际上监管权有两种典型模式:一是美国式多机构协调执法,由FDA、美国农业部、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和国土安全部等机构共同治理,以分领域治理为显著特征;二是以单独食品安全机构统一管理的欧盟模式,采取高水平的安全标准和技术力量防控风险,二者都强调风险信息在行政部门间顺畅流通及防控行为迅速统一。我国设有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综合协调机构,由卫生、农业、质监、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各司其职,分领域与分阶段治理同时存在,风险决策、过程控制和反应行动需部际协商、通报和配合,技术和管理职能交织在一起。权力纵横交错之处存在监管盲区和漏洞,监管主体群的整体性主体功能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我国安全标准水平尚不高,对风险无法形成有力的技术制约,完善合理的检验网络尚未形成,基层监管机构的职责与执法资源不足的矛盾突出,低水平能力建设成为食品安全执法的客观阻碍。
再次,监管权与经营者防控义务的协同通道不畅。经营性防控义务具有基础性,经营性风险信息披露是监管和监督的依据,制备安全设施、制定企业安全措施、依法披露产品信息(“种类包括产品来源、生产方法、生产的属性和产品特征”[8]等义务)是基本防控法律义务。《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经营行为禁止范围,规定了风险检测和评估目标、机构、程序和食品召回制度、安全标准更新、安全事故处置、食品成分营养、信息发布等制度,我国现已公布约600余项国家强制性安全技术规则。但在实践中,监管权对经营者内部管理透明度的强制不够,监管权对经营者的主体身份依赖度较高,监管重心在主体准入与市场行为上,信息追溯制度薄弱且缺乏社会公众的信息支持,疏漏了对风险载体——食品本身的规制;另一方面,对农村市场、街头食品、小作坊规制较差,防控法律关系向农场延伸度不够,缺乏防控农药、兽药等残留量等上游风险影响产业链安全的完善机制。
最后,食品安全责任的度量标准与防控权利(力)义务不匹配。风险可能是多主体行为累积的结果,食品流通量庞大且消费与损害的形成具有即时性(特别是农产品),将总污染度作为食品安全责任的度量标准才能补偿风险行为造成的公共健康破坏。但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在风险责任的追究存在以食品交易经济价值作为风险衡量标准的谬误,使食品安全违法成本与风险的真实水平严重失衡,容易造成食品生产、加工等环节的风险行为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合力对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三)风险信息制度的保障力较弱
防控制度体系“包括多个构成部分,包括:食品政策和立法、食品控制管理、检验分析实验机构、食品监管、执行和鉴定、应急准备与反应、食源性疾病监测和信息公开、宣传交易和沟通”[6],本质上就是风险信息在不同主体间传递、甄别、控制和反馈的过程。我国《食品安全法》第82条、《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条及卫生部等六部委颁布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规定了监管过程的信息内容、信息发布权限和程序,但对风险信息的沟通互动、信息传递的顺畅与充分性的法律保障水平较低。
一方面,风险防控信息机制的多方参与水平较低。由于社会监督权的缺位以及监管权与经营行为协同水平低,政府、消费者和经营者对风险信息的认知彼此割裂而缺乏共通性;信息在政府的监管部门之间的传递机制无法适应防控的客观需要,风险信息的统合与发布集中于卫生部门,但是信息的来源、甄别及管理行为却仍然分部门进行,形式上政府的风险信息口径统一,实质上预防的基础、防控的关系并未理清,风险信息的义务和责任主体在监管机构内的归属混乱。
另一方面,风险信息公开的范围、程序、透明度保障的单向性特征突出。虽然我国立法对风险信息的发布等做了一系列规定,但多为职权性规定,公开的信息范围、内容由监管部门单方决定,如转基因进口信息的公布仅限于名录,而没有公开做出安全认定的依据、数据等;缺乏对公众信息诉求的法定反馈程序,经营者和监管机构的风险信息公开义务缺乏互动性,总体上信息保障机制的透明度较低。
(四)防控制度体系的开放性不足
我国现行防控制度体系国际性视野较为缺乏,“检视我们的《食品安全法》除了散见于条文中的规定外,在总则中关于国际化或国际合作理念的哪怕字里行间有其意的条文也很难一见,这表现为对食品安全国际化的轻视或对借助国际合作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不信任”[9]。
一方面,我国参与防控制度国际合作具有片面性,国内制度的输出水平较低。虽然食品特别是农产品进口规模较大,但是国内立法关于风险预防与控制的制度在种植、生产、加工、运输等域外地区适用水平低,规制食品价值链域外阶段的立法、执法合作较为缺乏。加上我国的安全标准整体水平不高、技术支撑能力相对较弱,应对国际食品贸易输入性风险的能力比较薄弱,如转基因农产品引入的安全管理有待加强;域外制度的内化以及常规性合作没有归口的业务部门来进行,割裂了国内有限的防控合作资源。
另一方面,我国参与防控制度国际合作的深度不够。现有国际合作领域主要涉及执法力量和技术标准中,不利于发挥我国食品安全制度资源的比较优势,制度移植后与中华传统农艺的结合不够重视;合作利益的本土化力度不足,现有合作模式相当程度上是发达国家标准和监管力量在我国的延伸,以保障我国产品出口目的地国的食品安全,面临着先进国家制度势能的冲击而加重我国食品出口的压力;制度资源引入的转化深度不够,片面重视技术标准、硬件设备等物质因素,对他国保障食品安全的社会性、文化性资源等“软实力”的借鉴消化不足。
总的来看,我国风险防控机制既存在“质”方面的缺陷,也存在“量”方面的不足,核心是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法律价值评价存在偏差,在防控权利(力)义务机制和责任机制对“风险”规制不一,未根据风险分散性的特征来构建科学的权利义务结构,信息制度建设和国际制度合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未来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构建系统化的主要设想
未来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构建的系统化,要从广度和深度上完善法律调整对象和手段,从制度的本位主义出发,优化顶层设计和规则结构,补足防控制度中的缺失与制度短板,保障信息机制对防控法律关系的有力支撑,使制度体系符合风险存续的客观规律和防控需要[10]。
(一)防控制度的价值目标复归于社会本位
公众的食品安全利益是法律体系的中心法益,社会监督法律关系建立在完整的监督义务主体、监督权利义务内容、社会监督法律责任救济等内容之上,使制度重心从监管权行使复归于消费者权利,凸现公众对监管机构、经营者加以监督的法律权利。
保障公众社会监督权的法律效力的途径包括三个方面:(1)在食品安全基本法层面,确定监管机构、经营者接受社会监督义务以及未履行被监督义务时的法律责任,以法律强制力作为监督权的后盾,避免公众监督权脱离法律视野;(2)提高监管机构和经营者信息披露力度,提高食品标签、标识、说明书等风险信息的完整性和普识性,如欧盟专门编撰了标签识别手册,作为消费者辨识标签的辅助资料[11];监管机构的安全信息主要通过官方文件、声明、公告等途径达到公众等信息的透明度,将监管权启动、行使依据、处理后果、程序过程等纳入接受社会监督的范围。在风险预防中突出与公众的风险交流,特别是风险管理的互动水平,改善监管中风险信息发布的单向性,使监管力量与监督力量能协调一致针对食品安全风险;(3)要加强监管权对社会监督权利行使的应答水平,公众识别食品安全风险后,要么以风险行为来源主体作为被告寻求司法救济,要么通过转向求助于监管权处置风险。由于风险尚未转化为实质性损害,直接起诉还需要在私权外设立新的权利类型作为诉的要素,如部分学者主张的“食物权”[12],逐步建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救济机制。但我国的现状更适宜加强监管权对社会监督权的应答水平,建立对公众举报处理步骤、时限与回复义务,如欧盟要求对消费者投诉按标准格式统一分类,并使用的标准化投诉管理信息平台。
(二)构筑系统协调、层次分明的防控权力配置模式
调整我国《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综合协调、多部门共同监管的权力系统,形成风险决策与行动、技术与管理相分离的系统协调、层次分明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
首先,食品安全委员会要从部际协调机构转变为食品监管最高行政机构。从食安委的职能设定及人员组成来看,其是存在于卫生、农业、质监、工商、食品药品部门的监管权之间的综合协调部门,并未承担日常监管中的实质性权力,使得风险防控权力散碎于条块分割的部门之中。一方面,食安委调整当前由多部门负责人作为成员的组成方式,按照独立的政府部门建制模式进行“实体化”,行政地位高于其他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统一行使风险信息获取和风险评估、沟通的权力,作为政府获取、公布风险信息和与公众沟通并接受投诉的唯一机关,成为食品安全风险的决策机构;另一方面,食安委根据科学的风险决策,指挥其他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在其职责内进行风险管理,利用本部门的公共资源防控食品安全风险,建立起像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一样的决策职能与行动职能相分离,改变多部门协调带来的权力掣肘、信息流通不畅、风险防控权力受到行政体制限制的不利局面。
其次,食安委应当整合现有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技术力量,组成独立于卫生、农业、质监、工商、食品药品等部门之外综合性科学咨询机构,作为食安委的决策辅助机构。统一的科咨机构能减少各部门技术力量重复建设而带来的资源浪费,避免科学技术组织在风险监测、评估、决策建议、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受部门利益干扰,打破科学鉴定对象与科咨机构及其成员的利益关联,保障食品安全风险的技术认知的客观性、中立性,从而提高行政权力运用的系统科学性。
(三)提高防控责任机制与义务的一致性
防控体系应围绕风险来展开,风险预防、预警、召回和责任追究机制应互为补充、力度匹配,但如果末端防控未依照风险大小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依据,则会降低安全防控体系的整体水平。而我国恰恰使用食品经济价值等指标而非风险程度作为归责依据,违法成本与风险程度不匹配的矛盾较为突出。改善可考虑下述途径:
第一,采用根据风险造成人体损害的一般水平的追究机制。首先,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依据发布的居民平均营养水平和膳食结构,测定污染食品所含的损害物质类型与数量,得出污染物在单位食品中的比例,再与居民人均摄入该种食品水平合并计算出其流入消费环节后可能造成健康损害的影响面,根据影响面制定不同的风险处罚标准。其次,以食品是否转移到消费者作为时间划分,对尚未转移的食品结合风险处罚标准的一定百分比执行,对风险已释放给消费者的食品情况较为复杂,已造成消费者健康损害则按民事侵权处理,已售出但未通过召回、未通过民事侵权赔偿承担风险责任的部分,也要根据交易数量扣除民事侵权已赔偿部分,适用风险处罚标准。
第二,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等级的差异适用不同的罚则。如美国的食品安全法就采取了分级处理的方法,《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第301、303部分规定:对任何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都采取1年以下或1 000美元以下处罚或二者同时适用,对严重违法则纳入刑事违法中的罚则,2011年4月通过的《食品安全责任法案》(S.216)规定:故意或对生命和生命损害风险的忽视则按照美国法典第18部分实行经济处罚或处以十年以下徒刑,或二者同时适用。我国新制订的《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已将食品安全事故划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等级,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风险的定量问题,因而可以借鉴美国的违法惩处机制,采取分级定量处理的方法对违法主体进行惩处。
第三,也可考虑纳入加重惩处的机制,在上述方法中选定一定基本惩处依据,但对主体的故意行为和恶意不执行处罚的行为,可以考虑在基础处理依据上加倍执行的机制,这也是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第303部分和美国2007年《食品药品管理修正案》第902部分中管理药品的重要措施之一,对我国当前食品事故频发的现状具有较高借鉴价值。
(四)拓展防控制度建设的国际合作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食品安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国际交流既带来了食品生产技术、制度经验和资金,也扩大了食品安全事故的域外影响,法律制度的国际合作是防控法律系统的重要环节。我国是食品贸易的大国,食品安全立法中忽视防控制度国际合作的局面必须扭转。
一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防控制度建设国际合作。利用多边性制度合作平台丰富国际合作的渠道,充分利用 WTO、粮农组织、食品安全法典委员会等多边性国际组织的制度资源和协商平台,推动风险预防的技术、贸易措施、公共健康保障等各个方面的国际法造法活动与内国法协调合作,促进风险防控制度的国际统一性水平;深化区域性、双边性制度合作的成果,加强在风险防控科学技术研发、检验检疫机构、安全技术标准的地区性、双边性合作,通过共建科学咨询机构、互派常驻性执法机构等方式加强风险信息通报与防控制度衔接等方面的合作,将国际防控法律资源内化为国内安全利益。
另一方面,推进防控制度建设的国际互动。加强食安委以及其他部门对国际条约法、习惯法以及其他“软法”文件研究力度,根据我国国情加快将国际法律资源国内化的转化步伐,提高我国防控立法的国际化水平和立法质量,构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中的“软实力”;及时汇集国内风险防控经验,总结制度实施的成功与不足,结合域外制度状况辨识国际风险防控立法的发展趋势,凝练我国参与国际法律制度制定的基本立场和合理主张,扩大我国立法对世界立法的影响,从而形成国内法与国际法良性互动的局面。
四、结 语
由于食品安全风险的分散性特征,在食品安全制度建设上必然要求防控制度构建的系统化。而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存在较为严重的系统性缺陷,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立法思路,以系统论为指导,从多个方面提高防控制度的系统性水平。明确建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的核心是根据“安全风险”在食品价值链中的存续规律,在保障公众健康的社会本位指导下,系统架构安全风险防控法律关系。在法权结构上形成社会监督权、政府监管权与经营权的位阶等序,调整监管权的构成模式与运行规则,确保防控法律制度体系总体构成的完整性、各部分之间的协同性;加强风险信息的保障力度,通过利用国际国内两种法律资源,推动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制度向系统化方向发展。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ood safety risk analysis:A guide for national food safety authorities[R].Rome.WHO/FAO,2006.
[2][奥]路·冯·贝塔朗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J].王兴成,译.裘辉,校.国外社会科学,1978(2):71.
[3]湛垦华,张强.“系统基本特性的哲学沉思”纲要[J].人文杂志,1989(1):1-9.
[4]Hilbert van der Werf.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Design of an evaluation scorecard and indicators.Rome[R].FAO,2007.
[5]Michael R.Taylor.Lead or React?A Game Plan for Modernizing the Food Safet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J].Food and Drug Law Journal,2004(59):403.
[6]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Strengthening national food control systems A quick guide to assess capacity building needs[R].Rome.FAO,2006.
[7]Health & Consumer Protection Directorate-General.EU Consumer Policy strategy 2007-2013Empowering consumers, enhancing their welfare, effectively protecting them[R].Luxembourg.EC,2007.
[8]Patricia Farnese.Tracking Liability——Traceability and the farmer[J].Alberta Law Review,2007(45):208.
[9]汪江连,苗奇龙.新安全观视角下我国食品安全法基本理念研究[J].法治研究,2011(10):61-66.
[10]刘畅.风险社会下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困境与完善对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1-24.
[11]Directorate-General for Health and Consumers.how to read a label.Brussels.EC,2007:1-9.
[12]宁立标,罗开卷.论食物权的司法保障[J].法商研究,2011(3):5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