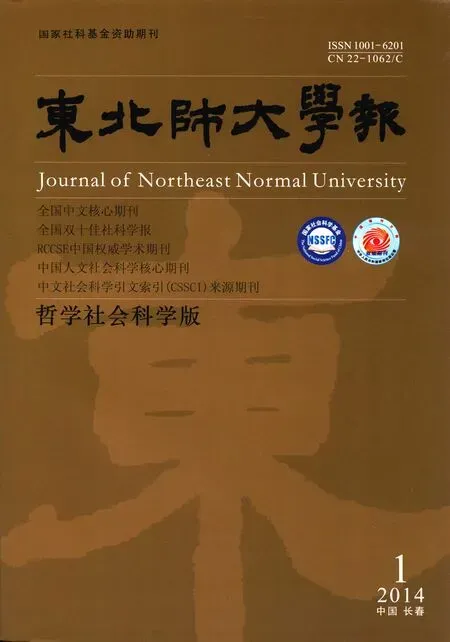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灿烂千阳》中女性主体的拉康式解读
刘喜波,葛 健
卡勒德·胡赛尼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用英语写作的阿富汗裔美国作家。他出生在阿富汗,小时候随父逃难到美国,接受美国的教育,却以阿富汗人的视角从事写作。《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这两部作品均获得极大成功,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出版商周刊》评论《灿烂千阳》呈现的是“不可宽恕的时代,不可能的友谊以及不可毁灭的爱。”[1]作者坦言自己写作的初衷是“希望这本小说能为那些世人所熟悉的、穿着蒙面服装、走在尘土飞扬街上的阿富汗传统妇女的身影,增添更多深度、细致与情感的意涵。”[2]
故事的两位女主人公虽然出生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经历,却在命运的转弯处相遇。从懵懂到坚毅,她们用自己的血和泪完成了主体的确立。笔者试图运用拉康的主体三界理论,分析她们是如何于家庭及民族的苦难中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主体自我的。希望通过对文本人物的深入分析,从内部找到造成妇女们苦难的真正原因,为身陷缧绁的人们找到一束照耀平等自由的明媚阳光。
一、实在界中的主体
三界说是拉康关于主体理论的核心内容。拉康认为,人的主体心理结构可分为三界,即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虽然拉康很少直接说‘实在界’是什么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之物,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参照物而已,相反,它确实是存在的。”[3]119实在界是指从出生到镜像前期,婴儿无法识别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区别,没有完整的自我概念,只有“需要”支配他的意念。“‘实在界’就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去说的寂静世界。从逻辑上说,‘实在界’总是先于‘象征界’而在场。这个既无对错也无真假的世界,显然就是指‘实在界’。”[3]132
《灿烂千阳》中主人公玛丽雅姆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贫寒艰辛。玛丽雅姆不明白为什么她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而只能每周与父亲见上一面,可是她喜欢父亲。实在界是混沌的界域,只凭需要行事。父亲每次都会带给她没见过的东西,给她讲她从来没听过的事情。父亲曾经告诉过她,“玛丽雅姆”是父亲为她取的名字,是晚香玉的意思。他喜欢父亲陪她唱歌,陪她钓鱼,总是高高地把她举过头顶,好像她是他的公主。她相信父亲说的一切。实在界中玛丽雅姆并没有完整的自我概念,只有需要支配她的意念。玛丽雅姆作为小孩子需要的亲情和温暖都被父亲所满足。所以,父亲是她最尊敬最喜欢的人。
母亲娜娜虽与玛丽雅姆日日相见,抚养她长大,可是玛丽雅姆却并不与母亲那么亲近。娜娜原本是扎里勒家的女佣,由于玛丽雅姆的出生,她和扎里勒的私情曝光,没有正当身份的娜娜被赶出家门。娜娜把这不幸归咎于玛丽雅姆,认为玛丽雅姆的哈拉目(非法)身份才是她一切屈辱和痛苦的来源。母亲对她的谴责和嘲讽,父亲对她的疼爱和眷顾,让她无法相信母亲平日对于父亲的评价。她认为母亲之所以欺骗她,是因为嫉妒她得到来自父亲扎里勒的爱。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实在界中的玛丽雅姆如婴儿般,只凭需要支配意念。所以,没有满足她需要的母亲,使她远离和讨厌。
故事的另一主角莱拉,也在她混沌不清的实在界中找寻需要所在。父亲很重视莱拉,从不疏忽对她的培养和教育。莱拉在同学中是最有天赋的,朋友们都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大人物。所以,莱拉亲近她的父亲,也珍爱她的朋友。塔里克是莱拉青梅竹马的朋友和爱人,在莱拉受委屈时,为她挺身而出。塔里克的父母亲也视莱拉为儿媳妇一样处处疼爱和照顾,莱拉也喜欢塔里克和他的家人。相对于父亲的疼爱和重视,母亲将感情都投注在莱拉的两个哥哥身上,因为儿子远赴前线战场而整日活在忧郁的气氛里,完全无暇顾及莱拉。莱拉被别人欺侮的时候,妈妈也只是说说安慰的话,而听说儿子在战场上牺牲,她悲痛至极甚至想要自杀。母亲的固执和对莱拉的忽视让莱拉在经历战乱的同时,心理也遭受重创。所以,她不与母亲亲近,甚至有的时候怨恨母亲。
在两个主人公的实在界中,她们都对于自己一无所知。不能明白何以为我,两人的父母亲又都站成对立的两边,使她们如婴儿般只满足自己的需要,喜而相亲,恶而相弃。实在界与想象界的交界处是恨,因为恨,主体不满足于现状,要找寻“我”的存在。于是,她们寻得自己的镜中之像,以此为我,并由此进入想象界。
二、想象界中的主体
想象界是虚幻的世界,源自镜像阶段,即当婴儿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镜中之像的时候,她把自己的镜中之像等同于自己,建立起虚幻的想象自我。“婴儿的镜像阶段并不仅限于婴儿时期,而是代表了一种永久性的主体的结构性矛盾,主体永久性地被他自己的形象所捕获”[4]。
玛丽雅姆在母亲自杀后被迫嫁给和父亲一样年龄的拉希德。之前,她被母亲称为哈拉目,被父亲所抛弃,而相对于他们的对待,最初的拉希德在一些事上会问及她的感想,会给她买布卡、丝巾、冰淇淋,那是她为人女儿时不曾得到的。她认为,她终于获得了幸福。这成为她自恋的最好证明,即她的完美自我。想象界前期,婴儿自恋于自己的镜中之像,与之认同并认为那便是其完整自我。但因为那并不是主体本身,只是误认和虚幻的自我,所以,这个完美自我注定无法实现。布卡-一种阿富汗妇女穿着的服饰,把全身罩在下面,与世隔绝,那实际上是拉希德男权的一种体现。在玛丽雅姆第一次怀孕却最终流产的现实面前,拉希德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对玛丽雅姆极尽侮辱之能事,稍不顺意,就对其非打既骂。后来,玛丽雅姆又多次流产,这使得拉希德彰的责难更变本加厉。玛丽雅姆逐渐意识到,自己之前认为的幸福,不过是过眼云烟,她自恋的镜中之像注定无法见光。至此,她的完美自我即镜中之像破灭。
想象界中,自我除了与其镜像认同,还与镜中之他者认同,拉康称之为二次认同。自我只是他者眼中之我,自我靠他者才能存在,没有他者即没有自我。玛丽雅姆在现实世界里已经得不到救助,这个时候只有灵魂上的投靠,才能让她的心有所依附,精神有所寄托。法苏拉赫毛拉曾经告诉她,“它们也会安抚你的,亲爱的玛丽雅姆,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传唤它们,它们不会让你失望。真主的言语永远不会背叛你,小姑娘。”[5]所以走投无路的玛丽雅姆只好把命运交与真主,希望这一想象界的小他者能够为她指引方向。但一边她希望得到救助,一边又不得不忍受拉希德的非人待遇。社会的大环境对于玛丽雅姆的影响,使她对待拉希德的打骂近乎麻木。拉希德在无形中已成为玛丽雅姆想象界中的又一他者,玛丽雅姆也成为其希望的“失声之人”。
莱拉十四岁便因为战争失去双亲和朋友,爱人客死异乡,又被迫嫁给年过六旬的拉希德,她的生命应是一片灰烬之色。可是与塔里克的孩子的出生,与玛丽雅姆冰释前嫌却让莱拉的生活重新充满阳光和希望,让她的镜中之像呈现完美之势。但镜像中的完美自我毕竟只是虚幻的假象。出逃的失败,再一次怀孕,让莱拉的完美自我几近破碎。她想象界中的自恋之像随着与拉希德的儿子的出生,以及与塔里克的女儿被迫送离而彻底毁灭。拉康认为“与镜中影像的认同是典型的想象关系。想象的关系既发生于主体内部也发生在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在主体内部的想象关系表现为主体对自我的自恋;发生在主体间的想象关系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认同”[6]。塔里克的再次出现让莱拉所有痛苦的过往又遇转弯。虽然彼此都不如当初完美,但两个人一如既往的真心相爱。于是,莱拉的生命又找到了延续的理由。她要和塔里克一起逃亡,带着他们的女儿,带着她的母亲-玛丽雅姆,去幸福地生活。至此,莱拉找到她想象界中的他者,即想象关系中的她认同的客体-塔里克。想象中他者的出现,第一个他者是母亲,婴儿希望得到母亲的认同,所以希望成为母亲欲望的对象来满足母亲的需要,即成为母亲欲望的菲勒斯,从而得到母亲的认同。塔里克真心希望莱拉重新回到自己的怀抱,来补偿对爱人这么多年的亏欠。莱拉也愿意和他再续前缘,共同为幸福努力。但由于母亲的欲望对象是父亲,孩子永远无法成为母亲的欲望对象,所以,想象界中形成的与他者认同的自我,依然是想象的,是虚幻的,不是真实存在的。
玛丽雅姆和莱拉,虽然都在想象界中认同他者而肯定自我,却只因想象界本身就是虚幻之域,无法成真,所以她们的自我也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主体的想象界终要因为“父亲之名”的介入,而阉割孩子的菲勒斯,使婴儿最终认同于大他者,离开认同母亲的想象界进入到认同“父亲”的象征界。
三、象征界中的主体
“象征界即符号的世界,它是一种秩序,支配着个体的生命活动的规律”[7]548。“象征界是法律之域,法律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规定了欲望的合理”。“在象征界中,幼儿心理发展的关键是经历俄狄浦斯情结的阶段和进入由语言秩序所体现的象征秩序”[7]549。拉康发展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认为,“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母亲都是欲望对象,而父亲都是一个竞争者”[7]531。“俄狄浦斯冲突的解决结束了二元的母子关系,创造了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新的三元关系:他者、自我和对象”[7]531。“俄狄浦斯现象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体与母亲处于直接的二元关系之中;第二阶段体现在伴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生,主体进入了象征秩序;第三个阶段的到来,认同于父亲,并通过自我实现将自己注册到象征秩序中去”[7]532。
在想象界,玛丽雅姆虽屈从于拉希德以及《古兰经》中的真主,但内心里对莱拉的女儿,同样身为哈拉目的阿兹莎的同情和怜爱,让她的意识开始觉醒,开始主动勇敢地反抗,这是她人生最关键的一步。在经历了俄狄浦斯情结之后的玛丽雅姆,终于认同父亲之名-爱与希望,这一大他者让她再不像过去那样软弱,没有自我。她开始重新考虑人生的意义,终于明白一味的妥协和迁就根本无法赢得存活于世的价值,只有自己先有了主体的意识,才能从内心真正的强大起来。“俄狄浦斯阶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是人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正是在这个阶段,儿童实现了从想象到象征的转化和过渡;也就是说,从二元直接的镜子关系进入三元、间接的象征关系”[7]532。所以,玛丽雅姆把对拉希德的反抗从思想上转移到了行动上,亲手杀死拉希德。在一定程度上,这象征着玛丽雅姆终于与自己的想象自我告别,认同于希望与爱,即象征界中的大他者,并通过自我实现将自己注册到象征秩序中去。
玛丽雅姆的一生可以用悲剧来概括,从出生开始,她就不具备当时社会所承认的身份,没有得到父母亲的疼爱。虽然后来,她理解了那是社会大环境之错而非父母所愿,但却让她终其一生都无法走出阴影。而与拉希德的夫妻生活,更是她后半生的梦魇。直到莱拉的出现,阿兹莎的出生,让她又燃起希望,渐渐从自己的想象界里走出来。从意识觉醒开始,渐渐完成主体人格的确立。她一人扛下杀死拉希德的责任,放莱拉去找寻幸福。虽然,她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可是她的赴死看起来有尊严、满怀希望与爱,那是她对于自己及这个世界的新认知——只有爱和希望能救赎我们的灵魂,成就我们的理想和价值。浴火之后的凤凰得到重生。
莱拉也在经历虚幻的想象界后终于认同父亲之名进入她的象征界。莱拉虽然出逃成功了,但是却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幸福,因为那是玛丽雅姆牺牲自己换来的。她逐渐意识到,只有自己幸福是不够的,还有更多的事需要自己去完成。“父亲”的出现,阉割了莱拉想象的菲勒斯,让她认同于象征界的大他者,即大爱与亲情。人生不能只有爱情,亲情、事业、梦想都是人一生要完成的责任。所以,莱拉转而认同象征界的大他者,真诚回归。“象征界是同父亲联系着的,拉康认为,抽象化的父亲在我们的文化中起着重大的作用”[7]549。莱拉接受扎里勒留给玛丽雅姆的遗物,代替她原谅父亲当年抛弃的行为。她也完成了父亲的梦想,开办学校,帮助那些战争幸存下来的人寻找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用希望与爱包容一切的莱拉,至此也完成了自己的主体确立,活出了真我的风采。故事的最后,莱拉又一次怀孕,那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不管多大的苦难,不管多残酷的战争都有过去的一天,而怀抱希望,并为之努力,才可以在尘埃荡尽之后,再现骄阳。
玛丽雅姆和莱拉主体确立过程殊途同归。他者眼中的自我是想象界中虚幻的存在,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所以,玛丽雅姆坦然赴死,莱拉去而复返,都是因为她们不再想成为别人欲望的菲勒斯,而希望成为独立的主体为自己而活。想象界与象征界的交界处是爱,正因为心中有爱,才不能自溺于虚幻的自我。人间大爱,至情至性都成为她们认同的大他者,从而走出想象界进入象征界[8]。
结 语
《灿烂千阳》是卡勒德·胡赛尼继《追风筝的人》之后的又一力作,虽未逃离战争和死亡的主题,但文中故事却更有深意。他以两个女人的故事为线索放眼整个阿富汗社会,写尽了阿富汗妇女的血泪,让读者对于阿富汗有了新的认识。阿富汗妇女们虽身陷苦难却能坚守人性之美好,出淤泥而更显皎洁,经狂风却倍加坚韧。本文从拉康的主体理论角度分析文中人物是一种新的尝试。两个女性主体都经历了混沌的实在界、虚幻的想象界和以法律为特征的象征界,最后完成主体人格的确立。那也是作者为之深深感动,并诉诸笔端以至成文的初衷。本文以拉康的镜像理论和主体三界说为依托,从新的视角推进《灿烂千阳》的研究,以期有助于对书中人物的理解,深化文本内涵。
[1]美国出版商周刊(Publisher Weekly).2007-09-01.
[2]尚必武,刘爱萍.卡勒德·胡赛尼访谈录[J].外国文学动态,2007(5):10.
[3]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Dylon Evans.AnIntroductoryDictionaryofLacanian Psychoanalysis[M ].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115.
[5]卡勒德·胡赛尼.灿烂千阳[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8.
[6]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85.
[7]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时贵仁.后殖民语境中的女性书写[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46.
——拉康对《孟子》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