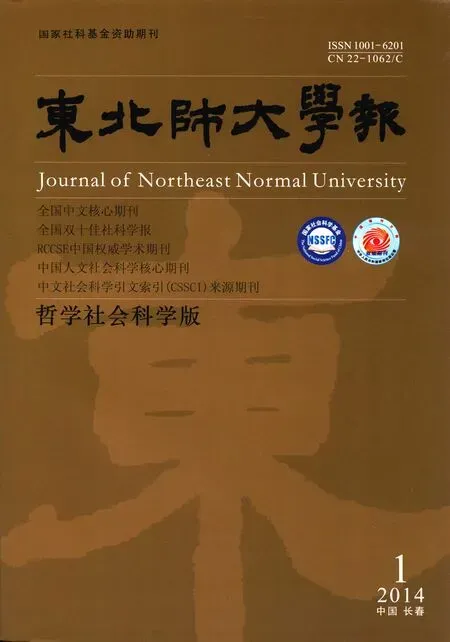论儒家自然人性论与礼乐教育的关系
张斯珉,乔清举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
礼乐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礼乐教育是儒者培养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一向重视礼乐教育的内在依据,孔子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说法,认为礼乐教育的目的是彰显仁道,仁是本质,礼乐是手段。孔孟之间的儒者则立足于战国初年流行的自然人性论,说明礼乐教育的必要性及具体途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包括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篇及《礼记·乐记》。鉴于两者的思想多有一致,本文拟以此为中心,探讨儒家自然人性论与礼乐教育的关系。
一
自然人性论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儒者对于人性的主流看法。孔子很少言性,《论语》中涉及性只有“性相近,习相远”一句。它只是肯定了众人之性具有相似性,并未阐明人性的具体内容。孟子和荀子则分别提出了“性善”和“性恶”的基本命题,两者都认为人性先天便具有某种道德属性。自然人性论则不同,它将人性视作天赋的材质及能力,本身并没有价值属性。例如,《性自命出》认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1]105。这里的“气”指的是材质,因而此处的“性”仅仅是指人与生俱来的、产生喜怒哀乐之情的能力。
喜怒哀悲之气决定了人性并非是封闭而晦暗的,相反,它具有与外物相接触并表现于外的倾向。《性自命出》云,“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1]105《乐记》也有类似的观点,“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2]984也就是说,在与外物接触之前,人性中天赋的材质处于未发状态,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只有当外物作用于人时,喜怒哀悲之气才获得具体的对象而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情感,即“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1]105也正是如此,内在的人性才能为我们所知。
然而,人在与外物的接触中,往往会沉溺于后者的诱惑而是非不分。对此,《乐记》有细致的分析: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2]984。
一方面,人性并不具备能够引导人恰当地产生喜怒哀乐之情的标准,换言之,性并未告诉人何者当喜,何者当怒,因此,“心无定志”,不能对好恶之情加以节制。加之外物的诱惑无穷无尽,这使人难免沉湎于其中而丧失持守,进而为了满足物欲无所不为。对此,《乐记》的作者明确加以反对。可见,自然人性论者同样肯定道德的意义,反对为了满足耳目口腹之欲而肆意妄为。但是,由于人性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并不包含先天的道德性,因此学者若要获得判断是非的依据,不能单纯地求之于内,必须依靠外部的教化。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否成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后天的教育,这体现了教育对于成就道德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人性也具备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性自命出》云,“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1]105这里揭示了人性与动物之性的根本区别:牛长雁伸之性皆与生俱来,是动物的本能。动物依据其本能即可生存,不需要后天的学习。人性则除了喜怒哀悲之气以外,还包括学习、思考的能力,这些能力需要在与外物不断地接触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培养。由此可见,人性不可能先天即完善,它的充分实现依赖于后天的引导与培育,这便为教育发挥作用创造了充足的空间。通过教育,人性中的诸多能力得以由潜存发展为现实,而人性也完成了由自然之性向人文之性的转化。因而,能否接受教育,接受怎样的教育直接决定了人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实现,“性相近,习相远”所描述的正是这一现象,《性自命出》则将其表述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1]105。
可见,对自然人性论而言,教育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关键,这其中又以礼乐教育最为重要。《乐记》指出,为了解决“物至而人化物”之弊端,“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2]986可见,通过礼乐教育,圣王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所遵守的行为准则,它使得人的喜怒哀乐之情能“发而皆中节”,进而能陶冶人性,成就君子人格。这便是礼乐教育的意义。故而孔子告诫其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乐记》也认为,“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二者都在强调礼乐教育在人格塑造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具体地说,礼乐出自人情并作用于人情,情是礼乐教育的着力点,即“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在自然人性论中,情是心与物的交汇点,是沟通内外的中间环节。《乐记》又称其为“心术”,并认为“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行焉。”[2]998情产生于人与外物接触之后,它源自于人性,又指向外物,因而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人性对外物的好恶须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另一方面,外物只有通过作用于情才能影响人性。礼乐教育也不例外:礼乐由圣王制定,而圣王制礼作乐所依据的正是自身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的情感。而对于常人来说,礼乐是外在于自身的,需要通过礼乐教育习得之,以此来约束和引导自身的情感,弥补人性中缺乏“喜怒哀乐之常”的弊端,塑造完善的人格。
二
虽然礼乐教化的对象都是人情,然而两者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制礼”的目的是确立社会等级,维持社会秩序,即“礼义立,则贵贱等矣”;礼教则侧重于对不当情感的约束与节制,是由外而内地控制,使人产生敬畏之情,即《礼记·坊记》所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2]1281;“作乐”的目标则是达成上下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内在情感的和谐一致,即“乐文同,则上下和矣。”故而,乐教是由内而外的引导情感,将其直接引向美善合一之境。
在自然人性论的语境下,虽然礼与乐在作用机制上存在差异,但二者皆为成就理想人格所必须的修养方法。由于自然人性论认为,性并不包含先天的道德属性,因而由性而发的情在价值上也处于中立地位,既可为善也可作恶。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既有对于恶的禁止,也有对于善的充拓。事实上,前者一般由礼教来承担,后者则与乐教相对应,礼乐相结合恰好涵盖了情之发动的所有可能。
具体而言,儒者对礼及“礼教”有三方面的说明。首先,礼的直接目的在于节制不当的情感与行为。孔子曾将“克己”与“复礼”相并列,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观点。可见,在夫子眼中,“克己”与“复礼”是同一过程。此处的“己”应理解为“私欲”,故而,用“克己”来说明“复礼”,就意味着礼更多地表现为对于私欲的克制。这并非是禁绝欲望,而是将其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孔子对于礼的理解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儒者所继承,《乐记》认为,“礼者,所以缀淫也”[2]997,明确肯定礼的作用在于制止人的过当行为。进一步,《乐记》以饮酒之礼为例,说明了用礼管束人情的必要性:
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2]997。
饮酒本非祸事,然而现实中人们往往缺少节制而饮酒过量,以致神智不清,行为缺乏约束,进而屡屡闯祸,这就凸显了制止嗜欲的重要性。为此,先王制定了饮酒之礼,通过往复的跪拜、揖献等一整套礼仪制度,培养宾主双方的恭敬之心,以裁制由饮酒而产生的愉悦之情,使其“发而中节”,合乎社会规范。故此,《乐记·经解》云,“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2]1257
其次,制礼须本于性情,稽于度数,合于天地之道,以分别高低贵贱,明确等级与秩序。《性自命出》云,“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序则宜道也。又序为之节,则文也。”[1]106礼根源于圣王合理的情感,但具体的制度还需要“当事因方而制之”,即考虑事物的种类和性质并予以恰当的处理。其中,至关重要的长幼尊卑之序必须合乎天道。《乐记》亦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和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2]1000,同样认为礼仪的制定既要本于性情,又须依照事物的度量分限。具体地说,制礼所要考虑的“度数”及其关系依次为,“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2]569这些度数及次序所依据的是天地之道,即“礼者,天地之序也”。由于天地生养万物的过程本身即产生差异、分别与秩序,而礼又本乎天道,因而礼制同样肯定差异与分别,其最终旨归必然是“明贵贱之分”。
第三,礼教的目的在于培养学者庄重严肃的仪容,这体现了一个人良好的修养。既然礼为天地之序,那么礼教旨在培养人对于秩序的尊重,而这表现为庄重严肃的仪容。儒家对此十分重视,《论语》中形容孔子的仪表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既庄敬严肃又和蔼可亲,这正是夫子深于礼的表现。《乐记》云,“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2]1030这里的“致礼”乃是“礼教至极”之义,这是说一个人若长期受礼教的熏染,动容中旋无不中礼,则其仪容自然庄重严肃,给人以不怒自威之感。《礼记·经解》亦云“恭俭庄敬,礼教也”[2]1255,同样认为礼教着力于端正人的仪表,使其恭敬而庄重,无轻浮之态。在儒家看来,庄重严肃的仪表反映的是人对于外在事物及他人的认真态度,这是其理想人格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然而,从自然人性论的立场上看,礼及礼教的这三方面特征都指向对人性的限制。如前所述,构成人性的是喜怒哀乐之气,它产生了对外物的好恶之情,而礼及礼教所宣扬的则是恭敬的态度及对秩序和等级的尊重。这两者并不一致,甚至毋宁说,在多数情况下礼教与人性是对立的,因为前者需要对情感加以裁制,使其不能随意地流露。这种对立使得两者始终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因而礼教很难让人的内心感到顺畅条达。另外,由于礼教偏重于外,对于人的心理状况关注较为有限,因此很容易流于形式,导致人格的虚伪。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心的所思所想不一致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显然与道德修养的目标背道而驰。这些事实都说明德育单纯依靠偏重于外的礼教是不够的,还需要另一种由内而发,能够引导而非抑制喜怒哀乐之气及好恶之情的教育方法,内外结合才能相辅相成。《乐记》与《性自命出》的作者同样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们在肯定礼教意义的同时,更为强调乐教的价值。
三
如果说“礼”的根本特点是“分”与“别”,那么“乐”的核心特征则是“和”与“同”,“乐者,天地之和也”。后者强调的并非是明晰等级与秩序,而是统和不同群体的情感,达到和谐一致的状态,即“乐文同,则上下和矣。”[2]987这种和谐一致的情感是人性中的喜怒哀悲之气自然而然地,恰如其分地流露,因而“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无过无不及,也不包含任何强制性。相对于礼,乐更能深入人心。同理,乐教也不同于礼教,它通过由内而外地对情感进行引导,使之由审美情感过渡到道德情感。
儒家对于乐的性质以及乐教的作用机制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赋予了“乐”这一概念以特定的内涵,即具有道德教化功能的乐曲。与“乐”相关的概念还有“声”和“音”,儒家的乐教思想对此三者既做出了严格的区别,又阐释了三者内在的关联,“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2]978可见,“声”、“音”、“乐”三个概念的内涵是不断扩大的:“声”产生于人性与外物相接触之际,是情感的直接表现,受到外物的影响而存在着差异。声是孤立的,只有当不同的声相互应和时才产生变化,进而出现节奏与旋律,这便是音或者乐。因而,“声”是构成音与乐的元素。
儒者真正关注的是“乐”和“音”的区别。《乐记》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2]982可见,乐与音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合乎伦理规范。《乐记》进一步明确了音的特点,“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2]978可见,音即“成文之声”,这意味着相对于声,音的特点在于有节奏,是一个结构完整而连贯的整体,能够系统地表达人的某种情感。总而言之,音具有人文性,但是其在价值层面却是中立的,既有“德音”亦有“溺音”。
德音谓之乐,乐与道德情感相一致,具有教化功能,即“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2]998乐是由圣王在治定天下之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雅颂”而成,具有陶冶性情,教化百姓的功效,是儒家成就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故而,《乐记》云“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2]982能辨别音的节奏,知晓音所蕴涵的情感,说明能够体察音的人文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之处。而能够分辨多种乐曲中不同的价值取向,并自觉地趋向于德音,远离溺音,则意味着其人明于是非曲直,深于礼乐教化,标志着其具有健全的人格。在儒家语境下,能够达到这一状态则为君子。
乐由圣王所作,表现的是圣王的道德情感,然而“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兴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2]1003由于人无喜怒之常,因而德音与溺音都能作用于人,并产生相应的情感。故而,乐教的目的是通过赏乐让德音直入人心深处,引导人产生相应的审美情感,由此自然地过渡为道德情感,并自觉地澄汰溺音对人性造成的不良影响。可见,乐教的作用机制包含三部分:外在的德音、由德音而产生的审美情感以及由审美情感油然而生的道德情感。《性自命出》云:
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观《赍》、《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敛。咏思而动心,喟如也。其居次也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始其德也[1]106。
《乐记》亦云:
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2]1013。
以上两段文字详细描绘了乐如何使人产生审美情感,以及这种审美情感如何进一步转化道德情感的过程。首先是外在的乐,即笑声、歌谣、琴瑟之声,《赍》、《武》、《韶》、《夏》以及由弦、匏、笙、簧、拊、鼓所作的德音等,它们或者舒缓而闲适,或清丽而婉转,或宏大而壮美,其共同点即“和正以广”,绝非靡靡之音,不会激发人不当的欲望。其次是由乐而形成的审美情感,即喜、奋、叹、作、敛等。由赏乐而产生的审美情感指向内心的条达舒畅,这种舒畅之感并非是嗜欲得到满足后的一时之快感,而是由内心的平和、安宁和肃穆而自然感发的愉悦之情。《乐记》将此描述为“悦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2]1038这样的愉悦之情不会引发人的狂躁之气,奸诈之心,而指向心与身、心与物的和谐。同样,道德也是通过约束自己的欲望,使之合乎社会规范,进而达成己与人,个体与群体间的和谐。因此,和谐是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的共同旨归,以此为中介,前者可以直接地、毫无障碍地过渡为后者。学者若能长期欣赏雅乐,自然能反善复始,体会到其中的教化之义,从而追慕古圣,修身齐家,动静语默皆合乎道德,即“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2]1006徐复观先生则专门对“化神”作了解释,认为长期受到雅乐熏陶的人,他的人生“是由音乐而艺术化了,同时也由音乐而道德化了。这种道德化,是直接由生命深处所透出的‘艺术之情’,凑泊上良心而来,化的无形无迹,所以便可称之为‘化神’。”[3]达到了“化神”即标志着乐教的完成,“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2]1005换言之,乐教最终使人心平气和,行为合乎礼仪,即“乐,礼之深泽也”。二者相结合则意味着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处。
综上所述,基于自然人性论的儒家乐教思想的作用机制即通过雅乐来感动人心,直入人性深处,使人产生愉悦的审美情感,并使得审美情感不断地趋向和谐之境,由此自然而然地过渡为道德情感,并引导人远离溺音,祛除由逆气产生的“悖逆诈伪之心”,最终成就理想人格。相比于礼教,乐教重在引导情感而非禁止情感的宣泄,因而没有过多的强制性,不会让人感到人性遭到压抑而难以接受。
四
由于自然人性论认为,人性并无道德属性,因此与孟子重在充拓人之四端的教育方法不同,对于前者而言,礼乐教育是成就理想人格的主要途径。“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对于人性,礼由外而内加以限制,乐则由内而外进行引导,二者相结合,目的在于使人获得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使得情感能不受外物的诱惑流于放诞,而恰当地、有节制地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
儒家对礼乐教育的重视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意义。今日的礼仪制度及高雅音乐在内容上与先秦相比已经有了根本区别,然而时至今日,礼仪教育依然能培养人的恭敬之心,强化人的秩序意识、规则意识;同样,高雅音乐也仍然能舒缓人心,陶冶情操,提高人的审美品位,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个人素质,成就理想人格。因此,儒家礼乐教育中积极意义值得今天的学者充分地加以开发。
[1]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24.
——长春市第一中学学校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