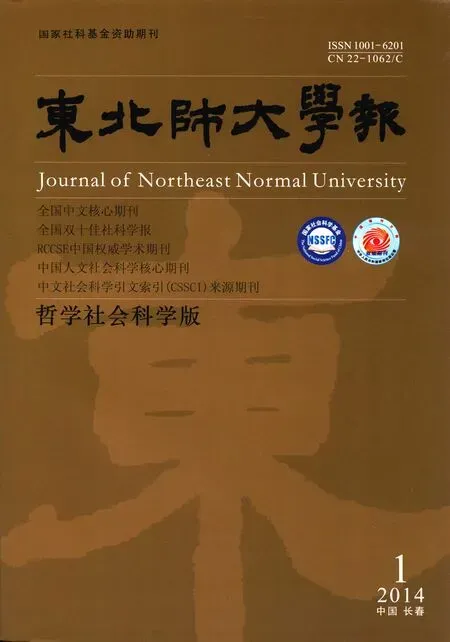儒玄思想视阈中的嵇康论体文
米晓燕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两汉以来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在魏晋之际遭遇到了玄学思想的猛烈撞击,这种撞击在思想领域结束了大一统的经学桎梏,促进了人们对哲学问题更为多元化的思考,因而魏晋玄学成为学界经常谈论的学术话题。但是,人们似乎过多地看到了玄学的猛烈,却往往忽视了儒学的坚韧。其实,这次撞击不是一种取代另一种,而是在撞击中各自迸发出色彩绚烂的辉光,交相辉映。思想的变化必然在文学的创作中反映出来,这种多元化儒玄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呈现出时代的特殊性。其中论体文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嵇康的论体文充分反映出这一时代特征。
一、儒玄共存的时代文化特点
汉代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在思想文化界居于主流地位。但是东汉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的黑暗和皇权的衰落,与之相互依托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影响,其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其对于思想文化的统治力也逐渐削弱,道家思想逐渐抬头,成为文人避世的精神资源。以《老子》、《庄子》和《周易》做理论基石的玄学思想,逐渐兴起并完善起来,并在魏晋之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玄学的产生是一个长期酝酿而又特殊开始的过程。汉末的纷乱导致了儒学的衰微,人们个性意识的觉醒、曹操名法为主的思想进一步促进了思想的解放。正始时期司马氏与曹氏在“萧墙”之内的权势斗争,将知识分子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怀有儒家济世的理想,却在现实面前碰了壁;积极的入世,往往得到的是政治的苦酒,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于是道家思想重新抬头,知识分子希望在老庄的庇护下远离政治,明哲保身,逍遥远祸。玄学终于在儒道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很快获得思想界的认可,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曹爽主政时期,重用了大批玄学名士,更使得玄风大炽,以何晏王弼为首的名士们“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1]从上层社会到民间文士,纷纷以玄谈为贵。
玄学虽然占据了主流,但是儒学并没有消亡。当时的文人名士仍然将注、释儒家经典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来完成,比如钟会作《周易尽神论》、《周易无互体论》、《孝敬》,司徒王朗作《春秋左氏传》等。这时期的学者甚至仍然将儒家经典作为学问的基础,去加以阐释和解说。比如玄学领袖何晏就主持撰写了《论语集解》,对此清代钱大昕评价说:
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竞事虚浮,不修方幅,在家则丧纪废,在朝则公务废。而宁为此论以箴砭当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是答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入儒林。若辅嗣(王弼)之《易》、平叔(何晏)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2]。
尽管是玄学家,他却对一部儒家经典做出了说经之家也难以达到的解读高度。在这部书中,何晏以玄解儒,在关键地方,运用玄学思想做画龙点睛的解读。王弼也说:“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及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3]。儒学的仁义、忠孝都是有必要存在的,只是要发乎自然,只要是发自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可取的。即自然为名教之本,名教是自然的外在表现。
玄学之花开在儒学的秋天,如傲霜的秋菊,是另一类的风景。王肃是以儒家思想立身,以阐释儒家经典著作立业的经学家。他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儒家经典作注,并整理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他在政治上为司马氏效劳,制定礼仪,成为后来西晋建立礼仪规章的理论基础,但他的经学著作中已经显现出玄学思想的雏形。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指出王肃的学术思想中兼采儒玄的特质:“汉儒说经各守师法,至郑君(郑玄)遍治经纬,兼通古今,择善而从,不执一说,蔚为大师,其学足以易天下。子雍(王肃)继起,远绍贾(逵)、马(融),近传父业,乃专与郑(玄)学为雠;其言心之精神是谓圣,又为玄学之宗。”[4]吴承仕可谓明见,其实这种玄学特征,早在他成长之初就已经显露端倪了。《三国志》本传记载:“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扬雄《太玄》阐述的是道家思想,《太玄赋》中就有:“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之句。他跟随宋忠学《太玄》并且能够为之做注解,可见其思想中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和深刻理解。另外,王肃的学术著作中,《周易注》排除章句,注重义理,援道释儒;《孔子家语》着力于以道家思想论证补充儒家经典[5]。这些都证明了在经学大师这里,玄学也已经渗透出来。
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玄学家们主张的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表面背离了儒家传统,纯任自然,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都深怀儒家思想。最为放诞的阮籍,不希望儿子步自己的后尘,最为狂傲的嵇康也教子以礼。刘伶超脱自然以酒放旷,向秀玄远深情都展现出玄学思想对其的影响,但王戎、山涛却更多地表现出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想追求。
同样,以儒治国的司马氏政权中,司马师是当时的玄学名士①《晋书·景帝纪》记载:“(司马师)雅有风彩,沉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在用人方面也表现出玄学思想影响下的放达旷远;钟会作为司马氏的核心成员之一,作玄学著作《四本论》。他既跟随服膺儒教的司马氏,但却还保持着对玄学的热情,并希望得到玄学领袖嵇康的肯定②《世说新语·文学》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司马氏集团的得力干将傅嘏表现出标准的儒者风范,但同样也谈玄论理:“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倡。”[6]傅嘏、荀粲、裴徽都是这一时期的玄学家,在傅嘏与荀粲为玄学的问题问难论辩,彼此争论却不解释的时候,而裴徽则替两个人解释玄理,沟通双方的心意,既说到了二人的心里,又沟通两个人的理论,往往让大家气氛和谐,心情都很愉悦。西晋重臣羊祜一生积极事功,仁义对人,儒家的仁义礼智、恭廉俭让在他的身上有很明显的体现。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羊祜淡泊名利,热心《老子》的做法又是受了玄学思潮的影响。唐人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著录,注解《老子》诸家中有“晋仆射太山羊祜”,其文“皆明虚极无为之理,理家理国之道”,《老子》作为“三玄”之一,得到羊祜的喜欢,并为之做注,也可见羊祜对玄学的认同与积极的参与。另外,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晋书·杨祜传》)可见,玄风影响之下的游燕山水之风对羊祜也有所影响。可见在政治领域中儒学的倡导和施行,并不能阻挡玄学的发展脚步,它在民间已经蔚然成风。
综上可见,从曹爽到司马懿,虽然有显有隐,但此消彼长而又儒玄并存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形成了魏末时期特殊的文化环境,并进一步带来了文学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的特殊变化。
二、儒者之心与嵇康的论体文
作为“竹林玄学”的领军人物,嵇康尽管自己也曾说少时“不涉经学”、“长而好老、庄之业”,表现出适情任性、崇尚自由、随顺自然的玄学家的个性,但是实质上嵇康对儒家思想却具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尊崇。
首先,他与传播儒家思想的最高学府——太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上书,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124)在长安设太学,主要讲授儒家经典。《晋书·文苑传》记载,赵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而请问姓名。康曰:‘年少何以问邪?’曰:‘观君风器非常,所以问耳。’康异而告之。”石经刻于石碑,主要用以传播经典。嵇康在太学抄写儒家石经,这本身就是将儒家经典视为圭臬的表现。《晋书·嵇康传》还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能够得到学经信儒的太学生们如此的拥戴,如果仅仅是一位冲虚旷雅的玄学名士,相信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其次,嵇康曾撰著有《春秋左氏传音》。《隋书·经籍志》经部载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只可惜,嵇康所撰的《春秋左氏传音》现已散佚,清代学者马国翰据《释文》辑得五节,据《史记索引》和宋庠《国语补音》辑得二节,录于其《玉函山房辑佚书》经部春秋类中。《春秋左传》为儒家经典著作,而嵇康对其关注并上升到研究层面,说明他对儒家经典著作的重视。另外,从他现存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他对《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相当熟悉,且运用自如,时时征引和化用。如《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其一:“鸳鸯于飞,肃肃其羽。”“鸳鸯于飞,啸侣命俦。”既化用了《诗·小雅·鸳鸯》的成句,又自然贴切的运用了鸳鸯的意象。其五:“寤言永思,实钟所亲”,是借用《诗·邶风·终风》中“寤言不寐,愿言则怀”之语,表达对兄长的思念而难以入睡的心情。他在《琴赋》中说:“若和平者听之,则怡养悦愉,淑穆玄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颜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列举了在音乐的影响下,一系列被儒家视为仁者的人物伯夷、颜回、比干、尾生、惠施、石奋的事迹,作者信手拈来,全无阻滞。本文又说:“总中和以统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动物,盖亦弘矣!”以此表明琴的中和之性,而其思想实是源于《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的思想是古代道德修养的较高阶段,也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这些都说明,嵇康受到了儒学的教育和思想的熏陶,并浸润于他的生命之中。
再次,嵇康入狱后所作的文章真实的展现了嵇康的内心世界。嵇康被钟会构陷下狱,面对生死,他流露出最原始的本性和心底最真实的感情。在《家诫》中,他对儿子谆谆告诫,不厌其烦,完全不像平时的任诞。明人张溥说:“嵇中散任诞魏朝,独《家诫》恭谨,教子以礼。”[7]一句“教子以礼”,展露了嵇康对名教礼法遵从的内心真实世界。鲁迅对此曾论道:“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8]他相信礼教,只是不满于司马氏政权借经学、名教与礼法做名堂,做统治的工具,因而才在《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等论体文中猛烈抨击“正统”儒学的虚伪与卑劣,汪洋恣肆地直斥六经,痛斥礼法,非汤武而薄周孔。而其真实的内心还是希望“怀抱忠义”,坚定儒家世教的立场。
嵇康对名教的坚定信仰,加重了其对司马氏政权伪名教的厌恶,因此他不惜与好友山涛绝交,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态度鲜明的表达了自己与司马氏政权不合作的态度。他的《管蔡论》更是将矛头直指司马氏父子。他在文中为管叔、蔡叔翻案,认为他们原是“服教殉义,忠诚自然”的贤者,所以“文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而并非因为亲情。嵇康在文中说:“且周公居摄,邵公不悦。惟此言之,则管、蔡怀疑,未为不贤,而忠贤可不达权;三圣未为用恶,而周公不得不诛。若此,三圣所用信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明代张采《三国文》评论此文说:“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马执政,淮南三叛,其事正对。叔夜盛称管、蔡,所以讥切司马也。”张采的评论,非常精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嵇康对周公的微辞,表达的是对以周公摄政自比的司马氏父子的不满。
嵇康的《圣贤高士传》集中体现了其对上古以来圣贤高士的崇敬之情。这正如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畅想的理想人生一样:“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在嵇康看来,建功立业之后,功成身退,重返自然,这才是理想的功成。他作《高士传》,撰述了范蠡、屠羊说、鲁连这些功成身退、奇伟高蹈﹑不慕荣利的高士,就是这种心理的直接反映。他希望建功立业,然而却因为自身孤高的品性,看不惯司马氏的残酷杀戮,又因为自己与魏室姻亲的关系,使他被迫放弃了出仕的理想而走向竹林,锻铁谈玄,追求高义。
笃信儒教的嵇康,在乱世黑暗之中找不到重建光明之路。内心的激愤无处排遣,惟以老庄思想来化解,在玄学的妙解论难中,在对前贤高士的仰慕中寻找安放心身的灵祗。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自述了自己由内儒转而外玄的过程和原因:“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
三、玄谈之风与嵇康的论体文
魏晋之际,论体文格外兴盛。对此,刘永济先生认为,魏晋之际论体文兴盛的原因,是“人竞唇舌”的玄谈,带动了“论著之风郁然兴起”[9]。事实的确如此,这一时期像何晏的《道德二论》、《无为论》、《无名论》、《圣人无喜怒哀乐论》,王弼的《难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钟会的《四本论》,都是以论辩的形式谈玄说理。而魏晋清谈之风的盛行,对论体文的风格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他们的论体文创作以玄谈内容为主,阐释观点,进行辩论;另一方面,在著论中,他们将论体文作为玄谈内容的延续和深化,多方面运用了玄谈的辩论方法。嵇康的论体文,则更是在此基础上,研习玄理,考辨名实,表现出尚玄崇理的显著特征。而且从形式上,嵇康论体文也绝大多数是与他人相互辩难①嵇康的论体文与其他作者辩难的情况:《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是与向秀的《难养生论》辩难的作品;他的《难自然好学论》对应的是张邈的《自然好学论》;他的《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对应的是阮德如的《宅无吉凶摄生论》、《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他的《释私论》对应的是曹羲的《至公论》;他的《明胆论》是与吕安互相辩难争论的内容,合成一篇。参阅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48。。
嵇康对老庄的自然思想颇为尊崇。在《养生论》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认为神仙是存在的,虽然神仙的得成有其天赋自然秉性:“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但养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坚信养生可以长寿。但想要通过养生以致长寿,便要遵循自然之理,顺应物性,达到形神相亲的玄学高度:“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强调形神关系,并指出欲“形”长存,必须养“神”,而养神的关键则在于“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即抑制欲望,淡泊名利,静心养性,用玄妙的“道”持守自己,用和谐平顺的方法调养自己。
嵇康养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音乐,因而他的论体文于此颇多论述。在他看来,音乐是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养生论》说:“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这是因为音乐的本质是“和”,有助于养神。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强调自然的阴阳变化在本性上是永恒的和谐的,这个朴素的哲学命题被嵇康用以阐释自己的音乐理论,因此他多次谈到音乐与“和”的关系。
嵇康认为声音的“和”是来自于自然,自然的音乐的本体是阴阳的协调,所以与人的哀乐是没有关系的。针对秦客提出的音乐中含有人的哀乐情感的命题,嵇康做出反驳。他认为音乐之中不含有人的哀乐情感。这是因为首先音乐是自然的产物,哀乐之情是人的心理活动,二者“殊途异轨,不相经纬”,不是同一个理论范畴,不存在交集;音乐对人具有的巨大感化作用是音乐和谐的旋律引发了人的个体自身已有的情感,并非是音乐本身具有哀乐的特征。秦客代表的是儒家正统的音乐思想。即《礼记·乐记》所阐述的:“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将音乐与哀乐,乃至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认识。认为音乐具有确定尊卑,控制情欲,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而嵇康的观点则体现了其崇尚自然的一贯主张,他借用玄学的“名实”辨析,对“音乐”这一概念做出自己的解释。他从玄学的思辨出发论证了这个问题,令人耳目一新。嵇康的音乐思想,究其本质也是道家天道自然观的直接反映。
嵇康的论体文不仅在思想上受道家影响,在行文论辩的方式方法上同样如此。其《养生论》以批驳世人谬说起笔,清新醒目;继而提出自己的养生观点在于形神相亲,然后层层论证分析世人不能长寿的原因,并提出了养生者的做法。文章结构严谨,立意新奇,析理绵密,广征博引,纵横阔论,尽显庄子洒脱恣肆的风格特点。在辩难时,嵇康的论体文采用了玄学清谈中的辩难方法。《答难养生论》中说:“又责千岁以来,目未之见,谓无其人。即问谈者,见千岁人,何以别之?欲校之以形,则与人不异;欲验之以年,则朝菌无以知晦朔,蜉蝣无以识灵龟。然而千岁虽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则狭见者谓书籍妄记。”养生本就是富有争辩的话题,而嵇康这样首先假设未知的千岁之寿是成立的,将之作为已知条件。然后反过来推理,即使有也是无法分辨的,即以所谓“已知”推断“未知”,甚至是拿未证结论作论证前提的方法,更见出玄学清谈演绎推理的特点。无怪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饰,想于文亦尔,如《养生论》……类信笔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续,然独造之语,自是奇丽超逸,览之跃然而醒。”[10]
嵇康的论体文以玄谈为主要内容,以论难为主要形式,以行文的汪洋恣肆、犀利有力呈现出对庄子行文风格的模仿和超越,有力的展现了魏末时期玄学发展的进程。但与此同时,他内心笃信的儒学根袛,在作品中,在行为中总是不可抑制的流露出来,时隐时现,如飞龙探爪,让人得窥真心。这些因素集中体现在他的论体文中,使之呈现出既有儒家的建功立业、温柔敦厚的外观,又多了玄学家汪洋恣肆、洒脱犀利的气势和美感,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
[1]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7:310.
[2]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文集·何晏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9-30.
[3]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95.
[4]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42.
[5]秦跃宇.王肃儒道兼治与玄学发微[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10):10-14.
[6]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7:236.
[7]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223.
[8]鲁迅.鲁迅全集·而已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4.
[9]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论说[M].北京:中华书局,1962:65.
[10]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