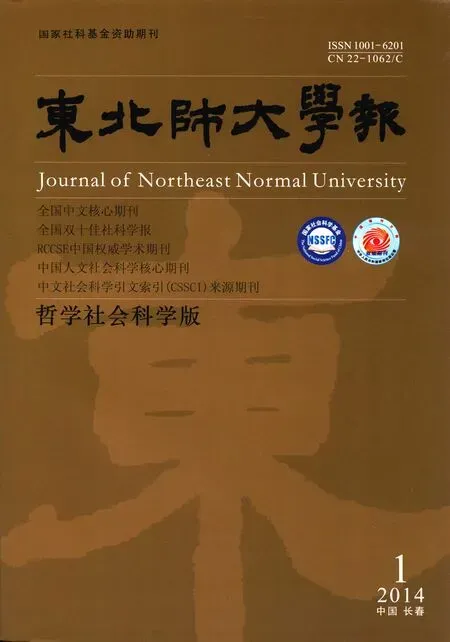从利科诠释学视域看葛浩文的文本翻译
朱锋颖,胡 玲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2012年,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成功也将人们的目光投到了其作品的英文翻译葛浩文身上。从1895年开始设立诺贝尔文学奖到现在,获奖的作家大多数都来自于欧洲和北美。亚洲作家很少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写作的语言问题:他们普遍使用的不是英、法、德等世界和诺贝尔评选的主流阅读语言,其作品需要经过翻译才能被其他国家的人阅读。而语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重要因素,因此好的翻译往往可以成就一个作家。莫言的大多数作品都由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翻译成英文,再经由其他译者将英文译本翻译成德、法等文本。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上,莫言作品的翻译无疑是中国作家中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因此葛浩文的英译本对莫言作品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葛浩文目前是英语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被汉学大师夏志清教授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同时还被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喻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接生婆”[1]。从利科诠释学的视域分析葛浩文的文本翻译,我们可以找到葛浩文成功的哲学基础。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利科是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研究的权威。究其原因,一方面,利科是胡塞尔德文版的《观念》的法语译者和注释者,这个经历使利科成为现象学的研究专家,并影响了其一生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利科从诠释学的视域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并出版了《论翻译》的翻译诠释学专著,给翻译研究带来了诠释学转向。正如理查德·凯尔尼所言,“利科的思想代表着作为翻译的哲学和一种翻译哲学”[2]Viii。
利科的翻译诠释学是从形而上学的维度对翻译现象和翻译理论的研究,其基本范畴是翻译的主客体关系。利科的翻译诠释学强调翻译中的客体是“文本”,而非“语言”,翻译的本质就是译者对文本的诠释。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在翻译他者的同时也在生成自我,进行着自我的创造,同时也关照译文的读者,对读者进行诠释。利科建议翻译超越“可译与不可译”的理论选择与争论,转向新的选择——“译‘不可译’”的翻译约定性的建构。
利科认为,只使用母语进行写作和思想的人,很难令其作品获得普遍的真理性。原因在于单纯地去寻求真理的普遍性的愿望受到了自身历史及传统文化的限制而产生了局限性。只有通过在不同语言与文化持有者之间进行思想的对话,才能在自身的文化中发现他者文化的特点,并能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的特点,可以同时将相互文化的普遍性和潜力发挥出来。正是在翻译的实践工作中,开始着对于普遍有效性的考验。
一、翻译的文本诠释本质
在海德格尔之前,诠释学的学科定位在方法论领域。在古典诠释学中,作者及原初的意义是理解和诠释是否成功的标准。在这种视野下,理解和诠释的重心不是读者,即诠释者,而是作者。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发展了诠释学的存在论。利科则指出诠释学应该是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应该将三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利科认为诠释学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联的诠释过程的理论,文本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言谈[3]41。利科通过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方法,使文本在读者面前获得展示,如此一来,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就突破了主客体的关系,实现了两者的融合。因此,在利科的诠释学的哲学框架里,翻译是以文本为基础,以译者与文本对话为主的诠释,是译者与文本的融合。这种思想改变了长期以来翻译的地位,使译者而非作者成为翻译诠释活动的主体,同时译者的主体性的发挥还必须与文本相融合,二者是平等的。
翻译是一种诠释,是在另一种文本中重新创作同一文本。葛浩文所进行的翻译正是这样一种诠释,他的译本使原作得以在全世界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流通,将原作的意义进行着传播,他经由翻译所创作的新的文本获得了各种奖项,为原作思想及文化的传播作出了翻译者的卓越贡献。而与此同时,葛浩文作为翻译,在译本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对原作的诠释,这种诠释也得到了广泛的传达。
二、翻译的“语言友好”的伦理原则
传统的西方诠释学者一直到狄尔泰,所进行的文本诠释都希望能解释清楚文本与理解之间所必然存在的“历史间距”问题,即文本与解释由于所处的历史时间的差异,理解肯定会对文本产生偏见或者误解。这并非主观故意,而是历史间距存在的结果。所以要想获得对文本正确的诠释,必须消除历史间距。而利科的观点则不同于传统的诠释学者,在他看来,文本是理解主体与写作主体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文本保留着历史的真实性,理解主体与写作主体正是在这种距离中进行着有效的交流。好的文本诠释者不应该从个人主观意愿出发,而应该是从客观存在的历史间距出发,在文本的写作与理解的互动之中,将文本从其封闭的历史系统中解放出来,成为面对读者的开放性意向对象。在这种双向交流的过程中,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获得不断的发挥,读者以此成为自我反思与创造的主体。因此作为翻译者,既是文本的诠释者,必然带有其个人创造,同时又是新的译文文本的写作者。好的翻译应该包含对他者的开放性元素。所有翻译都包含着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对话就意味着欢迎差异。这就是利科提出的翻译的“语言友好”的伦理原则。
葛浩文进行中国文学英译的过程遵循的正是利科所描述的诠释的过程:一方面他作为读者在诠释他者的文本;另一方面,他作为译者又在生成自我,进行着自我的创造,成为译文的作者。因此,作为译者的同时也关照译文的读者,对读者进行诠释。翻译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葛浩文既与汉语文本作者进行着对话,对文本进行着理解与诠释,同时又与翻译的目的语——英语的文本读者进行着对话。就如同葛浩文自己说的那样,好的翻译是再写作的过程。葛浩文认为,中国作者的著作都是为中国人写的,而好的翻译要懂得如何给外国人翻译,所以这个过程就是重新写作的过程。译者对文本作者的诠释过程也是对他者的理解过程,对原作的弱点及特点都要有深刻的了解。同时对译文的读者也有深入的探究,对原作文本和译作的读者所继承的不同文化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因此,葛浩文不是按照文本逐字、逐句进行翻译,而是对文本进行整体诠释后再翻译成目的语,这种整体性译文文本贴近美国人的审美情趣,引人入胜而更易被读者接受。
以莫言作品为例,其法文、德文等的译本都是以葛浩文的英译本为母本进行的翻译,所以葛浩文的英译文本又成为母本而要面对读者的诠释,其译者的身份也转变为作者。译文文本无疑带入了译者的历史,与读者形成新的历史间距。译者翻译时要关照作者原意、读者喜好、编辑建议和自己的理解,在其中寻求平衡的难度远远超出原作者。莫言作品的英译本的成功也与他对翻译的开放态度有关。葛浩文说:“莫言理解我的所作所为——让他成为国际作家,同时他也了解在中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未必在其他国家会被接受,所以他完全放手让我翻译。”[4]无论是莫言还是葛浩文,其文本获得的成功都与其对他者的开放和对差异的包容与接纳的态度有关,与他们坚持的“语言友好”的翻译伦理密切相连。
三、翻译的“译‘不可译’”的约定性建构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使翻译研究从对翻译策略的实践性的具体研究上升为对翻译性质的哲学本质思考。利科对“可译性”所认为的人类经验具有相同性,人类语言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他指出:“文化的亲缘性掩盖了对等的实质,对等是经由翻译产生的而不是翻译所预设”[5]35。利科认为文化的亲缘性是在长期的文化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只有持有不同语言的主体经历了长期的历史交流,语言之间的对等才得以实现,这种对等绝非与生俱来的先验存在。而将“对等”设定为翻译的完美的标准,则是不实际的。要判断译文和原文之间是否“对等”,不应该以语言是否“对等”作为标准,而应该以“意义”对等作为标准,而这种意义的对等,则需要借助一种与译文和原文相对独立的第三种文本。
文本的“不可译性”存在于语法、词汇及语音等各个语言层面。语言的多元性,是翻译无法逾越的文本的“不可译性”。由此,利科提出了翻译的“译‘不可译’”的理论。即翻译的成就,亦即翻译的风险就是对原文的创造性“背叛”。其翻译就是要将不同语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不可译之物找到可译之物,通过翻译借以建构“可比之物”,化“不可译性”为“可译性”。从古至今的翻译的历史实践表明,所谓的语言的“对等”只是一个两种语言之间是否存在约定性的问题,如果语言之间具有事先的约定性,那么就是如何进行这种约定性的运用的问题;而如果原文与译文之间没有事先的约定性,那么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力去建构这样的约定性。这不是语言的绝对“对等”,而是意义的对等的约定性的建构。由此可见,真正好的翻译所努力达到的目标应该是没有同一性的对等,并且即使这样的对等也不是先验或者是事先预设好的,而只是人为界定的而已[6]62。
葛浩文的翻译实践正是努力建构英汉两种语言的“可比之物”,实现翻译的“对等”的过程。葛浩文说:“我忠实地在为两部分读者服务,这一信念推动我兴致勃勃地将中国作品译成易读、易懂、易找到销路的英文书。”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的历史性,文本的历史间距都使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加以改变成为必然。因此对译者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原文的文化与译文的文化之间找到相似之物,从而建立约定性,这也是评判译文好坏的一大标准。葛浩文文本翻译能被广泛承认,正是因为他对汉语所代表的源文化和译文的英语所代表的西方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从而策略性地建立两种语言的约定性,实现翻译的“对等”。使译文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如葛浩文所译的莫言的《愤怒的蒜苔》中的一段原译文比较:
原文:他说:“杏花,你别糟蹋了那根蒜苔!一根能值好几分呢。”
女儿把蒜苔放在了身边,大声问:“爹,拔完了吗?”
他笑了笑,说:“要是这么快就拔完,可就毁了,那能卖几个钱?”[4]69
葛浩文的译文是:
“Careful with that garlic,Xinghua,”he said,“Each stalk is worth several fen.”
She laid it down and asked,“Are you finished,daddy?”
“We'd be in trouble if we were,”he said with a chuckle.“We wouldn't earn enough to get by.”[7]70
从这短短几行的译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葛浩文译文一方面极忠实于原文的精神,即忠实于原文人物的神态口吻,而非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在这种忠实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再创造,使译文读起来流畅自然,符合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如把原文“你别糟蹋了那根蒜苔!”译作“Careful with that garlic”,葛浩文在此并不计较字面表层语言的对等,而是忠实语言深层意义,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做了增、删或改等处理。
葛浩文曾说过,莫言作品最难翻译的部分是其“乡土味”[8],也就是文化的特征,因为文化的历史性,使文本产生的“历史间距”是最难诠释的。葛浩文长期的中国文学的英译实践使他逐步确立了两种文化间的“可比之物”,通过增删、改写等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翻译的“对等”。而莫言作为原作者对其文本的诠释的开放态度,葛浩文以读者为主体的诠释理念,都使葛浩文翻译的“对等”确立得更加容易一些。比如,当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时,觉得原文的结尾太过悲观,不合美国人的口味,就和莫言沟通。最终说服了莫言修改,使得小说的英文版本呈现出了另一个结尾。
四、小 结
利科的文本翻译理论把西方哲学中的结构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分析哲学等不同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从而推动了现代翻译诠释学的发展,对当代理论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利科翻译诠释学的视域看葛浩文的文本翻译,葛浩文的中国文学英译本的成功是有翻译诠释学的哲学基础的,是利科的翻译诠释学在实践维度上的极好的证明。在其翻译诠释实践中,葛浩文充分发挥了其作为读者的主体性,在翻译中坚持着“语言友好”的伦理原则,在翻译他者的同时也在生成自我,进行着自我的创造,建构了翻译之“译‘不可译’”的约定性,不仅使原作在以英语为主流阅读语言的世界获得了成功,而且其再创造的译本也使自己获得了创作上的成功。葛浩文的成功也为中国培养自己的优秀的翻译人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1]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
[2] Kearney,R.Introduction: Ricoeur's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in Ricoeur,Paul.On Translation.[M].Trans.EileenBrenan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3]Ricorur,P.Sur la Traduction[M].Paris:Bayard,2004.
[4]莫言.愤怒的蒜苔[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Ricoeur,Paul.On Translation [M].Trans.Eileen Brenan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6]方兴.从保罗·利科的“译‘不可译’”看翻译的可能[J].法国研究,2011(3).
[7]Mo Yan.The Garlic Ballads[M].Trans.Howard Goldblatt,Penguin Books,1996.
[8]佚名.专访莫言作品翻译家葛浩文:莫言小说的乡土味最难翻译[EB/OL].2012-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