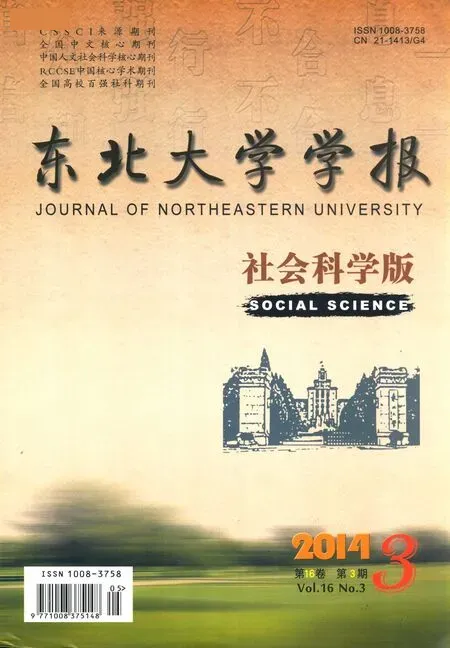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理论溯源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 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与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有着类似的理论渊源,二者均是女性主义学术向STS领域拓展的产物,均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根基,同时受整个后现代主义科学思潮与技术批判的影响;不过二者内部均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别借鉴和吸收了不同的思想资源或分析工具来发展自身的理论。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是女性主义技术理论的具体进路之一,它区别于其他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进路的重要之处在于同时坚持技术与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及其相互形塑关系,体现了更彻底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本文在此不试图勾勒出关于其理论渊源的宏大谱系,而仅从微观视角对直接影响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的几个主要思想或理论进行具体分析,从中亦可窥见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及研究主题的变迁。
具体而言,对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技术社会建构论和技术文化理论。
一、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
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较早注意到技术领域女性相对缺席的状况,并将目光投向了技术史,希望通过填补更多的女性发明家和技术精英进入技术史的名人清单,来揭示女性对于技术所做的、不应被忽视的贡献。这类研究本质上还没有对女性和技术的范畴提出质疑,只能为女性进入技术领域的资格和能力提供经验辩护,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随着女性主义发展出社会性别理论,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善。
在女性主义视野中,社会性别(gender)是为与生理性别(sex)相区分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首先意指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赋予两性个体的社会角色、文化特征及相应的行为方式和规范[1]。女性主义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对男女在各个领域的差异提出新解释,而不只是从生理因素上找原因,后者容易陷入生物决定论的困境。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概念的内涵被进一步拓展。它或者被看成是组成男女之间社会和性别关系的文化结构,是一切形式的劳动分工的基础,这些分工将妇女、妇女工作及其价值同人类文化的主流标准割裂开来[2];或者被认为是社会将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及性别区分转化为人类活动产品的一整套组织[3];或者被认为是表达权利关系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且具体包括“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文化象征”“对象征意义做出解释的规范性概念”“社会组织与机构”“主观认同”四个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相关因素[4];或者被区分出社会性别符号系统、社会性别结构和个体社会性别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其中社会性别符号系统代表二元论的文化图式,它涉及二元论的性别隐喻,并使之与现实中理解的各种与性别差异毫无关联的两分法相对应,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社会性别结构是指诉诸于这种二元论的文化图式来组织社会活动和制度,在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划分出等级体系;个体社会性别则是指社会建构的、与性别差异的实在或概念不完全相关的个体身份[5]。
显然,社会性别概念作为一种分析范畴,旨在探讨造成各个领域包括技术领域性别问题的社会成因。对于女性主义的技术社会研究而言,这一分析范畴的运用意味着其研究不再仅以妇女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以探讨技术对性别身份、性别差异、性别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性别观念、性别关系结构、性别文化对技术的塑造为主要内容。简而言之,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从“妇女与技术”研究转向了“社会性别与技术”研究。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学者充分认识到了社会性别概念的上述内涵及其意义。在他们看来,社会性别不仅是区分人群的重要方式,也是特定场域中权力分配的重要方式;不仅指性别身份,更指性别关系、结构、文化及意识形态。考察社会性别上述内涵建构过程中物质因素的作用,以及反过来它们在技术建构过程中的角色,使得将社会性别与技术这两个范畴并置在一起进行研究 的 意 义 不 言 自 明[6]4-5。 科 伯 恩 (Cynthia Cockburn)和奥姆罗德(Susan Ormrod)更是明确指出,不能忽视哈丁提出的社会性别的三层内涵中的任何一个,否则就会导致女性与科学关系策略的失败;对于女性与技术的关系而言,也同样如此[7]6。可以说,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将社会性别视为“探讨文化与技术之间关系的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8]。
社会性别理论的运用,使得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关注的主题发生了转向,同时研究的问题域也被大大拓宽了。社会性别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技术内在地是男性气质的吗?社会性别参与技术的设计、生产与使用的前提假设是什么?等等,都是在新的研究框架下所应考虑的问题。然而,这一理论的运用所带来的更为深刻的影响是对“技术”及其价值有了新的理解。正如莱曼(Nina E.Lerman)等所言,社会性别分析挑战了关于什么是或者不是“技术”的惯常假定,以及哪些技术是重要研究对象的习惯假定[8]。事实上,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家用技术及其性别化特征的研究上,这一技术类型或者说技术场域常被之前的技术社会学和技术史研究所忽略。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不但揭示了家用日常技术的重要意义,更拓展了技术本身的内涵,即技术不只是人工制品,同时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当然,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对技术内涵的拓宽,同时更是受益于技术社会建构论的结果。实际上,当社会性别理论被引进技术的社会研究领域时,必将面临着如何构建或追溯技术与社会性别之间共同形塑关系的问题,这同时需要从技术研究领域的既有传统中吸取资源。
二、技术社会建构论
技术社会建构论强调的是社会对技术的影响,它的理论意义在反思和批判技术决定论的背景中被凸显。它是社会建构论向技术研究领域的延伸,主要通过案例实证来分析技术如何被建构,因此也可以称为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社会学[9]。一般认为社会建构论有强弱之分,其中弱建构论仅表明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强建构论则进一步认为技术的内容亦是社会建构的,技术的价值及其有效性并非源于其内在的逻辑规定,而是由社会因素决定。SSK影响下的技术社会建构论采取的基本都是强建构论的立场,即认为技术设计和技术内容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均可对其展开社会学分析。
从一般意义上看,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吸收了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基本理念。因为如果假定技术是按照自身内在逻辑独立发展的产物,就无法阐明社会性别对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技术的社会性别文化意涵,也就无法实现女性主义批判和变革技术进而实现技术领域性别平等的政治诉求。事实上,在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看来,技术和性别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技术离不开生产、处理和使用它的人而存在,并且,人类总是通过一定的范畴概念来组织他们的技术活动,这些范畴区分和定义了人类本身,包括年龄、财富、教育程度、职位、宗教和社会性别[6]3。其中,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在人类与技术的互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8]。可以说,性别与技术的社会建构观念构成了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具体而言,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对技术社会建构论的批判性借鉴主要体现在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中 的 “解 释 柔 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相关社会群体 (relevant social groups)概念,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上。所谓“解释柔性”,是指技术不具有边界固定的内在含义,每个主体不仅包括技术的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也包括技术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均参与了对技术功能与内涵的解释,使用者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技术的含义。显然,这一概念对于探讨主要作为技术消费者的女性在技术变迁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的许多经典案例都阐明了这一点。例如,瓦克曼(Judy Wajcman)以微波炉由军用产品、男性休闲产品发展为家用电器的历史表明了女性使用者对这一技术的占用与重构[10]。为了解释实践中新技术的内涵常常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一事实,SCOT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相关社会群体”概念,用以说明技术内涵与界定过程中统一意见的取得方式。女性主义学者对此概念提出了批判,认为它忽略了作为边缘群体的女性,并因此使得对技术进行社会性别分析的重要意义被忽视[11]。柯旺(Ruth Schwartz Cowan)更是提出了“消费者联结”(the consumption junction)的概念以避免技术“相关社会群体”的空泛和难以界定的问题,她要求将消费者置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位置,而且必须从他们的视角看待这一网络的形成与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12]。如此一来,女性作为技术消费者在相关社会群体所构成的网络中的位置将变得举足轻重。
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行动者”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每一个行动者就是一个节点,它们彼此处于一种平权的地位,相互连接,共同编织成一张无缝之网。它意味着技术与社会并非各自独立的领域,相反它们是共同构成和建构的网络关系,技术本身作为行动者之一,在研发、设计、生产、市场、分配、销售、保存等过程中,承载了其发明者、研发者、改进者与生产者的利益与价值观念,参与了对技术使用者的建构和塑造。女性主义学者积极将这一思路吸收并贯穿到其技术研究之中,探讨了技术人工物从发明、生产到销售,以及技术系统标准化的整个过程中,隐含着对女性作为消费者形象的塑造和对女性经验的否定。例如,他们明确指出ANT与SCOT一样忽略了边缘人群或缺席人群的作用,其行动者大部分是男性英雄、大项目和重要组织,是一种“管理者和企业家的”行动者网络模型;ANT没有认识到技术系统的稳定和标准化必然意味着对未被标准化者的经验的否定[13]。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学者还强调技术使用者始终与技术人工物互动,能改变技术人工物的内涵与使用方式,为此将研究视野从ANT关注的技术创新与研发拓宽到生产操作、市场销售、消费和终端使用者。结果发现,妇女是技术生产的隐形的廉价劳动力,她们是秘书、清洁工和厨师,是销售团队的一员,是家用技术和生育技术的主要使用者,妇女对技术的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意义[14]。可见,女性主义学者一方面借鉴了ANT强调技术作为行动者的重要意义,以此用于分析技术对女性和社会性别的建构,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批判了ANT对女性经验与利益的忽视,以及女性作为消费者对技术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
女性主义学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皆致力于为受压迫群体寻求平等地位,二者均具有很强的政治批判性,其研究思路的共通性尤其体现在对劳动过程和劳动分工问题的研究上。瓦克曼曾坦言,她和当代的许多女性主义学者一样,对性别与技术的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与分工研究的影响[14]。
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生产技术、劳动控制和阶级关系之间具有密切关联,阶级冲突会对技术发展产生影响。资本家不断开发和应用新技术以使劳动力分工更加片段化和去技能化,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劳动力变得更加廉价和易于控制。正如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所言,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劳动过程发展的趋势是最大程度地把劳动技能和操作技术转由机器和工具来完成,工人逐渐成为无需更高技术和技能的劳动者;技术革命和管理制度的变革给雇佣劳动者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被奴役[15]。
早期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便在此思路下考察了生产领域技术革新对女性雇员的影响,并且认为新技术的应用导致了女性劳动力的去技能化。由于秘书和打字员等办公室职位多由女性承担,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尤其是办公自动化对这类人群的影响成为其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新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女性职员从繁琐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大部分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却对之持悲观看法。他们的调查研究显示办公场所的女性(尤其是怀孕女性)长期暴露在视频显示终端操作环境中,一方面身体和安全受到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工作压力和强度并没有因新技术的应用而得到改善,相反办公自动化和无纸化办公的出现给她们造成了更大的就业压力,并使得她们的工作进一步被碎片化、去技能化和被贬值[16]29-30。以此延伸,柯旺等学者还探讨了家用技术的进步是否节省了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的问题,发现结果恰恰相反,新技术的应用给母亲们带来了更多的工作量,妇女并没有因新技术的发展而从家务中解放出来[17]。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女性主义学者对这类研究及劳动过程理论提出了批判。首先,技术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给不同岗位的女性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不能均质化处理。其次,工作场所的女性雇员很多不是拥有熟练技能的工人,新技术对其造成去技能化的影响的判断不完全合理。最后,最为重要的是,对技术及其影响的理解不能仅从“资本家-工人”这一单一的社会关系维度来考察,不能忽略性别、种族、年龄等其他维度。正如瓦克曼所言,生产关系的建构除了源于阶级划分,也受性别划分的影响;雇主作为雇主、人作为人,都对建构和维持职业的性别划分感兴趣[18]。为此,女性主义学者进一步将注意力从技术对女性雇员的影响转移到生产领域的性别技术政治和劳动性别分工,其研究表明生产领域的技术政治除了受阶级关系的影响,同时也渗透了性别斗争和性别意识形态。例如,相关案例研究表明,拥有熟练技能的男排字工人在组成工会抵制新技术的应用并维护自身的原有位置时,有意地将缺乏熟练技能的女工排除在共同体之外[16]36。此外,随着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工作的社会性别定型(the gender stereotyping of jobs)或者说劳动的性别分工始终保持着稳定性。科伯恩和奥姆罗德对微波炉制造业的性别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都是男性,而女性仍被理解为具有细心、细致、耐心、关怀等特质,因而更多地从事流水线工作,例如给商品贴标签[7]42-46。
显然,女性主义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过程的理解,表明社会性别分析和阶级分析一样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过程及其与技术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根本主张,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共同构成了女性居于屈从地位的根本原因,而技术恰恰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换言之,技术不仅是资本利润的重要帮手,是有产者剥削无产者的工具;同时也是父权压迫的帮手,是男性控制女性的工具。在父权制的框架中,即便是处于底层的有一定技能的男性工人,他们也趋向于利用技术来排斥较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女性。这些研究的拓展,促使女性主义学者不得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女性总是缺乏技能的?为什么技术总是与女性气质相冲突?技术的性别气质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些问题促使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的场点从工作场所拓展到社区和家庭领域。与此同时,如上文所述,女性主义学术提出了社会性别理论,新技术社会学也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在整合二者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将研究主题从“技术-女性”转移到“技术-社会性别”,开始追问技术的父权制文化本质。
四、技术文化理论
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创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当前的文化理论广泛吸收了现象学、新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等哲学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符号学、叙事学等文学理论,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构成一个众多学科交叉融通的领域;其根本含义在于探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各种实践活动过程中是如何生产和表达、体验和重构“意义”的[19]。文化研究主要流行于三类群体之中,包括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部分人类学家和由于性别、种族、阶级等原因而“被遗忘的”文化群体。它具有明显的学术倾向,强调性别研究及各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研究对处于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系统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地方性、情境化的历史分析的重要性;参照其他价值来评价科学技术的成就[20]。
以此观之,女性主义学术在整体上都具有文化研究的气质,性别研究本身即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有的女性主义STS研究中,对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情境化特征的强调,一直是 哈 丁 (Sandra Harding)、哈 拉 维 (Donna Haraway)等学者的基本观点之一。类似的,文化理论框架下的技术研究强调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将技术视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更为关注日常生活与境中的技术变迁,重视对技术展开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分析;强调将技术视为一种话语或文本,一种消费目标和交流媒介,不允许在物质和文化之间作任何的区分,将技术视为物质和文化的无缝融合。女性主义的技术社会研究深刻反映了这些基本观念。正如莱曼等女性主义学者所言,技术和性别一样,包含了身份、结构、制度与表征的多重内涵,其研发、使用及意义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是特殊历史与境中的产物;文化研究框架下的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不仅研究物质也研究人,人类的选择、创造力、知识、意识形态、假设和价值观内在于技术人工物和技术活动之中[6]3-5;文化实践永远都不是外在于技术发展,相反它总是技术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21]。白馥兰(Fransca Bray)坦言柯旺等人的技术社会研究给了她启示,她认为技术是一种文本,是符号、表征经由物质媒介而呈现的实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它属于特定社会,是其所属世界的图景象征和对该社会秩序斗争的体现;技术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制造人:制造者在制造过程中被塑造,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被形塑[22]。
在瓦克曼看来,技术的文化理论对传统女性主义分析的贡献在于关注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参与个体性别身份建构的方式和过程,以哈拉维为代表的赛博格女性主义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14]。实际上,以历史和社会学分析见长的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继承和丰富了技术文化理论,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开始关注衣服清洗、儿童照料、缝纫、饮食卫生等这些被传统研究所忽视的日常生活技术,强调这些具有女性气质的、与日常生活实践紧密相关的技术传统及其价值,要求对技术的定义进行审视和重新界定。这与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技术的重要性的强调不谋而合,同时亦是对主流技术精英史传统的反思和批判,最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将技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实践的重要意义。第二,他们将技术社会研究的重心从技术创新转移到了技术消费,确认和强调了消费及使用者对技术的形塑;这实际上是将技术从实验室中解放出来走向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实践,并在其中实现技术意义本身的表达、修正与再建构,已是对SCOT和ANT的超越。第三,他们从宏观的社会性别结构与符号系统入手分析了技术与个体社会性别身份的相互建构关系,表明技术的象征表达是极端性别化的,男性与技术的亲密关系内在于男性性别身份和技术文化的构成整体之中;进一步明确了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第四,他们日趋关注生育技术、美容技术、媒介技术等对身体的建构。这一方面削弱了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性别区分的观念的稳固性,表明关于男女的划分是在广泛的文化实践话语中发明的;另一方面将身体变成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的重要场点,身体不只是文化符码,更具有认知功能,它与技术融合形成技术身体,参与了对文化和实践的建构,这实际上超越了文化理论的语言中心主义路径,为技术-身体-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思路。
五、结 语
结合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的理论溯源,可以初步分析和总结其研究主题和理论框架的变迁。早期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的主题是探讨“技术-女性”之间的关系,焦点是生产领域的劳动性别分工问题,这直接受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影响,侧重探讨的是技术变迁给女性造成的影响。随着社会性别理论的成熟和技术社会建构论的发展,其主题转变为“技术-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研究,基本的理论框架也逐渐明确为“社会性别与技术的共同形塑或者说共同生产”,更注重二者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同时,在与其他技术文化理论观点的相互影响下,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日益拓宽了对技术的定义和理解,研究主题侧重以具体的技术人工物为切入点,从文化实践、生活方式、符号象征等角度阐释作为物质与文化的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与文化符号系统的性别之间的无缝接合,形成了文化研究的转向。尽管如此,这里仍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变迁只是较为粗线条地反映出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大致经历的发展脉络,它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主题不可以在同一时期出现。事实上,关于技术变迁给女性造成的影响至今仍然是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的焦点之一。
作为女性主义技术理论的研究进路之一,以柯旺、科伯恩、瓦克曼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学者更擅长和侧重从历史和社会学的维度分析技术与性别问题,形成了对技术、性别及其相互关系的独特理解。它与生态女性主义、赛博格女性主义等研究进路共同推进和丰富了女性主义技术理论,其主张有助于深入理解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本质,增进对技术及其价值的理解,帮助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代社会文化中的技术论争;同时对推动技术领域的性别平等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女性主义的技术社会研究本身亦是一种话语和文本,是一种物质-符号技术,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学术研究和政治诉求在物质形式、意识形态、语言符号,以及生活实践等各个层面的无缝接合,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术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
[1]Archer J,Lloyd B.Sex and Gende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21-38.
[2]凯勒E F.性别与科学:1990[M]//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78.
[3]卢宾G.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M]//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1-71.
[4]斯科特J W.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M]//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68-170.
[5]Harding S.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17-18.
[6]Lerman N E,Oldenziel R,Mohun A P.Gender and Technology:A Reader[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
[7]Cockburn C,Ormrod S.Gender &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3.
[8]Lerman N E,Mohun A P,Oldenziel R.Versatile Tools:Gender Analysis and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J].Technology and Culture,1997,38(1):1-8.
[9]邢怀滨.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20.
[10]Wajcman J.TechnoFeminism[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36-37.
[11]Grint K,Gill R.The Gender-technology Relation:Contemporary Theory and Research[M].London:Taylor &Francis,1995:18.
[12]Cowan R S.The Consumption Junction:A Proposal for Research Strateg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M]//Bijker W E,Hughes T P,Pinch T J.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7:262-263.
[13]Star S L.Power,Technology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ventions:On Being Allergic to Onions[M]//Law J.A Sociology of Monsters:Essays on Power,Technology and Domination.London:Routledge,1991:26-56.
[14]Wajcman J.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Technology Studies:In What State is the Art[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00,30(3):447-464.
[15]Braverman H.Technology and Capitalist Control[M]//MacKenzie D,Wajcman J.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2nd ed.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9:159.
[16]Wajcman J.Feminism Confronts Technology[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17]Cowan R S.More Work for Mother: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M].New York:Basic Books,1983:210-216.
[18]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得森,等.科学技术论手册[M].盛晓明,孟强,胡娟,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46.
[19]陈玉林.技术史研究的文化转向[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16-17.
[20]盛晓明.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科学的文化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9(2):15.
[21]Lerman N E,Mohun A P,Oldenziel R.The Shoulders We Stand on and the View From Here:Historiography and Directions for Research[J].Technology and Culture,1997,38(1):9-30.
[22]Bray F.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