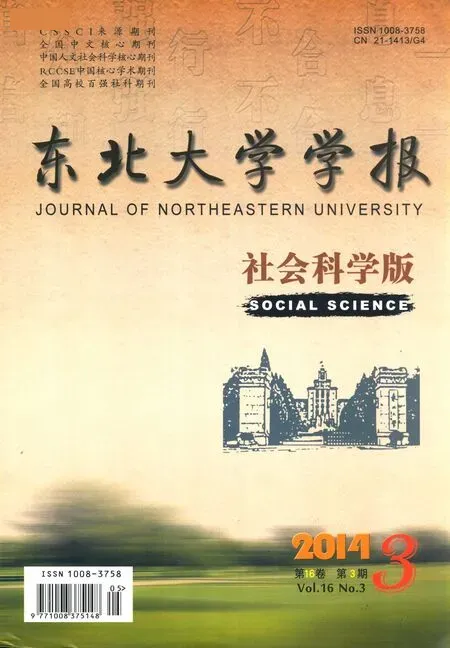文化女性主义视域中的技术
易显飞,章雁超,傅畅梅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2.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3.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社科部,辽宁 沈阳 110136)
文化女性主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赞美与弘扬女性气质,限定男性统治文化的价值。文化女性主义被认为是“价值重估派”,主张推倒重来式的重估与女性有关的价值,重新开拓女性的价值空间。在文化女性主义看来,女性所需要的不是那种“统治欲望”或“权力欲望”,而是要展现作为女性“最本质的东西”,即女性可以按女性应有的自然本性成长,获取知识和自由生活[1]。她们通常不谈论“政治问题”,认为两性不平等根源于父权制文化[2]。男女两性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处于性别文化的二元结构中。如果不考虑性别,就不能充分地认识技术,性别是审视技术不可或缺的视角。文化女性主义进入技术哲学研究领域,以文化为中介透过性别审视技术,即聚焦于“性别-文化-技术”的相互建构关系,透视技术的性别隐喻。本文拟对文化女性主义主要学者的技术观进行阐述,并对文化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进行评析。
一、摩尔根:采集技术与挖掘技术
技术与人类社会相伴相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技术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与人是共同进化的,生命的一切领域普遍地被卷入“技术化”的潮流[3]。在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在生存技术的发展上,男女两性的差别同时也呈现了出来。人类学家摩尔根认为,“采集技术”更多地呈现了女性的特征,而“挖掘技术”更多地属于男性的领域。人类控制地球,是以控制生活资料为条件的。只有当人类控制了生活资料,人类的自由度才会不断得以提升。人类早期的生存技术主要靠在有限的生活环境内以植物的根和果实作为天然食物,以维持早期人类的生存[4]14。人类自直立行走以来,制作的工具与以前相比,也更为有效。当时的人类凭借优越的智力,发明了“石刀技术”,即用压制法从石核上取下长而锋利的薄片,这就是所谓的“石刀”。尽管旧石器时代晚期相比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生存技术要先进得多,但由于生产率低,这种技术依然是非常原始的。人们靠“采集技术”采集野生植物和捕捉动物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摩尔根指出,无论哪一种动物都需要不断获取食物来保证生命的延续,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如果我们按照生理结构的演化程序往上推,就会发现,每升一级,食物就复杂一些,那么到了人体结构,食物的复杂性也就达到顶点。但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是一种杂食动物,实际上或许也可以说,人类是依靠“采集技术”以果实为主要食物,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极其原始的时期[4]15。
制铁技术的出现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经验中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制铁技术的发明对人类的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人类发现天然金属而且学会将金属熔化并铸造的时候,当人类将天然铜和锡熔合发明铜的时候,当人们进一步发明熔炉并从铁矿中提炼出铁的时候,人类的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摩尔根提到,有了铁,就产生了用金属制成的锤子、斧子、有铁铧的犁、铁剑等。这样,“挖掘技术”出现了,它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没有铁器,人类的进步便会停留在野蛮阶段,便很难跨越这道鸿沟。有了铁器,人类也就从此进入到文明阶段[4]28,从性别文化史来看,以女性为主导的“采集技术”逐渐地被以男性为主导的“挖掘技术”所取代。
人类生存技术的变革,“采集技术”逐渐地被“挖掘技术”所取代,是基于对生存品质提高的诉求。人类为了改变原来那种到处游荡的生活,进而希望能够生活得更稳定一些,即人们希望相对能定居在一个地方,因此,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必须从向自然界攫取转向人类能够进行食物的生产。于是人们发明了磨制石器,以及骨头制的、蚌壳制的工具,用来砍伐林木,挖掘洞穴,建筑永久性的住居。这样,人们既从事一定的采集,从大自然中索取;另一方面,也广泛种植并进行其他一些生产活动。在此过程中,人类生存技术也逐渐地发生变革,“采集技术”的重要性逐渐弱化,“挖掘技术”处于技术体系的中心地位,男性逐渐取代女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男性文化逐渐取代女性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技术作为劳动资料的核心部分,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且是很重要的文化现象,按照摩尔根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它不仅改变人类的经济活动、生存方式,同时也改变了历史上的性别文化及性别地位。
二、芒福德:容器技术与支配技术
古典技术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站在女性的立场肯定了女性在人类历史上对早期技术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从性别文化的角度出发,通过技术考古学研究,将技术区分为“容器技术”与“支配技术”。“容器技术”具有女性的生命特质与文化特质,“支配技术”以男性骨骼和肌肉力量为特征。
芒福德认为:“在女性的影响与支配下,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外,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宽口瓶、各类缸、蓄水池、箱子、柜子、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些容器。”[5]16他认为,这些工具都是典型的具备女性特质的“容器技术”。芒福德认为这些容器(container)就是技术,并且认为容器技术是女性器官的延伸。“容器”技术不同于工具和武器,在技术哲学家卡普看来,诸如工具和武器之类的技术是人体器官的延伸,但在芒福德看来,“容器技术”也具有同样的品质,它是“人类中的女性”器官的延伸。在新时器时代,不但容器技术呈现了女性的特征,而且诸如嫁接、扦插、田园管理等农业技术也主要受女性的影响,这些技术的产生及进步对人类的存续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女性的影响和支配之下,新石器时代突出地表现为一个容器技术的时代,但是这一时代的突出特点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却很容易被当代赞美机器技术进步的学者们所忽略、所遗忘。新石器时代是女性主导的社会,不是男性统治的社会,在新石器时代,是“容器技术”显赫的时代。然而由于男性占统治的时代比较久远,所以现代很多学者忽略了容器技术的得天独厚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以至于在机器时代之后,以机器为代表的支配技术占据了技术发展的主导地位,加之男性文化的不断张扬,以至于人类忽略了“容器技术”,忽略了容器技术的价值和意义。
与“容器技术”相对应的是,以男性特征为主的技术是“支配技术”。在芒福德看来,工具、武器和机器的文化编码是男性,容器、建筑和城市的文化编码是女性。它们体现了不同的文化隐喻。通过远距离操作并驯服对象的机械、武器等技术都是男性文化编码。男性特征的支配技术还表现在“男性至尊的抽象概念”,“刚直遒劲的直线、巨形,严密封闭的几何图形,阴茎状的尖塔,直至最后表现于数学和天文学的起源等等”[5]20。这种“支配技术”既包括旧石器时代男性骨骼和肌肉力量支配下的技术成就,也包括工业革命后带有进攻性的武器技术、强控制性的巨型机器技术等。这些技术以力量为标志、以征服与统治为特征,与社会性别文化所倡导的男性文化特质具有一致性。
在技术研究与人类学研究中,女性的这种容器技术常常受到男性人类学家和技术史学家的忽略,芒福德指出这是不公平的。容器技术呈现的文化特征是扎根于生命、生存和繁殖,而以机器为代表的支配技术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则是秩序、控制、效率和权力。芒福德认为,在史前时期,器具优于工具,容器作为器具的重要体现形式,它先于工具,且容器技术多为女性所发展。可以说,芒福德的这项研究工作是在为技术史文本的女性“缺席”进行席位填补,他或多或少地重新找回了隐匿在技术史背后的那些女性技术发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芒福德是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先驱。
三、艾斯勒:“圣杯”技术与“剑”的技术
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是美国人类文化学家,被誉为“文艺复兴新女性”[6]。从文化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艾斯勒依据不同的性别文化,将技术分为了“圣杯”(the chalice)技术与“剑”(the blade)的技术,前者是以男女合作谋求维持和改善生活的技术,后者是男性占主导为实施毁灭和统治的男性化暴力技术[7]。在她看来,“圣杯”与“剑”隐喻了两种文化:“剑”在印欧地区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是暴力、杀戮和抢劫的象征,它代表着生杀大权,代表着统治的权力,代表着毁灭的权力。“圣杯”在古代欧洲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代表着人类的“生命之门”,意味着创造和孕育生命,因而,“圣杯”代表着一种给予的权力,代表着一种养育的权力,代表着一种启迪的权力。艾斯勒将“圣杯”视为人类社会伙伴关系的组织模式的文化象征,而将“剑”视为统治关系组织模式的文化象征。她指出,在历史上,男女合作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特征是“和平”,而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特征是“战争”,正好可以用“圣杯”和“剑”来象征。
艾斯勒借助于许多考古学家的著作,并基于史实的分析指出,在1.5万年前的人类社会,女性不是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到了大约在公元前2 500年,古代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和谐的、崇拜女神的、高度发展的文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男性的暴力统治和为了毁灭的目的而使用的技术[8]。艾斯勒基于人类考古发现的丰富资料,并探究了人类远古的神话原型,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开端,人类所采用的是男女伙伴“合作关系”模式,那时的人类社会,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压迫。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男性权力统治模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其突出特征是靠暴力维持的等级制度社会。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即使在男性权力统治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男女合作的伙伴关系的声音仍不断地时强时弱地出现。“圣杯”文化并没有被“剑”文化彻底摧毁,这意味着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人类是有可能走向一种伙伴合作关系的未来。
艾斯勒运用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但又非单纯的女性主义立场的思考方法,一方面提出了她所要阐述的核心问题,同时,她对许多问题的见解也为我们全方位思考人类社会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她启发了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这主要缘于她在书中不仅分析了女性问题,也分析了克里特的政治结构,进而启发人们思考集权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其二,由于艾斯勒认为男女平等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权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问题,这一点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观点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由此,我们可以思考今天的人权问题,因为女性问题首先就是一个人权问题,当女性问题、女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人权问题的解决就是一句空话,人间正义也不会存在。其三,她启发了我们对“技术问题”的思考。“女性特质的技术”发达的时候,社会和谐平稳发展,人与自然互为伙伴;而在“男性特质的技术”占主导的今天,人、社会、生态均出现前所未有的异化。不同的性别文化主导下的技术发展,存在着天壤之别,如何基于性别文化的和谐,去思考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是技术哲学研究的迫在眉睫的任务了。
四、文化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评析
1.文化女性主义技术认识的共同特征:“性别—文化—技术”之间的相互建构
从摩尔根的采集技术与挖掘技术的划分、芒福德的容器技术与支配技术的划分再到理安·艾斯勒的“圣杯”技术与“剑”的技术划分,文化女性主义视野中技术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同时,这三者之间又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以文化为中介透过性别审视技术,突出性别文化在技术中的呈现,展现了“性别-文化-技术”之间的相互建构。
技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交织于语言与意义系统中,技术、语言与意义的社会化同时也是性别化的过程,性别之网与社会、技术交织的“无缝之网”镶嵌为一张网。技术或技术制品的意义的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都可以在技术使用中“重读”技术的价值与意义。以男性为主体的技术发明与创新者在制品形成的过程中诠释了它的最初意义,但是女性,虽不是技术制品的主要创始人,却往往是技术传播与技术使用者,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可以对该技术赋予新的内涵与价值。技术建构论者把技术看做“施动者”,认定技术的功能与意义的改变会影响到(社会)日常生活经验的形成。在这里,“技术的”与“社会的”之间的边界常常也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边界,正是在作为“施动者”的意义上,技术从与“男性气质”相联系转向与“女性气质”相联系的过程同时也是技术“去技术化”的过程。女性化往往意味着社会化,而社会化则意味着去技术化[9]。
2.技术发展的指向:拓展包含女性气质在内的新技术体系
在摩尔根看来,技术发展是从采集技术走向挖掘技术;在芒福德看来,技术发展是从容器技术趋向于支配技术;在理安·艾斯勒看来,人类技术是从“圣杯”技术转向“剑”的技术。也就是说,文化女性主义者认为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挖掘技术、支配技术和“剑”的技术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体现男性文化的技术占主导地位对于人类的整体发展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用女性文化形塑技术进而拓展出基于女性气质与文化的新技术体系。
在文化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气质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传统的女性气质观点中,女性往往被赋予生育、养育的角色,在社会发展和技术领域中少有她们活动的空间。文化女性主义反对单一男性的理性思维规则。在她们看来,男性气质的技术看来好像是自由和客观的,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征服与侵略、自我与功利、霸权与反人性等文化品质;而女性气质的技术则是女性思维方式与文化气质的呈现,其文化表征表现出的是合作、关心、责任、和谐与善。可以认为,在技术的发展上,文化女性主义在强调文化上男女的差异性基础上更为关注的是要拓展包含女性独特气质的新技术体系,在她们看来,女性文化更优于男性文化,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技术问题,正是男性文化主导下的艾斯勒意义上的“剑”的技术大量发明与随意滥用的产物。基于此,人类未来的出路同时也是技术的出路在于,将女性文化与气质延伸到技术领域,拓展包含女性价值在内的新技术体系。
基于文化女性主义技术认识的共同特征是“性别-文化-技术”之间的相互建构,也就是说,文化女性主义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的,正是因为技术的建构性,技术与性别之间的协同作用才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可以认为,作为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在技术发展中也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3.技术变革的价值实现:用女性文化形塑技术
把技术建构成男性的气质,或者说按照技术能力来建构男性的气质,是男权社会的现实。在技术领域,为什么少有女性?女性为什么基本被排除在技术发明、创新领域之外?在文化女性主义者看来,这与人类社会中对女性的地位、对女性价值的评估有直接的关联。在文化女性主义看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技术,对技术进行批判要力图使性别和技术的争论超越技术的使用范式,把技术本身的政治性质作为分析的焦点,与此同时,还应充分肯定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的利益、需要和价值观,并认为目前的技术没能很好地满足她们[10]。这也就是说,不仅在技术发明、技术的社会化方面女性的价值没有得以体现,而且作为技术使用者,女性也没有被充分关照。
文化女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要塑造一种独立的女性文化,体现女性所特有的气质,大力张扬女性在技术发展中的文化表达[11]。在这样的核心价值的支撑下,在传统视域中被悬置的女性特质将得以重新呈现,如女性所体现的母性的力量、重情感、主张合作、和平、关爱等。吉尔曼认为,如果女性有足够的智慧发现其自身的力量和潜在的美,那么女性永远也不会希望成为男人,会争取与男人相似[12]。文化女性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女性不但不能向“有问题”的男性文化看齐与靠拢,而且要以女性文化和价值为导向,张扬历来被贬低的女性文化。技术发展需要联合、创造和维护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通过女性参与到技术发展中去得以实现。这些观点为女性参与技术领域打下了文化理论基础,也进而为女性的“实质性”解放与技术的“真正”进步提供了可能的价值实现途径。只有通过技术与性别的共同形塑,女性在技术变革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总体上,文化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为探讨技术发展及女性地位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并展现了一种积极的态度,为女性参与技术变革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由于文化女性主义者未能认识到社会变革中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对文化特别是“女性文化”的实践力量过于高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文化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思想在技术发展现实中的作用。
[1]Fuller M.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NewYork:W.W.Norton &Company,1971:38.
[2]Hennessy R,Ingraham C.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Dfference,and Women's Lives[M].New York:Routledge,1997:7.
[3]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00.
[4]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5]Mumford L.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M].New York:Harcourt and World,1961.
[6]罗依D.理安·艾斯勒——她的著作及她的影响[J].黄觉,译.国外社会科学,1996(3):56-60.
[7]艾斯勒.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M].程志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
[8]闵家胤.艾斯勒和她的《圣杯与剑》[J].国外社会科学,1992(7):76-79.
[9]Lohan M.Constructive Tension in Feminist Technology Studies[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00(12):895-909.
[10]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得森,等.科学技术论手册[M].盛晓明,孟强,胡娟,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48-149.
[11]肖爱平.论西方女性主义对主流正义论的批判[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4(2):117-121.
[12]Gilman C P.Women and Economics[M].New York:Harper,196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