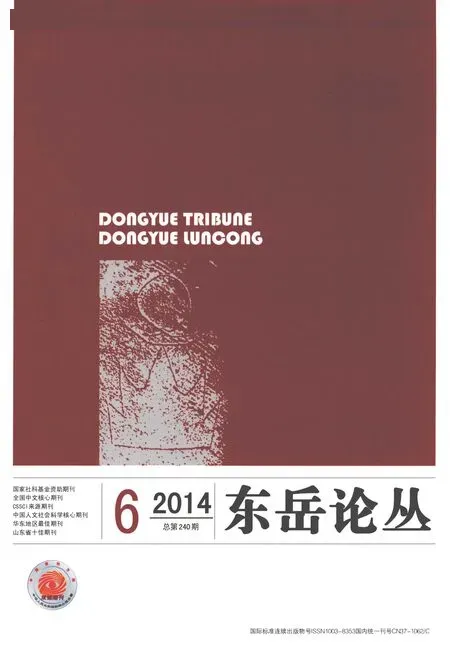从文本细读看瞿秋白精神生态
张显凤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滨州256603)
从文本细读看瞿秋白精神生态
张显凤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滨州256603)
瞿秋白精神世界中具有诸多互相矛盾对立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济世与避世的愿望在其心里兼而有之,他虽然选择了前者,但避世的愿望时有流露;肉体的病弱,既激发了他向死而生的决心和斗志,又使他时时生出消极退缩和随波逐流的念头;其精神结构中信仰与怀疑、肯定与否定精神并存,使他对于“革命”和“自我”等问题的认知复杂多面。这昭示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艰难心路历程,也预示了革命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多余的话》;精神生态
《多余的话》历来是瞿秋白研究中的热点,《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作为瞿秋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心路历程的文学记载,在瞿秋白的研究中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通过对这三部作品的细致研读,笔者发现瞿秋白精神世界中具有许多贯穿始终的互相矛盾和彼此对立因素,就像心理学上的双重人格,“它们看起来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却又和谐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①李江涛,朱秉衡:《人格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构成了瞿秋白独特的精神质地。简言之,在精神生态构成上,瞿秋白始终是一个二元性的矛盾统一体。
一、在入世与出世之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从容就义之前的绝笔,是他对人生的最后告白,虽然“多余”,却不吐不快,说明这些话大多是瞿秋白生前在内心深处埋藏已久的肺腑之言,表现的是作者心灵深处久遭压抑的另一个自我,由此入手,可以发现他在一些问题上的原初倾向性。
比如,瞿秋白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②瞿秋白:《瞿秋白散文名篇·多余的话》,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第229页。谈到当初赴俄的动机,则说:“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③瞿秋白:《瞿秋白散文名篇·多余的话》,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第229页。。从此类表述中,可以看到瞿秋白人生理想中隐逸避世,文艺借以自娱的传统士绅意识特征,独善其身是他人生理想的底色。
然而与社会现实的紧张关系,使瞿秋白欲想避世而不得,最终只能选择做“过客”式的抗争者,《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即生动记录了瞿秋白的这一矛盾复杂心态。且看《饿乡纪程》的卷首语:“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④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这一鲁迅式的开篇用生动的文学意象和极端化的情绪体验喻示出作者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没落的士大夫家族之一员,瞿秋白的家庭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也破产了,家庭的悲惨处境,决定了瞿秋白根本没有条件逍遥避世。社会方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在政治上并没有真正走向民主共和,外有列强相逼相欺,内有复辟帝制军阀割据,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上,由于外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传统的小农经济破产,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中国依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希求变革无疑成为这一时期有识之士共同的潜在心理。
这样,在五四运动前后,内心深处潜伏着改变个人生活和社会现状要求的瞿秋白,虽然骨子里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偶然”地学习了俄语,“偶然”地成为学生领袖,“偶然”地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经历了新文化的洗礼并看到俄国革命的“一线曙光”之后,有机会作为《晨报》特聘记者远赴苏联。这一选择既和瞿秋白与社会现实的紧张对立有关,又与其对于自身的阶级和文化属性的体认相联。瞿秋白意识到:“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西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是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⑤《瞿秋白散文名篇·多余的话》,第234页。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则使他找到了新的归属:“‘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①《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213页,第17页,第10页,第8页,第58-59页。。瞿秋白奔赴苏联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是一种必然,和社会现实的紧张关系驱使他为改变现状而积极求索。
而且,“饿乡”的典故出自清代管同的《饿乡记》,喻苏联为“饿乡”,即表明瞿秋白已将当时的苏联视作知识分子的精神圣地。对于他用赴“饿乡”比喻自己奔赴苏联的心情,夏济安认为这是传统儒家济世精神的崇高表现②Tsi- an Hsia,The Gate of Darknes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18.。因此,当堂哥认为赴苏是自趋绝地时,瞿秋白说:“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我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如同‘出世’一样”③《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213页,第17页,第10页,第8页,第58-59页。,由此可见,瞿秋白决定赴苏时甚至是抱着“其九死而犹未悔”的决心,为中国的新生甘做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和殉道者,其匡时救世的决心跃然纸上。
但是,瞿秋白内心深处的消极避世愿望即使在旅苏游记中也是有迹可循的。比如他在火车上“随手翻开”的是“一本陶渊明的诗集”④《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213页,第17页,第10页,第8页,第58-59页。,这一漫不经心的动作和叙述正可窥见其心灵深处潜伏的避世思想;关于赴苏的目的,瞿秋白先有如下明确的表述:“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⑤《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213页,第17页,第10页,第8页,第58-59页。,而旅途中被迫滞留哈尔滨时,他又写下了这样的话:“所以我冒险而旅俄,并非是什么‘意志坚强’,也不是计较利害有所为——为社会——而行,仅只是本于为我的好奇心而起适应生活,适应实际精神生活的冲动。”⑥《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213页,第17页,第10页,第8页,第58-59页。这一前后相抵牾的自我表述,也正反映了其思想中“独善其身”与“匡时救世”之矛盾。
此外,瞿秋白骨子里对文学的热爱远胜于对政治的兴趣,这不仅在《多余的话》中有明确的表述,在《赤都心史》中也有不自觉的表现。《赤都心史》被作者称为“心弦的乐谱”,其思想情感的坦白与真诚毋庸置疑,但全篇四十九节文字中,有九节记录的是作者的纯文学活动——翻译的诗歌,题赠的诗作或自我抒怀的诗歌作品;在所记载的相关参观游览活动中,其游程和游感大部分都是写意式的粗线条概括和总结,篇幅也很短,唯独到托尔斯泰故居参观后所写的《清田村游记》,不仅对游览过程记载细致完整,笔调轻松愉快,而且篇幅也特别长,以一节文字占了全书总长度的十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多余的话》中所提及的对政治的消极态度和对文学的钟情以及二者的错位,早在旅苏之初就已初露端倪,在借文艺自娱以独善其身与投身政治以匡时救世之间,瞿秋白虽然选择了后者,但却始终无法忘情于前者。
二、沉重的肉身与高蹈的精神
在有关瞿秋白的研究中,他的病很少被提及,更遑论它对瞿秋白思想和创作的影响研究了。事实上,据同一时期在苏联的曹靖华回忆,1922年瞿秋白的肺病已经相当厉害了,医生说他的一叶肺已经烂了,顶多支持不过两三年,但瞿秋白一直坚持工作,直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才住进莫斯科高山疗养院⑦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尽管对苏联的物资匮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事实仍然超过了预想的期待,不仅黑面包的酸臭不是能想象的,莫斯科的苦寒亦让人窒息,所以尽管豪情满怀,在抵达目的地的第一天,瞿秋白对新的环境将“磨练”其意志还是“亏蚀”其精力,其实是心怀忧虑的。
在《饿乡纪程》中肺病只是一个看不见的在场者,在《赤都心史》中,“肺病”已经现形为瞿秋白在苏联生活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一绝症自1919年首次发作起就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他才会在旅苏之初写下了这样的话:“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生命于我无所轻重”。⑧《瞿秋白文集》(第一集),第17页。
尤为重要的是,疾病通过影响旅苏游记对“心弦的乐谱”和“社会的画稿”的书写,也参与了瞿秋白精神生态的形塑过程。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瞿秋白的游记写作是一次成长和抉择的仪式”,是他“投身左翼革命的门坎”⑨张历君:《镜像乌托邦的短暂航程》,《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第111页。。“疾病”作为这一重要过程的“参与者”,它的影响不可低估。
首先,它影响到瞿秋白对实际社会生活考察的广度和深度。兹将瞿秋白在苏联的主要参观访问活动列举如下:在美术馆、剧院里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参加克鲁泡特金的葬礼并会见其夫人;与马雅可夫斯基会谈;访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及参观幼稚园;访苏俄通商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见到列宁和托洛茨基;访问托尔斯泰故居;出席远东大会。而几乎同时期游俄的社会民主党创始人江亢虎不仅参加了类似或相同的访问与会议,还参观了莫斯科科学院、公学、大学、工厂、医院、军官学校、远东大学、母子养育院、赈灾展览会、历史博物馆以及人类博物馆等,亲临清洁党员队伍的“共产党演说会”和“外交部共产党诘问会”,并对苏联社会政治危机、知识分子政策、新经济政策执行初期的社会状况及赈灾等社会现实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描写和介绍10参见江亢虎:《新俄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相比较而言,瞿秋白“参观游谈”的范围很难说得上是广泛和深入。
其次,疾病也影响到瞿秋白的写作和思考方式。因为身体的病弱不仅客观上限制了瞿秋白的活动范围,同时也影响到其感知世界的方式。现象学的分析指出:“疾病代表着一种已被改变的生存状态,一种个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本质的改变。”11[美]图姆斯:《病患的意义》,邱鸿钟等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饿乡纪程》中不时流露出的朝圣者的狂热与殉道者的高昂气息,就与结核病患者容易亢奋的精神状态及其蔑视肉体存在的潜在心理密切关联,而且,肺结核对生命的持续性威胁无疑会大大强化作者的生命意识,所以,即使是写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我们亦很难看到瞿秋白对会议组织、流程、议题等问题的客观性介绍,相反,他更注重气氛和意境的营造,通过对声音、形象和色彩的把握,用写意的笔法来描绘“莫斯科的赤潮”——这也是其旅苏游记具有绘画美和意境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赤都心史》中,瞿秋白更多地通过沉静的内倾性感知和思考来完成自我精神的蜕变之旅,在“他粗粗地领略了一个粗糙、简陋、却也有清新、和谐的俄式初期社会主义”①瞿虹:《瞿秋白赴俄心路历程研究》,刘福勤主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六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9页。之后,日渐沉重的疾病迫使他更多地将审视的目光转向“自我”和书本上的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接受和思考则更多地停留于概念和理论层面,从而无视和忽略了苏联社会主义初期建设实践的复杂性和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政治危机,知识分子政策,清党,余粮征集制与大饥荒的关系等等。这样,瞿秋白新的精神世界的建立就不免带上了某种凌空高蹈的色彩,这也预示着他在深入革命实践之后会缺乏应付复杂现实问题的精力和能力,终至觉得自己象“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②《瞿秋白散文名篇·多余的话》,第232-233页。。
正如桑塔格所指出的:“结核病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③[美]苏姗·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一方面,肉体的病弱,激发了瞿秋白向死而生的决心和斗志,虽然苏联革命的胜利仅仅是黑魆魆的天地间“一线细微的光明”,但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光芒照亮了他,使他甘愿为之献身而至死不渝。但是,另一方面,虚弱病体的束缚,又使瞿秋白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实干能力不足,体力不济,时时生出消极退缩,随波逐流的念头,使他没能成为自己所期望的勇敢坚定的革命者。这是他矛盾痛苦的根源之一,也是促使其临终前作出深刻乃至否定性自我剖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对“自我”与“革命”的双重态度
在《多余的话》中,作者不留余地自我否定和自我清算的勇气令人震惊和迷惑,同时也给身后的研究者们留下了一个谜,众多研究者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其实,瞿秋白这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精神也是由来已久的。瞿秋白始终是一个冷静的自剖者和自审者。《饿乡纪程》开头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对过去的生活道路和心灵历程做出回顾和总结,习惯于以第三者的立场反观自我甚至否定自我。《赤都心史》中,一方面肯定“我”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充满朝气和力量,一方面又在《生存》和《中国之“多余的人”》等著名篇章中质疑乃至否定“自我”的行动能力及生存方式、意义和价值。其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精神相交织,互相交融,构成了其二元性表现之一斑。
此外,作为一个革命者,瞿秋白最初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认同和接受就是有所保留的,或者说停留于理智认同的层面,在感情上却未必能完全接受。《饿乡纪程·序言》中,“红色”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也是鲜血与革命的写照,瞿秋白对它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说:“‘红’的色彩,好不使人烦恼!我想比黑暗的‘黑’多少总含些生意。并且黑暗久了,骤然遇见光明,难免不眼花缭乱,自然只能先看见红色,光明的究竟,我想绝不是纯粹红光,他必定会渐渐的转过来,结果总得恢复我们视觉本能所能见的色彩。——这也许是疯话”。可见,在理性层面上,瞿秋白认同了暴力革命的手段,认为“黑暗久了”,“自然只能先看见红光”;可在对革命的期许上——即所谓“光明的究竟”,显然超出了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本身,认为其“绝不是纯粹红光”,他之所以立刻接着说“这也许是疯话”,表明聪慧敏感如瞿秋白已感知到了这一想法的不合时宜。
《赤都心史》中的《什么!》一篇也微妙地表明其对于“革命”的复杂感受。《什么!》记载的是作者听说的两件革命时期的轶事,其中一件说的是一个被没收了土地和财产的乡间地主不明白什么是革命,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到处申诉,结果最终疯掉了。这则记述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作者近于零度叙事的客观立场;其二,文章详细地记录了农场主被“革命”时的自我辩解之词,其主要内容有“我从小辛苦到大,劳动者,真正的劳动者,现在……得有一些财产,原是大家的,……不过,不过,挣到这步田地也不容易。”④《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201页。在这里,面对个人话语和革命话语的交锋,瞿秋白貌似客观化的叙事立场早已昭示了其在《多余的话》中所坦诚的“二元性”——绅士意识或游民式的感情与无产阶级意识的对立,前者讲求仁慈礼让,讲求中庸之道,希望避免斗争,后者强调的则是对敌人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质言之,无产阶级革命要求革命者用阶级性来改造人性乃至主宰人性——这也是后来知识分子改造的一大主题,瞿秋白对此清楚得很,并努力“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感情”,“极勉强”地用“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作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⑤《瞿秋白散文名篇·多余的话》,第234-235页。,可惜的是始终都没有成功。这也是瞿秋白称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不愿“冒充烈士”而就死,甚至称自己不配被称作“同志”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产儿,瞿秋白在入世与避世,个人与社会,精神与肉体,文学与政治等的对立间做着艰难的取舍,其最终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本身即是对自我的一种“改造”。他在旅苏游记和《多余的话》中所昭示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矛盾心路历程和不彻底的“自我改造”,也预示了革命将从外部对知识分子做出改造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同时,历史地看,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他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即鲁迅所谓的“历史的中间物”,他在新与旧,身与心,自我与社会,绝望与希望,避世与入世,退缩与抗争,沉默与言说之间挣扎与突围,他的矛盾,他的两难,也是民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嬗变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与磨砺。只不过,这痛苦在他这里如此丰富而深刻,瞿秋白,一个精神矛盾统一体,因而也成为民国文学史上一个“说不尽”的存在。
[责任编辑:曹振华]
I206.6
A
1003-8353(2014)06-0125-03
2013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生态视野中的现代域外游记研究”(20131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十二五”重点学科“文化生态学”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张显凤(1976-),女,山东师范大学博士,滨州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