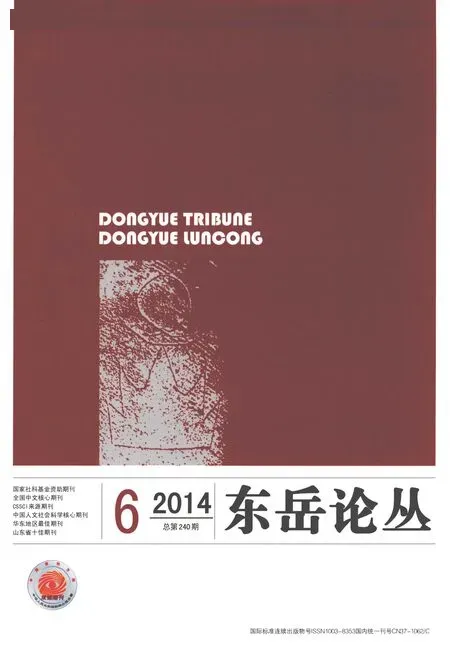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以关键词为视角的历史叙事*
[美]陈建华(Jianhua Chen)著,符杰祥、陈心湛译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以关键词为视角的历史叙事*
[美]陈建华(Jianhua Chen)著,符杰祥、陈心湛译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个经典研究课题,本文从关键词角度追踪“革命”词义起源与变化的历史脉络,对这一开展过程作一提纲挈领式的描述。在二十世纪初经由孙中山、梁启超的话语实践,“革命”与英语revolution和日语kakumei的意义相融合,既含“汤武革命”的传统,又含渐进改良之意。从五四“文学革命”和二十年代初“新”、“旧”文学之争,到二十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形成,贯穿着一根建立民族国家与整体改造社会的红线,而通过新的史料——如周瘦鹃、张春帆的小说理论与创作,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日常改良实践及其“新旧兼备”的文化政治。另以“革命加恋爱”小说为例,旨在突破关键词的局限而使“革命”更具文学感性的书写,而对于“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文学记忆的挖掘,则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面认识。
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孙中山;梁启超;传统;现代性
在近现代中国广为流传的众多关键词中,由“revolution”翻译而来的“革命”一词或许最具英雄气、最富魔力,且影响最为深远。早在1902年,梁启超(1873-1929)便已惊呼:“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①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第1-7页。可见国民对“革命”热烈响应之慨。翌年,邹容(1885-1905)编写的宣传册《革命军》刊行,掀起了全国性的反清情绪,著名文学史家钱基博(1887-1957)称“海内风动,人人有革命思想矣!”②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本,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版,第336页。梁启超与钱基博的言论不仅说明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初已打下根基,而且从梁、钱的夸张修辞也可见他们也不免“革命”一词的蛊惑。诚然,革命话语的惊人影响力持续至1980年代;虽然刘再复的“告别革命”的说法不免乐观,却某种意义上不失为后毛泽东时期对于“阶级斗争”热度消退的表征。
正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 -1985)》(1986)一书所言,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特征是“革命”,该词基本上用作一个比喻,指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然而,“革命”一词是什么意思?它的具体用法、意义以及功能究竟为何?在“伟大的中国革命”这一表述中,“革命”被赋予崇高的意义,但“革命”一词有它自己的故事要讲。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犹如一根红线贯穿着它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其话语实践以种种方式渗透于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学、文化等领域,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象征、民族危机的呐喊、群众运动的奇观、图腾与禁忌的仪式、文学艺术的正典、日常现代性的活塞。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这个关键词,中国革命的叙事就会失去血髓和灵魂。
本文将聚焦“革命”一词的历史演进的几个横截面,强调该词与政治、文学的关系。我将描述在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革命”话语如何通过世界革命的翻译而占领了社会意识的前沿,如何一再被呼唤,给主体的现代性追求注入新的精神动力,又如何形塑了近现代中国各阶段的文学场域。其间始终贯穿着革命与改良、传统与现代、本土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张力。
“革命”的翻译
“革命”一词源自古代中国的王朝危机。古代儒学经典《易经》含有该词最早使用的一个例子:“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①《 周易正义》,见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上海,锦章图书局,卷5,8a。公元前十六世纪成汤以武力消灭夏朝而建立商朝,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商而兴周。《易经》中的“革命”被赋予一种神圣的光环,然而以天意人心的名义给武装叛逆戴上合法的冠冕,事实上与儒家的伦理准则相违背,因此这一“革命”理论对于现世皇权来说含有批判甚至威胁之意。由于这种模糊性,革命话语在历史记录中成为禁忌或常常潜藏于字里行间。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词常以反义出现,如“叛乱”或“造反”用以描述古代农民起义,当然指以失败告终的农民起义。
在十九世纪末世界革命风潮中,“革命”又经由日语翻译而被唤醒。儒家的革命观念在八世纪时便引进日本,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直至十七世纪才遭到质疑,德川时期的忠义之士把汤武指斥为王朝叛徒,并声称革命只能由君主授予其合法性。因此“革命”便含有在既有政权领导下的渐进改革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日人在明治时期用kakumei来翻译英语revolution。如雷蒙·威廉斯指出,在十九世纪西方revolution并非专指政治上“暴力推翻政权”,它也涵盖“广泛世俗领域中发生的根本的改变,或本质上新的发展”之意②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revise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273.。在热切接受西方文明的明治期间,在kakumei的翻译中也蕴含该词的复合意义。
1898年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其政治抱负并从日文译作中学习西方人文思想。他被kakumei所指的社会各领域变革的新解读所吸引。为了唤起国民的改革热情,他极力传播“革命”之说。他发明了大量以“革命”为后缀的新名词,其中最著名的是“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③参看陈建华 Jianhua Chen,“Chinese‘Revolution’in the Syntax of World Revolution,”in Lydia H.Liu,ed.,Tokens of Exchange: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355–374.。梁启超的号召引起热烈反响,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小说杂志与文学副刊风起云涌,出现了大量文学作品,热心传播西方理念并谴责清政府。结果被唤醒的“革命”意识伴随着历史记忆,反而激发了反清情绪,这与梁启超维护清廷的预期相反,却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作了有利铺垫。
孙中山(1866-1925)的反清“革命”口号同样源自日本翻译,却出自偶然。1896年孙中山因反清活动在伦敦被监禁、审讯,释放后逃亡日本。据说在日本神户,他从报纸上了解到日人称他为“革命党”。这唤起他的汤武革命的记忆,兴奋中含有恐惧。孙中山幼时受教育时就知道无人可自称“革命”,反政府者只会被谤为“造反”。采用“革命”一词,他的反清运动由是变得合法而尊荣,事实上当时反清情绪高涨,他的革命口号收到实效,相形之下,梁启超意在改良的“革命”主张黯然失色。
就孙、梁二人而言,“革命”这一口号蕴含了他们救国方案的本质区别。在1905年改革派与革命派就“革命”的内涵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梁启超及其支持者坚持非暴力手段,而孙中山一众认为清政府已堕落至无药可救的地步,且清政府本身以种族统治为基础,而汉人要重新掌权,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在争论中,梁启超的改革派失势。尽管如此,在改革与革命之争后,“革命”变成传统和现代的复合体:除却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夺权,也包含社会各方面的根本性改变,即政治暴力手段与建设美好未来的愿景交杂在一起。
五四“文学革命”
在1912年民国建立之后,从表面上看,举国上下在立宪体制下致力于富强之邦的建设。这场成功的政治转折被称为“大革命”。当袁世凯军阀政府掌权之后,很快背离了革命初衷,由是产生普遍的幻灭。袁下令全民尊孔读经,并以自己称帝的方式恢复了王朝统治。更有甚者,在称帝过程中与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于是,在1913年初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遭到暗杀后,孙中山号召声讨袁氏而举行“二次革命”。然而“二次革命”收效欠佳,不仅是因为袁世凯的北洋军队过于强大,也是由于此时革命已不得民心。甚至在国民党内部也有部分人认为袁世凯固然可恶,但立宪体制更为宝贵,再度革命不仅危及民国的合法基础,而且将祸乱相生,没完没了。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混乱,地方军阀连年相互争战,虽然他们都需要最高权力的民国议会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
1917年,以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1891-1962)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1879-1942)的《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为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上述的历史语境里展开。尽管两篇文章分别标以“改良”与“革命”,它们都无情抨击了中国文学传统,并称其毒害了国人的灵魂。从字面上看,“文学革命”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一脉相承,即要求文学领域的根本改变。然而,陈独秀以“革命”为号召,刻意要与胡适的“改良”相区别,在对旧有文学与文化传统的断然否定之中,同传统意义上的暴力政治有着内在联系。事实上,五四的激进主义与陈独秀的革命理论一拍即合。其中分享了一种思维模式,即总结晚清以来一系列改革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慈禧和袁世凯背后的旧文化过于顽固,必须彻底根除,必须代之以新文化,而这种替代过程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
鲁迅(1881-1936)的短篇小说形象地体现了这种革命观念。他于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把矛头对准“吃人”的礼教。他的小说里的众多人物,从士人到平民,都是旧文化、特别是儒学教条的受害者。小说情节一般设定在小镇或乡村,人物通常在情绪上和精神上都被政治腐败、家庭伦理、科举制度、封建迷信等恶势力所毒化和压迫。在《药》与《阿Q正传》中,鲁迅谴责1911年的辛亥革命向旧文化妥协并造成新的压迫者。受尼采“重估旧价值”思想影响的鲁迅,其视野之广度和深度远超他的同代人。狂人在“铁屋子”中呼吁“救救孩子”,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他自身也是吃人社会的一份子。在再现被牺牲的灵魂时,鲁迅对于受压迫者表达了深刻的同情。“孩子”作为尚未遭受瘟疫般社会毒害的比喻蕴含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也代表了鲁迅的价值批判,这不仅针对旧传统,也针对新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
随着五四的反偶像主义愈益发展,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自觉。新文学领域中涌现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西化文体的作品,表现了“铁屋子”中那种绝望及迫切向往思想解放的心态。“新文学”的特点不仅在于内容上拥抱西方现代主义运动,更在于形式上由文言转向白话。这一“语言转向”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深远影响。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清廷和民国政府都力图进行语言改革,却收效甚微。在五四期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钱玄同(1887-1939)、刘复(1891-1934)等人都从理论上提出把白话当作文学语言的主张,同时积极帮助教育部推行“国语”运动。在1920年代初,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要求白话代替文言的教育法规。的确,白话的垄断地位对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精神、传播现代知识,以及日后动员群众参与解放运动的目标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国语”合法性的确立,新文学很快朝中心移动,并与都市大众文学社团发生论争,五四正典也随之形成。1921年茅盾(1896-1981)担任了上海的权威小说杂志《小说月报》编辑,随即将该刊变成了文学运动的新阵地。与此针锋相对,上海流行小报《晶报》的主要作家袁寒云(1889-1931)对《小说月报》的艺术质量进行了嘲讽,并谴责该报崇尚欧化语言与风格而摈弃代表传统精粹的文言。在争论中,郑振铎(1898-1958)指斥那些流行作家,是商业动机使他们沦为“文丐”和“文娼”。
论战一度白热化,更多新旧阵营的作家和刊物卷了进来。代表五四阵营的主要有茅盾、郑振铎、郭沫若(1892-1978)和鲁迅,旧派方面有袁寒云、周瘦鹃(1895-1968)和包天笑(1876-1973)等。除却语言这一中心话题,双方在文学的功能和民族“想象共同体”模式方面也存在深刻分歧。茅盾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当是合乎历史进步的文学”,即一种能为世界各民族所理解、接受的表达方式。他鄙视流行小说,称之为缺乏历史自觉和现代技法的“记账簿”。他特别批评周瘦鹃的爱情故事,认为其缺乏艺术的良心。郑振铎则提倡反映被压迫者疾苦的“血与泪的文学”。两人一致批判《礼拜六》——周瘦鹃编辑的“消闲”杂志,斥责它逃避现实黑暗、引导青年远离救国的崇高理想。
作为抗辩,周瘦鹃提出在现代社会压力下寻求放松的都市居民需要消闲文学。他认为他的杂志仿效了英国的《伦敦杂志》和《海滨杂志》,具有满足都市大众文化需求的普世性;他对于中国的都市前景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像在西方一样,也会得到发展。正如他所言:“新崇其新,旧尚其旧,各阿所好,一听读者之取舍”①鹃:《自由谈之自由谈》,《申报》1921年3月27日,第14版。。听凭读者的选择,实际上表明周瘦鹃对自由贸易准则的信心。显然在这场论争中,且不论五四精英主义及其拥有高等教育系统的文化资本,新文学获得了向往现代性和怀抱救国使命的年轻一代的拥戴。并非偶然,在流行作家退出论争后不久,白话便因其“国语”正宗地位的确立而高奏凯歌。尽管如此,都市消闲文学的市场仍继续在蓬勃发展②陈建华Jianhua Chen,“An Archaeology of Repressed Popularity:Zhou Shoujuan,Mao Dun,and Their 1920s Literary Polemics,”in Carlos Rojas and Eileen Cheng - yin Chow,eds.,Rethinking Chinese Popular Culture:Cannibalization of the Can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91–114.。
由于五四时期历史进化的观念被广为接受,新旧文学之争显出非同寻常的意义。原本泛指的“新”与“旧”开始意识形态化,前者指涉历史进步、拥有美好的未来,后者意含落后、颓废与逃避主义。在1930年代,左翼作家继续攻击旧文学,进而给它贴上“封建小市民”、“鸳鸯蝴蝶派”的标签。而通俗作家由于在理论上处于下风,且在民族危机加深时,不免感到愧疚,最终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自动淡出了。
“革命文学”之争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卷土重来,此时受到渴望早日结束军阀混战的民众的欢迎。1924年,在苏俄和中共的协助下,孙中山领导北伐军自广东出发,势如破竹,以致重又听到“大革命”的欢呼。然而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北伐的神圣光晕骤然消失。蒋介石(1887-1975)在掌权之后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迫使毛泽东(1893-1976)及其追随者转向农村开展农民革命。同时,一批共产党员从战场退至上海租界,组织地下抵抗势力。在政治陷入危机之时,文学再次承担了不凡的使命。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谴责了蒋介石的背叛行径后出逃日本,他在稍早时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过“革命文学”,此时则成为共产党作家的迫切需要。作为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郭沫若代表五四传统发言,这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将五四的激进主义更朝文学政治化的方向推进。由此文学完全为“革命”服务并与共产党在农村和城市的群众政治运动紧紧捆绑在一起。
1928年初,隐蔽在上海租界的共产党人展开了一场“革命文学”的意识形态辩论,这始自于创造社理论家成仿吾(1897-1984)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除呼应郭沫若的关于文学应当成为革命大业“留声机”的主张之外,成仿吾进一步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陷在于眼光狭窄,而革命文学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服从无产阶级的解放目标。与此同时,李初梨(1900-1994)、彭康(1901-1968)、朱镜我(1901-1941)等创造社新成员创立《文化批判》杂志,热情介绍马克思的理论;受到当时日本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1894-1983)的影响,他们热衷于诸如“奥伏赫变”(译者按:原文为德语,意谓“扬弃”)、“辩证法”和“意识形态”等关键性概念。在处理文化问题上他们突出主观思想的作用和辩证思维,同时在分析文化现象和从事有效的思想宣传方面,极其强调“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并在论战中把它用作“批判的武器”。李初梨、彭康与太阳社的钱杏邨(1900-1977)一起攻击五四文学的精神领袖鲁迅,把他卡通式地形容成多愁善感、消极而陈腐的“醉眼朦胧”之人。从“革命文学”视角出发,他们说崇尚“个人趣味”的“文体家”鲁迅已然过时。作为反击,鲁迅尖锐批评创造社青年作家们观念的幻觉及自恋地迷信“批判的武器”,而逃避真正的革命行动。同时他也质疑当时所谓“无产阶级文学”的流行口号,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产物,完全脱离生活的真实经验。尽管意见相左,争论各方都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都为“革命文学”的性质与前途担忧。日后鲁迅透露他曾受到创造社的年轻作家的逼迫而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是翻译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1856-1918)的著作《艺术论》。
受到挫折的共产党人正面临如何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新组成统一的文学战线的任务,因此“革命文学”之争似是一场及时雨。尽管内部发生过尖锐争执甚至人身谩骂,他们中的多数达成了一致,于1930年成立了“左联”,接受了鲁迅与共产党干部的领导。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一事件被正典化地视为现代中国文学踏上正确道路的起点: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学创作继续沿着五四的道路前行,并肩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用茅盾的话来说,这一“转捩点”见证了知识分子从五四的个人主义转向了五卅的集体主义。事后看来,在“革命文学”原则指导下的文学运动显然为政治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前景,且蒙上了乌托邦的理想色彩。在政治方面,与准备向现状妥协的国民党分道扬镳,而革命化的文学首先用来动员民众,目的在于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比如,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同时力图建立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新的民族国家。在文化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思想的左翼作家积极介入都市中心的大众文化,尝试使用某种“大众语”,藉以再现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现实主义。为了赢得都市读者的支持,他们创造了诸如“革命加恋爱”的新小说类型,将传统文学套路、现代描写技巧和革命理念融为一炉。他们最大的成就或许是把上海电影工业转变成娱乐与教育并重的机制,并生产了一批具有思想意义的影片。比如1933年根据茅盾的小说《春蚕》改编的电影描绘了本土小本经营如何在半殖民地中国必定破产的情状。此一微缩悲剧给观众带来了某种关于本土与全球资本主义下的社会结构的深层见解。
“革命加恋爱”小说
1920年代末,蒋光慈(1901-1931)、丁玲(1904-1986)、胡也频(1903-1931)和茅盾等人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大行其道。在意识形态层面,“革命加恋爱”小说与“革命文学”的争论联系密切,这类小说大多为长篇。自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小说这一形式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直至1920年代末才突然兴旺起来。之所以出现一种历史叙事的新的欲望,一方面是失败的“大革命”所含的悲剧史诗与复杂人性对于现有小说带来形式上的挑战,另一方面出于迎合市民读者的兴趣,他们喜欢兼有浪漫爱情和英雄事迹的小说。“革命加恋爱”小说致力于塑造新的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鲁迅尖锐批评这类无产阶级形象,认为是那些不熟悉工人、农民生活的作家向壁虚构的产物。这批评固然有道理,然而也正是那种想象――多半怀着对苏维埃革命的憧憬之情,却为现代文学开启了新的篇章。
“韦护穿一件蓝布工人服。”丁玲的小说《韦护》开头这么描写。小说描写主人公韦护从苏联归来后给群众作“革命”启蒙。从他的自省中透露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如何彻底转变了他的人格与世界观,在此丁玲呈现了一种新型的革命主体,具有某种理论与历史的深度。该小说最吸引人之处在于描绘韦护女友丽嘉及其朋友们的快乐而自由的氛围,“她们讲的是自由,是美,是精神,是伟大。”①丁玲:《韦护》,《丁玲文集》第1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这些细节暗示了对于苏联的想象。韦护的革命理念还是由于周遭的恶劣环境而失败,最终忍痛与丽嘉分离,决定赴广东加入北伐革命。在此丁玲颠覆了传统小说中常见的“为情而死”的套路,而引入了新的革命高于爱情的伦理观。
在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中,苏联的影响更为明显。主人公素裳是一名聪慧热情的“现代新女性”。身为国民党高官之妻,却厌倦了无聊无味的生活。直到共产党人施洵白进入了她的生活,点燃了她的激情,二人相知相爱。在施洵白惨遭素裳的丈夫秘密处死之后,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庭,远走莫斯科去寻找革命理想。与《韦护》不同,《到莫斯科去》聚焦于女主人公的思想转变。在阶级意识觉醒之后,素裳对《包法利夫人》中自私、虚荣的女性形象产生鄙夷,这么表达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毋宁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文学趣味的转变。标题中的“莫斯科”作为“广东”的对立面出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更具共产党色彩。
蒋光慈的《短裤党》和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则将重心放在群众运动上,展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集体力量,而非个体英雄。尽管所塑造的党的领导者形象大多缺乏个性特点,但以欢欣的笔调描绘了革命群众运动的节庆般的狂欢、奔放的热情,海洋般的旗帜、口号与歌声、对胜利无法抗拒的渴望,以及创造历史的自觉性。爱情主题贯穿始终,却都显得高尚圣洁,很少有身体的欲望。男女间以同志的身份开始相互了解,最终将情感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之上。因此蒋光慈和胡也频的作品多不为现今的评论家所肯定,但作为“革命文学”的最初实践,他们的作品为后来的“革命文学”创作起了开路作用。
无疑,革命加恋爱小说在茅盾的《蚀》与《虹》那里达到了巅峰。作为共产党早期成员、五四激进传统的代表人物的茅盾,参加了北伐;见证了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之后,他移居上海并开始小说创作。在1920年代初他曾大力介绍欧洲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小说创作理论,企盼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优秀作品也会在中国出现。
茅盾的第一部小说《蚀》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随即遭到钱杏邨与李初梨等人的严厉批评,认为小说缺乏无产阶级“革命”意识。茅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二人关于“颓废”与“消极”的指责,承认他当时情绪确实低落。然而茅盾坚称他小说的目标受众为“小资产阶级”,并认为他们应当成为不可或缺的革命力量。纵然褒贬不一,富于启示的是茅盾有意将小说形式革命化,巧妙地把历史意识渗透在叙事之中,同时在情节、人物塑造方面都显出现代主义的艺术手腕。《蚀》包括《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虽然联系松散,但结构恢宏,全景式地揭示了混乱中的复杂社会关系以及历史运动的悲剧性。其中包括孙舞阳、章秋柳等“时代女性”,她们迷人而浪漫,拥有“大革命”式的冒险精神,仿佛在乌托邦空间中自由自在,不受传统妇道的约束;通过这些新女性,茅盾力图表现传统必然要被现代所克服,以及历史的进步趋势与个人欲望之间的和谐,却多以失败告终。比如奉行活在“现在”的章秋柳企图把颓废的浪荡子史循从他黑暗的“过去”拯救出来,最终却是个苦涩的反讽:在洞房之夜,两人酒酣而尽兴狂欢,史循力竭而亡,章秋柳则染上了梅毒。尽管如此,由于茅盾熟悉二十年代上海知识女性的社交生活,一些叙事细节显得活色生香,如孙舞阳服用避孕药,或不戴束胸等习惯,把她塑造成追求性解放的“新女性”。
在茅盾1929年的长篇小说《虹》里,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被表现得更为成功。作为对“革命文学”之争的回应,茅盾重新诠释了五四激进传统。小说反映了自五四至五卅期间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逐渐觉醒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武装自身的。主人公梅行素是四川的一名学生,思想上受到《新青年》杂志的影响;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离开落后的家乡前往大都市上海。在小说结尾,她在五卅群众示威队伍里与租界警察做无畏的抗争,极富象征意味地行进在人群的前列,加入革命的洪流并领导群众走向未来、走向解放。
《虹》一开始描绘了梅行素在驶向上海的轮船上,倚着栏杆,“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①茅盾:《虹》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在奇伟清丽的巫山美景衬托之下,茅盾运用了“江山美人”的古典美学,塑造了这样一位“东方美人”,然而她是献身于民族斗争的现代女战士。叙述者如是称:“但是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的人。”文本隐含着古代楚王梦见巫山神女的典故,但是神女被一位西方女神所取代,梅行素被比作北欧神话中的命运女神Verdandi,勇敢而充满活力,目光注视着前方,象征着现在受着未来的指引。
梅行素被称为“现在的信徒”,其形象塑造被纳入预设的时间框架,如同北欧女神一样,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的人”,坚定追随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历史进步的观念。全书共分十章。讲述梅行素离开四川前往上海的第一章对整个叙述结构至关重要,接着倒叙她在四川的生活,直至最后三章承接第一章,写她在上海的生活。对梅行素来说,离开四川意味着告别守旧、陈腐的过去:“现在这艰辛地挣扎着穿出巫峡的长江,就好像是她的过去生活的象征,而她的将来生活也该像夔门以下的长江那样的浩荡奔放罢!”在此时间与空间的隐喻是可互换的,但是时间最终还是让步于空间,因为在时间上梅行素一直向前,而从空间上看她则是一步步走向篇末上海的五卅游行。
在上海,梅行素出现爱情与革命的人格分裂。她投入革命团体中并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大都会的诱惑。她穿旗袍、高跟鞋、乘坐人力车,像一个忙于日常事务的中产阶级妇女。然而,梅感到无聊、孤独和抑郁,承受着现代性压力下都市人的精神症候。她暗恋上了革命团体领袖梁刚夫,并竭尽全力吸引其注意:“她渐渐替自己规划出课程来了:留心看报,去接触各方面的政团人物,拿一付高傲的脸孔给梁刚夫他们瞧”。这样描写类似欧洲的成长小说,通常是一个外省年轻人来到都市,适应新环境,经历了“升沉起伏和内心躁动”,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②Franco Moretti,The Way of the World: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London:Verso,1987),4–5.。当然,虽说主题类似,但与个人奋斗不同的是,梅行素处处压抑自己的情欲,让位于民族解放的革命理想。“她惟一的野心是征服环境,征服命运!几年来她惟一的目的是克制自己的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
《虹》为评论界认作茅盾“最佳”作品之一,夏志清先生认为,这一“现代中国早期长篇小说”体现了“心理现实主义”的纯熟技巧③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3rd e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148;David Der-wei Wang,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40.。的确,《虹》标志着中国新文学长篇小说的确立,而具有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它是个复杂的机体:糅合了传统文学的元素、西方现代主义、都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的理论。以相当激进手法在现代历史意识的史诗结构中塑造了梅行素这一形象,茅盾将传统的“小说”形式现代化,同时也为民族文学创造了一种小说主体,解决了自晚清“小说界革命”以来就提出的理想人物的问题。同时,这部小说在政治与美学上多所借重外来的资源,体现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视域。它不仅在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凸现了中国解放运动的主体,也借用或挪用左拉、莫泊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④详见陈建华 Jianhua Chen,“Mao Dun’s Rainbow:A Modern Epic and Bildungsroman Novel in 20th Century China.”In L’Oriente Storia di una figura nelle arti occidentali(1700 – 2000),the Second Volume,eds.,Paolo Amalfitano and Loretta Innocenti(Rome:Bulzoni Editore,2007),57–77.。
“革命”的变调
1920年代末,蒋介石将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作为其革命箴言,而毛泽东则在江西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发表其名言:“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当时“革命”是时髦话头,在大量报纸期刊上大量出现,在歌颂北伐革命的主旋律中可听到不协之音。如《中央日报》开设了名为“摩登”的文学专页,在宣言里赞扬国民党领导下的“摩登国民运动,摩登革命精神之产物”,然而也告诫只有“厉精图治”才能称得上“摩登之国民党”,否则“腐化恶化,自速其亡”①《摩登宣言》,《中央日报》,1928年2月2日,第3张,第4面。。实际上该专栏成为徐悲鸿(1895-1953)、田汉(1898-1968)等知名人士作品的发表园地,更崇尚欧洲现代派艺术与文学,大量刊登了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的翻译作品。另如叶浅予(1907-1995)等人办的《上海漫画》在创刊号上高呼“小瘪三万岁”,对时局表达讽刺和牢骚,代表了都市大众的心声,甚至有言:“革命尚未成功者,就是中国人还未死完。若有一人存在,犹有命可革。这许多人都未死,故革命尚未成功。”②厂独:《革命尚未成功的妙解》,《上海漫画》,第1期(1928年1月),第3版。对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作如此“妙解”,对于正在节节胜利的北伐运动,可谓极尽挖苦之能事。
“四·一二”之后,国民党在实行“白色恐怖”的同时,还派专员审查报纸,颁布电影管制条例等。这不光是针对政敌,而是在广泛的思想与文化领域中推行党治。在这样的情势中,出现“革命”的众声喧哗,听似一片颂扬北伐的主旋律交响,其实遍布讽刺和挖苦之声。这与其说是对国民党官方表达不满,毋宁说反映了市民社会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常态。其背后不仅是大众尊奉日常欲望的逻辑,浸透着渐进改良的精神,还因为印刷资本及其文化机制仍在自由运作,言论空间尚未丧失殆尽之故。
其实,“革命加恋爱”小说在当时并非左翼作家的专利。比如,从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连载张春帆(? -1935)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紫兰女侠》③《紫兰女侠》,《紫罗兰》,第4卷,第1-24号 (1929年7月-1930年6月)。,就值得注意。小说主要描写清末时期一批江湖女侠帮助孙中山发动1895年广州起义的故事。在政治倾向方面它似乎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却不那么主流,其实表现了一种市民大众对“革命”的民间诠释立场,由此也可见印刷资本主义机制给创作带来某种独立性。
张春帆是旧派小说名家之一,民国初年即以描写十里洋场妓院生活的长篇《九尾龟》而名扬文坛。《紫兰女侠》也意在彰显《紫罗兰》这一杂志品牌。所谓“给列位看官作一个酒后茶余的消遣罢了”,含商业与游戏性质,却花样翻新,追随“革命加恋爱”的小说类型。然而,“革命”的内涵与共产党左翼的同类小说却大相径庭。正像作者声称,这是一部“革命外史”,即采集一些有关民国起源的珍闻轶事,从清末孙中山反清“革命之役”写起,中经“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直到北伐时期。在二十年代末“国民革命”节节胜利的脉络里,小说似乎意在高奏一曲歌颂“三民主义”的“革命”主旋律,然而稍加细察,可发现另有一种自由主义的色彩。
小说以何紫兰和柳安石为主线,经过一系列周折而终成眷属,还穿插了其他几对恋人的罗曼插曲。主要的悬念是一直夹在何、柳中间的少年仇紫沧,长得跟何紫兰一模一样,最后真相大白,原来是女扮男装,既充作何的男友,又是她的替身。显然作者也在玩三角恋爱的游戏,却浸透着一种另类革命的意识形态。所谓“紫兰女侠”,是由一班男女自行组织的一个革命同志会,住在离广州几十里外的紫兰村里,一个颇具诗意的世外桃源。会长何紫兰统领一群女侠,每个人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紫”字。她们也是革命的同路人,当何紫兰向柳安石介绍说:“敝会虽然赞助革命,恰不是革命党,和革命党的破坏宗旨略略的有些异同”。换言之,她们所信奉的是非暴力革命,或合乎改良精神的“社会革命”。柳安石是粤中某中学教员,自称“不是革命党人”,因此听了何紫兰的话,欣然同意。原来他根本上并未认同孙中山,声称“我的革命主张,本来和急进派不同,是主张联合全国会党蓄养出一种潜势力来,然后用政治革命的手腕解决时局的。这般的办法,既不妨碍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也不阻碍国际间的邦交。这武力解决的革命,是我不赞成的。”
小说里处处突出柳安石见义勇为与人道关怀,有一处写到革命党人要杀一个满人,柳加以制止说:“革命是统一大同主义,不能用狭义的解释,强分内外。”这里显然不同意孙中山的种族主义了。另一处柳说:“要知道革命事业不能专讲破坏的,万不得已只好破坏个人而维持团体。”又说“少一次破坏,就为国家地方多留一份元气,这是我和革命党宗旨不同的地方”。柳的这些论调,包括他的加入这样武力的“政治革命”是出自形势,他所倾心的是“社会革命”,并非作者杜撰,令人想起清末康有为、梁启超那一派立宪主义的主张。不过在国民党北伐革命高奏凯歌的语境里,听上去并不那么协调。
女侠们同革命党一起作战,主要在于暗中配合,排难解纷,常在革命党人陷于危机时出现。当然,对于小说来说,也是特意制造的关键时刻,表现她们的飒爽英姿,江湖本色。如写到一对革命党夫妇被清兵拖到船上、将遭杀害之际,船上突然闪现一道紫光,从空中落下一个紫衣少女,喝道:“不许杀!”只见她“穿着一身称身可体的紫绡衣裤,恰淡淡的,不十分深,头上裹着一条紫帕,连鞋袜都是一色紫的,空着一双手,只腰间紫绡带上缀着两支银色小手枪,生得削肩细腰,明眸皓齿。”她们佩戴小手枪,显得十分现代,但她们照样实行“和平革命”的宗旨。其实何紫兰的新式武器“电枪”,是一种不伤人的无声手枪。不过,在武器方面是现代化,她们在文化上却是国粹派,不光是崇尚功夫武术,连紫兰堡里所有屋里的摆设都是本土产品,没有一件洋货。国粹主义也见诸她们高明的土法医治。一位受重伤的革命党人被送到紫兰堡里,何紫兰以“出汗法”给她治疗,即令她在沙地上打滚,她还是不出汗,于是由四人将她抛到半空中,她受了惊吓出了汗,体内透了气,伤也就治愈了。何还讲了一通身体被电气支配,剑术有红光、白光的玄理。这些描写显然有矛盾处,会令人觉得好玩,作者着意标榜这种文化的民族主义来体现“纯洁”的主旨,其实单是这紫罗兰本身便是舶来品。她们把它用作同志会的“证章”,似乎也跟拿破仑的“百日复辟”的传奇有关,即拿氏从厄尔巴岛重返巴黎时,凡是拥护者皆佩戴紫罗兰徽章,作为辨认的标志。
在体现爱情的“纯洁”方面,小说宣扬“贞操”论。如在紫兰堡中养伤的李若英“虽是个开通女子,他恰看得贞操极其重要。他说一个女子的贞操是全部份爱情的代表物”①此处的“他”为女性的“她”,在旧派小说中男女都写作“他”。,亦诤诤告诫:“世上的女界同胞们,若先受了青年的诱惑,在全部份爱情未有寄托之前,就丧失了贞操,……至少在自己的心灵上终是一件不痛快的事。”所谓“全部份爱情”,意谓灵肉一体,丧失贞操,等于丧失爱情,在这方面作者仍在坚持传统价值。这和五四以来有关新女性的性解放的观点背道而驰,在新文化作家的“革命加恋爱”小说里,普遍描写灵与肉的分裂,纯粹的爱情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如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出卖肉体并不妨碍她的革命理想,或张资平笔下的苔莉,女性意识更为生物性冲动所占据,而在茅盾的《虹》里发展到另一个极端,即梅女士干脆要克服“母性”而成为“主义”的化身。换言之,爱情已经臣服于革命。
这些紫兰女侠也是新女性类型,与一般旧派小说里贤妻良母的类型不同,她们受到国民革命的感召,在新天地里大显身手,仿佛是一部儿女英雄传的现代演绎,更带有集体理想的色彩。最后一幕是从众人眼中看去,柳安石与何紫兰俩人在花园里:
何紫兰手中拈着一枝紫罗兰,插在柳安石襟上,口中说道:“我别无所爱,平生第一只知爱国,第二只知爱爱国的英雄,你就是爱国英雄中的第一人。”柳安石倏然立起身来,低声说道:“我的爱你,也是由于爱国而兼爱爱国的女英雄。你把我算作第一个爱国的英雄,我惭愧得很,你才算得爱国英雄中的首领呢。”
这里皆大欢喜,不脱团圆剧窠臼,肉麻的卿卿我我是才子佳人式的,却谱出儿女英雄的“爱国”合奏。小说的结局为这个小团体设计了某种理想的蓝图,呼应了在卷首便出现的紫兰堡的乌托邦母题,此时同志会接受了某富翁的巨额捐款,计划在江苏北部的海边建设一个“模范港”,由三个葱茏小岛映带四周的一个冬暖夏凉的天然海港,作为同志会的总部,把广州紫兰堡改作分部,意味着他们小天地的美好未来。
早在1907-1908年发表《九尾龟》的同时,张春帆在《月月小说》杂志上连载标为“立宪小说”的《未来世界》,或可视作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姊妹篇。书中鼓吹“立宪救国”、“改良政体,组织国民”,还提倡“满汉团结”、“女子教育”等,确是梁氏的忠实信徒。在二十年之后的《紫兰女侠》里,这些主题一一重现,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民国以来“革命”不已,国无宁日,共和政体破残不堪,公共空间愈益萎缩,因此“立宪救国”仍是国人的未圆之梦。尤其在“大革命”之后蒋介石推行“党治”之际,《紫兰女侠》标明与孙中山反清“革命”相区别,取一种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疏离的另类姿态。
尾声:文化大革命及之后
在现代中国,随着语言系统由文言文转向白话,“革命”一词的使用也经历了巨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与儒学的政治文化千丝万缕的“革命”一词,在“五四”反传统、反儒学的汹涌波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同一个民族复兴的寓言,“革命”多次折戟沉沙,又多次在危机之际复苏,似乎从来不曾丧失其天意民心的光晕。在世界革命文化的哺育与调适之下,它代表着对美好未来的期许,也包含着传统与现代——或用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的话说——“区域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张力①Joseph Levenson,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革命”话语的内在活力终于在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达到了巅峰的展示。
将毛泽东与古代君王汤武之流相提并论是幼稚的。然而从语言角度看,“革命”传统源自于汤武;事实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和共产党中国的诞生也不外乎是以暴力推翻旧政权的历史重复。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的道德理想推动的;通过清除“修正主义”与“党内资本主义”,他似乎在寻求某种纯粹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他不断提倡“将革命进行到底”、“造反有理”之类的口号,“革命”话语不曾摆脱过去被压迫的创伤记忆。五四的激进主义展开其内在逻辑,也终于臻至其极致。文革在列文森看来更近乎“区域主义”。如“革命加恋爱”小说,在195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红色经典”的创作范式。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与电影《聂耳》为例,这一类型以精致的政治与情欲的审美方式建构了民族国家与爱情的迷思②Ban Wang,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23–154.。然而这一文学传统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也被视作“封资修”的文化渣滓而打入冷宫,从这一点也可见共产主义者的文化视野变得狭窄起来。虽然,文革也有“世界主义”的一面,甚至在“样板戏”中也有芭蕾舞、交响乐等形式——当然,那是经过高度筛选,且仅具象征的意义。在更为宏观的语境中,毛泽东一面宣称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同时认同古代法家的思想渊源,这反映了他的极其奇特的本土和全球视野。
文革之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革命意识形态不再得到国家机器的支持,因此逐渐淡出。最近据报道说中国政府宣布删去“革命烈士”一词中的“革命”,仅保留“烈士”③Jane Macartney,“Revolutionary change for China’s heroes,”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asia/article3412469.ece.。在“告别革命”的时代,被人们有意无意遗忘的不光是革命史上的痛苦与黑暗面,也包括“革命”话语及其崇高道德和乌托邦理想。在全球现代性笼罩的时代,这种遗忘越发加速,像本土价值一样从记忆中抹去。然而,“革命”一词并未消失,经常在媒体中出现,指各行各业中“变化”或“改革”,这就接续了一个世纪之前梁启超的用法了。有时“革命”也见诸于学术会议的议程表上,成为历史反思的课题。无论见与不见,革命话语印刻在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深层,与既存权力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如何纪念、重估中国现代的革命遗产也是我们今后必须面对的课题。
[责任编辑:曹振华]
I206.6
A
1003-8353(2014)06-0105-10
*本文译自王斑(Ban Wang)主编,Words and Their Stories:Essay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Leiden/Boston:Brill NV,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