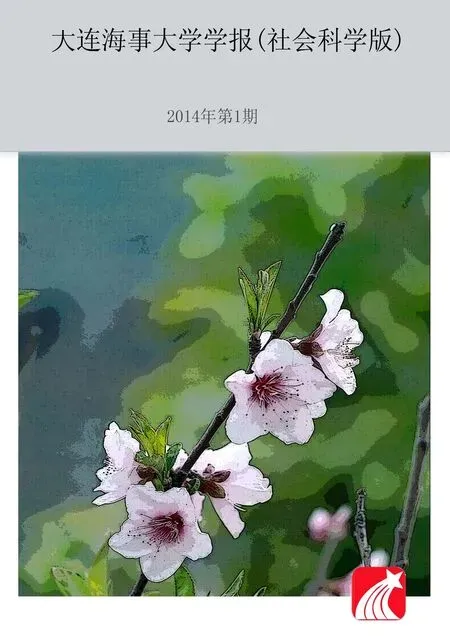超越平凡生活的本真追求
——《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简析
张连义
(菏泽学院 科研处,山东 菏泽 274015)
《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是朱文颖的又一力作,作品以对烟雨江南生活的热衷显示出明显的絮语特征,但在其将笔触伸向江南平凡生活的同时,也由于对烟雨江南的内部刺探显示出超越性的特征,从而呈现出柔弱外表下的韧性,也证明着江南性格的多重特征和江南文化的多重意蕴,为人们展示出本真的江南生活意蕴。
一、江南生活的女性絮语
南方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散文化特征,作为南方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朱文颖的小说犹如南方女性闲暇时的絮语,在漫不经心地倾诉着饮食男女的普通生活故事。故事是小说的基本构架,在一定程度上说,小说就是故事。朱文颖的《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琐细、缓慢的絮语活生生是烟雨江南的文字再现,貌似碎片化的絮语流淌着南方性格演绎的平凡故事。对平凡生活的本真追求使朱文颖的小说呈现出明显的散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作品的故事性,但作品确确实实是在讲述一个关于江南生活的故事,就如王尧先生所说:“如果认为朱文颖的小说没有故事,那是误解。南方尤其是江南的作家笔法大多细腻,散文化的叙述,常常让叙事沉浸在诗性和潮湿的蔓延之中。”[1]细腻的笔法、散文化的叙述使朱文颖的小说呈现出“散”的特征,在在是江南烟雨笼罩下的青山小楼的艺术再现,而其间蕴涵的无数变化,又使其呈现出移步换景、错落有致的“园林风格”。
《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我”的女性叙述角色使整部作品成为南方女性的独语,而作品大量采用的回忆式叙述更由于叙述者的剪裁具有了跳跃性特征。跳跃的快节奏与女性絮语的慢节拍的融合使作品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也使作品成为一种女性视角下的家族生活历史片段的组接。
“关于外公童有源,我的外曾祖母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在她怀孕的时候,不知什么地方正在打仗。一会儿开炮、一会儿打枪的,整日都不得安宁。其实我们都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她的意思其实是说——那躲在娘肚子里角落里蜷成一团的外公,他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创伤,结果才变成了这个样子。”[2]3
这是作品的第一段,典型地表现出朱文颖作品的散文化特征,也预示着作品将要讲述一个家族历史的生活故事。作品以童莉莉贯穿全书,但“我”的回忆与现实生活的穿插无疑又在丰富着童莉莉的形象,从而使童莉莉的形象鲜活起来,也使童莉莉的一生流动起来。童有源、“我”在作品中的角色无疑是童莉莉的前世今生,三个具有相同气质的家族成员毋宁是同一性格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呈现。因其在不同时代的生活演绎,使得作品的内容成为流动的历史。作家选取江南日常生活结构故事,以日常生活的变更展示时代的变化,使作品始终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历史内容与生活气息相融合,使作品成为江南生活的流动历史。生活于现实,每个人都逃不脱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在作品中,时代演变退为背景,主角依然是生活中的饮食男女,或者说作家更注重他们的日常性。他们是一群在宏大历史中生活的饮食男女,男女饮食自然成为他们在作品中的常态。无论是具有良好出身的潘家还是满怀政治理想兢兢业业工作的常德发,展现出来的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面。也因为饮食男女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作品呈现出琐细、散漫的特征。
吴义勤先生以“大时代的小生活”[3]形容这部作品,张清华先生也以“南方想象”概括作品的特征,切中了作品的脉搏。“《莉莉姨妈》中历史叙述的‘策略’是值得注意的,它所采用的是一种‘私人场景’与‘宏大历史’之间迎面相遇又迅速躲开的交错方式,这是人物的态度,也是小说叙事的态度。历史因为碎片式和‘微观化’而显得更加漫长,个人记忆的恍惚旧梦,使它‘四两拨千斤’式地虚构出当代历史的曲折,以及它戏剧性的翻覆与跌宕。”[4]琐细的生活、跳跃性的思路、独具江南特色的场景以及江南女性的南方想象,整部作品绘制出一幅苏州饮食男女的普通生活长卷,但这些饮食男女并没有超越于时代,而是与历史潮流一起流淌。只不过,他们的世俗生活和市井气息显示出与时代的疏离。
二、江南性格的韧性诠释
朱文颖认为其作品具有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特征,不少论者对此表示认同。但散文化、碎片化不等于凌乱与琐屑,而是如同阳光照射在水面映出的粼粼波光。朱文颖选取时代变化大潮中饮食男女的普通生活,表现了他们在历史潮流中的浮沉,同时也刻画出他们对生活的坦然,童有源、童莉莉和“我”身上更是贯穿着对平凡、琐细生活的拒绝,并以执着的追求显示着内心的纯真,从而使作品以女性絮语昭示出南方性格的韧性。“‘细小’首先是源于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它是碎片式与微观化的,虽然小说涵盖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社会生活,但并非一种宏大叙事。它叙述与描绘的是一些发生在‘历史夹缝’里的人和事,他们是南方化的,有着南方的‘精细精致,妩媚柔软,小心翼翼,以柔克刚’。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奇怪的,不管不顾的。在革命与暴力的时代里,他们做着自己的事情,想着自己的心思,在时代的潮流里硬是挤出自己的一小块空间;在剧变的商业大潮中,他们有些疲惫与感伤,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所终,他们总是像时代里的局外人。唯有一些细部与场景是恒久而延续的。不论历史怎样庞大、粗暴,怎样坚硬、杂芜,那些看似散漫却又坚韧的、散布在南方的日常生活细节与文化气脉,总能找到自己的身段与方式。这种‘身段’甚至还谈不上‘对抗’,甚至只是屈身而过,但就像水流的势能,而这就是南方的力量所在。”[5]长流的细水汇集在一起形成瀑布飞流直下,自有其内在的壮观与气势。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南方絮语中蕴涵的诗意和力量,只不过这种力量内蕴于细水长流形成了流动的韧性,流动性遮掩了韧性。在南方尤其是南方女性的阴柔之下隐藏着傲慢、执着甚至刚强,阴柔与刚强、缠绵与决绝、执着与柔弱的有机统一才是完整的南方性格,而所谓缠绵悱恻的烟雨江南只不过是日常表象,是可以窥见的日常生活,不屈和刚烈才是其质地,才是支配他们生命的内核。如果烟雨江南构成一幅静止的图画,那么童有源、童莉莉乃至“我”等对平凡生活的拒绝和从未放弃的浪漫追求则催生了江南烟雨的流动,从而使江南形成完整流动的图画。其实,平凡与浪漫的混合才真正构成了江南生活的特征,才是江南生活的意蕴,才使生活于其间的人生获得了存在的意义。
童有源、童莉莉、“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抗世俗的生活,童有源的率性、童莉莉的浪漫、“我”的天真,诠释着一家三代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童有源追求的是评弹、是艺术,童莉莉追求爱情的浪漫,而“我”则追求生活的天真,童氏家族的三代人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着追求的执着与情怀的浪漫,雅致成为其共同特征。其实,评弹也好、浪漫爱情也罢,在其执着的背后是古典文化的韵味,古典文化以雅致生活的形式在他们身上得到呈现。面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现实生活,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古典文化作为逃避的依托,不但满足了自身浪漫化的情感诉求,也对抗着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的侵蚀。2012年冬季,李欧梵在苏州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出,抵抗现代性无所不在的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内心的固有节奏,以自我的内心时间对抗现代快节奏的生活。童氏家族中三个具有个性追求的人对古典雅致生活的追求,带有明显的时间上的静止性与做事的随意性,或者说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时间做事的,他们这种不自觉中表现出的对时间的追求不仅使自己与时代保持着心理上的距离,而且也成为对抗箕踞变化的时代的法宝。作品中,63岁的童莉莉以对美的追求对抗着岁月匆匆的脚步,其实,童莉莉对美的刻意追求毋宁看作是一个隐喻,以容貌的光鲜抗拒时间在人体上留下的印痕,以年轻的心态抗拒衰老的容颜,也是以内心的时间对抗物理时间的侵蚀,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演绎着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三、本真追求的文学意义
童莉莉们的纯追求显示出作家真诚的写作态度。其实,无论是童莉莉对常德发、潘小倩故事的着迷和冥想还是“我”对生活的感悟的升华,都带有强烈的互文性质,显示出个体内在的自我分裂,以及对沉闷现实生活的不满和理想人生的追求,显示出一种超越性的人生态度。柔声曼语下的韧性成为南方性格的典型特征,童莉莉们成为江南性格的典型代表,表达着作家理想化的人生追求,寄予着其本真的生活姿态。“其实我们生而长大,大都会由纯真而变得世故。然后如果修得好境界,反而可能拥有‘更加纯真’的心态。这就是有创意的心态,也是生而快乐的心态。”[2]308作家对纯真作出了自己的阐释——纯真会被事故侵染,但被浸染之后的体悟是“更加纯真”的心态。纯真源于个人的清澈内心,内含着对世俗生活的拒绝,而对秉持纯真理想的作家来说,对平凡生活的拒绝不仅是免于被世俗所埋没,更是通过天真的姿态追求一份心灵的纯真,以真实的自我的显现达到生活的快乐。快乐的途径在于本真地活着,在于以赤子之心坦诚地面对俗世的生活,既不被世俗生活所同化,又不因世俗生活的压抑而流于内在的分裂从而异化为双面人生。当抱持这种本真心态融入社会的时候,即是达到了人生的极致,一种雅致心态与世俗生活的相融。就此看,作家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为了更好地活着,写作也不过是活着的一种形态,是更好地活着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写作达到内心的愉悦从而使物我两忘并最终诗意地栖息于大地,才是作家写作的真正意义。
在现代社会,个体被牢牢捆绑于现代工业机器的车轮,日常生活已经将个体模式化为现代社会的物质性存在,个体被时代所淹没,个体在获取舒适生活的同时也迷失了自己。现代性以无所不在的影响将个体裹挟进时代的车轮。在此意义上说,本真内心的追求是为了抗拒日常生活的消磨,以“抱元守一”的姿态刻意地与俗世保持着距离,通过与世俗的疏离显示出自身的存在,从而拒绝无所不在的现代性的侵蚀,昭示出个体活着的意义与价值。“我真正惧怕的是日常性的消磨。”[2]300“……我渴望危险。渴望那种类似于已经逝去的青春期的危险。我等待那种支持生命与写作的饱满的情感、真挚的危险……我等待它们归来。为了更好地活着,而不仅仅是写作。”[2]296平凡的人生无法阻隔日常性的消磨,返回内心,保持内心的纯真和浪漫的执着成为抗拒日常性消磨的有效途径。童有源、童莉莉和“我”虽然不能摆脱俗世生活的缠绕,但始终保持着内心的本真,以“处子”之态与俗世保持着距离。其实,本真更主要是一种生活姿态,对理想的追求或者说真挚的危险的拥抱,才是生活本身的意义,才是个体生命的确证。“真的,我觉得那三十几个像疯子一样没日没夜、没天没地的日子,它们突然之间美丽了起来,再次流动了起来,它们改变了模样,那几乎就是我生命里最充满力量、也最美好的时光。”[2]293本真使个体的生活获得意义。也正是在本真的追求上,作家的写作姿态与童莉莉们的追求具有了互文的性质,二者共同诠释着江南性格并刺激了平凡生活的活力。“听了很多次以后,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同样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莉莉姨妈在讲述常德发和潘小倩的故事时,有点像讲自己的某一部分,那异常强烈地想要完成却一直都没有完成的某一部分……”[2]197《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呈现的是江南生活的琐细缓慢与漫不经心,但这种疏疏点点的言语却蕴含着对雅致的执着追求,从而使江南的散淡生活具有了浓浓的韵味与诗意。
一切似乎如此的诗意而充满诱惑力,但在现实中这一切又谈何容易。孙倩倩是作品中不大被人注意的人物,也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形象。孙倩倩在世俗社会应付自如,同时又能保持一份内在的童真,颇有“大隐隐于市”的意味。不过,即使这样一个人物也有着面对俗世生活的无奈,正如她对“我”所说的,她们一家总要生活,总要生存,不能适应又能怎么样?在貌似洒脱的背后隐含着无助与无奈。这也注定了所谓的纯真只能是“在路上”。童莉莉爱情的分分合合、“我”追求中的痛苦与茫然也只是纯真追求的进行时态,作品对童有源的有关叙述更是“在路上”的绝妙隐喻。“在童莉莉的记忆是,父亲似乎总是在路上。这些年来,他几乎常常这样。想来就来,说走就走。这还是好的。有时他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还有些时候,童莉莉走上苏州老宅那道嘎嘎作响的楼梯,突然看到父亲正坐在二楼朝南的窗户那里晒太阳——那是童莉莉的母亲平时常坐的位置。”[2]15不甘于平凡的生活去追求一种浪漫的理想的人生,但浪漫的人生却是以平凡为归宿的,不甘于平凡只能不停地追求,“在路上”也就成为一种常态。其实,也只有“在路上”才能显示人生的意义,才能证明个体活着的生命与价值。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理论认为,我们都是不真诚的造物:“每个人都是他者,没有人是他自己。”真诚性是不容易恢复的,它要求一个新的“定位”,一种针对我们的有限性展开的正面冲突,一种“真诚的向死而生”。它意味着倾听良知的召唤,展示对存在之彰显的“忧虑”(care)。而且,首要的是,它要求一种新的“决心”,“这意味着让自己从迷失在‘他们’中被召唤出来”[6]。现代社会中人存在着被社会同化的危险,个体显示存在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以真诚的态度张扬出个性,或者说是以本真的个性的张扬标示出个体的顽强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童氏家族三代人的本真追求显示出的正是他们的个性,是以个性的追求对抗琐细、平淡的生活。就此看,朱文颖的创作恰恰诠释了存在主义的理论。作为旅游城市的苏州,其休闲性已被公认,但同时它也是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尤其是地处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大后方,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生活于此间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性的洪流。当大众都在随波逐流的时候,童氏家族的童有源、童莉莉们以对雅致生活的追求显示出顽强的个性,并以此超越性的追求抗拒着现代性无处不在的侵蚀,也显示出南方性格的柔韧。
[1]王尧.在南方生长的诗学——《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阅读札记[J].当代作家评论,2011(3):106.
[2]朱文颖.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3]吴义勤.大时代的“小生活”——评朱文颖长篇新作《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J].当代作家评论,2011(3):118-122.
[4]张清华.南方的细小、漫长与悲伤[J].当代作家评论,2011(3):115.
[5]金莹.朱文颖:在南方,“颠覆”南方[N].文学报,2011-06-09(005).
[6]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