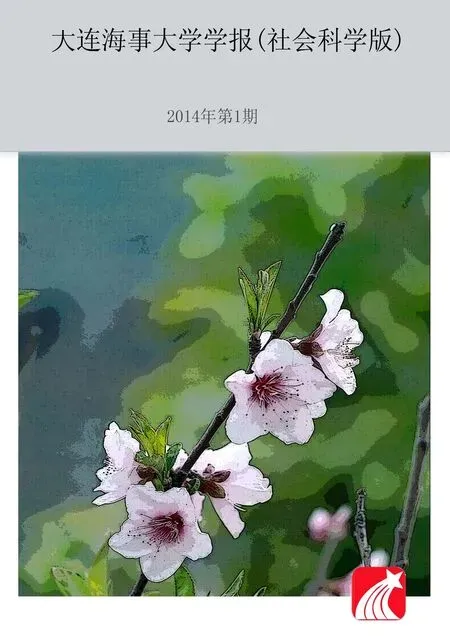凋零的美国南方文化
——论《欲望号街车》中的南北方文化冲突
马喜文,吕春媚
(1.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2.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一、引 言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美国戏剧的发展历史是最短的。直到20世纪早期,一些美国的本土剧作家才相继出现。1920年到1960年期间,美国集中出现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剧作家,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其中一些作家开始关注当时最为热门的社会问题——南北方文化冲突。1861年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对美国的政治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方最终的失败造成了南方传统生活方式的毁灭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沦丧,贵族沦为平民,工厂取代了农田,曾经一度繁荣的南方文化逐渐走向衰败。战前,南方人富庶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优越感,优雅的生活方式已经在他们的记忆中根深蒂固。战后,他们不能接受失败,也不能应对生活中出现的新困难,只能一味地沉浸在对昔日荣耀的回忆中。这时,美国文坛上出现了很多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关注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如何走出南方战后的困境成为这些现代作家的话题。他们将作品中的人物置身于南北两种文化中,就像是田纳西·威廉姆斯《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和米契一样,在不断探索中找寻摆脱困境的出路。
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战后作家之一。由于在南方长期生活,他已将南方的文化印记深深地植入了心间,可以说他是南方文化的最佳代言人。在南方目睹了过多的贫穷困苦,他一直致力于描写南方人在美国内战战败后所面临的困境。《欲望号街车》(AStreetcarNamedDesire)是他的杰作,是南方种植园文化在北方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人文悲剧。[1]女主角布兰奇是美国文学创造的众多醒目的女性形象之一。她对南方文化的坚持,她对真爱的执着追求,她自相矛盾的性格和一度放荡的举止都是评论家钟爱的话题。本文将重点分析布兰奇和米契两个在夹缝中生存的人物,试图将南方人在战后的冲突与困难中艰难前行的生活图景展示在读者面前。
二、布兰奇——“南方神话”中的淑女
南方文化的产生和形成与其种植园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17世纪早期,与北方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比,南方优越的自然环境使殖民者轻松地创建了南方种植园产业,并将欧洲的贵族传统移植过来。这种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初步构建了南方文化。然而,南北战争的失败使南方在政治、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开始逃避现实,追忆往昔种植园生活的点点滴滴。在缅怀过去的过程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随之产生,这就是“南方神话”。“南方神话”描绘的是“一幅栩栩如生、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的水彩画:残存于想象的古老南方是一片拥有繁茂庄园和快乐黑奴的热土,大片装有玻璃窗的白色房屋里居住着高贵的精通诗文音乐的绅士们和淑女们;以棉花为主要产品的南方经济稳定繁荣;幸福和睦、其乐融融的完美家庭则是这幅美景的中心”[2]。事实上,“南方神话”是南方人对其旧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美化。《欲望号街车》中的女主人公布兰奇也是这样一位心怀“南方神话”的恋旧者。她带着重新编织的梦想来到了北方化的城市新奥尔良,以期寻找庇护,然而迎接她的却是冰冷的工业化社会。
布兰奇是“南方神话”中南方淑女的典范。她纯洁优雅,文雅善良。对于她来说,美貌是她唯一可以依赖的事情,她坚信只有容颜永驻才有可能实现梦想。然而真正摧毁她的并不是逝去的青春,而是南北方的文化冲突。一方面,她不能背叛南方祖先们遗留下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她承受不了来自北方的咄咄逼人的压力。当这两种文化强烈碰撞之时,她很难在新文化中找到立锥之地,也不能在心理上保持独立生存的空间。
布兰奇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南方人的特质。她柔弱、敏感、骄傲、优雅的特征均体现了她对南方文化的理解。布兰奇的柔弱在剧本一开始就有所交代。当她出现在天堂路时,有一段关于她羸弱身姿的描写:“她柔弱的美丽必须躲避强光的照射。她那游移不定的举止和白色衣服让人联想到飞蛾。”[3]103*本文此处及后文所有《欲望号街车》的引文均为笔者译。布兰奇惧怕强光是因为她有着太多不可见人的秘密。当刚遇见妹妹斯蒂拉时,她立即要求关掉灯,好像是在阳光下会立即融化掉的雪人一样。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读者和观众发现布兰奇害怕所有的光线,甚至连白炽灯的光线都令她坐立不安。
布兰奇经常身着白衣,剧作家威廉姆斯把她比作一只白蛾而非一只天鹅或一片雪花。原因在于白蛾比起后两者在颜色上更加苍白,在含义上更加悲壮。蛾子经常能够让人们联想到不幸或者软弱。布兰奇在失去了南方家园的家产后决定离开家园,到新奥尔良去投奔自己的妹妹,然而她却没有意识到这座已经北方化的城市的威胁性。而她试图从新兴北方工业阶级的代表斯坦利身边夺回妹妹的行为更无异于飞蛾扑火。
布兰奇的敏感是她柔弱性格的副产品。一到斯蒂拉的家,她就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是一个不速之客。当她注意到妹妹的沉默后,便开始怀疑斯蒂拉并不欢迎她:
布兰奇: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而你却不欢迎我的到来!
斯蒂拉:布兰奇,你怎么这么说?你知道不是这样的。
布兰奇:不是吗?——我已经忘了你曾经是多么安静的一个人。
斯蒂拉:你从未给我说话的机会,布兰奇。所以我已经习惯了在你周围保持安静。[3]111
布兰奇之所以如此敏感多疑是因为她身处异地,担心自己的命运。如果斯蒂拉不接受她,她就会走投无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发现斯坦利对她怀有敌意时,她竭力拉拢斯蒂拉,希望她能够站在自己的一方。布兰奇的敏感并不能够拯救她的未来,她无法躲避已经预知到的危险,无法释放已经感受到的压力。事实上,她的敏感让她更加迅速地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布兰奇来自于有法国血统的南方贵族家族,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文学和法语。当她向米契介绍自己家族的时候,她自豪地说:“我们是法国裔。我们最早的美国祖先是法国胡格诺教徒。”[3]157这种贵族的傲慢已经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无论现在多么潦倒,她始终试图在穿着上与众不同。当她第一次出现在新奥尔良的街头,她的装束与周围的环境是如此格格不入:
她的样子与周围的环境是不相称的。她身着一件质地柔软的紧身胸衣和讲究的白色西装外套,戴着珍珠项链和耳环,白色的手套和帽子,看起来好像是要参加在郊外花园举行的夏日茶话会或鸡尾酒会一样。[3]103
事实上布兰奇所有的羽毛、裘皮、钻石都是仿制品。她用这些赝品把自己包裹在高傲的优越感里,用虚伪的贵族式的生活方式来反衬北方人的平庸和卑贱。布兰奇南方淑女的骄傲感也让她鄙视斯坦利的出身。斯坦利身上每一个北方人的品质都成为她攻击的对象。她称斯坦利为“波兰佬”(这是侮辱从波兰来的人的一种方式),嘲笑他浓重的北方口音,指责他粗鲁、原始的生活方式。布兰奇在剧中是这样形容斯坦利的:
……他太平庸了!……他毫无绅士风度!……他就像动物一样,有着动物的习性!吃饭像是只动物,走路像是只动物,说话也像是动物!……成千上万年过去了——斯坦利·科瓦尔斯基——石器时代的幸存者!在丛林里狩猎,然后将生肉带回家!你不要退化与野兽为伍了![3]180-181
布兰奇的骄傲和自信让她不能接受自己亲爱的妹妹竟然已经习惯于目前这种平庸的生活。她幻想能够将斯蒂拉拉拢到自己的一边,但这是斯坦利所不能够容忍的。两人的冲突也就由此而产生。
和布兰奇南方女性的特质不同,生活在工业化的新奥尔良人具有北方人的特点。北方化的城市是建立在工业的基础上,城市肮脏、拥挤,人们挥汗如雨地工作在工厂的车间里。而南方人生活在广阔无垠的庄园,以他们土地上的产品为生,过着恬静的乡村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性格的人们。像剧中的斯坦利一样,北方人彪悍粗鲁、为所欲为。斯坦利的世界非对即错。当他怀疑布兰奇对他们有所隐瞒时,就告诉她要直截了当、光明正大。他的生活毫无掩饰。
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北方新兴工业阶级逐渐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他们是十分现实的一群人,追求物质主义,珍视真实、实际的事物,而幻想并非他们生活中的要素。当布兰奇将要被带往精神病院时,除了米契之外,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现得无动于衷。斯坦利竟然站起来挡住布兰奇的逃路。在布兰奇被带走之后,男人们的扑克游戏继续进行着。斯蒂拉为发生在姐姐身上的事情不停地哭泣,她的邻居安慰她说:不要相信那件事(斯坦利强奸布兰奇),生活还要继续。北方人的麻木和冷漠在这一场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布兰奇鄙视斯坦利,同样,斯坦利把布兰奇看作小偷和荡妇。他不能接受布兰奇的生活哲理,讽刺她记忆里的崇拜者,质疑她所描述的百万富翁男友。当他知道了布兰奇在家乡不光彩的过去后,他不失时机地羞辱她。斯坦利刻薄的话语让布兰奇所剩无几的南方淑女的尊严和优雅荡然无存。
布兰奇一直相信如果她能够找到可以依附的人,她就会找到自己的栖息之所。事实上,她没有意识到只要她生活在新奥尔良——这个北方化的工业城市,她就不会找到自己最终的归宿。她的柔弱在残酷的北方变得更加不堪一击,她的敏感在冷漠的北方显得格格不入,她的傲慢在现实的北方成为众矢之的。“斯坦利战胜布兰奇标志着美国新兴的野蛮势力完全地摧毁并颠覆了美国旧南方所固有的文明礼教,取而代之的是以粗野、放肆、追求肉欲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新型的现代工业社会。”[4]真正摧毁布兰奇人生的并不是斯坦利,而是南北方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南方神话”在强大北方的威慑下终究会破灭。
三、米契——南北文化的综合体
米契在第三场“扑克游戏”时第一次出场。和其他三位粗暴无礼、令人厌恶的牌友相比,米契看起来的确有些与众不同。随着剧情的不断展开,米契成为布兰奇期望托付余生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英俊潇洒、才智过人的男人,恰恰相反,米契此时是个碌碌无为、穷困潦倒的推销员。但是他的敏感气质吸引了布兰奇,使他看起来比起周围的人更加优秀,更具有绅士风度。米契的这种气质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他和布兰奇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他也是一个寂寞孤独的人,在遇见布兰奇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母亲的呵护之下,没有什么和其他女人交往的经历;他也曾经受过失去爱人的痛苦,当他倾听布兰奇讲述她年轻爱人的故事时,他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布兰奇内心的寂寞和苦楚;和布兰奇一样,他也不敢直面残酷的现实,宁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游走。米契的温柔和感性让布兰奇感受到了久违的南方绅士风采,也让她重温了昔日的美好时光。她幻想在米契的呵护下,有机会能够再次成为南方娇嫩的花朵,纯洁、柔弱。
米契虽然有着南方绅士的特点,但是他却离“南方神话”中南方绅士的标准相差甚远。他身材魁梧,笨手笨脚,说话时带着生硬的南方口音。他的思考、办事方式完全和北方男人一样。当发现布兰奇有着不光彩的过去时,他暴露出与斯坦利一样的冷漠和残忍。如果不是他懦弱的个性,他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斯坦利。他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对诗歌和文学的理解。当布兰奇谈到某些诗句时,他总是感到困惑不解。艺术和文学对他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物,他所需要的是生活的必需品。和所有的北方男人一样,他缺少浪漫的思想和精神,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米契秉承了南方绅士的气质,但因身处剧烈变化的南北冲突,终日为家庭生计所累,面对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社会现实,他美好的想象无处栖身,米契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着南方绅士的演变过程。[5]
如果说布兰奇是作为南方的代表在和北方的工业文明进行着抗争,那么米契则是一直在和自己进行着斗争。他身上的南方的特质和北方的品性使他成为一个矛盾特征的综合体。他独特的敏感吸引着布兰奇,但他软弱的性格使他既拯救不了布兰奇,也令自己身处困境。一旦他的敏感气质遭遇到阻碍,他就会将真实感受隐藏起来。最终,他得以存活下来,但却终日饱受良心的折磨。
四、衰败的南方文化
南方文化走向衰亡可以从布兰奇和米契两位主人公的命运窥见一斑。他们都生活在自我的冲突中。他们的相似点让彼此相互靠近,却又相隔万里。最终,两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布兰奇遭遇暴力而走向疯狂,米契屈服于强权并推开了布兰奇。两人都不得不放弃心中的南方而委屈求存。
布兰奇最终疯了,当“Blue Piano”再一次在她的耳畔响起时,她的神经彻底崩溃了。斯坦利、残酷的现实和过去的虚幻把这个昔日南方的淑女逼疯了。斯坦利想要把她逐出自己的领地,残酷的北方现实试图约束这个南方女子,她的过去逼迫她永久地生活在幻觉之中。布兰奇最终只能逃到她虚幻的世界里,在那里她能够感受到一丝安抚和欢愉,一个昔日辉煌的南方世界。她愿意在那里找寻她逝去的青春。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她能够坚守自己的南方生活方式,能够骄傲、优雅、美丽地生活下去。
在《欲望号街车》这场残酷的南北方文化冲突中,南方经受了惨痛的失败。南方家族随着土地的丧失而灭亡了。而南方文化的两位继承者(布兰奇和斯蒂拉)也消失了。一位早已忘记了自己南方的特质,期待着和爱人在北方的环境中开始崭新的生活;而另一位,只能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回忆着南方的家园。
米契是本剧中最令人失望的人物。当孤独寂寞的时候,他渴求获得布兰奇的爱恋,然而他却承受不了来自现实的压力。他的温和与感伤都是虚假、伪善的。他的懦弱和最终的妥协断送了他的前程、希望和机遇。当他最终决定站在斯坦利一方时,他放弃了重新开始生活的权力。他的放弃使最后一粒南方文化的种子枯朽在冰冷的北方土壤中。
五、结 语
美国的南北战争彻底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战前,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按照不同的方式生活着。在北方,人们在工厂工作谋生。没有富庶祖先的他们丝毫不在意自己的仪表和风度。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而在南方,土地所有者们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享受着奴隶们带来的服务。他们丝毫不为生活而担心,艺术和娱乐是他们生活的重心。战后,南北方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在北方,战争激发了人们追求权利和财富的热情。北方不仅在机械文明方面而且在现代精神文化方面成了先驱和主角。[6]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谋求更好的生活。同时,北方人也变得更加现实。而在南方,战争摧毁了农业的基础,摧毁了蓄奴制,中断了南方战前短暂的经济繁荣,使南方大大地落后于美国其他地区。南方业主开始失去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开始质疑这个社会和他们曾经拥有的信念。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另找出路来应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北战争的失败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南方的封闭保守状况,而且使南方成为美国唯一具有向后看的历史意识和深沉的悲剧感的地区。”[7]
《欲望号街车》中主人公们悲剧式的命运恰恰呈现出了南北方在战后发生的变化。布兰奇沉溺于旧日的美好时光。每当生活中出现危机,她就会把自己藏匿于昔日的影子里,用南方贵族的尊严将自己包裹起来。米契害怕母亲有一天会离他而去,他将会孑然一身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喜欢布兰奇,但是他的生活经验让他无法理解布兰奇的苦痛。南北方文化的差异让他感到彷徨,最终他选择了放弃和逃匿。本剧的结尾预示着南方种植文化的终结以及南方文化的衰败。在南方的旧文明逐渐被工业化所取代的过程中,南方人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经受了重大的变革。南方人的精神家园随着物质家园的丧失而丧失。《欲望号街车》反映了剧作家威廉姆斯对南方文化价值观念在现实中的境遇的反思。
参考文献:
[1]徐锡祥,吾文泉.论《欲望号街车》中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J].外国文学研究,1999(3):95-98.
[2]陈曦.“南方神话”的幻灭——试论《欲望号街车》南方传统价值观的解构[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0):154.
[3]WILLIAMS T.Tennessee Williams[M].New York:Quality Paperback Book Club,1994.
[4]赵冬梅.《欲望号街车》——一部聚焦多元社会文化冲突的缩影[J].当代戏剧,2010(3):26.
[5]肖潇.《欲望号街车》中南方绅士的进化论解读[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8):120.
[6]张禹九.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南方文化[J].美国研究,1992(2):54.
[7]肖明翰.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动因[J].美国研究,1999(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