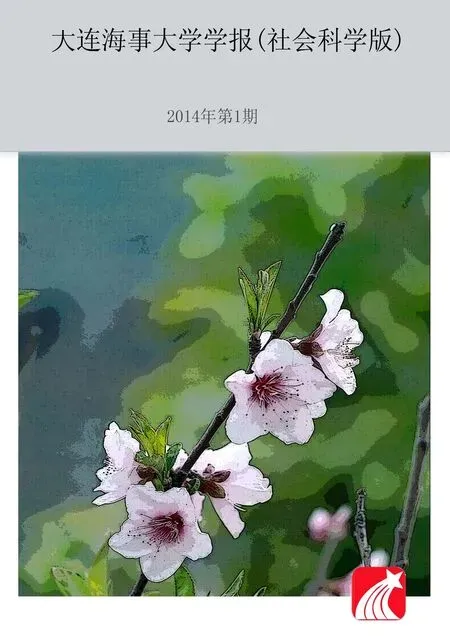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李大博,王 莹
(1.大连外国语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2.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一、《红楼梦》与家族文化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的横空出世,打破了中国已有小说视野范围的局限,它在对《金瓶梅》所开创的世俗人情小说有选择地继承的同时,更加丰富、充实了广阔社会关系中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份世情人情的理悟平台,是小说中的神话世界,即石头故事和太虚幻境;而这份世情人情的展现平台,是小说中的两大世界,即大观园的理想世界和贾府的现实世界。在这一个个平台之上所上演的,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之魂和生存之态。一部《红楼梦》既书写了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人情世故,也展现了一部封建家族风云变幻的百年盛衰史。
1.家族文化的内涵
家族文化,这一概念流源亘古。所谓家族,并非现在人们习见的直系血亲的小户小家,而是“从远古一直延续下来的那种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氏族之家”。“这种家不仅同姓,而且共财。同时,这种家还拥有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某些行政和司法的职能(如代为官府征收赋税、征召兵役),与‘国’颇相类似……个人与家发生的各种联系,亦可以视为与国发生的联系,甚至亦可视为个人的生活世界本身。”[1]以家族为核心的家族文化观念,即融合了家庭、家族的血亲链接,并与中国宗法制度、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休戚与共的传统文化观念。在家族文化的影响下,个人命运与家族命运紧密相连,古语道:丰衣足食以立身,达官显贵以立功,书香门第以立言,帝王世家以立天下。这既是个人博取功名的基本原则,也是家族得以绵延、繁盛之根本。相反,一旦家族分崩离析,家族文化发生断裂,个人命运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2.家族文化在《红楼梦》中的凸显
《红楼梦》第一回中,跛足道人诵出一曲开山奠基之歌——《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而后,甄士隐又有感而发诵出更加冷峻的《好了歌注》:“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其实,由这两首开篇之曲即可看出,所谓盛衰枯荣、喜怒悲欢正是世事无常的虚空,个人与家族的沉浮,是无法抗拒的历史更迭。《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为全书营造了一种家族整体走向的“忽荣忽枯、忽丽忽朽”(脂砚斋语)的基调,也是对宁荣二府家族兴衰际遇的一种概括和预示。《红楼梦》的家族文化观念即是以家族荣辱际遇为基本框架,从而展现了家族盛衰的沧桑巨变。
家族文化观念是《红楼梦》不容小觑的主题,贾府是一个典型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第一回),也是这种家族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望族,正体现着历史和文化的深远传统。而且,这个家还由于‘敕造’、由于贾元春之被选为后妃而与国(皇家)密不可分。所以,它的动静节律、兴衰成败就不仅展示出生活于其中的贾母一干人的生存样态与生活方式,而且更反映出一个时代甚至整个民族的生存处境与历史命运。”[1]所以,贾府的由盛转衰,既是一个家族命运的走向,也代表着一个封建王朝、一种封建文化的必然走向。
众所周知,《红楼梦》突破了以往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索的结构方式,采取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接又相互制约的网状结构,从而成为“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叙事结构的典范之作。在这个广密的网络结构中,以贾府为中心的家族文化传播开来,并贯穿了整个家族命运与个体命运的始终。
(1)家族文化观念与家族关系网。家族文化观念影响下的家族关系网,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市井黎民。一方面,借助贾家这个显性平台,史、王、薛三大家族也隐性地呈现在小说中。相互制约、相互扶携是《红楼梦》四大家族彼此心照不宣的关系网络根基,如史家的衰落在先、家道相对凋敝,史湘云时而借宿贾府,史老太君对其格外顾眷怜惜;王家根基稳固,王熙凤凭借强大的家族势力在贾府稳坐“管家人”的宝座;薛家以皇商起家,虽资财不乏,然而当急需一定的政治权利以安身自保时,还是要向贾府求援。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四大家族关系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以贾府为轴心,展现了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既包括人情冷暖的变化,如刘姥姥三进贾府的不同境遇,尤其是这一乡间老妇对巧姐的好心救助与贾府纨绔子弟对巧姐丧尽天良的发卖;也包括市井生活百态的呈现,如宝玉私塾就读中的几番“额外收获”,既有茗烟“狐假虎威”般的理直气壮与巧舌如簧的市井言语的淋漓展现,也有宝玉与贾兰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叔侄关系的隐秘描画(第九回);还包括绿林豪侠般的江湖义气,如“醉金刚”对贾芸的仗义爽快相助(第二十四回)。可以说,在家族文化的广阔视域中,贾府串起了一个时代的百态文化。
(2)家族文化观念与个体命运的走向。家族文化观念影响下的个体生存状态与命运走向,既包括贾府现实世界中集权者的权力之争,也包括大观园理想世界中一干儿女的情感归宿与命运走向。首先以贾府权势的集大成者——王熙凤为例,看一看家族文化观念影响下的贾府当权者的命运走向。作为贾母的直接授权对象,王熙凤管家的种种方法和手段充分展示了这位管家少奶奶的泼辣干练、“一百个男子也不如”的魄力。但随着贾母的离世,夺权者们相继搬出了家族伦理文化与强大的族权,其管家权受到了夺权者们的诟骂,加之其“无子无嗣”的处境与家族伦理本位文化的冲突,最终被休金陵。凤姐之悲,是家族文化观念影响下,错综复杂的家族利益之争的必然结果,更是以己之悲演绎家族兴衰的必然呈现。其次,看看家族文化观念影响下大观园一干儿女的情感归宿。由抄检大观园开始,这个理想世界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众芳遭遣离散,这是贾府盛极而衰、家族败亡的前奏。家族文化之根在于家族血脉传承、根基稳固、兴旺发达,因此,众望所归的宝黛之恋,终究敌不过拯救家族命运的重要性,宝玉的婚配者只能是祖业殷实、具有重整家族命运之能的薛宝钗。此外,元春的政治婚姻、迎春的“经济补偿式”婚姻、探春的重洋远嫁……毫无疑问,家族文化观念影响下的家族利益是个人情感难与争锋的家族文化中最为坚实的构成。
《红楼梦》是一部承载了家族文化观念的史诗巨作,上演了围绕着贾府这个大家族的一桩桩或大或小的世态图景、一幕幕或喜或悲的人情离合。这一鸿篇家族画卷、这一独特的家族文化观念,无疑对中国现代“家族文化小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张爱玲的小说便是《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影响下的杰作。
二、《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多元呈现
庞杂繁复、半新半旧的家族文化奠基,支离破碎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张爱玲性情的早慧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并由此奠定了张爱玲小说苍凉的基调。“她的祖父家、外曾祖父家、外祖父家,全是望族。这些家族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衰落下来。她没有完全超脱这种家族意识的影响,时时顾影自怜,有一种破落户的身世之感。她之所以酷爱《红楼梦》与此不无关系。这种破落户意识也影响了她对所处时代的认识。晚清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时代变革。这种变革无疑是带着动荡、血污、偏激等种种缺陷的,但大方向是进步的。张爱玲对这一变革的进步性认识不足,更多地看到了它的破坏性。”[2]张爱玲的苍凉之笔不同于《红楼梦》结局的苍凉之悲。《红楼梦》展现了人情世情美好繁盛的一面,而后盛极而衰,是贾府等名门望族的必然宿命,是美好的幻灭;而张爱玲笔下的芸芸众生是带有各自的人性缺陷上场的,私欲是每个人都有的特质,是每段情感都有的隐患,她是将美好毁灭着给人们看。对张爱玲而言,苍凉是一种情感基调,也是一种情感底色。
1943—1945年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高产阶段,也是终其一生的小说创作高峰期,代表作为小说集《传奇》。作者力图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张爱玲的全部心血、《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其刻骨铭心的影响、显赫家族的家族文化烙印,都融汇在这部《传奇》中。
1.家族文化之婚姻观念
《红楼梦》中众芳命运多舛,小说第五回借“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隐喻了大观园众女儿“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悲剧命运走向,众女儿悲剧的突出表现是她们不自主的婚姻:元春的政治婚姻、迎春的经济补偿婚姻、宝玉与宝钗的家族间强化权势的联姻,都是宗法社会家族婚姻观的典型例证。在以贾家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家族婚姻观念里,男女婚配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家族利益的强化与家族血脉的传承,而个体间在情感与心灵层面的契合则完全被排斥在家族婚姻观念的构建因素之外。
到了张爱玲家族所处的时代,《红楼梦》所表现的家族婚姻观念仍在延续,张爱玲的父母——张廷众与黄逸梵的婚姻就是两家势力联合的助推剂。闺阁中的黄逸梵无法决定自己的婚姻与未来命运走向,待其养母过世,娘家对其人身和伦理的限制减少了;待其产下儿子,完成传宗接代的家族血脉传承使命后,黄逸梵开始远涉重洋,重新寻求对自我的定位。可以说,这种家族文化影响下的一旧和母亲冲破家门的一新,两种截然不同的家族婚姻观念,都为张爱玲所关注,并重现于其小说创作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作家像张爱玲这样广泛而深入地反映和批评过现代中国的婚恋问题,也就是说,还没有第二个中国现代作家像张爱玲这样尽心尽力而且成效显著地完成了时代所交付的这一任务。”[2]
《传奇》中的《倾城之恋》便是典型代表。白流苏顺从家族安排被迫接受了一份旧式婚姻,但不出几年,由于实在无法容忍丈夫的纵情声色而主动选择离婚,这是旧式女子的“新式”果敢,读者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在白流苏的身上有着黄逸梵的影子。而后白流苏回到娘家,花光钱财后遭到哥嫂的整日唾骂,后来与范柳原偶然相识,白流苏与范柳原交往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她深感娘家已无法再住下去,她要通过与范柳原结婚寻求终身的经济保障。此后,两人开始了各怀鬼胎的交往,直到战争偶然成全了他们的婚姻。与范柳原交往伊始,流苏就已经不自觉地走上了旧式婚姻的老路,即以利益的获得为终极目的。她已然是一个谈着新式恋爱的旧式女子,唯一不同的是,她不是以家族利益至上,而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唯一不变的,不过是利益二字罢了。
在白流苏的两段婚姻中,由流苏母亲(白氏)态度的微妙变化,也可以看出张爱玲对旧式婚姻观念的精确拿捏与描绘。流苏与前夫不合,白氏虽然心疼女儿,但她更期望流苏能够忍气吞声维持这份婚姻,否则,白氏家族的名誉必然受损,维持家族稳固的姻亲关系网也必然受损。而流苏遭哥嫂排挤后向母亲哭诉,白氏更是以言语搪塞,以冷漠摧毁了女儿对家庭的最后一点留恋和乞求。而后,流苏遭范柳原冷淡后又被追慕,自觉有伤尊严,而白氏却间接地催促女儿主动投怀送抱,如果女儿能梅开二度,对白氏而言,这份更有经济后盾的姻缘不仅能一雪女儿离婚之耻,也会再次提升家族声誉。白氏不见得不怜惜女儿,但这份亲子之爱更多地被冷酷的家族利益所吞噬,她不自觉地做了家族婚姻文化观念的执拗捍卫者。而小说结尾处,“四奶奶决定和四爷进行离婚,众人背后都派流苏的不是。流苏离了婚再嫁,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难怪旁人要学她的榜样”,更是对旧式家族婚姻文化观念的绝妙讽刺。
2.家族文化之血亲关系
《红楼梦》人物众多,宁、荣两府中的人物关系更是异常庞杂。以直系血亲关系为例,其中独具特色的,上如贾母与两个儿子(贾赦、贾政)之间,既有因贾母的情感偏袒而导致二房管家的特殊选择,也有因伦理角色差异而引发的直接冲突(如第三十三回面对宝玉挨打,贾母的表现);下至探春与赵姨娘之间,由于母亲“半主半奴”的尴尬地位、心怀鬼胎的处事方式与女儿为人坦荡的傲骨,二人冲突摩擦不断,血亲关系也是众所周知的冰冷。《红楼梦》以其独特和深邃的视角,为人们展现了家族文化之血亲关系的特征,即血亲关系在个体情感抉择与家族利益角逐中发生了质变,从而蒙上了更多的物质与利益的尘埃。
自幼目睹父母千疮百孔的婚姻,张爱玲曾以相依为命的姿态理解并同情父亲。父女间的血亲关系原本是亲密而融洽的,但是随着家道中落与第二次婚姻的开始,父亲对女儿由亲密到疏远,由爱而恨,张爱玲开始重新审视她与父亲的血亲关系以及整个张氏家族中一段段变质的血亲关系。她在《红楼梦》中找到了源头与先例,并将这份亲情丧失的痛投诸笔端。
《琉璃瓦》中的一家,这是一个看起来其乐融融的富裕大家庭,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与筹算。对一家之长姚先生而言,“女儿是家累,是赔钱货,但是美丽的女儿向来不在此例……姚先生对于他的待嫁的千金,并不是一味的急于脱卸责任。关于她们的前途,他有极周到的计划”。而女儿们偏偏与他背道而驰,或为了报复父亲出于政治谋划的联姻,而亲手扼杀父亲的政治前途;或忤逆父亲复兴家族产业的志愿,而坚持自己的意愿,寻个倒插门无钱无势的未婚夫,以便牢牢牵制并掌控自己的婚姻。血亲关系中掺杂着针锋相对的斗争,亲子之爱变异成血亲之争,自我利益的维护成了彼此的奋斗目标。
再如《创世纪》中以变卖祖传古董而养活一家人的当家老太太紫薇,本想对儿孙显露的慈爱却成了一无是处的奢侈品,血亲之爱早已被水滴石穿的日常花销腐蚀得锈迹斑斑。看儿子,是“一直很安顿地在她身边,没有钱,也没法作乱”,看儿媳,是“这样的一个糊涂虫”,看孙女,是“还有个明白的?都糊涂到一家去了”。只有她自己是清醒的,清醒地斥责着拖累她的亲人,清醒地斥责着玷污她祖业的儿孙。张爱玲通过对这个垂暮老太太的精雕细刻,将《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中血亲之情的变异,又一次升华到了绝顶的境界。
3.家族文化之财产继承与权力之争
财产继承与权力之争,一直是《红楼梦》中贾家家族矛盾的中心话题。荣国府中大房与二房、二房中的嫡子派与庶子派一直相互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对当家执政权力的争夺、对家族财产继承权的觊觎。因为财产继承,二房中的宝玉与贾环情愿或不情愿地被推至斗争漩涡的中心;因为家族管理权,大房与二房的积怨日久弥深,大房虽有碍于贾母的偏袒却也在伺机而动,一旦贾母离世,大房就立即与二房庶子派联手,最终权力之争加快了整个家族的分崩瓦解。
流淌着两大名门世家血统的张爱玲,对家族权力之争向来不陌生。到张爱玲父母这一代,张氏家族与黄氏家族在家族财产划分上一直纷争不断,家族积怨从未消退,甚至因财产分配问题而大闹公堂。两个大家族的内部成员面对家族财产的继承问题,其处理手段绝不亚于《红楼梦》中一干虎视眈眈的夺财者。
张爱玲虽未直接参与家族权益之争,但与其同住的母亲与姑姑都是双方家族财产争夺的当事者与参与者。在父系一方,张爱玲目睹了姑姑张茂渊与父亲张廷众由相处于同一战壕,共同对阵他们同父异母的兄长,到张廷众中途私受家财而半路倒戈,导致亲妹妹张茂渊血本无归;在母系一方,母亲黄逸梵为了追回属于自己的一份古董遗产也是得罪了一干长辈,导致在娘家名声扫地。甚至在张茂渊与黄逸梵这一对患难与共、情谊深厚的姑嫂之间,也存在因财产借贷而产生的情感隔阂。所以,耳濡目染于财产争夺的家族氛围,张爱玲形成了对财物极为敏感的特殊心理。张爱玲的小说中虽少有对财产争夺的赤裸裸的描写,但其笔下的各色人物,绝不同于鸳鸯蝴蝶派作品中深陷“情网”的痴男怨女,而多是受困于自己的“财网”观念而不能自拔。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姑侄两位女性采取了两种殊途同归的追求幸福的方式。一方是寄生女性梁太太,她早年与家族决裂,毅然嫁给年逾耳顺的富商做小,待伺候了他归西,她也年华不再,为了弥补年华流逝与心灵压抑带来的缺失感,她自恃精明地左支右绌,以金钱敛色,一干人等也对其前倨后恭;另一方是对拜金主义由抵制到沦陷的葛薇龙,她冷眼旁观着姑母那种可笑而愚蠢的举止,轻蔑于她那急切地填补性饥渴的求爱方式,但她的刻意逃避在那个凭姿色和身世而纵情声色的交际圈里显得无力而渺小,她最终选择了合意但无钱的乔琪乔,痴心地用自己在交际场上赚来的钱供他挥霍。张爱玲通过对梁太太嘲讽下的戏谑与对葛薇龙评判下的同情中,道出了现实中原来人情冷暖与人心向背的最大裁决者竟是经济基础。
《茉莉香片》中,对财产吝惜地恪守而导致神经错乱的聂介臣,当他惊恐地发现儿子聂传庆在支票上疯狂练习签名时,“他重重的打了他一个嘴巴子……因为那触动了他暗藏着的恐惧。钱到了他手里,他会发疯似的胡花么?这畏葸的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而对聂传庆而言,父子之爱早已荡然无存,只有这必然属于他的家财才是安稳的、永恒的,所以他隐忍着父亲的毒打与唾斥。“总有一天……那时候,是他的天下了,可是他已经被作践得不像人。奇异的胜利!”这里的财产继承有着诡异的性质,有着父亲狂热的不舍与儿子狂热的幻求。虽然张爱玲是以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作为这个故事的原型,但在她的笔下却没有一丝的不舍与同情,正是以转身的冷酷,尽情地将财产与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描摹开来。
4.家族文化之地域文化色彩
关于《红楼梦》中贾府的所在地,红学界向来争议不断,但公众普遍接受的说法是贾氏家族祖宅在金陵,即南京,宁荣二府府宅坐落在北京。因为贾政是京官,且兄弟间多承袭祖辈旧职,所以贾氏家族合家住在京城敕造宁荣两府中。由于祖籍与居住地的不同,贾府的家族文化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一面是贾府上位者,如贾母等人,有着南京六朝古都的遗民风貌,有着精致的生活品味与精准的艺术视野,是源远流长的世家大族文化的守护者与发扬者,是古都文明的传播者与开拓者;另一面是贾府下位的雇佣者们(除家生子外),有着皇都市民出身的身份优越感,作为天子脚下的一等公民,她们说着一口流利的京腔,骨子里带着北京文化继承者的优越感。南京与北京,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贾府丰富而多元的家族文化内涵。
张爱玲的父系与母系家族都是上海文明的忠实继承者与维护者,他们一面有着上海旧贵族的游手好闲、惶惶终日,一面又有着上海新市民的时髦靓丽、纵情声色。对张爱玲而言,她一面自幼便热衷于游荡在老上海阴暗的祖宅里,热衷于探索祖宅里祖辈遗留的秘史,热衷于奔跑在上海的老弄堂里观察着往来行人,反复聆听着《苏三不哭》的小曲;另一面,她又沉浸在大上海的殖民地文化中,喜欢母亲的光鲜亮丽的小洋房与欧式风景画,痴迷于三里洋场的大戏院与好莱坞电影。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里坦言:“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从家族背景看,张爱玲有着上海人的血统,从个人性情看,张爱玲有着上海人的血液。
《传奇》中的几个故事,多是发生于大上海,虽有几篇是以香港为背景,但是故事的主人公们多是上海人。尤其当上海人旅居异乡的时候,更能凸显出他们骨子里的上海性情。《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出洋时的他嫖得尴尬而不够精致、恋得矜持而自恃高洁,归国后经历了与朋友妻子一段无疾而终的危险恋爱,与自己妻子间彼此轻蔑、彼此折磨的索然无味的婚姻。他经历过性与情的漩涡,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是上海人,他有自己的怯懦与自私,他有自己的利弊与权衡。正如小说结尾所写:“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
《留情》中的米先生与他续娶的郭凤,为了结婚而结婚,彼此客气有加地维系着婚姻,一个感慨着前妻对自己的百般恭敬,一个怅然若失着眉目清秀的早逝的前夫,他们都是看透彼此却又从未挑破的沪上般配的夫妻。在小说结尾,“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郭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他们都是平凡普通的上海人,有自己的一套既定持久的原则与处世哲学。
三、结 论
基于《红楼梦》极高的文学价值与文化内涵,其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也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作为《红楼梦》家族文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传承者,张爱玲以其终身的创作成就传承、践行着《红楼梦》所演绎、传承的家族文化观念。作为张爱玲小说的接受者,只有全面理解《红楼梦》家族文化的内涵,才能深刻领悟张爱玲小说背后的深层旨意。
参考文献:
[1]成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19-220.
[2]钱振刚.清末民国小说史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205-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