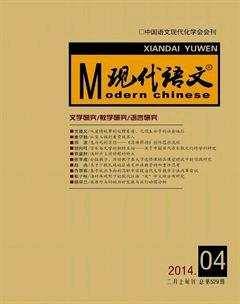读·思·行
摘 要:文言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与载体,其教学方法应在我国古代阅读理论中深入开掘。“读、思、行”揭示了我国古人阅读的一个完整过程。“读”不仅要张弛有度的“诵”,更要“熟”;“思”要在“求甚解”和“不求甚解”的“对话”过程中进行;“行”是阅读的最终旨归,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关键词:诵 熟 求甚解 不求甚解 行
文言文是我国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为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艺术佳品,其中每部作品又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明,用吕叔湘的话说就是:“我们中国历史长,文化遗产丰富,现在的青年如果不学文言文,这个遗产就丢了,不好。”[1]因此,我们必须在学校教育中选择经典文言文,以恰当的方法带领学生领略其中的优美文字和文化韵味。但自“新文化”运动以降,随着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西方的文艺理论在我国大行其道,无论写作、阅读都对西学顶礼膜拜,而相关领域的“中学”则被打入另册。
当我们翻开早已落满灰尘的古代典籍,可以看到,从《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到王国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的经典论述,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艺理论、阅读理论是何等丰盈。但正如吕叔湘所言,一方面由于受封建社会中后期“读是为了写”这一观念的影响,阅读成了写作的附庸;另一方面我国传统阅读理论多数是和文字学、哲学、文学、史学、科学有关,终使我们缺乏一门独立的符合汉语汉文特点的符合国情的阅读学的出现。
笔者认为,正如印—欧语系的语法系统并不适宜用来分析、解释汉—藏语系的语言这一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一样,对文言文的教学也不应“崇洋媚外”,而应在我国古代的阅读理论中寻求相应的方法。
一、读
中国人最为熟知、也最爱用来教育下一代的一句话是出自《三国志·魏志·董遇传》的“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短短八个字,极好的注解了中国人对读的重视。在中国古代的书院、私塾当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学生的脑袋摇来晃去的“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而宋代苏轼对读的推崇更是登峰造极,他不仅说“三分诗,七分读耳”,还说“纵格下者,能抑扬高下,迎其辞而读之,听者忘厌”。(《宋稗类钞》)下面我们循着古代学者关于“读”的理论,来考察现在的文言文教学。
(一)诵
现代汉语中,“读”的意思是“看着文字念出声音”,而“诵”字也是“读出声音来”的意思。而在古代汉语中,读、诵都有诵读义,但有区别。读是看着文章念或不出声地阅读,诵是大声朗诵或背诵。可见,出声与否与声音高低成了区别读和诵的关键。
宋代朱熹提出“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古今图书集成·学行典·训学条规》)元代程端礼也说:“每细段读二百遍,……字字句句要分明,不可太快,读须声实,如讲说然。”(《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一)如今,学生在学习文言文时虽不必“每细段读二百遍”,但“字字句句要分明”“如讲说然”还是必须的。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做起来实则不易,尚需师生平日多加诵读才可收到实效。
值得注意的是,课堂教学中的朗读,尤其是中小学低年级,在朗读时常常出现如明人薛瑄所说的“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五)的现象。这样的朗读“心杂气粗,急声以诵”(《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五),使诵读者无法“密察其意”(《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五),而更多的成了一种表演。如某初中语文老师,在教李白的《将进酒》时学习余映潮老师执教《安塞腰鼓》时组织学生诵读的方法,也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组,按照男领、女领、男女领、男合、女合、众合等百人大合唱的方式组织学生诵读。像这样“读诵斗高声”式的朗读,放逐了诵读的本意,无法“使我之心,即入乎唐人之心,而又使唐人之心,即为我之心”(郑燮《板桥集外诗文·集唐诗序》),恐更难以使“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总得来说,诵读应张弛有度,在“毋增、毋减、毋复、毋高、毋低,毋疾,毋迟”(崔学古《幼训》)中做到“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谕纪泽》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二)熟
我国古代阅读理论中对“读”常以“熟”作为基本的要求,能熟读也就意味着能背诵了,如北宋司马光曾说“书不可不成诵”(《三朝名臣言行录》)。而学习之人只有达到了“熟读”才有可能向更高一级的“精思”迈进。翻阅古代阅读论,可以看到,读与思是连缀在一起的,即“熟读精思”。清张伯行说,“学者读书,须是白日诵读熟,夜间反覆思量,方能有得”(《困学录集粹》卷三)。《荀子·劝学》中也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置言之,古人的读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是边读边思,读思并进,最终“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为不枉用功力耳”。(朱熹《朱文公文集·答沈叔晦》)由此可见,“熟读”对于阅读教学的顺利开展具有关键意义。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公开提出“书读不熟,不开讲”。从这一主张我们可以看到古代阅读论的影子,而时下的语文教师又有几个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并付诸实施呢?不是教师们不能,而是他们不敢:繁重的教学任务,巨大的考试压力,甚至关联到自己的绩效工资……即使再有魄力的教师面对严峻的现实也折腰了。学生课文读不熟,教师只能满堂灌、牵着学生走。说了多少年的“少慢差费”,学生课文读不熟当是一条重要原因!
“每细段读二百遍”的方法在如今看来是很不合时宜的,也是不科学的,但对于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每位学生读个三五遍总还是有必要的。为了给这三五遍留个活口,语文教材的选篇数量能否再压一压,语文教师能否改改篇篇讲解的教学方法,各科老师能否少布置一道作业题,学生家长能否与孩子一起读读课文!使学生“开编喜有得,一读疗沉疴。”(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送石赓归宁》)endprint
二、思
明王守仁在回答一友“读书不记得,如何?”的提问时说:“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可见,古人追求的并不只是“记得”,而是更高远的“明得”。“思”便是这一升华过程的关节,“熟读”之后的“精思”直接指向“消化”“自得”。所谓“消化”,王守仁解说道:“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而“自得”一词自在《孟子》中出现以来,便为古代学者常加引述,宋朱熹更是说道:“为学勿责无人为自家剖析出来,须是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工夫,要自见得。”依笔者所见,古人所提出的“思”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里仅选取“求甚解”与“不求甚解”一法谈谈文言文学习中的“思”。
中国古代阅读论中关于“不求甚解”和“求甚解”的争论可谓久已有之。
《孟子·万章上》中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到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再到《二程集》中提出“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他们均主张读书要“不求甚解”。而清冯班则针锋相对的提出“今者朝读一书,至暮便竟,问其指归,尚不知所言何事”,主张读书要求甚解;元陈端礼也提出“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朱熹更是说出“看文字如做贼,须知盗发处,自一文以上赃罪情节,都要勘出。若只描摸个大纲,纵使知道此人是贼,却不知何处做贼”。(《朱子语类》卷十)我们无意在这里评判两派观点,只是由此引发—种视角来审视中学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学习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学生无法理解某些词语所表达的意思。而文言文中的词多数是单音节词,“这种单个汉字作为文言的词具有的语法功能的潜力要远远大于白话文中的词汇所具有的语法功能。……(它)所代表的恰恰是—组有着内在联系的意象与概念的集合……它其实并不是西方语言学意义上的作为语义的最小单位的‘词,而毋宁说是‘意象与概念的混沌体”[2]。所以,文言文教学需要在古今异义、—词多义、词类活用等常用词法,省略句、判断句、倒装句、被动句等特殊句式方面做到“拘文字”“求甚解”。例如教《狼》时,对于“其一犬坐于前”这句就必须做到“求甚解”。学生在读这个句子时常会读成“其一犬/坐于前”,这样一来,句子的意思就成了其中的一只狗蹲坐在屠夫面前。明明是两只狼,怎么突然冒出一只狗来,众多学生大惑不解。此时就需要教师给学生讲明白,“其一”是名词偏正短语,是“其一狼”的省略形式,“犬坐”是动词偏正短语,“犬”这一名词在此处用作状语,而“于前”是介宾短语作补语。只有这样“求甚解”讲明白,学生才能将其正确地读为“其一/犬坐/于前”。
除此之外,“求甚解”的方法还可以采取“对话”的方法。“对话”一语是作为西方后现代的概念被引入教育领域的。但当我们翻阅中国古代阅读理论时,又会惊喜的看到我国古人早已提出了类似的思想。
汉杨雄在《法言》中说:“朋友以磨之”;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须切磋相起明也。”金圣叹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也说:“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天下万事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事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另一处,他又说:“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绝不是此一人自己文字集。”而朱熹则说的更加显豁,“大抵读书,……如与古人对面说话。”
从以上挂一漏万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学者已经初步意识到阅读不仅是一种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对话,而且阅读和学习中“求甚解”的过程还需要“朋友以磨之”。以我们的理解,这里的“朋友”是指具有相同阅读经历的人,“朋友”之间的“磨”是“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一)的过程。
我们在做到“求甚解”的同时,还要适当的“不求甚解”。这就要求广大语文教师一方面在教学中力避“以章句训诂为事”的过度阐发;另一方面不要像一些初中语文教师在教文言文时采取“不可一字无来历,不可一字不落实”的原则,甚至对一些学界仍存争议的问题也不放过。这种“寻行数墨”(《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式的学习,破坏了“古人律诗亦是一片文章,语或似无伦次,而意若贯珠”(宋范温《潜溪诗眼》)的特色,换以“经生分篇析句之学”,长此以往,“其何足以知此哉?”。(《陈亮集·经生发题·书经》)
三、行
古人学习,不仅主张“熟读精思”,更要求“知之莫若行之”。在他们看来,读和行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读是起点,行是终点。
颜之推明确指出:“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掌诸事,及有试用,多无所堪……难可以应世经务也。”《二程集》中指出:“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清颜元以学医类比,指出:“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铒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歧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读尽天下书,而不习行六府六艺,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节精一艺者之为儒也。”(《颜李丛书·存学篇》卷一)另一处,他又说:“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颜李丛书·存学篇》卷四)
由此可见,古人对“行”很是重视。如今,中学生“读”文言文,“思”文言文,最终的指向当是“行”文言文。这里的“行”不是要学生去写文言诗文,更不是“为了写好白话文”,而是“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在积累、感悟、运用中,使学生“接受文言文中蕴含的文化遗产”。换言之,就是让学生“学法”于教科书中的文言文,“得法”于课外的古诗文阅读。这就要求教师在学生掌握知识与方法之后,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学生推荐适合学生阅读兴趣、与课文难易程度相当或稍高的文言文,让学生在自己阅读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如作为与语文教科书相配套的《语文读本》,就选编了很多与教材中文言诗文相关或水平相仿的作品。学习了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安排学生阅读《语文读本》中的《后出师表》,这样一来“读”“思”“行”的过程才算完整。但是大多数教师从未将安排学生阅读《语文读本》作为自己的一项教学计划,大多数学生也只是在拿到新书时翻着看看,之后便再也不翻看了。甚是可惜!
道教经典《太平经》中有言:“得书读之,常苦其不熟,熟者自悉知之。不善思其至意,不精读之,虽得吾身,亦无益也;得而不力行,与不得何异也?”古人丰富的阅读理论为我们勾画出了文言文阅读的基本线路——“读”“思”“行”;古人数千年的阅读实践也极有力的证明了“读”“思”“行”是适合文言文阅读的。“这些古老的智慧不是急风暴雨般的浇注就能心领神会的,也不是简单的诵记就可以得其真传的,它需要反复的咀嚼、不断的玩味、再三的琢磨,需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功夫,还需要‘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行,做到‘学、问、思、辩、行的有机结合,才能从微言中晓其大义。”[3]面对扑面而来的西方理论,我们不应迷失于其中,而应以宽广的眼光适时的回顾中国的传统理论,读之、思之、行之!
注释:
[1]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6页。
[2]潘庆玉:《语文教育哲学导论:语言哲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64页。
[3]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7页。
参考文献:
[1]曾祥芹等.古代阅读论[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2.
[2]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Z].北京:中华书局,2000.
[4]潘庆玉.语文教育哲学导论:语言哲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5]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M].长沙:岳麓书社,2002.
(何遥 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1112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