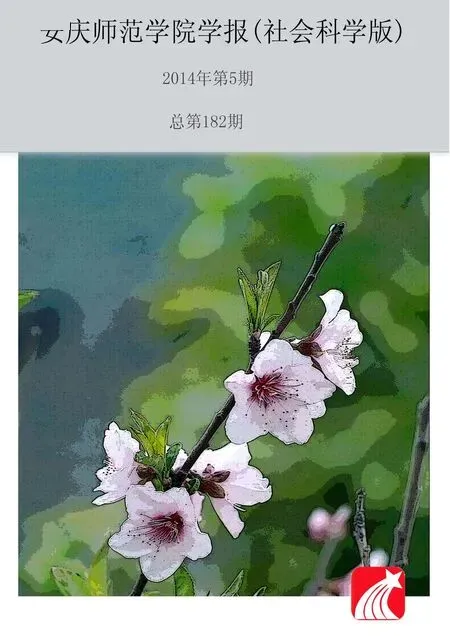姚文燮的《昌谷诗注》与其诗学思想
顾 冰 峰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姚文燮的《昌谷诗注》与其诗学思想
顾 冰 峰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姚文燮的《昌谷诗注》是李贺诗歌注解中影响比较大的一种,姚氏认为李贺诗歌蕴含着“孤忠、哀激”之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形成了其注本“以史注诗”的特色。这又与姚文燮以“性情论”为核心,并强调有所寄托的诗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昌谷诗注》中的“讥讽”和“自伤”说正是姚氏这种诗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姚文燮的诗学思想其实是受了家族学术、当时的“杜诗学”等影响而产生的,并且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意义。
姚文燮;《昌谷诗注》;“性情论”;以史注诗
姚氏家族从元初迁至桐城麻溪后,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望族,并且产生了很多文学名家,如姚范、姚鼐、姚莹等,这些人都是桐城文派的重要作家。处于明末清初的姚文燮则属于麻溪姚氏的第十二世祖,他的《昌谷诗注》后来成为影响比较大的李贺诗注本。姚文燮认为李贺诗歌寄寓着“孤忠、哀激”之情,这是其注本“以史注诗”的基础。而这一认识又与他以“性情论”为核心的诗学思想相一致。本文将对姚文燮的诗学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并结合《昌谷诗注》来考察其一致性。同时,在桐城文学及清初诗坛的大背景下,姚文燮的诗学思想有着其特殊的意义。
一、姚文燮及其“性情论”
据《桐城麻溪姚氏宗谱》(《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第52-56册,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编,燕山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简称《宗谱》,文中所引有关资料,如不另外说明,则俱出此宗谱)记载,姚文燮生于天启丁卯(即公元1627)年三月六日,卒于康熙壬申(即公元1692)年,字经三,号羹湖。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士,历任地方僚佐,入《清史稿》八四三卷《循吏传》,其所撰《昌谷诗注》、《薙簏吟》十卷、《无异堂文集》十二卷存世。
姚文燮并没有专门论诗的文章,但其诗学思想往往体现在他所写的诗序中。他在《潘俨思诗序》中说:“夫诗,以道性情也。是故有真性情者,必有真诗。”[1]92其《牧云子诗序》又云:“诗者性情之物也。”[1]136其《莲园诗草序》亦称:“夫惟自抒其性情,则知今古人不相越,故其言至近,而其意可通于千百年以上,《三百篇》岂其邈不可及哉?”[1]192从这些序中可以看出,姚文燮认为诗是为了表达性情,《三百篇》也是作者“自抒其性情”,所以通过性情便可以上达《三百篇》之旨,由此“性情论”成为其诗学的理论基础。但姚文燮所说的“性情”有其侧重点。其《潘俨思诗序》云:“昔人谓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惟以礼义为情,斯可谓之性情耳。”这句话表明,其所谓“性情”主要偏向于“情”,不过是加了一个“礼义”的限制。诗“道性情”、“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说法从《诗大序》“吟咏情性”开端,此后为人所常道,但姚氏的“性情论”有其特殊内涵。在《牧云子诗序》中,他更加深入的阐述了这种“性情论”,其中有云:“人有性焉,不可得而移也。而善适其性者,在能用其情。举天地万物之有情无情,而一归于我之情,使有情者不得自有其情,而无情者于我独见其情之甚深,斯情至而性见焉。”[1]136姚氏这里虽然将“性”与“情”分开而言,但很明显他比较注重于“情”,即是说,“性”因“情至”而现,“情”是主要的因素,“性”不过是“情至”的结果,也就是他所说的“能用其情”的结果。后又云:“夫移人之性者,莫若过于势位,性为势位所移,举天地万物之有情者皆归于无情,并且自失其情,亦安在所为诗也。”[1]136此处所说“性移”而“自失其情”,与其将“失其情”视为“性移”所导致的结果,不如将其理解为因未做到“能用其情”而“失其情”;而失去了“情”,也就无所谓创作诗歌了,所以此处还是在强调“情”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姚文燮又加入了“理”。在《刘君因诗序》中云:“诗有词理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则无迹可求,质而自然,诗之至也。”[1]95这正是姚氏“性情论”比较特殊的地方。同时,其所说的“理”也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壬寅诗自序》最能表现他的诗学思想,云:
客曰:“子之才人所共见,至于理犹未穷焉。”世岂有不穷理而能诗者哉?嗟乎!天下事无一不根诸理,无理无所为诗,然往往论诗而求理者,其去理愈远,此非惟不可与言诗,并不可与言理也,以诗不必言理而理自具也。诗止有情与法耳,而深于诗者,第言情并不乐法,盖情至而法见焉。分言情与法,即与执言理者均失矣。情能藏法,法能宣情,惟才能用情与法,情深入而不能出,与浩渺飘忽而不能制,纵横驰突而不能收,失于法也,并失于情,实才不足以胜之耳。如情本多也,数字括之,而不见少;情本尽也,一句止之,而觉有余,甚至连篇累什,纚纚千百言,……情有不能自主,而一一有以主之者法也,才为之也,故屈以之伸,离以之合,旧使之新,俚使之雅。而以法生情者,情即生法,蛩吟非俭,獭祭非袭,房中非亵,神仙非诞。雕龙绣虎,岂曰华侈?牛鬼蛇神,毋嫌诡谲。古今才人虽不一类,然惟真才人乃真理学也。曾有诗人而不穷理者哉?抑不能不名为才人而可名为诗人乎哉?……今夫听讼之才,一则曰:能执法;一则曰:能得情,爰知出入惟谨,恐违于情而戾于法也。诗律之于刑律,无二律也,即无二理也。少陵云:垂老渐于诗律细,不独为近体言也,诸体皆有律。少陵其洵深于情者哉?[1]89
这里的“情”其实是指“性情”,姚文燮很详细地论述了诗中“情法理”三者的关系,其所谓“理”其实是“情”与“法”的融合。姚氏认为“无理无所为诗”,但“诗不必言理而理自具”,“诗止有情与法”;又“情至而法见”,情又要靠法来“主之”。其所谓“法”是指创作诗歌的方法或者章法,即“数字括之”、“一句止之”之类,具体而言,就是后面所言的“屈以之伸,离以之合,旧使之新,俚使之雅”四种,做到了这几点自然就可以很好的表现自己的“情”了。这样的论述又和前面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相通,并且依旧表现出偏重于“情”的倾向。而能够做到“法”则是“才”的问题。又以听讼喻作诗,认为“能执法”而“能得情”就是合理,也就是合于诗律,所以要和于“理”就要有“才”,这样的才人就是“理学”家,真才人才能名为诗人,因此诗人也就是“理学”家。他还认为杜甫也是深于“理”的,这里的“理”似乎是指诗律。但姚氏所说的“诗律”已经不是一般理解的平仄格律等诗歌创作规则,他所指的是将“情”与“法”相互融合之后,而能够表现出更深层次的寄托。所以他才认为:“以法生情者,情即生法,蛩吟非俭,獭祭非袭,房中非亵,神仙非诞。雕龙绣虎,岂曰华侈?牛鬼蛇神,毋嫌诡谲。”正是因为诗人在这些“雕龙绣虎”、“牛鬼蛇神”的意象当中寄托了某种思想感情,即“理”之所在,所以“真才人乃真理学也”,诗人也由此而成了“理学家”。不过这种“理”说到底,似乎更多的还是以“情”为基础,因此他认为杜甫是“洵深于情者”。
从中可以看出,姚氏所说“蛩吟非俭,獭祭非袭,房中非亵,神仙非诞。雕龙绣虎,岂曰华侈?牛鬼蛇神,毋嫌诡谲”,其实背后是针对李贺诗歌而言的。《史远公诗集序》云:“余生不好异,且不能异,第不敢狥世之所谓同,而人遂有异之者。”[1]94也和他注解李贺诗且不以其为“怪”的看法相一致。在《何令远诗序》中姚氏认为,李贺与杜甫、白居易诗歌是相近的,所谓“相近”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诗歌中所共有的“寄托讽喻”之义,即“理”。也正是因为李贺的诗有“理”,所以是真才人。他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也是基于上文所论述的他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诗学思想。
由此,姚文燮逐步构建了自己以“性情论”为核心,强调诗歌应有所寄托的诗学思想。他的这种诗学思想是和其“诗注”思想相通的。
二、《昌谷诗注》之“以史注诗”
《昌谷诗注》的撰写时间是在1657年左右。而此前后一段时间也正是姚文燮诗歌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据其《薙簏吟》和《壬寅诗》两诗集自序,此两集所收就是庚寅年(1650年)到壬寅年(1662年)所作的诗。这样,其诗学思想与《昌谷诗注》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
姚文燮对李贺诗歌的基本认识在其《昌谷诗注》自序(按,《无异堂文集》中所收与诗注中此序文字稍异)中有很充分的说明。其中云:
世之苛于律才人,与才人之苛于律世,两相厄也。人文沦落之日处才难,人文鼎盛之日处才尤难。屈原、贾谊才同而世不同,世不同而处才之受困又同。
又云:
且元和之朝,外则藩镇悖逆,戎寇交讧;内则八关十六子之徒,肆志流毒,为祸不测;上则有英武之君,而又惑于神仙。……贺不敢言,又不能无言,于是寓今托古,比物徵事,无一不为世道人心虑,其孤忠沉郁之志,又恨不伸纸疾书,纚纚数万言,如翻江倒海,指陈于万乘之侧而不止者,无如其势有所不能也。故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
其后又云:
故必善读史者,始可注书;善论唐史者,始可注贺。使我尽如贺意,我之幸也,贺之幸也。即我未必尽如贺意,而贺亦未必尽如我意。第孤忠哀激之情,庶几稍近。[2]367-369
在这里,姚文燮提出了李贺“孤忠沉郁之志”和“哀激之情”的说法。姚文燮认为李贺的诗是上续“《诗》三百篇”的,继而又是续《春秋》的。“《诗》三百篇”历来被人们认为有“怨刺”的作用,孔子《春秋》更是以“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著称于世,屈原《离骚》、贾谊《鵩鸟赋》也都饱含着个人的怀才不遇和哀怨之情。在此,姚文燮则认为李贺的诗和“诗三百”一样具有怨刺讽喻的作用;而将其比之于《春秋》,则不仅是为了说明其中有“微言大义”的讽刺笔法,而且也在于指出其有记史的作用。由此,他认为李贺诗歌与“诗三百”、《春秋》等在主旨上是一样的。可以说,姚文燮的这种认识,蕴含着“诗歌应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功用”这一传统的诗教观。而后姚文燮结合唐代元和朝的史实,进一步认为李贺的诗寄寓着自己的“孤忠沉郁之志”和“哀激之情”,甚至于“命辞、命意、命题”三个方面都具有深刻的怨刺内容。这当然也是从序言一开始所提出的“处才难”的观点所引发出来的,姚文燮所表达的是李贺与三百篇之作者、孔子以及屈、贾等都同样怀才不遇,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他们的哀怨之情是前后承续的,所以在李贺诗歌中也饱含着孤忠、哀激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是姚文燮对李贺诗歌的基本认识,而所谓“孤忠、哀激”其实就是姚氏所说的“性情”。
不难看出,为了阐发李贺诗歌中的“孤忠、哀激”之情,姚文燮在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基础上,进一步将李贺诗比附于历史进行解读。在其凡例四则中还说:“世称少陵为史诗,……昌谷余亦谓之史诗也。”[2]385在这里姚文燮更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李贺的诗歌同杜甫的诗歌一样都是“史诗”,其实在自序中已有“以贺诗为唐春秋可也”[2]369这样的话。这种“诗史”观也就决定了姚文燮在注解李贺诗歌时运用“以史注诗”的手法。而姚氏在自序中曾说自己是“直以贺注贺”[2]369,但是为《昌谷诗注》作序的诸家基本都认为姚氏是以己意注贺,进而认为他的“诗注”可成一家之言。如钱澄之在序中批评训诂章句之学,指出这是“无我之弊”,其言外之意即是肯定姚文燮“自信我之意即作者之意”[2]373的注释方式;方拱乾也认为姚氏注昌谷是“印证当时时事,出己意以为解”[2]378;而姜承烈认为韩婴、向秀、郦道元“皆不以书注书,而以我注书,借古人自成一家言”,而姚氏与三人“齐驱并辔”[2]381,也在肯定姚氏“以我注书”,能成一家之言。由以上诸家序言中的意见可知,姚氏的《昌谷诗注》并不是其所自称的“以贺注贺”,而实是“以我注贺”,也即是其“以史注诗”的实质。而这种手法的运用,最大问题在于容易牵强附会历史事实。据笔者统计,《昌谷诗注》存李贺诗242首,而在姚文燮的注解中,明显引唐朝史事的诗共有104首左右,其中有76首左右在王琦的注解中没有引用史事来注解,甚至有些地方王氏表示了不同意见。如《秦王饮酒》,王琦言:“姚经三以为为德宗而作。德宗性刚暴,好宴游,常幸鱼藻池。琦按:德宗未为太子,尝封雍王矣。雍州,正秦地也。故借秦王以为称。其说近是,而以为追诮则非也。”[2]79王琦注云:“长吉用此不过言虎之伤人累累,与苛政绝不相干。而旧注多云为讥猛政而作者,非是。”[2]254王琦的注解向来被认为是比较客观的,这样来看,姚文燮的注解确多有附会。其实,在建宁重刻《昌谷诗注》的时候,姚氏进行“较定”(原作此),“为易其附会过甚者二三十条”[2]371,这本身就说明姚文燮自己也意识到注解中有一些地方是属于穿凿史实的。
当然,也正是这样的“以史注诗”,才使得他可以更自由的依据自己的“性情论”诗学思想,来阐释李贺诗歌中所寄寓的“孤忠沉郁之志”和“哀激之情”,这在《昌谷诗注》中则具体表现为“讥讽说”和“自伤说”。
三、《昌谷诗注》中的“讥讽”与“自伤”说
在《昌谷诗注》中,姚文燮往往用讥讽、自伤和失意等说法来解读其诗篇。据统计,在诗注中明显运用自伤、失意和讥讽等说法的注解有154首左右,而直接运用“自伤”、“失意”、“不遇”、“讥”、“讽”、“诮”、“嘲”等词来注解的有95首左右。由此而形成他关于李贺诗歌的“讥讽”说和“自伤”说。这就是他在自序中所提出的李贺诗歌所蕴含的“孤忠沉郁之志”和“哀激之情”的具体体现,也即是其以“性情论”为核心的诗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讥讽”说,此说比“自伤”说要更普遍一些,其中明显用“讥讽”说来注解的有97首左右,而直接出现讥、讽、诮、嘲等词的注解有71首左右。直接标以“讥”、“讽”的,如《李夫人》注云:“德宗贞元二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皇后。是月丁酉崩。……贺思往事,作此以讥,而拟之李夫人者,明乎不足为后也。”[2]407《天上谣》注云:“元和朝,上慕神仙,命方士四出采药,冀得一遇仙侣。贺作此讽之。”[2]403《苦昼短》注云:“宪宗好神仙,贺作此以讽之。”[2]456与此同旨的说法有“诮”、“嘲”等。如《难忘曲》注云:“时襄阳公主下嫁张克礼。主纵恣,有薛浑等皆得私侍。克礼不能禁,竟以上闻。贺吟此曲以诮之。”[2]444《瑶华乐》注云:“秦皇、汉武屡见篇章,此又以穆王咏者,总之嘲求仙服丹之误也。”[2]469此外,还有“伤之”说,如《相劝酒》注云:“李藩尝谏宪宗,以太宗饵天竺长年药为戒注云:‘励志太平,拒绝方士,何忧无尧舜之寿?’帝不听。然其时朝贵希宠固恩,迎合上意,屡进方士丹术。贺盖伤之。”[2]468此说亦和“讥讽”说相同旨。其实,姚氏“以史注诗”方法的运用往往基于此“讥讽”说。而较能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则是姚文燮对李贺《感讽》组诗的解读。在李贺集中《感讽》诗有两组,一组在卷二,共5首;一组在集外诗(此在《昌谷诗注》中题为《感调》),共6首。在这些诗中有10首引用了唐朝具体的史实来阐释其中的“讥讽”内容。第一组《感讽》诗,姚氏云:“数诗皆感讽往事也。”[2]435然后对此5首诗俱引用唐德宗朝的史事进行解读;而后一组诗中,姚氏分别引用贞元、天宝、元和等时期的唐朝史事进行解读,且有时用“讥”、“感讽”等词直接点明主旨。而姚文燮的这种李贺诗歌“讥讽”说正是与《诗经》所含有的怨刺功能一脉相承,而这也正与自序中所言的“孤忠沉郁之志”相对应。
“自伤”说,此说在姚文燮的注解中往往有之。其中,明显运用“自伤”说注解的有57首,其中直接出现自伤、失意、不遇、不偶等词的注解有24首左右。如《同沈驸马赋得御沟水》注云:“自伤流浪。”[2]391《南园》其四注云:“自伤其年壮无成,调饥莫慰。”[2]409《休洗红》注云:“见此益自伤年华矣。”[2]478等。李贺有时吟咏他人他物,姚氏注解为凭借他人他物以自伤。如注解《李凭箜篌引》谓:“但佳音难觏,尘世知希。贺盖借此自伤不遇。”[2]389《南园》其十一注云:“自叹才高不遇,而托叔夜以相况也。”[2]411等。与此属同一主题,还有“自慨”、“自叹”等说法。如《七夕》注云:“贺盖借苏以自慨也。”[2]392《送沈亚之歌》注云:“贺叹沈即自叹。”[2]393与此相联系,又有“失意”、“不遇”、“不偶”等说法,如《客游》注云:“失意浪游,离家久客,时裂帛系书以寄乡信也。”[2]446《浩歌》注云:“此伤年命不久待而身不遇也。”[2]404《三月过行宫》注云:“幽郁穷年,芳时不遇,又安能得觐龙光乎?”[2]437《伤心行》注云:“高才不偶,羁绁京华。”[2]422有些注解虽未出现“自叹”、“失意”等说法,但从其表述中也可体会出此含义。如《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注云:“乃贺自顾落落,大非彻比,郁抑穷愁,唯借长吟以遣中夜。”[2]425又《京城》注云:“此贺罢归时出长安之作。……至此不堪告人,惟吟咏以自遣耳。”[2]480而对于含有特殊意象的诗,姚氏则更突出的运用这一方法。如《竹》注云:“此借竹以喻己也。……贺独才大遭摈,能不对此重感耶?”[2]391《马诗》其一注云:“贵质奇才,未荣朱绂,与骏马之不逢时,同一慨矣。”[2]414《昌谷北园新笋》其二注云:“良才未逢,将杀青以写怨。芳姿点染,外无眷爱之情,内多沉郁之恨。然人亦何得而见之也?深林幽寂,对此愈难为情。”[2]430以上这些解读,则是表现了所谓李贺不得志之后的“孤愤”、“哀激之情”。
还有一些注解,则同时有以上两种寓意。如《马诗》其二十二注云:“汗血本王家所宜珍也。自少君去后,人只见有青骡。而主上唯方士是求,则才士不足贵矣。”[2]421又《长歌续短歌》注云:“秦王指宪宗,言骋雄武,好神仙,大率相类也。觐光无从,忧心如沸;饥渴莫慰,荣茂惊心。……乃遇合维艰,故不禁浩歌白首耳。”[2]429-430在姚文燮看来,这两首诗不仅有李贺对主上好神仙的“讥讽”,还有一些才士不遇的“自伤”之情。“讥讽”与“自伤”其实是相互联系,融为一体的。诗人往往因看到时代的缺陷而产生不满,所以会有所“讥讽”;亦因处于这样有缺陷的时代中,而其济世抱负又得不到实现,由此而“自伤不遇”,其实就是所谓“不平则鸣”,此与其自序中所言“处才难”相应,也因此李贺有的诗歌确实有所寄托。而在姚文燮看来,李贺诗歌中所寄托的“孤忠沉郁之志”和“哀激之情”就具体地体现在“讥讽”和“自伤”之中,而这就是李贺的“性情”。
姚氏在序言中所说的“命辞、命意、命题”也即是李贺诗歌中“法”的具体表现。他在诗注中对此自然也有分析,如果“讥讽”和“自伤”说是姚氏所认为的李贺诗歌的“命意”;《感讽》、《马诗》、《竹》等诗则可用来说明其“命题”;而“命辞”则可指在具体用字用词方面,如《李凭箜篌引》注中云:“‘中国’二字,郑重感慨。”[2]389《送沈亚之歌》注云:“‘白日下’骂得痛快,‘重入门’三字写得悲凉。”[2]393等,其实与《壬寅诗自序》中所言“数字括之”等说法相通。如此,李贺诗歌便达到了姚文燮所说的“执法”,正符合上文所论述的姚文燮的诗学思想认为“情至而法现”,“执法”而“得情”,即为合“理”。而在序言中论及李贺诗中之“理”时,其言云:“杜牧之言,贺理不及《骚》而为《骚》之苗裔也,是不必以《骚》抑贺也;又谓少加以理可奴仆命《骚》也,是又不必以贺抑《骚》也。《骚》理何必皆贺,而贺理何必皆《骚》也?”[2]369他认为李贺诗歌之“理”是和《离骚》之“理”有所不同的,其自序另有言云:“贺则幽深诡谲,较《骚》为尤甚。”[2]367此处“幽深诡谲”实指诗中之“理”的表达。而此“理”就是以上二说所体现之“性情”与“命辞、命意、命题”之“法”相融合的结果,并且“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即有所寄托。这样便将其诗注与其诗学思想统一了起来。姚文燮在凡例四则中说:“总之,不度其时,不得其情,不入其隐,则毫厘千里。”[2]386这句话则正好综合说明了他的“以史注诗”(时)、“性情论”(情)和强调有所寄托(隐)的诗学思想。
四、余 论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姚文燮的诗学思想是以传统的诗学观念为基础,以其别具一格的“性情论”为核心的,并且强调应有所寄托;而这一思想实质上又是其解读李贺诗歌的理论依据。这种诗学思想的形成,是和其家族学术传统、与当地的其他家族(如桂林方氏)的交往、桐城前辈的诗歌主张等多方面因素分不开的。
据笔者粗略统计,《宗谱》中十二世以前(不含十二世)治《易》为15人,治《春秋》为3人,治《尚书》15人;到姚文燮等十二世时,又有治《易》5人,治《春秋》5人,治《尚书》2人。这些数据大致表明,在姚文燮时,其家族学风发生了转变,始以治《易》和《春秋》为主流。姚文燮虽然治《易》(承其父亲、祖父),但肯定会受到家族中《春秋》学的影响。在《单午良春秋稿序》中,姚文燮说:“余家自王父辈以及昆季,数十年以《春秋》售者七八人,余虽习风岐大易,然与诸兄弟联席共研,亦时窥见一斑。”[1]119这说明,姚文燮对《春秋》也有比较深入的研习。而在其《昌谷诗注》自序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痕迹,不妨再征引序言,如其云:“《诗》三百篇,大抵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作也。《诗》亡而后《春秋》作,孔子之不得志也,以《春秋》续《诗》也;屈贾辈以骚续诗,是以诗续诗也,是又以诗续春秋也。”这其中就表明,姚文燮认为李贺诗歌具有同《春秋》一样“微言大义”的讽喻内涵,而其“诗史”观肯定也受到了《春秋》学的影响*其实,孟子提出的“《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姚氏文中“然”字作“而”)这个观点在清初受到了普遍关注,详参张晖《诗史》第四章第二节,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版,第196-223页。。另外一方面,桐城在明末清初时,各大家族出现了很多的诗文名家,他们之间难免会有相互影响,桐城姚氏和方氏之间的交往就很多。姚文燮与其中方拱乾父子、方文、方以智等人就有交往,方拱乾曾为《昌谷诗注》写序;而姚文燮的母亲则是方孝标的姑母,方孝标曾写过《贺姑母姚太孺人诰封序》[3]等文;方文是当时著名的遗民诗人,在姚文燮的《无异堂文集》中,每文后有其师友的评语,而其中《昌谷诗注自序》后有“方尔止曰”的评语,方尔止即方文,或可说明姚文燮与方文有过交往;姚文燮又曾为方以智《通雅》写序[1]81。桐城方氏家族自明代就以理学传家,方孝标治《易》,并极力赞扬程朱理学。而就《昌谷诗注》所用的注解体例而言,并不同于训释名物字词的章句之学。汉学长于训诂,宋学长于义理,这早已成为公认的看法。姚氏《昌谷诗注》多用散文式的语言进行疏解,训诂名物并不多见,可见其旨在于探索其中的义理。应该说姚文燮的诗学思想是以宋学为基础的,这一点应该是受其家学与地域学术的传统的影响。另外,姚文燮与桐城前辈钱澄之的关系非常紧密,钱氏曾两次为《昌谷诗注》写序就可见一斑,而且姚文燮也曾给钱氏的《田间集》写序,他在序中云:“道人(指钱澄之)……生平厌人分别四唐,谓‘唐诗莫工于少陵,今少陵集具在,其中亦初亦盛,亦中亦晚,或一篇中有为盛者、中者、晚者,孰得而优劣之?彼优初盛而劣中晚者,乌足与论诗。诗以道性情也,吾适吾性而止,而格律矜哉。’”又云:“余发燥即受道人知,以余可言诗也,与为忘年友。”[1]97正是这样的“忘年友”关系,使得钱澄之的“性情论”等诗学观无疑影响到了姚文燮的诗学思想。以上足以说明姚文燮是将家学、地域学术、前辈诗学思想等融为一体,创建了自己的诗学思想,这其实是对家学以及地域学术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如果再进一步,将姚文燮放到当时整个诗坛来关照,就会发现他所处明末清初也是诗歌阐释学比较发达的时期,尤其是“杜诗学”兴起以后,钱谦益的影响巨大,“以史注诗”的注解方法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在姚文燮的《无异堂文集》中,卷三《贺季参戎加衔序》和卷四《龙眠诗传征诗引》两文后都有“钱牧斋曰”引语,可见姚文燮与钱谦益或曾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而姚文燮注解李贺诗也应该是受到了“钱注杜诗”影响*此观点已被很多人指出,可参郝润华《论〈钱注杜诗〉的诗史互证方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70-76页;郑子运《明末清初诗解研究》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223页。。所以对《昌谷诗注》与其诗学思想进行研究,也可以窥见这一时期的诗学和诗歌阐释学的某些特性,尤其是“杜诗学”兴起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蒋寅认为,清初在伦理上对诗学传统的复归,首先表现在对已成为诗学根本概念的“性情”的重新解释[4]104。而李世英等又认为,清初诗学理论上的旗帜一是“性情”说,一是“诗史”说,并且从创作方面看,遗民诗人是清初诗歌创作的主流[5]。具体到姚文燮而言,他虽非遗民诗人,但桐城遗民诗人很多,其中钱澄之、方拱乾及父辈姚孙棐就是其例,姚文燮紧接这些诗人之后。前文所探析的姚文燮诗学思想也是建立在对“性情”的重新解释上,在他看来,“性情”就是“孤忠沉郁之志”和“哀激之情”,这便是一种伦理上对诗学传统的复归;并且由此对遗民诗人的两种诗学理论进行了融合而建立了“性情”说和“诗史”说的内在联系,即前文所论《昌谷诗注》之“以史注诗”。钱澄之在《重刻昌谷集注序》中言:“姚子……盖欲以忠爱概天下之诗教也。”[2]373其中所言“忠爱”就是姚文燮“性情论”的核心。蒋寅又认为,清初诗人对“性情”的重新解释,逐渐转变为一种返回“诗教”的意识[4]105,而从钱澄之的这个评价可以看出,姚文燮的理论创建也正体现了这种返回“诗教”意识。同时,“性情论”也是清初诗人否定唐宋诗之争的一个理论工具[6]。而姚文燮继承钱澄之“厌人分别四唐”的观点,并试图用“性情论”来阐释诗歌,虽然他还没有涉及宋诗的问题,但这一尝试对于清初诗坛诗歌宗尚的转变确是一种积极的努力;而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性情论”也为后来桐城诗派融合唐、宋诗歌的诗学取向打开了门径。
姚文燮并非当时诗坛的名家领袖,从整个诗坛而言,他的诗学思想似乎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他的种种解释和探索,无疑是在诗歌阐释与创作上努力寻求突破的一种表现。而他也通过这种努力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并符合主流趋向的“性情论”诗学思想,这或许是其《昌谷诗注》能够流传甚广的内在原因。而桐城诗派的形成必然是与包括姚文燮在内的桐城先贤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的探索分不开的,虽然姚文燮的诗学思想与姚鼐等家族后裔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桐城地域诗学的流变与发展。
[1] 姚文燮.无异堂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 王琦,等.李贺诗歌集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 方孝标.方孝标文集[M].石钟扬,郭春萍,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7:42-44.
[4] 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 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6.
[6] 张晖.清初唐宋诗之争与“性情”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88-96.
责任编校:汪孔丰
2014-05-01
顾冰峰,男,北京人,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间:2014-10-28 14:19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21.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21
I207.22
A
1003-4730(2014)05-009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