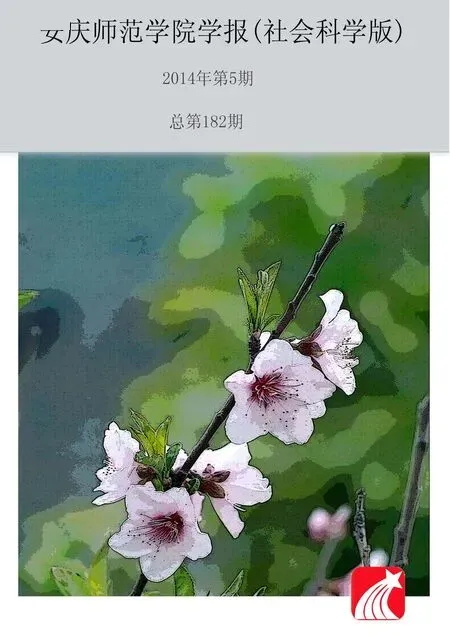论程小青侦探小说的本土化
程 海 燕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论程小青侦探小说的本土化
程 海 燕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创作虽然模仿的痕迹很重,但是他对《福尔摩斯探案》的借鉴却是经过选择、改造和变形的。他的《霍桑探案》在主要人物形象及其思想内涵方面不同于《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开场方式与案件发生的背景也有所不同,而且他强调的侦探小说所具有的“启智”和“移情”两个方面教育意义上与前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为侦探小说的本土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程小青;侦探小说;《霍桑探案》;本土化
程小青原名青心,乳名福临,祖籍安徽省安庆市。祖上务农,家境贫寒,因为战争不得不全家迁往上海。他在1893年出生于上海南市的淘沙场里。1914年,他首次创作了《灯光人影》,被《新闻报》副刊《快活林》选中刊登。1916年,他与周瘦鹃等人共同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共12册)。在翻译过程中,他产生了塑造中国本土福尔摩斯的想法。1919年,他发表了以私家侦探霍桑为主角的《江南燕》。与那些“乘兴而作,尽兴而止”的作家不同,从1919年开始一直到解放前,他一直坚持创作侦探小说共74篇,结集为《霍桑探案》约280万字。他是为侦探小说在文学领域争取一席之地的“先驱”。
由于中国本土在西洋文学进入之前接近侦探小说形式的只有“公案小说”,而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在“叙事模式、文本角色、破案方式、叙述视角”上都有很大的不同[1]。因而中国近代的侦探小说主要是吸收、借鉴国外侦探小说而形成的。程小青塑造的霍桑更有“中国福尔摩斯”的称号,显然是借鉴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所以李欧梵先生在《福尔摩斯在中国》这篇评论中写到霍桑形象时说“这个角色更接近‘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谓的‘模拟’,即被殖民者学他的主子,外表惟妙惟肖,但独缺肤色,而且也有主体性的问题”[2]。诚如范伯群所言,程小青“是一位模仿多于创造的侦探小说家”,但是他确实在西方侦探小说的本土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创造的“霍桑”也绝非故作爱国,“矫枉过正”的福尔摩斯的翻版。下面通过《霍桑探案》对《福尔摩斯探案》的借鉴以及它的本土化特征两个方面来分析程小青侦探小说的本土化。
一、本土的文化内容
要将侦探小说这种西方文学形式本土化,首先就要做到在作品中表现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适当揭示社会伦理情态,反映现实的本土问题。在这一点上,程小青对侦探小说的选择是符合现实的,当时上海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并且频频出现各种犯罪案件。他创作中体现的本土文化内容主要是通过主要人物霍桑的形象展现的。
首先,霍桑虽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但也并非是无瑕疵的英雄,他也有普通人的缺点。比如《打赌》这篇小故事中就写了霍桑的失败经历。好友孙芝年为母亲过寿,霍桑也参加了,而且因为心情好,多喝了几杯。宴会过程中,孙芝年的表嫂何氏戒指上的珍珠突然不见,于是请霍桑帮忙寻找。霍桑经过推理,认为是何氏的小儿子不小心吞食了珍珠,可是真相却是何氏因为当时慌忙,自己将珍珠放进衣服口袋了,她在掏手巾为儿子擦眼泪时珍珠掉了出来。通过这件事,作者使读者相信霍桑并非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
其次,不同于福尔摩斯对待官方警察的傲慢态度,霍桑对待官方探员的态度基本上是比较友好的。虽然有些时候也批评“他们处理疑案,还是利用着民众们没有教育、没有知识,不知道保障固有的人权和自由,随便弄到了一种证据,便威吓动刑遍地胡乱做法”[3]。这很明显具有进步性。但是他在很多情况下他还是选择借助官方探员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比如在《断指团》一案中,他就因为相信那些探员而深陷险境。而且他对一些探长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尤其是“汪银林”这个人物。这些内容都说明了霍桑这个人物作为现代中国的侦探对法制的认识是有限的。他虽然认识到了当时的法律与正义是有矛盾的,但是却不明白当时的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利用的一种工具罢了。这很符合当时上海的具体情况,私家侦探虽然被部分人接受,但是他们的权利是极为有限的,如果像福尔摩斯那样我行我素是不可能解决案件的。而且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中庸”思想的影响,普通人做人做事都不会那么极端,而是会选择比较适中的方法对待事情。
此外,他还有着明显的“平民”思想。霍桑这个人物其实是有程小青自己的影子。程小青在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帮人浆洗和缝补衣服把他和弟弟妹妹抚养长大,所以他从小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接触的人也多是平民老百姓,因此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也有比较强的平民意识。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迎合广大读者的审美品位。中国传统墨家思想中的“兼爱”思想是包含着平等的观念的,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读者或观众总希望在小说或戏剧中出现那种见义勇为、锄强扶弱、压制强权的英雄人物来伸张正义,因此程小青在创造霍桑的形象时就为他加入了浓厚的“平民”思想,他总是站在平民的立场来看待和处理各种案件。在《沾泥花》中,仆人施桂因为来访的客人面貌丑陋、衣服破烂,而不愿意立刻通报,霍桑发现后便训斥他:“你怎么忘了?我们都是平民……这里不是大人先生的府第,怎么容不得褴褛人的足迹?”
正是受到这种平民思想的影响,霍桑办案对待罪犯的态度并非一视同仁,经常是道德战胜了法律。在《白纱巾》一片中,霍桑说:“在正义的范围之下,我们并不受呆板的法律的拘束。有时遇到那些因公义而犯罪的人,我们往往自由处置。因为在这渐渐趋向于物质为重心的社会之中, 法治精神既然还不能普遍实施,细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故而我们不得不本着良心权宜行事。”在《案中案》里,仆人陆全太忠实于老主人,而设计刺杀孙仲的故事感动了霍桑。为了帮助陆全,他仔细推理发现孙仲的真正死因是服用了过量的安神水,从而使其免受法律的制裁。
二、本土的艺术精神
对于本土艺术精神的体现,最突出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学作品的重新认识。《霍桑探案》借鉴了《福尔摩斯探案》的叙事模式,采用了“单向视角”的有限制的叙事方法,不同于以往中国小说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作者以包朗的视角来展开叙事,这样既能够拉近读者与整个案件的距离,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又能方便作者为情节设置各种悬念,增强大侦探的神秘感。当新文学的作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加以否定,站在西方文学的视野下来审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学时,程小青却对传统文学作品有了重新的认识并且借用其中的叙事技巧。
不同于《福尔摩斯探案》,《霍桑探案》在故事开场方式上借鉴了中国传统宋元话本小说的“入话”式开场方法。“入话”是指为了等候迟到者,说书人在故事开场之前先说一首诗词起兴,或者一个简单的故事。而这些诗词或者故事会与后面的主要故事中的某些人物或者地点有关。可是总体上与下面的故事没有什么强烈的联系,而是阐述了一些对于当时社会现象的批评与思考。在《霍桑探案》中类似“入话”的故事开场方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一些短小简单的故事开场;二是关于报纸文章或者日常生活而展开的议论与批评为开场。第一类主要有《迷宫》《江南燕》等篇章。《迷宫》开头是霍桑与包朗在火车车厢中对于私犯进行的分析,以及两名乘客关于一件有趣的盗窃案的交谈。与后面发生的失窃案并无多大的联系。《江南燕》的故事开头除介绍了霍桑的个人经历以及和包朗的朋友关系外,还写到了霍桑凭借推理得出包朗去黄天荡划船的事。随后才进入了关于江南燕的珠宝盗窃案的侦探。第二类作品较多,主要有《白衣怪》《催眠术》《断指团》等。比如《白衣怪》的故事开头是包朗到霍桑的家中, 看到报纸上一则大学生因为争风吃醋而杀害旅馆中舞女的新闻,并且讨论了当时大学生的伦理道德问题。与下面裘海峰的杀人案件并无直接联系。《催眠术》第一部分以“扇子哲学”为题,以包朗和霍桑二人关于该不该用电扇的讨论,点出霍桑厌恶国人太会享受而懒于活动的状态。《断指团》故事以包朗因神经衰弱和霍桑来到南京修养开始,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自己的行踪报道。批评对社会上那些捕风捉影的人,感到个人隐私的缺乏尊重。
将“入话”的方法带入侦探小说这一紧张复杂的小说体裁中,虽然有些不协调,但是却非常符合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这种开场方式比西方侦探小说的直接报道案件的小说要更有人情味,这些议论贴近读者的实际生活,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能够带领读者渐入佳境。关于社会现象的评论也能体现出作者本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既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艺术性也有所提升。
他在语言方面,也体现了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尊重。既运用了诗歌,又有方言的使用。在《黑地牢》中,看到飞进办公室的蜜蜂,包朗便吟了唐代诗人罗隐的《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霍桑就将最后一句改为之“为人辛苦为人甜”,原因是:“照原句的含意,怜悯蜜蜂酿成了蜜,不能自己享受,却给不知何人享受故而对蜜蜂表示悼惜的慨叹……这是颓废的观念,在这个新的时代,不但不足为训,简直要不得!现在我给它改一改,而且加以正面积极的解释,就显出这小生命的伟大性。它采花,它酿蜜,为的是人,不是为自己。生存在这个时代的人,谁也应得有这‘为人’的观念,那末民族才得滋长繁荣,人类才得团契睦洽,世界才得安宁和平!”这样在侦探故事中谈诗歌,而且诗与案件并无关系,这只有在中国的侦探小说家笔下才能看到,这也就是传统文学隐藏在作者笔下的所谓“趣味”。在方言的运用上主要采用的是一些乡间理语、上海俗语,比如里弄、木作、捐客、白相人、堂信,体现了浓郁的上海风味。
本土艺术精神的另一方面就是“与本土生活的情感和文化联系”,作家作品对生活的表现不是肤浅的,而是饱含了作者对于本土生活的深切关注,充满了作家的思想和感情因素。通过文学来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曾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原则。“而以此为价值导向的文学具有世俗化的取向,或通常所说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不难理解了。从五四时期开始,作家们就自觉地肩负了改造‘国民性’和救亡图强的社会责任,几乎所有作家都把目光投向社会的合理性问题( 社会正义) 。”[4]91程小青的创作虽然在思想深度上不及鲁迅等作家,但是也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霍桑探案》中我们可以从他对案件发生的背景描写中感受到他对“现代性”的思考。
《福尔摩斯探案》中最明显对于时代的思考就体现在反对封建迷信思想上。在当时的中国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即使在上海这样一个当时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文化进步明显的地区,也还有很多人相信“鬼神”的存在,所以程小青在创作侦探小说时,主要考虑到的就是反对迷信的这一主题。他在《催命符》《白衣怪》等篇中都通过人物的言语制造出了一个所谓的“鬼”的形象,然后通过一步步的案件侦查证明根本不存在“鬼”,只不过是犯罪分子利用这种迷信的方法来实施犯罪罢了。《催命符》里那个能催人性命的不过是曾经被死者打过的普通医生华济民,《白衣怪》里死者经常看见的貌似哥哥的穿白衣的“鬼”不过是由家中老仆人方林生假扮的。
此外,《霍桑探案》中的案件主要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家庭生活背景下,描述的主要是子女与父母长辈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发生的悲剧故事。《霍桑探案》的创作时间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段时间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和租界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上海。当时的上海人口众多,工商业十分发达,而且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众多。而程小青对当时半殖民地的上海以及苏州等地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现代性的反思。在作品中霍桑和包朗曾多次提出由于现实社会物欲膨胀,金钱成为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尺,传统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的道德戒律开始崩溃。在《活尸》中作者这样写道:“朋友的交情、夫妻的结合、师生的关系,一切都商品化了。”旧道德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新道德又还未建立。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个新旧道德青黄不接的时期,处处都暴露出反常的现象,因为传统的伦理基础,既然因对封建制度的崩溃,连带地起了摇撼,新的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间失去了正轨,青年们的行动便无所适从,往往趋入歧途。”总之,《霍桑探案》中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缺乏法治思想,并且处在封建思想笼罩下的家庭中。通过的案件更加贴近生活实际,往往更能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与那些选择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案件相比反而更能体现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在供读者娱乐以外,还能起到一定的揭露社会矛盾与黑暗的作用。
要将西方侦探文学本土化,就要将它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与交融,就要把它与中国百姓的生活融合,书写本土生活,并深入生活:思考其中的问题,真正做到文学作品反映本土生活,这就是成功的本土化作品。程小青的创作虽然没能做出十分深刻的人生和人性的阐释,但是却做到了反映本土生活的各种现象,尤其是当时上海的市民生活,并且还对其有一定的思考,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融入本土生活
当时《霍桑探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读者都曾写信给程小青本人,大众对霍桑这个人物的喜爱程度不亚于现在的韩剧。虽然徐念慈认为侦探小说的长处全在于“布局之曲折,探事之离奇,于章法上占长,于形式上占优,非于精神上见优者也”[6]43,读者看侦探小说很少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寻找刺激,但是程小青在创作《霍桑探案》时则有着明确的“文以载道”的教育目的。这种教育主要体现在“启智”和“移情”两个方面。
关于“启智”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当时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在《霍桑探案》中都可以看到。而程小青自己对这一方面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我承认侦探小说是一种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除了文艺的欣赏之外,还具有唤醒好奇和启发智力的作用。在我们这样根深蒂固的迷信和颓废的社会里,的确用得着侦探小说来做一种摧陷廓清的对症药啊。”在《霍桑探案》中有《白衣怪》《催命符》《别墅之怪》《怪房客》等一系列“闹鬼”事件,还有在《虱》中所谓的“五鬼搬运法”,霍桑都运用科学的侦探方法证实了这些并非是鬼怪在杀人,只不过是有人在犯罪罢了,破除了各种封建迷信的传说。此外,程小青还在《从“视而不见”到侦探小说》中指出阅读侦探小说能培养“精密的观察力”。他在文中说:“我们天天张着眼睛,而实情所‘见’的却实在很少很少;所以‘视而不见’除了有特殊训练以外,委实是一般人的通病……我敢大胆地介绍一种疗治‘弱视’病的膏方,那就是侦探小说。”他认为,读者在读侦探故事时,多数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侦探一样,通过观察书中所写到的环境,人物的语言动作和细微的表情来亲自推测案情的结果,犯案的过程。而把他们阅读时的这种精密的观察力和注意力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那么自然能够治疗“视而不见”的社会通病,人们也就会对各种现象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成为一个关注国家和社会现实的有用的人,实现对大众的启发智力的教育意义。当然体现在作品中还有各种实际的科学知识的传授,《血手印》中就介绍了一种辨别血迹的方法:用一种淡亚马尼亚液滴在怀疑有血迹的刀面上,如果刀上的痕迹变成了绿色,那么是果汁,如果痕迹不变色,那么就是血迹。
关于“移情”的作用,《霍桑探案》通过许多的案件,对当时社会上的青年人、知识分子、普通妇女进行“劝善”的教育,引导人们要勇敢维护自己的利益,年轻人不应该沉溺于你追我赶的爱情或者各种物质享受之中,不应整日昏昏沉沉虚度光阴没有生活的目标,而应该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或者财力为祖国为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尽一份力。正如张碧梧所说:“侦探小说的情节大概不外乎谋杀陷害和劫财等, 读者读了之后……恐怕不过只在脑中留下这个恶印象罢了……我以为在这种情节当中,务必使他含蓄着劝善惩恶的意思才好。譬如说某富翁被贼党害死, 便须附带说明这富翁平日的吝啬盘剥的行为;又如说某妇人被人害死,但所以会被人害死, 实固品行不端, 以致结下了仇恨。如此读者读完之后,必会生出 ‘自有取死之道’的感想。”[5]《白衣怪》中的裘日升不仅设计陷害自己的亲哥哥,而且生活作风极不检点,甚至对自己的养女也有非分之想,害死哥哥的事被侄儿海峰发现后,被侄儿所扮演的哥哥的“鬼魂”所吓死,实在是一个不知廉耻的长辈,所以死有余辜。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件事教育大学生们不要莽撞行事,做事要思考清楚。《青春之火》中张效琴的哥哥张有刚为了霸占妹妹的财产,想方设法破坏她和姜志廉的爱情,阻止她出嫁,甚至借着喝酒殴打她,实在是禽兽不如,最终张效琴为了摆脱这种压迫而杀死了哥哥。读者读完故事都会同情这样的杀人凶手,同时憎恶那些为了金钱而放弃亲情,毫无良心的坏人。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会友好待人,珍惜亲情。这样惩恶扬善的“移情”的目的就实现了。此外,文中还有大段关于社会现实的议论和说教的文字。当然也是因为作者怀有一颗正义爱国的热心,希望对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受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
正如陈平原先生在强调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传统文学和西方小说两方面“移位”的合力时指出:“中国小说接受西洋小说刺激而发生变化是一毋庸置疑的事实;可中国小说接受的是经过选择、改造、变形的西洋小说。不考虑这种移位过程中的‘损耗’未免低估了这一文学运动的艰难曲折。就作家心理而言,在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对待西洋小说的态度大体上发生过如下变化:从‘以中据西’到‘以中化西’到‘以西化中’再到‘融贯中西’。这不是四个截然分开井然有序的阶段,同一个作家可能徘徊于两种甚至三种态度之间。”[6]255很明显,程小青的态度介于“以中化西”和“以西化中”这两个阶段中间,既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浸润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又希望以侦探小说来起到“启智”和“移情”的教育意义。一方面程小青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传统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的个人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上过私塾,也阅读过大量的中国传统小说。而另一方面在西洋文学大量涌进的时代,他被西方文学那些新的叙事技巧、新的思想所深深吸引和影响着,所以他率先在侦探小说的创作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另外,“传统文学更多作为一种修养、一种趣味、一种眼光,化在作家的整个文学活动中而不是落实在某一具体表现手法的运用上”[6]143,而西洋小说的影响却恰恰表现在各种创作技巧的运用上,所以这种明显的叙事方法往往比那些隐藏在作品中的“趣味”更容易被人发现。通过《福尔摩斯探案》与《霍桑探案》的比较,可以发现程小青在侦探小说的创作中既体现出了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趣味”,又接借鉴传统小说的“入话”的叙事技巧。
四、结 语
“所谓文学本土化,其最基本的内涵是文学与其产生的本土现实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看其关联是否密切,能否体现出本土的深刻和独特,能否以独特深度和个性呈现出其意义。具体说,它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学内容。其次是来源于本土的文学思想。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本土文化传统,二是与本土生活的情感和文化联系。最后是融入本土生活。”[7]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中主要人物以及众多案件都是反映了本土的生活现象,在故事开场方式上程小青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入话”的方式,并且在具体的创作中运用了许多具有传统特色的语言。而且主要人物霍桑的思想内涵也是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民思想,作者创作也是本着“文以载道”的教育意义,并且在描写各种案件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反思。
虽然程小青在人物模式和叙事结构上借鉴了《福尔摩斯探案》的技巧,没能对当时社会进行深入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人性问题,但是他笔下的侦探形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写霍桑,不光是为了给人取乐,做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为了‘剥鱼肉,露骨头’。” 他的侦探小说是深深扎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中国传统文学中,吸收西方侦探小说的光芒而成长起来的文学作品。
[1]任翔.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115.
[2]李欧梵.福尔摩斯在中国[J].当代作家评论,2004(2):13-14.
[3]程小青.霍桑探案集[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56-158.
[4]杨经建.从超越性到世俗性——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表征之一 [J].天津社会科学,2009(6):91.
[5]张碧梧.侦探小说琐话[J].侦探世界,1923(4):16.
[6]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贺仲明.本土化: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另一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2):81.
责任编校:汪孔丰
2013-12-10
程海燕,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间:2014-10-28 14:19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04.html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5.004
I207.42
A
1003-4730(2014)05-0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