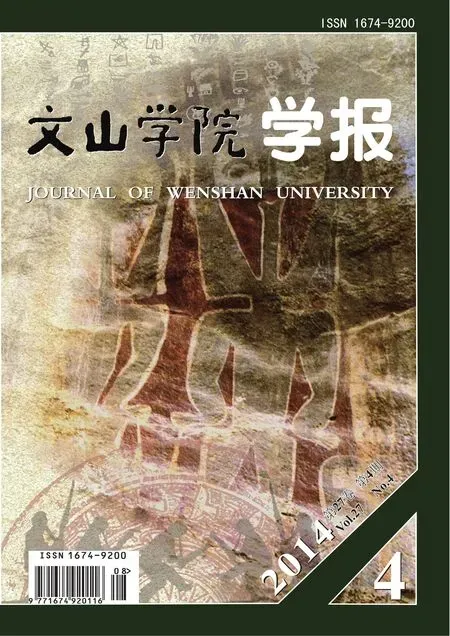论西南联大的民俗研究
刘 薇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论西南联大的民俗研究
刘 薇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在滇8年,联大的师生结合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从多学科、多学派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少数民族民俗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用西方的理论方法与田野作业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俗学学科的构建和完善,为研究少数民族民俗学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西南联大;民俗学;研究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和教育之精华免遭灭顶之灾,华北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等学府和一些科研院所纷纷西迁。一时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教大迁徙运动。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大迁徙中,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到湖南长沙联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于日军的不断入侵,东南沿海相继陷落,教育部命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昆明,到昆明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云南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既是中国的西南边陲,又是中南半岛的北端,这样,云南就成为了典型的边缘文化区和多民族聚居地。西南联合大学可以说是全国人才最为集中之地,教授们大多留学欧美和日本,掌握了当代最为前沿的学科理论,而缺乏长期的田野调查机会,对他们来说,来到云南诚然是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把研究领域延伸到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领域。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和语言学者等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开展民俗文化调查研究,如罗常培从民间信仰分析其姓氏来源;马学良以礼俗解释其经书等。这一时期,民俗研究成为各个学科田野调查中关注的重点。本文通过分析总结西南联大对民俗的研究成果,对此时期的研究作回顾性的述评。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对民俗的调查研究
抗日战争早期,除了西北、西南以外,大半个中国的土地都已经沦陷,西南边陲的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成为连接国际的重要交通要道。云南地方当局计划修筑一条由石屏通往佛海(勐海)的省内铁路,以连接滇越铁路。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决定从筑路经费中抽出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文化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情况,以供筑路时参考与运用。在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和冯文潜教授的积极争取下,最终由南开大学获得这项工作,并得到3万元的经费资助,且以此为契机,筹建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抗战尽微薄之力;另一方面也为西南联大学者进行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提供了契机。“按《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规定,是以协助推进边疆教育为目的,但同时,广义的或非意识的教育内容,既社会的一切生活样法与文物制度也同样要深入研究。”[1]584-586研究室从制定计划到进入田野调查,都以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习俗为切入点,进而深入地了解民族文化。研究室聘请陶云逵为主任,先后参加研究的成员有黎国彬、黎宗瓛、邢公畹、高华年、袁家骅、赖才澄等人。研究室的成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红河而下,对红河哈尼族、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苏等兄弟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为了让调查研究成果问世,在艰苦的环境中刻蜡版油印,出版了研究室的刊物《边疆人文》,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语言人类学专刊,乙种是综合性的双月刊。《边疆人文》乙种双月刊自1943年至1946年在昆明油印共三卷;第四卷由国立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在天津编印。在昆明油印的三卷共计发表论文32篇,其中23篇是对民俗学的研究,占总数的72%。[1]588-589从发表的论文来看,研究室成员通过田野作业掌握了大批口头和实物资料,记录了即将消失的民间习俗文化,是西南联大对民俗研究的重要机构。
二、民间信仰的研究
西南联大时期对民间信仰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涉及到搜集经书典籍、仪式调查、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等研究。1942年陶云逵从云南大学转入西南联大,加入边疆人文研究室。按研究室的计划主要对云南新平县地区民间信仰进行考察。先后撰写了《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西南部族之鸡骨卜》等。[2]《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是1942年夏季根据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调研计划,对坐落于新平县杨武坝之东的一个黑夷寨子的实地调查研究。介绍了族谱、族长、宗族成员参与的民俗活动,进一步调查研究了图腾崇拜,大寨黑夷由于受到汉人的影响,每个宗族都有一个汉姓,但在汉姓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少为人知的取一类动植物或器物之名的宗族姓,从当地人生产生活和神话传说中可以了解到,宗族姓中隐藏着对图腾的崇拜,如对宗族姓所指的姓物有一定的禁忌,汉姓同姓可通婚,而同宗族姓则不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联系国外图腾崇拜的研究,推断出这一地区族群中还保留着图腾崇拜的现象。《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1942年在新平县鲁魁山大寨对黑夷鸡股骨卜的占卜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并根据调查材料绘制鸡骨卜征兆图象和对其所系之卜的译述,把占卜事项分为献神、送鬼、叫魂、讼事、出行、婚姻、疾病、盖房、担倮护送、牲畜、打猎、子女、财产、宇宙天象14类。第二部分,以其他人调查到的滇西南和四川雷波等地区的占卜习俗进行比较得出,当时我国西南藏缅、苗、傣等语系族群都有、或曾经有鸡骨卜的风俗,汉语社会中的鸡骨占卜方式是由非汉语部族传入的。
北京大学学生马学良随学校来到云南,并在1939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培养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李方桂、罗常培导师的带领下,开始在云南省的路南、寻甸、宣威、禄劝、武定等地区调查,他总结出了“以俗释经”“经俗互释”新途径来解读彝经,既要对经书译解,又需重视民情和礼俗研究、考察各种祭祀仪式,来解答经书中疑惑不解的问题。他在彝族地区结识毕摩数十人,搜集彝文经书2000余册,译注彝文经典10部,编出《彝文字典》初稿,调查礼俗、搜集和礼俗有关的文物。陆续撰写了《灵竹和图腾》《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倮族的招魂和放蛊》《宣威倮族白夷的丧葬制度》《黑夷风俗之一——除祸崇》《倮民的祭礼研究》《倮译〈太上感应篇〉序》《倮文作斋经译注》《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宣威河东营调查记》。[3]马学良在研究彝族语言文字期间,对《作斋经》和《作祭经》作了重要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亲临斋场、祭场,详细记录了祭品摆放的位置、毕摩仪式中所颂的经典等,通过参加到仪式过程中来加深对经文的理解。
吴泽霖1941年应聘到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他曾多次亲自和指导学生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搜集民族文物,筹建丽江边胞服务站并负责该站的指导工作。1943年8月亲自到云南丽江县纳西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他撰写了《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麽些人的婚丧习俗》。[4]《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对东巴教的传承方式、经书中创世神话、祭祀仪式过程,以及放蛊、日常生活中的征兆都有较为详细的研究。《麽些人的婚丧习俗》记述纳西族从订婚到结婚的仪式过程,丧葬过程中所颂的经典,通过分析舅父在整个丧葬过程的重要地位,认为纳西族中曾流行过母系制度。
闻一多在研究上古文学时,许多内容都涉及到民间文化,在抗战时期,更是运用民俗学的方法,去解释生活中的民俗。《道教的精神》等论文都是他对民间信仰研究的贡献。[5]
罗常培考察发现宗教信仰在姓氏上可以反映出来,他前后写了三篇《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涉及到的原始材料来源于云贵川地区的6个部族。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材料来分析民间信仰在姓氏上所遗留下来的遗迹。
1943年高华年经罗常培推荐,参加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调查工作。他在调查语言时,除了记录故事、歌谣外,还对当地的习俗进行调查,撰写了《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鲁魁山罗罗的巫术》。《鲁魁山罗罗的巫术》对峨山莫石村日常生活中的白巫术和黑巫术进行了详细调查,他认为“调查不仅是知道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找出各民族间彼此有关的材料,探究它们的来源,追寻人类原始的心理,找出他们历史的背景出来,这是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者的职责”。[6]
三、民间口头传统的研究
抗战时期闻一多参加了被称为“小长征”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到昆明,路途中他指导学生刘兆吉采集民歌2000多首,编辑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同时带领马学良对民族宗教、民俗、民谣、神话传说等进行调查,到昆明后,马学良通过整理沿途收集到的素材,写成了《湘黔夷语掇拾》一文。一路上,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生动的民间歌谣,优美的神话传说等,不仅丰富了闻先生的神话、古典文学研究,也引起了他对民俗学方面的兴趣。他在1942年5月应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邀请,为训练团演讲了“神话及中国文化”。[7]1942年12月在中法大学演讲《神话与诗》。[8]在抗战时期先后发表《姜嫄履大人迹考》《伏羲考》《说鱼》《神仙考》《龙凤》《两种图腾舞的遗留》等。[9]闻一多从民间歌谣到神话都试图用民俗学的视野进行阐释。
抗战时期对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并不是单纯就语言层面的语音搜集和研究,其显著特点是把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与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知识相结合。民俗文化的调查离不开语言,在异族文化区进行田野调查时,用当地语言与调查对象沟通是深入了解族群核心圈内文化的手段。同时在搜集语言材料时,是以记录当地民族文化记忆(民间故事)和日常生活为主要语言素材,因此语言学者对民间文化研究的著述尤为丰硕。
马学良在田野调查时注重对神话的搜集研究,同时倡导来到边疆的人士应注意搜集神话,他认为神话是知识的积累,包括了民族文化、历史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撰写的《云南土民的神话》《云南倮族(白夷)之神话》,[10]是通过分析彝族中搜集到的神话,阐述了神话与生活之间的密切性,特别是神话中对民间信仰的解释性意义。罗常培在1942年~1944年期间先后三次赴滇西大理一带进行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调查,搜集当地多则故事和多首当地民歌,先后撰写了《大理的几种民间传说》《茶山歌》《路南夷风音乐序》等。[11]高年华1941年在昆明第八区东亩堡核桃箐村调查时找到一位黑夷发音人杨富顺,花了4个月工夫,记录了30多则故事2000多个词汇,1942年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黑夷语法》,由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语言人类学专刊(乙集)》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他的《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1945年夏路南县政府编修县志,邀请袁家骅去做语言调查方面的工作,在路南时偶然从朋友处看到光未然所写的《阿细的先基》,于是想到了去发现其原文。他和小学教员在雨天里行走60多里到了凤凰山,找到了为光未然《阿细的先基》的发音人毕荣亮,整理完成了《阿细民歌及其语言》,内容包括丰富的神话、男女的恋情和民族风俗,不仅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科学记录提供了借鉴方法,也为了解阿细人早期的生产、生活民俗、婚姻习俗保存了珍贵材料。邢公畹1942年应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邀请来到西南联大,1942年到罗平去调查台语,共搜集到《风俗谭》3篇,故事传说3篇,1943年在新平县磨沙乡请到一位会讲故事的白成章傣族老人,从老人的口中收集到多则民间故事、民歌,还亲自参加具有当地民俗特色的捕鱼活动。《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及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是在白成章老人处搜集到的借钱葬父故事与董永故事的比较研究,认为傣族地区的借钱葬父故事是由汉族地区传入的[12],为故事比较学的研究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四、对民俗学调查研究的特点
抗战时期的民俗学研究作为民族调查组成部分被赋予特殊的学术价值,少数民族鲜活民俗事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积累了一定的搜集、整理资料的方法,学者们把西方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使其研究方法更具前沿性和科学性,为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民间信仰和口头传统的研究,不仅保留了丰富的原始素材,而且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多学科交融的研究范式
多学科交融的研究包括方法的多角度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参与者。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端,仅仅是歌谣的采集与研究,到了20年代末以及整个30年代,逐渐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在方法论上吸取了这些学科的方法。”[13]580在抗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西南联大学者对当时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民俗事象实施的实地调查,不仅从本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而且把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来进行关注研究。联大学者大多具有在欧美和国内高等院校深造的学术背景,接受过系统全面的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理论的学习和训练,拥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同时通过田野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材料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基本摒弃了大汉民族主义思想和文化中心论观念,标志着用现代学术理论方法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研究的开端。抗战时期,虽然在云南报章杂志上介绍国外社会学、民俗学理论的著述并不多见,但在对云南民俗文化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大多学者都在有意或无意地介绍和运用到了西方的理论来对云南民俗文化进行阐释。
(二)民族凝聚力的体现
中国民俗学的兴起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五四”前后,整个知识界眼光开始向下去关注民众的生活。1922年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说到,歌谣加以选择,可以“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从歌谣的征集活动目的可以看出,知识精英们从口头传统入手认识和了解民众思想,从而召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早期的民俗学参与者,大都富于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文学修养,这很容易使他们把自己的治学功力和兴趣,与民间文学、民俗学相结合。随着中西学术的交流,中国学者受到外来冲击的时候,激发了民族的自尊心,怀有对民族的忧患意识,激发他们走向民间去寻找民族精神之路。抗战时期,云南地接英、法控制下的缅甸、越南,边地不断遭到英、法等国的侵略,片马悬案未决,江心坡又被强占。学者虽然处境窘迫,但对关涉国家、民族利益之事表示出极大关注。1942年8月陶云逵在给冯文潜的信中写道:“不来边荒不知边疆问题之严重,磨沙至元江之摆夷村对泰国已有羡慕之思,而思茅且有摆夷自设傣语新式学校。无论从学术,从实际政治,边疆工作刻不容缓。”[14]492介于云南多民族聚集区和边防战线的特殊地理位置,民族关系是当时最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一方面,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利用民族关系进行侵略,提出西南一带的彝族、傣族与泰人同族的关系,意图煽动泰国向中国西南各地发动扩张领土的野心。此时,民族同源性,是联合少数民族地区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武器,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从神话、民间信仰习俗等角度阐释云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同源关系,唤起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另一方面,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甚至是各民族支系之间,由于缺乏交流,对各民族日常生活不了解,以观念自分,由隔阂而生误会,由误会而至仇视或斗杀。这都是由于彼此的不了解和猜疑所致,学者们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开启各民族交流的首把钥匙,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在民族和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平日被掩盖着的,不被人们注意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三)有计划有组织的科学调查
如果说,抗战前民俗研究更多的是学者个人兴趣爱好的体现,那么,抗战时期的调查,已经转入有计划的调查为主的阶段,向学校提交调查计划并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从吴泽霖提交的《黔滇苗族调查计划》[15]557和边疆人文研究室提交《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15]584等计划中可以看出,调查前都需对调查地点、参与者、调查范围、经费、预期成果,做出详细的计划安排。调查都是在有计划、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进行的,调查人员都具备田野调查的基本素质,配备了仪器设备,这就保证了调查资料收集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五、对民俗学研究的意义
云南因地处边陲,封闭落后,民族众多,民间习俗各异,国人对此所知甚少。抗战以前,外界对云南少数民族的了解大多来自于西方传教士的著述,这其中有不少的偏颇之处。抗战时期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是民俗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它不仅为学科后期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而且揭开了云南少数民族“神秘”的面纱,让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风民俗,有效地避免了长期以来被“异域化”“魔幻化”的倾向。
(一)推动民俗学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
西南联大到昆明后,学校没有条件购买配套的教学设施,原来的书籍、仪器在转移时被遗失或破坏,给教学工作的开展带来不利;另一方面云南是民族文化的宝库,学者到云南后如入宝山,被多民族的文化所吸引,纷纷把研究方向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联,而民俗是进行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田野调查中特别关注民俗的调查研究,以研究民俗学为对象的论文明显多于前期。同时学者也认识到民俗是存在于鲜活的生活中的,民俗调查迫在眉睫,陶云逵在1943年发表于《边疆人文》上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一文中谈到,图腾制在他们的生活中尚有余音可寻,此现象在不久的将来势必完全消逝而由另一种符号与团体形式代替,他的担忧在当今得了印证,目前图腾崇拜在云南新平地区的生活中已难寻踪迹。马学良在1945年发表于《边政公论》上的《垦边人员应多识当地之民俗与神话》一文中,就积极倡导搜集研究神话,认为要研究神话并不只是记几则故事,而是通过神话走进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学者的这些观念使民俗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运用田野调查法,突破了以往对文献依赖的局限,从而能真实地反映民俗的本真面貌及其相应的生存状态。在调查方法上,学者们继承20世纪初期中国民俗学搜集民俗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吸收了当时西方的先进理论,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实地调查活动。陶云逵《西南部族之鸡骨卜》一文中,在实地参与调查过程,根据当地占卜书和巫师对占卜习俗的介绍,绘制近百种占卜征兆卜,并对每一个征兆现象作了详细的译述,同时注重文献资料考证,做到了田野调查、历史考证、他人在不同地域的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和借鉴。陶立璠就认为:“现代人搜集的民俗资料,只要不是研究者本人的调查所得,也是第二手的资料。根据历史的文献资料和他人调查的资料也可以进行民俗学的研究。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者不可能对所有民族英雄、所有地区的民俗事象都作调查。借用他人的科学调查资料,是允许的”。[16]71-72
(二)抢救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遗产
学者关注民族经典文献、口头传统、收集当地民俗文物,并积极翻译整理,抢救了民族的文化遗产。袁家骅在对彝族支系阿细人的歌进行采录的过程中,从实际材料出发,不仅记录下了丰富的神话,也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的调查方法,看到了阿细人所唱歌词以外的一些民俗文化特征和社会功能,并把他们描述出来,去研究它现实存在的状况和环境,去认识了解创造和保存这些文化遗产的民众。吴泽霖筹建了丽江地区边胞服务站,并指示该站工作人员注意搜集当地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用具的实物和照片,该站工作人员经过半年的努力,先后在纳西族、傈僳族和藏族聚居地区收集到两百多件文物和照片,这批文物于1943年从丽江送抵重庆展出,吴泽霖在展览会上向参观者介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为内地民众提供了一次近距离了解少数民族的机会。在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这批文物现存部分由清华大学移交给中央民族学院收藏。马学良的研究毕业论文《撒尼倮语语法》在对彝族语法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在文后附了多篇调查话语材料,包括撒尼人的神话传说、婚丧嫁娶习俗。他除了记录口头文化遗产,还尽其所能地购买收藏彝文经书,在离开彝区之前,一方面想方设法接近当地毕摩和土司,劝说他们勿将藏品售与传教士,一方面呼吁学术机构来购买这些珍贵的藏品。经他与多方协商,北平图书馆派编纂员万斯年前往武定协商征购事宜,购得不少珍贵的经书和当地民俗文物,这批文献中除了武定毕摩们赠与马学良的两千多册彝文经典外,另外以低廉价格出售和赠与的方式,收到彝文写经507册,彝文写经卷子一轴,彝文刻经15块,汉文档册12册。[17]2013年4月笔者在清华大学刘晓峰教授的带领下,有幸来到清华大学图书馆,见到了马学良抗战时期在云南收集的彝文经典,据负责此批经典修复的刘蔷老师介绍,2004年清华大学学校教育基金立项支持,对这批从云南打包一直和清华大学抗战时焚余书混放在一起的典籍进行整理,经过彝文专家朱崇先教授等的整理,已知这批彝文典籍共有1册刻本和250册写本及传本,成书年代从明末到民国二三十年代都有,大多是清代的写本。这批彝文典籍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彝族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彝族民俗的重要文献史料。民俗文化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演进,民俗文化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学者的研究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生产生活、民风民俗等现象真实写照的反映,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这些地区的民俗文化及其历史变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中的古老习俗,并非仅仅是一种民族的生活状态的一个过程,在它们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人们的智慧。
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民俗被充分的挖掘与关注,民俗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强调,在各学科学者参与调查下,对民间信仰、故事和歌谣进行了记录和研究,并通过发表的形式向外介绍,内地人士通过这些介绍了解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民间文学作品,学者们的著述真实地记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集体记忆、口承文艺、生活习俗,这些材料弥足珍贵。但是,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 无论是发掘、整理还是研究都分散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缺乏系统性,缺乏对民俗学进行自觉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梳理,缺乏专门从事民俗学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没有正式提出民俗学学科的建设理念。这些都制约着民俗学学科从广度到深度上的学术交流。
[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陶云逵.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3]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文集[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4] 吴泽霖.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5] 闻一多.道教的精神[N].中央日报,1941-01-13.
[6] 高华年.鲁魁山倮倮的巫术[J].边疆人文,1946(3):3.
[7] 闻一多.神话与古代文化[M]//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8] 闻一多.神话与诗[M]//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9]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3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10] 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11]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邢庆兰.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J].边疆人文,1946(3):35-43.
[13]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14]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15]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8.
[16] 陶立璠.民俗学概念[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17] 张廷银.收集地方文献须责任与识见并驾而行——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述论[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1):22-27.
On the Study of Folk Customs Made by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IU W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China)
Eight years after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is transferred to Yunna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rried out meticulous researches into ethnic minorities’ folk customs from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school perspectives by making good use of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rich ethnic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province. Their achievements were remarkable.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they adopted were a combina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and field work. With their pioneering endeavors and contributions, China’s folk custom’s studies had been established and perfected.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studies of folk customs; research contribution
K892.474
A
1674-9200(2014)04-0032-06
(责任编辑 杨永福)
2013-11-06
云南教育发展与西南联大研究基地开放性青年基金项目“西南联大对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贡献”(YED11Q001)。
刘 薇(1980-),女,四川会东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