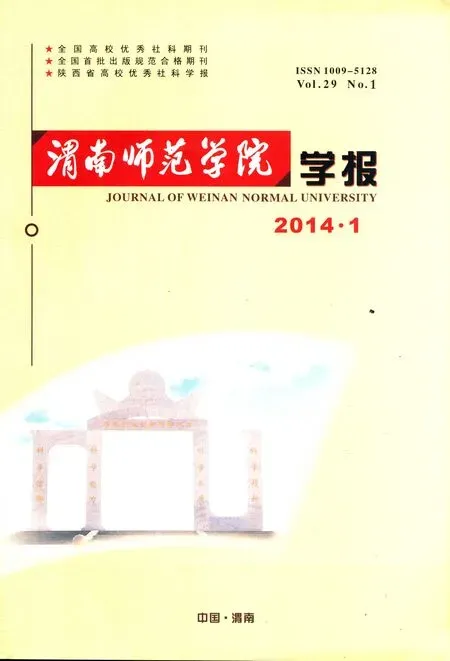《易传》政治伦理思想特点诠释
靳浩辉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部,北京100091)
《周易》作为一部历经西周到战国的思想巨著,包括《易经》与《易传》两部分,《易经》具有浓厚的卜筮文化色彩,而《易传》在继承了《易经》卜筮文化的同时,具有非常明显的人文文化倾向,其中包括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尤其是政治伦理思想。《易传》政治伦理有别于其他著作,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可见,“推天道以明人事”是《易传》最别具风格的特点,人间的诸多伦理形态都来自于天道的启示,人道本于天道;阴阳之间具有等级差别,阳尊阴卑的同时,阴阳互补,两者缺一不可,可见阴阳的对立统一也构成了《易传》政治伦理的特点之一;《易传》赞同变革、变易,渴望改变无道腐朽的政治统治,同时也把变革的范围统摄于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之内,可谓在“不易”中开展“变易”;《易传》极为重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把崇德看作是广业的前提和基础,与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思维路径相通。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易传》政治伦理思想的特点。
一、推天道以明人事
《易传》“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特点在《彖传》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其解释都是先推天道,后及人事。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睽》卦)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卦)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卦)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卦)
《彖传》这种“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包含着天、地、人一体的思维内容,而且这种一体是以“人效法天地”为基础的。
《序卦》在论述宇宙的生成过程时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是对《咸》卦的阐释。《易传》以宇宙生成的自然过程推导出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进而把社会之所以有上下礼义之制,也认为是由“天地”所生。这是因为天地本身就具有尊卑、贵贱之义,即所谓“天地之大义”。
《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因此男女、夫妇,以及父子、君臣,也就有了尊卑、贵贱之别。所以《家人卦·彖传》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显然,《易传》推天理以明人事,把“天道”与“人道”、自然与社会合为一体,于是,整个宇宙秩序即体现为上下、尊卑的伦理关系。
《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认为天、地、人各有其性命之理,即天道为阴阳,地道为柔刚,人道为仁义。根据“《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的本义,“一阴一阳”乃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地道、人道都是阴阳之道的体现,这就是说,人道之仁义本属于天地阴阳之理。
总之,《易传》“推天道以明人事”,认为“人道”源于“天道”,“天道”与“人道”合一,整个宇宙秩序即表现为上下、尊卑、贵贱、仁义的伦理关系。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思孟学派那里已初见端倪,而《易传》则把这一思想模式提高到了宇宙论的理论高度,并由此回答了道德的本原、人性的来源,以及理想人格的道德境界等一系列的问题。以后,无论是汉儒董仲舒的“天副人数”,还是宋儒程朱以“天理”为本的道德本原论,都以不同的理论形式体现了这一特点。[1]128
二、阴阳对立统一
《易传》认为自然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界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在《易传》看来,“一阴一阳之谓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共同遵循的原则。阳的秉性为刚,阴的秉性为柔,阳代表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处于领导、主动和施予的一方,阴代表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处于服从、被动和接受的一方。在人类社会而言,君臣、父子、夫妇同样适用阴阳原则,阴象征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坤卦·文言》),阳与之互补,象征着天道、夫道、君道。阳为尊,阴为卑,阴阳具有尊卑不同的地位。但同时,阴阳之间又相依相存,互补统一。如果缺少任何一方,或者阴阳失和,阳刚过头、阴柔太甚的话,就会导致否塞不通的消极局面,如果阴阳协调、刚柔相济则会形成一种畅达和谐的有利局面,才能促进万物繁衍生长。因此,阴阳两方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如果阳尊阴卑,协同配合,统一的一面将居于主导,反之,对立的一面将会凸显。
《系辞》进而对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把阴阳所涉及的范围扩展开来,阳和阴是与天地、日月、昼夜、暑寒、刚容、健顺、明幽、伸屈、进退、男女、贵贱、君民一一相对的,因而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重要思想。认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生活,万事万物都普遍具有阴阳两性,阴阳总是相伴相随的。
《易传》进而把阴阳观念引申到政治伦理的方向。阳象征君道,阴象征臣道、民道。“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坤卦·文言》)“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系辞上》)《易传》把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应用到君臣、君民关系之间,既强调君尊臣卑,又重视君臣共治;既强调君贵民贱,又重视养民惠民。可见,《易传》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以阴阳对立统一思维为指导的。
《易传》对阴阳内涵的阐述,既吸收了儒道两家,又超越了儒道两家。[2]36孔子思想的根本精神属于阳刚类型,表现为对理想的执着,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知其不可而为之”。与此相反,老子思想的根本精神则属于阴柔类型,表现为对客观规律的顺从,贵柔守雌,自然无为。在《易传》的太和思想中,儒道两家的根本精神不再彼此排斥,而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阴阳协调的互补关系,阳刚与阴柔紧密联结,表现为中和之美。它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象传》),“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辞上》)。阴阳互补的状态也叫做“太和”。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这也就是《易传》的政治伦理思想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三、变易与不易
《易传》认为,整个宇宙世界都在变化运动。《丰卦·彖传》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系辞》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意思是说,太阳正居中天必将西斜,月亮圆满盈盛必将亏蚀;天地大自然有盈满有亏虚,都伴随一定的时候更替着消亡与生息。世界和宇宙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唯变所适”的。
在《易传》看来,运动变化是普遍性的、永恒的和连续的。《系辞》说:“阖户谓之神,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意谓关闭门户包藏万物叫做坤,打开门户吐生万物叫做乾,一闭一开叫做变化,来来往往地变化无穷叫做会通。不管是天上的天象,还是地上的万物,都是不停变化运动的;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才会使事物的发展不受阻塞,事物才能不断的发展。可见,《易传》中的“变”是说明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永恒性。《系辞》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是说日日增新不断更善叫做盛美德行,阴阳转化而生生不绝叫做变易。万事万物,推陈出新,生生不已。这两句话可谓揭示了《易传》中关于运动、变化、发展的深刻涵义。
不过,《易传》认为,万物的“变易”还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系辞》曰:“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贞”是“正”的意思,“贞胜”指坚守正道就能获胜,“贞观”指坚守正道就被人瞻仰,“贞明”指坚守正道就焕发光明。“贞夫一”,是说天地万物的“变易”都应该遵循正道。[3]253所以,守正道则吉,逆正道则凶。正道就是事物变化的法则,是“不易”的。“不易”的正道为何?在《易传》作者看来,正是尊卑有序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尊卑地位是不容改变的。
可见,《易传》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强调尊卑等级,《泰卦·彖传》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阳健代表君子、阴顺代表小人,依此比附,认为父子和君臣间的关系是上下的、有等级的、主从的,进而把这些关系固定化、绝对化,给予不可违背的特性。《家人卦·彖传》以尊卑有序来规定“正家而天下定”。《易传》认为,尊者为阳,卑者为阴,阴顺阳则吉,阴乘阳则凶。意思是说,尊者需要卑者来侍奉,卑者应顺从尊者,遵从尊者的指挥,不能凌驾于尊者之上。
另一方面,《易传》根据万物的“变动不居”“与时消息”,相应地提出了变革的思想。《革卦·彖传》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如果统治者腐朽无能,是可以通过革命来推翻他们的。《易传》肯定汤武革命,认为他们顺天应人。这种变革说对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可谓影响深远。
但是,《易传》肯定变革,并不是为了否定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相反,它是在维护尊卑等级制度的前提下提倡变革的。为了防止这种制度被革掉,《易传》阐述了一系列民本学说。如《大畜卦》所说的“养贤”和“尚贤”;《颐》卦讲的“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损》卦和《益》卦提出的“损上益下”,《节卦》倡导的“不伤财,不害民”思想,主张节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剥削压迫。
总之,在表面上看“变易”和“不易”是相互矛盾的,其实两者都统一在“理人伦而明王道”的纲领之下,“变易”是就改变纷乱的社会等级秩序而言的,“不易”是就维持正常的社会等级秩序而言的。
四、崇德与广业
《系辞》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在《易传》作者看来,崇德是提升自身的品德,属于内修的功夫;广业是建立恢弘功业,属于外化的范畴。崇德是广业的内在要求,广业是崇德的外在体现。二者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系辞》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可见,盛德大业是对统治者的双重要求。
首先,先看《易传》对崇德方面的叙述。“先王以作乐崇德,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豫卦·大象》),“忠信所以进德也”(《乾卦·文言》),进德也是崇德,均指通过不断地修身养性来提高自身道德。对于君子崇德的内容,标准为何,以及期望修养到何种境界。在《易传》作者看来,《乾》卦所代表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君子崇德内修的方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大象》)“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系辞》)“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固穷矣。”(《需卦·彖传》)《易传》认为,在遇到艰难险阻时,应以刚健有力、积极进取的态度去面对,才可以趋吉避凶,不至于陷入困境。
《易传》在强调刚健的同时,也对阴柔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坤卦·文言》)阴柔在下者纵然有美德,也只是含藏不露而用来辅佐君王的事业,不敢居功自傲。这如同地顺天、妻从夫、臣忠君的道理。《明夷卦·彖传》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明夷指光明受到损伤,在蒙受巨大的患难之时,只有内含文明美德,外呈柔顺情态,如周文王那般“用晦而明”,才能渡过难关。
由此可知,《易传》推崇的是一种“刚柔相济”的品性,如同《小象》对《鼎》卦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的解释:“玉铉在上,刚柔节也。”只有刚柔并用,相互融合,方能“大吉无不利”。
以上对刚柔相济、健顺相融的论述,也包含着卑弱尚谦,遁世守身的内容。这可能受到了老子“弱者道之用”的影响。《易传》是融合战国时期不同学派思想的著作。在道德修养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儒道两家思想的兼容并蓄,《乾卦·文言》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这段对潜龙之德的论述,勾画出一个遁世无闷的隐者形象,与老庄崇尚隐士的思想有所契合,也与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相似。
其次,崇德和广业分属于内修与外化两个范畴,《易传》作者基本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随着个人修养的提升,社会也会相应的改善和安定。孔子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百姓安则国家安。《易传》继承了儒家这种内修外化的思维方式,《乾卦·文言》曰:“德博而化。”《乾》卦九二的小象曰:“德施普也。”《家人卦传·彖传》更是提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先有正家之德,方能定天下。这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是一致的。
《易传》的“广业”主要指两个方面:齐家和治国。齐家方面主要有《蛊》卦所涉及的如何处理与父母的关系,《归妹》卦所论述的婚姻关系问题以及《家人》卦所蕴含的家族关系问题等等。治国方面主要有治民、养民、尚贤和教民等内容。
总之,《易传》的崇德与广业之间是相互贯通、相互融合的。崇德是广业的基础,广业是崇德的深入,两者共同构成了《易传》政治伦理思想的一种鲜明的特点。
五、结语
《易传》政治伦理“推天道以明人事”,抒“阴阳变化”之思,彰“变易与不易”之道,从天道的高度确定“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阳尊阴卑,即君尊臣卑、君尊民卑的等级制度,从而使之成为“不易”之道,构成了《易传》政治伦理“形而上”的特点;又从“崇德与广业”的角度要求为政者内外兼修,内圣外王,构成了《易传》政治伦理“形而下”的特点,所以说《易传》政治伦理特点具有鲜明的广融性和圆润性——“形而上”与“形而下”相交融。
[1]朱伯崑.易学哲学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2]王博.易传通论[M].北京:中国书店,2003.
[3]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