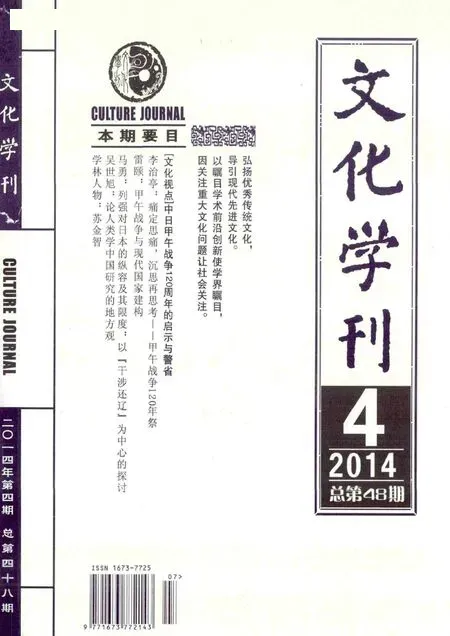从《礼记》看儒家“礼乐”之政治功效
吴蕴慧
(苏州市职业大学,江苏 苏州 215104)
《礼记》中有关礼乐的内涵和功用的描述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念。礼乐即礼节和音乐,古代帝王常用兴礼乐为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1]。古圣先王制礼作乐,其目的不是满足人们口服耳目的欲望,而是为了防止人欲横流酿成大乱而人为地加以节制,“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2],也是用以教导人民摆正好恶之心从而返回做人正道的,所谓“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3]。儒家治理天下之道其实就是实行礼乐之道。
一、礼乐之情实别异
《礼记》对礼有众多描述,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礼的内涵和功用。首先,礼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4],是先代圣王用以顺承自然之道来治理人情的[5],是用来防止人民淫纵、显明男女之别、作为人民生活纲纪的[6]。
乐就是音乐。作为同是发音载体的声、音、乐是有所区别的,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和境界。人心有感于外界事物的活动表现于声;声相互应和产生变化就形成音;排比音节用乐器加以演奏,用盾牌、斧钺、雉尾、旄牛尾进行舞蹈,就形成乐[7]。音产生于人心,乐通于人情事理[8]。乐是天地和合之道的表现,是中和之气的纲纪。
(一)乐由中出,礼自外作
乐活动于内心,礼发动于外貌,“乐也者,动于内者也”[9]。乐反映内心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是不可以改变的;礼反映社会的伦理,这种伦理也是不可移换的,“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10]。乐从内心发出,显得平静;礼在外表兴作,具有文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11]。
(二)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礼乐的学说包涵着人情,“乐统同,礼辨异”[12],乐的功用在于统一、协同人们的情感,而礼的功用在于辨别身份的差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13],情感和同就能互相亲近,等级差异就能互相尊敬。乐用来陶冶内心,礼用来规范举止。礼乐交互作用于内心而体现于外表就会形成愉悦、恭敬、温和、文雅的品格,“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14]。盛大之乐与天地具有同样的和气,盛大之礼与天地有同样的节序。有了和气,万物才不丧失生长的本性;有了节序,才能按时祭祀报答天地生成万物的功德,“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15]。礼依据天地万物的品类殊异、尊卑差别而实行,乐依据天地万物流动不息、和合化育而兴作,“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16]。乐贵在和同,遵循圣人的精神而顺从天道;礼重在区别事宜,遵守圣人的精神而顺从地道。所以圣人作乐来顺应天,制礼来配合地。礼乐昭明完备,犹如天地各尽其职,“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17]。
(三)礼乐之器文与情实
礼乐的载体之器以及表现形式均不一样。钟鼓管磬等乐具和雉尾、笛形的六孔籥、盾牌、巨斧等舞剧,是乐之用器,屈伸、俯仰、舞蹈的队列、舒缓迟速的动作,是乐之表现形式;盛稻饭粱饭的簠、盛黍饭稷饭的簋、盛牲肉的俎、盛肉酱、醃菜的豆,各种规格、文饰,是礼之器用,升阶降阶、上堂下堂、转身行走、袒开外衣、掩住外表等等,是礼之表现形式,“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18]。而单用盾、斧的舞,不能算是完备的乐;仅用熟牲的祭祀,不能算是完备的礼,“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非达礼也”[19]。因此,理解礼乐情实的人,方能制礼作乐;懂得礼乐之表现形式的人,才能够传述礼乐,“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20]。
乐的实质在于穷究人之本心、通晓声音之变化;礼的原则在于显明诚敬、去除虚伪,“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21]。乐的情理在于符合伦常而无害,乐的职能则是欢悦喜爱;礼的本质在于中正无邪,礼的准则则是庄敬恭慎,“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22]。
(四)礼主其减,乐主其盈
礼是通过各种不同的仪式使人民互敬的活动;乐是通过各种不同的乐曲使人民互爱的活动,“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23]。礼乐侧重点有所差异,礼有勉力答报的因素,而乐有反躬自制的因素,“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24],礼谦让收敛而又能勉力进行,以勉力进行为善;乐丰满充盈而又能反躬自制,以反躬自制为善。礼一味谦让收敛而不能勉力进行,那么礼就会导致消亡;乐一味丰满充盈而不能反躬自制,那么乐就会流于放纵。礼能够勉力答报,就会产生和悦;乐能够反躬自制,就会获得安适。礼的勉力答报与乐的反躬自制其意义是一致的。礼乐能依照天地之情理,上达于天而下据于地,随阴阳并行,与鬼神相通,穷尽极高极远之所,探测极深极厚之处。乐昭示天之和合化育之功,礼处于地之生成万物之位,“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25]。
(五)礼者缀淫,乐者象德
礼是用来制止过分的,乐是用来体现道德的,“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26]。致力于“乐”可以调理心境,产生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态,合乎天道、通乎神明,从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而致力于“礼”主要用以调理身形举止,使外貌庄严而态度恭敬,从而轻易怠慢的念头无法乘虚而入。受“乐”所熏陶的仁德发自内心,则人民没有不听受的;由“礼”所制约的情理显于外表,则人民没有不顺从的。
不过,凡是物极必反,“乐胜则流,礼胜则离”[27],乐过分了就会招致放荡,礼过分了就会产生隔阂。“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28],嗜乐过分就会有沉迷费事的忧患;行礼粗略就会发生不诚不信的偏差。
二、礼乐之政治功能
礼乐摹仿天地之情理、通达神明之恩德、升降上下之神祗,从而凝结成精妙义蕴与繁缛表现相结合的体式,以统理父子、君臣之法度,“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29]。礼乐教育人们互敬互爱,其基本情致是相通的。致力于礼乐之道的统治方能和谐顺达而无所畏难,所谓“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30]。具体而言:
(一)安上治民,移风易俗
古代帝王创业成功就制作音乐,政治安定就制作礼仪。功业大的,所作的乐就完备;政绩广的,所制的礼就周全,因此,观察一个国家的礼乐,便可以知晓这个国家的治乱,“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31]。礼之精神在于追念生命以及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乐的精神在于欢庆文治武功的成就,于是,先王圣者制礼用来节制事宜,治乐用来引导心志,“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32]。
礼教通行则不相争夺;乐教通行就没有怨恨。礼乐的政治功效就是揖让而治天下,具体而言:暴民不兴,诸侯归顺,兵器不使,刑器不用,百姓没有忧患,天子没有恼怒,如此则乐教通行;融洽父子之亲情,显明长幼之次序,四海之内都来敬奉天子,如此则礼教通行,“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33]。
(二)礼乐刑政,其极一也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34],“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35]。“礼乐皆得,谓之有德”[36]。礼乐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37],礼有理之意,乐有节之意。君子没有道理的事不为,没有节制的事不做。不能习《诗》则情意隔绝,行礼难免错谬;不能习乐则质朴无文,行礼就显得单调。道德浅薄则气质轻浮,行礼就流于空虚。在孔子看来,礼乐刑政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礼是用来引导人们的心志,乐是用来调和人们的歌声,政治是用来统一人们的行动,刑法是用来防止人们的奸邪,都是用以和同人心从而走向国家大治的正道,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38]。礼乐联合人们的情感,整饬人们的仪容,“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39],礼仪建立则显示了贵贱的等级;乐章相同则上下情感得到交流,也就互相和睦了。好恶的标准昭明彰著了,贤人与不肖之徒就有了显然的区别。用刑罚严禁凶暴,以官位拔举贤能,政治就均平公正了。凭着仁心来爱民,依据道义来匡正,人义并施,如此则民众大治的局面就得以实行了。
从本质上而言,《礼记》所体现的儒家为政思想其实就是礼乐治国之道。礼乐治国倡导的是仁义为基础的王道,而非暴力所推行的霸道,以礼来调节民心,以乐来协调民声,构建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