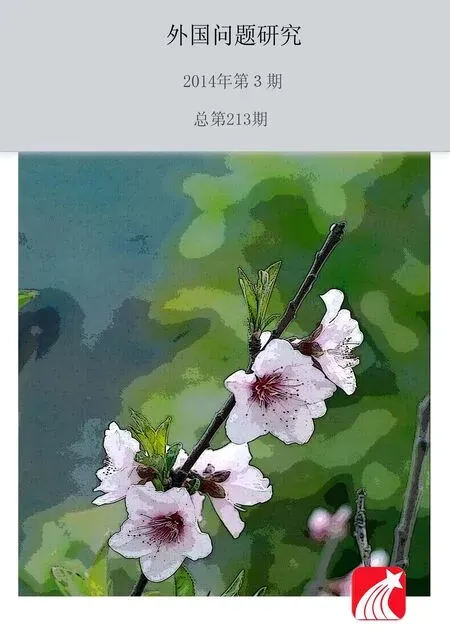日本中世末期兵农分离的原因
李 征
(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天津 300071)
中世是日本历史上较为独特的历史时期,不同于世界一般民族“中世纪”与“封建制”相一致的情况,日本历史还单独衍生出一个江户的近世社会,产生了一个时代特征明显的历史阶段。日本的中世与近世,其最重要转变期在于“织丰时期”。织丰政权虽然存续的时间短,却产生了一个独特的以幕藩体制、士农工商身份制为特征的近世社会。中世走向近世的重大转变之一即为对武士的改造,即“兵农分离”。正是这一阶层转变,使得武士成为脱产者,丰臣秀吉称之为“钵植花木”。对于大名而言,由地方领主变为从将军受恩的分封领国制;对于下级武士而言,脱离土地,迁居城下町,地侍基本消失。对于农民而言,《刀狩令》及《身份统制令》解除农民武装,切断其与武士的联系并固定其身份。“兵农分离”政策有一石三鸟的效果,这种多重管制对武士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夸张地讲,整个江户时代武士的核心特征,都是由“农兵分离”所产生的。
国内学术界关于“兵农分离”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尚无专著出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多集中于“兵农分离”的过程及意义影响等方面。如李文《德川早期日本兵农分离政策的实施及其历史意义》(《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一文,阐述了“兵农分离”政策实施后的影响与意义,侧重于德川时代。王顺利《论日本封建制第二次转型的原因》(《日本学论坛》1999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日本中世到近世的转变,是就整体封建制进行的研究。赵连泰《太阁检地的历史作用》(《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一文阐述了太阁检地对实现全国统一及“兵农分离”所起的作用。左学德《太阁检地的历史前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检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后两篇论文都以“检地”为研究对象展开讨论。此外在通史及日本古代史的专著中有所涉及,但往往描述多,分析少,因此国内研究整体较为单薄,无论深度与广度都有待继续挖掘。
一般印象中,“兵农分离”是丰臣秀吉在统一全国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中的一项。如家永三郎:“秀吉通过实施太阁检地与刀狩令,武士与农民严格加以区别,所谓的‘兵农分离’实现,大名领主与农民阶级的对立成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构造。”[1]268再如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丰臣政权的历史意义在于确立了近世封建社会的基本构造,作为支配阶级的武士与作为被支配阶级的农民的对立关系基本完成,近世社会关系构成形成。武士在城下集体居住,农民有一块保有耕地种植,原则上身份交换被切断。1591年颁布法令,严禁武士从事町人、百姓工作,严禁百姓放弃农业生产,从事商业活动。武士家臣团内部统治强化,‘兵农分离’完成。”[2]161再如井上清:“秀吉检地后,将耕地与耕作者固定,禁止放弃耕作,离开农村。职业自由被剥夺。另外,土地的买卖与典当被禁止。为维持这一体系,禁止农民武装,执行《刀狩令》……从寺院、百姓、町人处收缴刀、枪、弓、矛及其他一切武器。武士,包括中间、小者及奉公人在内,禁止改变身份成为农民或工商业者,并从村中迁出移居城下居住。这样士农工商的身份、职业、住所从此区分并加以固定。兵农分离制度建立。”[3]248以上是日本史著作中较为通用的关于“兵农分离”的表述。中国的日本史著作中也大多有如此表述,此处不再一一列出。上述以及类似的表述符合历史事实,但往往会引起误解,即“兵农分离”是秀吉建立并实施的。实际情况是“兵农分离”的发生及其延续时间要早于秀吉政权。应仁之乱以后,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兵与农就已经开始分离。兵与农分离是一直伴随着战国大名成长的,并且延续了整个战国时代。武士“脱产”在战国时期,特别是中后期是一种通行作法。丰臣秀吉只是在统一全国后加以强化推广。进入德川时代,家康用法律与制度加以固定,由此造就了兵农完全分离的近世武士形态。本文试图纠正一般描述中的歧义理解并分析其产生的内在历史要求,即“兵农分离”的原因及其内在逻辑,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展开论述。
一、政治原因
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并非是其个人的政治意图与理想愿景,而是一种社会倾向与趋势的因势利导。“兵农分离”的政治原因在于将军衰落,大名成长。大名的成长导致了阶层分化,从属于大名的家臣及脱离农村的“职业武士”开始出现。应仁之乱后的战乱格局加速了社会阶层分化进程。政治格局的另一个特点是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农民斗争加剧,“惣村”*惣村,也写作“总村”,是指村的结合体,非近代意义的自然村。日本中世由地缘而结合的农民自治的共同村落组织形态。镰仓时期,地头控制庄园、公领,农民因为水利分配、道路修筑、边界纷争、战乱及盗贼等原因,出于自卫的目的而加强结合。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逐渐演变为由畿内地区发生的复数结合体的“总乡”、“总庄”并向全国扩展。室町时期,守护权力加强,惣村为确保自治,与守护及国人的结合加强。村中实力者与守护或国人结成主从关系。惣村最兴盛时期是室町中期,应仁之乱时为对敌自救,其自治力达到顶峰。进入战国时代,惣村的自治权被剥夺,最终由秀吉的兵农分离及太阁检地执行而消失,演化为江户时代的自治近世村落。形成,各种地域与类别的“一揆”*“一揆”的本意是一共、一齐、一发的意思,是指农村为减少租贡盘剥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小规模的有一个自然村的共同举事,大的一揆有“山城一揆”、“总国一揆”等跨区域的一国甚至数国的大的暴力武装斗争。不断发生,农民斗争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构成了对统治阶级的威胁,也为统治者打击武装农民势力提供理由。政治纷乱与“一揆”频发是“兵农分离”的重要政治原因。
室町时期走向战国的重要特征就是守护被大名取代。守护并非是“国”*日本旧制的行政单位,起源于律令制形成,后作为领地的支配区与军事警察的管区仍以地域为单位而使用,室町后期以后,国渐渐成为地域或地方的概念而非行政概念,江户时代的行政单位已经划为藩,但国仍然在一定程度使用,直到明治维新废藩置县为止。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因政权形式不同而有所区别,如萨摩藩由大隅、日向及鹿儿岛三国构成。的中间机构,其本身就是整国的支配者(也有守护同时兼任数国),而地头是村的支配者,随着幕府权力的变化两者的矛盾开始产生。“镰仓时代的特征是幕府与地头结合,而室町时代的特征是幕府与守护结合”。室町后期,将军权力减弱,幕府政治混乱、腐败堕落加深,大名主围绕权力的争夺逐渐形成了两派,1467年两派因为将军继位问题在京都开战,“应仁之乱”爆发,以细川胜元为代表的控制24国的16万东部军,对抗以山名宗全为代表的控制20国的9万西部军。持续10年之久的“应仁之乱”的结果是“足利将军家与守护大名共倒”[4]158-159。
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取代守护大名的是地方实力大名,因处于这一时期,也称“战国大名”*战国大名在战国时期的不同阶段,其所指对象也不尽相同。早期一般泛指由小名主或地方实力国人(有官职的在地武士,也称“侍”)、领主成长起来的名主,人数也众多。只有到了战国后期,战国大名才特指一些横跨数国的有实力的大名主。它与守护的区别在于守护是职务的担任者,而大名并非职务,没有法定身份,只是一个社会阶层。。大名是实力派地方领主,大名取代守护是战国的时代特征。各地方大名割据一方,战乱加剧。大名成长主要有两种方式:确保自己的绝对领主权,吞并其他大名,两种方式往往同时进行。因此排除从土地到自己的一切中间力量,重新整顿社会关系,成为大名成长的主要手段。中间力量一般包括公家、寺社势力。这时大名在领国内往往形成“一本支配”或“一体支配”[4]175,即领导力量一元化。传统的层级进献的土地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大名的需要,大名收编地方中等名主与小名主,使其成为家臣,如遇阻力就以武力破除,因此中小名主大量消失。这一过程中土地所有权变得更为简单,其结果即只有大名具有领主权。这种破除层级所属的中小在地领主势力的措施也构成了秀吉检地中“一地一作人”*“一地一作人”指一块耕地只有一个耕作者,即实际耕作者为纳赋交租对象。的基础。村与村之间横向联系被禁止,地侍数量锐减。在地中小领主消失就意味着兵与农分离,或理解为领主与土地的分离。因此,“兵农分离”在战国早期就已经萌发并且伴随了大名的成长。另外大名与大名的兼并战使一些大名更具实力,战国时代是日本少有的战乱时期,坂本太郎曾描述为:“从各国的情况看来,几乎都是旧的领主被新兴的部下所排斥掉,统治阶级像走马灯似的不断变化,主被臣讨,父被子弒,既无道义,亦鲜廉耻,有的只是贪图个人的安逸、富贵的利己心。所依仗的仅仅是压倒敌人的武力和策略。”[5]253“战国”的名称也因此而来,大名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速了“兵农分离”的过程。
日本室町时代,除了体现统治阶级内部混乱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也日益加深,其表现即为“农民一揆”。农民斗争数量多、规模大、时间久、周期频繁。“国人”*也称“国人领主”或“国众”,指与在京的名义上的领主对应的在地的实际领主或名主,一般担任管理职务。、名主层与地域而结合的“惣”出现。其中通过庄家而要求减负年贡及劳役的反抗一般称为“庄家一揆”。为切断守护与庄园领主支配,努力实现自己支配的国人武士、“给人”*战国时代,接受来自大名恩赏的家臣化的在地武士。、地侍领导的对抗斗争被称之为“国人一揆”。以地域为特征的也称“某某国一揆”。农民斗争除了规模大外,还有与宗教结合的特点。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向一揆”即为农民阶层与宗教势力结合的体现。一向宗前身是净土真宗本愿寺派,他们组织僧侣、武士、农民、工商业者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通过武力对抗政府,分别领导了越中一揆,加贺一揆、享禄一揆、畿内一揆、三河一揆等斗争,其中发动于1570~1580年的石山合战,成为史上最大的“一向一揆”。虽然如此,仍然受到织田信长的血腥镇压。1428年在近江国与京都等地出现了农民与市民相联合的一次大抗争,民众聚集要求政府颁布“德政”,遭到拒绝后就抢砸寺院、土仓,袭击酒屋、仓库,破坏烧毁文书、票据。斗争起义者称“私德政”,并颁布德政令,刻碑纪念。农民阶层的自觉意识使其赋予自身合法性、合理性与正义性。统治阶级自然称之为“恶党”,“凡亡国之事不过如此,日本自有国以来,土民蜂起,未有之事也”[1]252。
室町、战国时期是日本农民起义、斗争最多的历史时期,“一揆”是室町,战国时期的重要时代特征。之所以农民斗争会在这一阶段突出的表现出来,其原因就在于领主阶层过多,使得盘剥加重。因此在客观上要求减少领主等级或简化领主权。减少盘剥的层级与减轻赋税比率可以取得同样效果。因此大名打压中小名主、国人、地侍,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领主层,减轻了农民负担。这种简化的最终结果是只有大名与农民两个层级,没有中间领主。大名对农民直接盘剥与控制。“太阁检地”即为满足简化土地领主权的内在要求而推广。另外“农民一揆”频发也与地侍、国人的领导有关。在地武家是统治阶级眼中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将这些在地武士分离出原有阶层及环境成为一种稳定社会的现实需求与解决办法。因此大名成长,收编压制小名主、领主,调整分化农村阶层,是“兵农分离”的内在要求,构成其政治原因。
二、经济原因
室町时代是幕府权力逐渐衰落的时代,在应仁之乱后表现加剧。从经济角度看,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生产力提高导致领主阶层分离,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引起庄园解体,由此对应的社会阶层发生转变,即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成为市民阶层。而武士脱离农村,成为城下町的“职业军人”,构成最早的“人造”市民阶层。所以“兵农分离”既是经济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15世纪前后,日本农业生产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农业用水的“给水”组织不断产生,分水组织分工更趋于专业化。肥料普及效果显著,草木灰、厩肥被广泛使用。农业生产对肥料的重视程度加大导致生产力提高。水稻的种类也经过实践选取,不断改良,形成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种植。从越南地区进口的“大唐米”开始推广。新地开垦逐渐增加,水田外的麦田组织种植增多,燕麦、大麦等不同品种的麦、粟、谷作物成为新的品种加以推广。纤维原料、麻、绢、苧、草棉开始在部分地区种植。作为商品作物的灯油原料荏胡麻,作为涂料用途的漆类原料及消费品类的菜类作物都有不同程度种植,地区经济特征开始呈现。畜类饲养、改良也有进步,陆奥运驹、由斐驹、筑紫牛、周防牛等畜力饲养增多,畜力使用率更为提高,已经成为小农经营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
农业技术革新,生产力提高进一步加快了社会的流通与流动,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开始增多,商业发达成为一种必然。中世活跃的商业城市町开始显示出其蓬勃生机,表现为手工业繁荣,独立专业制作形成。订购商品开始出现,锹、锄、鎌、剑、刀等铸造业发达。市座增多,一些庄园开始的每月3次市场繁荣到每月6次,甚至部分定期市场开始出现[1]233。商业繁荣导致服务于商业的金融、流通、运输、批发等二级市场开始出现。
技术革新、生产发展、流通增加、交换范围扩大在相当程度上侵蚀了原有初级的农本经济,封闭式的庄园逐渐瓦解。庄园瓦解直接导致了武士的分化,庄园内的小武家的独立性逐渐丧失。不同于自然形成的村落,庄园是一种联合势力的结合体,所以庄园解体后,依附于庄园的武士存留即成为问题。中小武士被大名收编,成为大名的家臣,从属于大名。这种家臣收编带有强制性,中小领主、名主、国人虽不情愿却无可奈何,毕竟成为家臣不如自己拥有独立领主权。大名禁止中间私人力量的结合,在实际的领国内有绝对支配地位。虽然大名就是由他们这样的中等名主成长起来的,但到了战国中期以后,这些没有成长的中等级的名主,已经没有机会再成长,因此被实力大名收编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诚然,这些有实力或土地的中等程度领主,即使成为家臣,也有较高的地位与家格,甚至还能担任领国的管理职乃至进入大名的核心管理圈,但是武士“脱产”是不可抗拒的。对于小名主、国人、地侍而言,放弃土地,成为武士,或者留在农村,成为普通的实际耕作者——日语中称之为“百姓”的农民,只能选择其一。一般观念认为成为武士一定好于成为农民,实际上并非如此,确实有一部分小领主因为厌恶做武士或不舍与土地的割裂回到农村居住,成为一名真正的农民。也有一些因为不甘于这两难的选择而逃走的小名主或国人武士,成为浪人。“浪人在这一时期开始增多,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4]179这些脱离户籍及农业生产而靠自身技能生活的人也是早期市民的构成部分。一般而言,成为百姓的居多,毕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土地是立命之本。
松本平八郎认为“日本应仁、文明时期农业生产的提高,手工业发达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即为:名主层从农业及农村中进一步游离,成为完全脱离土地之外的地租收取者。”[6]448以小领主为基础的领主阶层从亲自管理耕作的农业中解放出来,成为城市的食利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使部分农业从业者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这是社会学的一般规律。日本的情况并不例外,只是中小领主进入城市并非自觉自愿,往往是身不由己。大名用武士身份“换取”了他们的“领主”身份。这些地主、地侍相当于被大名“赎买”从而脱离农村迁入城市,虽然并不是自由的地主阶层,也不具备经营自由,但脱离农业生产,迁入城市(城下町)却是事实。中小领主消失后,大名对农民的管制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农民地主、小领主已经“侍化”[4]181,大名收编了农村中的“精英阶层”,这样农民运动就相当于失去了领导者,日本史书表述为“中核丧失”。
中小领主武士“脱产”,独立性丧失是战国时代武士分化的最重要表现。因为这些身份不固定的亦农亦武的小领主是两种社会势力的中间阶层,当社会变革加剧时,中间阶层首先会受到影响。日本战国时代是最混乱无序的时代,其原因之一在于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农业技术进步与生产发展导致了与原有旧体制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节。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导致了庄园的解体,原有的依托于庄园的武士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而“兵农分离”的自然发生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当时的现实问题,即“兵农分离”后的日本政治走向统一,秩序趋于恢复,社会走向稳定,回答了庄园制瓦解而产生的新问题。因此“职业武士”集聚的城下町既是农业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军事原因
武士阶层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除上述政治经济原因外,也有军事变革这一原因。如枪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的战争模式,而新的战争模式对“军人”身份的武士提出更高的职业要求,以往中世纪的大小首领齐上阵的战争形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接近于近代军事战争形式的集团化、制式化不断增多,规模战、阵地战、流动战成为主流,这构成“兵农分离”重要的军事原因。
日本与西方接触最早是在室町时期。西洋人漂洋过海的殖民扩张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给日本社会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同时也改变了日本历史的演进。同时传入日本的器物中,“枪”无疑成为最抢眼的物件。当时被称为“铁炮”的火绳枪在天文11年(1543年)由葡萄牙人船队漂流至种子岛而传入。枪由于其巨大的威力,传入不久即可在本国生产并迅速传遍全国。制铁工业的贸易中心地堺很快就成为枪的中心产地,大名们对枪非常喜爱并很快投入使用。1563年,毛利氏进攻出云尼子氏的白鹿城,毛利氏死伤45人中,被枪击中的就有33人[3]230。此时距第一支枪传入日本才时隔20年,可见日本人学习与运用能力的超长之处。织田信长能统一天下,也是因为他首先较为迅速地建立了独立枪队。无论是对一向宗的打压还是对其他大名的战争,都显示出枪的威力与优势地位。
1575年的长篠合战在日本军事史上有重要意义。首先,新式武器的威力在实战中得到一致认可。战国时期交战的大名并非只有织田信长有枪,然而信长组织的完全独立的枪队却是少见的。枪队规模式的集团排阵打法给其他大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原有追求个人武技,弓矢、长矛、甲胄骑马战逐渐衰退。其次,步兵地位上升。武田军是全日本最杰出的精锐骑兵之一,实际战果表明,即使是精锐骑兵也敌不过以枪队为主力的步兵集团军。武器改变了战斗主体的地位,足轻成为新的战斗力量,由此导致其被大量扩充使用。足轻因为是最下级的武士,向来是不受重视的底层,而由枪的流行发端的足轻群体,对于战国大名而言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足轻的使用为小武士脱离农业生产提供了一种动力与可能,因此实现武士身份的转变更为容易与简单,即拿起枪就可以成为一名武士。冷兵器无法对抗火器,骑术、拥有武技武艺、刀弓箭术的武家逐渐让位。一条兼良称之为“武艺颓衰之世”[7]也是真实写照。兵器的变革导致兵器持有者地位的改变,这也充分体现了由于技术变革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变动。
此外,战斗规模发生改变,阵地规模战、集团战成为主流。集团战是指大名的家臣团全部集合,成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单位执行战斗,而区别于以往独立武家的以个人格斗,被称为“一骑打”的战斗形式。不同兵器、不同服装、不同战旗、不同从属关系的中世“合战”逐渐淘汰。士兵大量聚集,配套统一武器、规模化、制式化成为主流[4]183。以往的战争由主人支配,其所有家臣均需负担费用,大名以下的家臣要自备军械、粮食、服装、补给、个人武具及费用参加战斗,战斗结束后回到村里参加组织生产。这种落后的中世纪的动员机制已经衰落下去,新的战争单位由不同层级的武士转化为同一层级的大名之间的战争。大名为交战单位。以大名为首领的财力保障、动员机制、交通运输等内容成为战争的重要保障。集团战所有的费用均由大名负担,个人已无需负担,因此可以看作个人小武家的解放。
行军的需要也为武士脱产提供了动力。战国时代的战争规模与流动范围已经远超过室町中前期,以往的战争领主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往往只在领地及附近组织发生,武家的纷争也往往以领地为基础,即都是地域性的小范围、短距离的战争。而战国时代是全国走向统一的时代,统一者除解决自己的领地内问题外,还要去远方为统一而战,即“远征战”。家臣武士统一居住、统一训练、统一行动使得小武家成为军队中制式的个体单位,作为中世纪的武家独立性消失。战争级别的升格与军人内在的职业要求使得武士必然朝职业化发展。“常备军”的建立也必然要求武士集中生活。集中的军事区域往往在大名“城”的近侧,“城下町”由此形成。因此,“兵农分离,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开始有序进行。”[3]202新的技术变革为社会变革提出新的要求,阶层分化虽早已进行,但“枪”的使用无疑加速了阶层分化,成为“兵农分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 语
正是由于上述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兵与农才得以分离。诚然,如此重要的社会阶层演进也有文化心理、宗教思想及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但就其主要方面,按照社会学中结构论可以从上述三方面探讨。“兵农分离”是一种适应当时社会情况与社会需要的阶层关系的调整,有其自发性。战国时代的主要问题是中央权力衰退,大名割据一方,阶层混乱,农民斗争加剧等社会矛盾,因此“兵农分离”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进行的阶层调整。“兵”与“农”既可以看作两个职业,也可以看成两种身份,更可以归结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构成传统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如果重要的社会阶层矛盾可以调节,则社会矛盾一定会趋于缓和。诚然,就实际的历史情况看,兵与农不可以看作完全分离,因为秀吉的《刀狩令》执行得也不十分彻底,“百姓中的武器并未全部被缴除,他们也并未彻底解除武装,此后很长时期内百姓仍然拥有刀枪、火绳枪”[8]。此外,农村的地侍也并未完全消除,有一些留在农村,成为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者。但就整体看,“兵”与“农”基本得以分离。应该说“兵农分离”导致的阶层固化是一种走向传统与保守的社会形态,不同阶层间联系被阻断,流动遭禁止。各社会阶层成为独立发展的封闭阶层。但对于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即通过推进“兵农分离”,国家统一,社会重新纳入有序之中。分离后的武士“脱产”,成为寄生阶层,不能扩张成长,失去“独立性”。丰臣秀吉等统治者,从根本上斩断了武士的根基——土地经营(大名除外)。这与中世武士对待农民的“征贡、私法、完全控制”[4]177不可同日而语。武士在历史上第一次被改造,即武士“脱产”,并为明治维新时废除武士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日] 家永三郎,黑羽清隆.新讲日本史[M].东京:三省堂,1976.
[2] [日]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Ⅰ[M].东京:岩波书店,1963.
[3] [日]井上清.日本的历史[M].东京:岩波新书,1965.
[4] [日]中村吉治.武家与社会[M].东京:培风馆,1948.
[5]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日]松本新八郎.中世社会的研究[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6.
[7] [日]铃木良一.应仁之乱[M].东京:岩波新书,1973:95.
[8] [日]网野善彦.日本社会的历史[M].刘军,饶雪梅,译.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