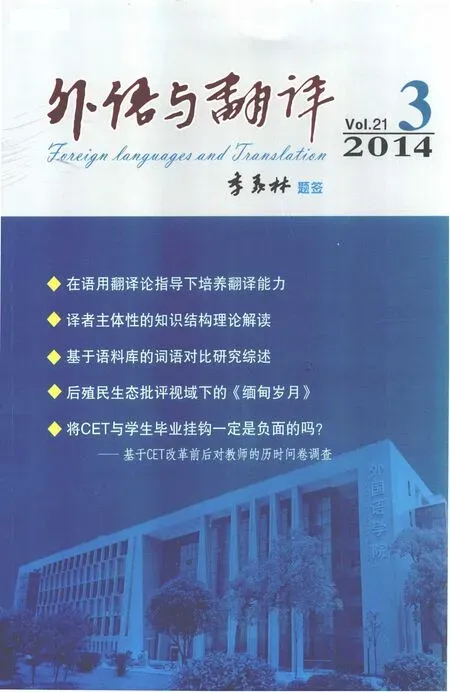从“一般杂志”到“青年界之明星”——论《新青年》之成功
(烟台职业学院公共管理系,山东烟台,2646702;山东工商学院政法学院,山东烟台,264000)
一、初创——举步维艰
1913年,陈独秀亡命上海,他无事时常常到他的安徽老乡汪孟邹开办的亚东图书馆去, “他(陈独秀)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因为汪孟邹“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便是日后的《新青年》。1915年9月,《新青年》正式创刊,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之初的《新青年》并没有突出的特色,也难以获得社会与思想界的关注[1]。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论》评价早期的《新青年》“只是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
创办之初的《新青年》不为社会所关注,首先在于《新青年》定位的偏差。虽然陈独秀的理想是把《新青年》打造成一份在思想界有影响的杂志,但实际情况却与编者的想法大相径庭。读者大多认为它与其他教育杂志一样,不过是一份“以青年教育为目的”的杂志而已。如第1卷第1号的“通信”栏目就刊登了署名“章文治”的读者来信,询问“沪上学校如林,何者最优”。而第2号则刊登了署名“李平敬”与“王珏”的读者来信,前者询问有关上海法文学校的情况,后者则因为学费昂贵,只能放弃学业,准备自学中文、洋文及算学,写信的目的即是请《新青年》编辑指导。第3号中署名“吴勤”的读者希望学习西方逻辑之学,但由于西文水平太低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而坊间相关著作良莠不齐,于是就向《新青年》编辑来信讨教,希望予以指点。
其次是缺乏知名的撰稿人。陈独秀标榜“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但是检视第一卷的文章作者,高一涵、易白沙、李亦民、汪叔潜、高语罕、刘叔雅、薛琪瑛、潘赞化、汝非、萧汝霖等在民国初年与“一时名彦”还有很大差距。如高一涵,《新青年》创办之时他正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1918年才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而到了1924年,高一涵还因为商务印书馆只知敷衍名人,自己没有大名气受到商务的薄待而不满。当然,杂志并不需要所有作者都是名家,通常主要作者中有一二位声名显赫者即可。例如梁启超之于《时务报》,章士钊之于《甲寅》。而作为《新青年》“主撰”的陈独秀,在民国初年的知名度其实也不可高估。1915年10月16日,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在给胡适的信中介绍《新青年》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汪孟邹)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写,与秋桐(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可见,此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对于陈独秀此人也并不知晓。
《新青年》命运转变,实得益于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2]。1917年1月,作为杂志主编的陈独秀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这座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这一任命不但为《新青年》做了无形广告,同时也为《新青年》作者队伍扩充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如第二卷的作者中新增加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杨昌济、马君武、苏曼殊、吴虞、吴稚晖等人;第三卷新增加章士钊、钱玄同、蔡元培、恽代英、毛泽东、常乃德、凌霜等人;第四卷的新作者主要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鲁迅、林损、王星拱、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林玉堂等人。新作者,特别是一批北大教授的加入不仅使《新青年》拥有了更为稳定和丰富的稿源,而这些学界名人无疑又为《新青年》的招牌增添了许多亮色与光环,毕竟名人对于青年读者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1918年就有一位年轻的读者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表达对《新青年》编者们的无限景仰和崇拜之情:“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
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的境遇就立马改观,直到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的“双簧戏”触动了林纾的神经。林纾先后在上海《新申报》发表《荆生》《妖梦》等小说攻击《新青年》同仁,而且还在北京《公言报》刊登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新青年》。面对林纾的指责,蔡元培随即撰文回应。作为当时文化界的名流,林、蔡二人之间的辩驳迅速成为各大报刊的焦点内容。正是在媒体的关注和炒作下,《新青年》为更多人所知晓。
二、发展、成熟——脱胎换骨
日后《新青年》逐渐畅销,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万五六千份,这在民国出版界堪称奇迹。其成功原因除了前述因素外,还有几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一)刊物的命名
《新青年》以“青年”作为刊物名称,应该是经过多方面考量的。从词源学上说,“青年”一词并非古已有之,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的新名词。而且经过仔细追索我们发现,在20世纪初以“青年”命名的报刊基本上是由基督教青年会主办,除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主办《青年》《上海青年》外,还有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会报》(1901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的《广州青年》(1909年)。而国人创办的以青年读者为阅读对象的刊物则多以“童子”“少年”命名,著名者如 1903年由革命派在上海创刊的的《童子世界》和 1911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可见陈独秀取“青年”而不是“童子”“少年”,颇有借重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刊物市场影响的意图[3]。
(二)议题的选择
在《新青年》编辑的精心选择和策划下,一些讨论议题最终超越了媒介层面,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得到更加热烈的回应与讨论。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即是一个典型例子。《新青年》讨论妇女问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5年9月创刊起到1916年12月,是为探讨妇女问题的发生期,卷号从第1卷第l号到第2卷第4号;第二阶段从1917年起到1918年底,是为探讨妇女问题的发展期,卷号从第2卷第5号至第5卷第6号;第三阶段从1919年始至1921年9月,是为探讨妇女问题的深入期,卷号从第6卷第1号至第9卷第5号。在这期间,特别是“易卜生专号”的推出,更是引发社会各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如《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都紧随《新青年》之后,纷纷翻译介绍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或者开辟“妇女专号”,就妇女解放、恋爱婚姻自由、离婚、贞操、废娼等道德问题展开讨论。妇女解放这一话题逐渐从媒体的焦点转而变为社会焦点,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三)与读者交流
早在创刊之初,《新青年》就着重声明:“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4]而且自第2卷第1号起又“新开‘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新青年》“通信”栏目每次刊登读者来信多则8、9封,少至2、3封,最多的一期刊载读者来信多达25封。经研究者统计,《新青年》办刊过程中一共刊发通信、议论约360余封(篇),以7年计,每年6号算,平均每号有读者来信、议论约4封(篇)。而“通信”“读者论坛”两栏目的篇幅在整本杂志中常常占到1/4甚至1/3。对于《新青年》开辟的“通信”栏目,读者无疑是很欢迎的。如有青年读者就反馈“通信一门,尤足使仆心动。因仆对于耳目所接触之事物,每多怀疑莫决。师友中亦问有不能答其质问者。今贵杂志居然设此一门,可谓投合人心应时之务”。更有读者宣称“见贵刊有通询答问一栏不竞雀跃”,言语虽显夸张但对“通信”“读者论坛”栏目的喜爱可见一斑。
(四)勇于创新
《新青年》创新之处颇多,最主要者当属用白话文办报。虽然早在晚清时期用白话文办报办刊就已出现,但主流报刊一直还是用文言文。直到《新青年》创办后,白话文办刊才为其它主流刊物所采用。其次如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古代书籍不标点短句,近代中国的报刊最初也不分段落,后来一些大型报刊稍有改进,发展为行右圈点,而白话报则在末尾空一格的方式以示句读。这种方式不便于阅读,同时也不便排版。《新青年》采纳了钱玄同的意见,在第4卷第1号中采用一整套新式的标点符号。随着《新青年》影响力的扩大,新式标点符号也逐渐为各种报刊部分采用,成为报刊编辑界的标准。
三、结论
《新青年》创刊之初命运多舛并不被社会所关注。
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扩充作者队伍,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均出现在作者名单中,这些名人对青年读者的影响力非同凡响。与此同时,作为当时文化界的名流的林纾、蔡元培二人之间关于《新青年》的辩驳成为各大报刊争相报道的焦点内容,在这一背景下,《新青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随后《新青年》又在刊物命名、议题选择、与读者交流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其销量猛增,堪称民国出版界之奇迹。
综上所述,《新青年》从最初创刊的举步维艰到后来的发展壮大完成了“一般杂志”到“青年界之星”的华丽变身,其经过的坎坷历程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仅此从出版史研究角度做些粗略的探讨。
[1]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J].近代史研究,2007(1):21-40.
[2]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4]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以基督教青年会档案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