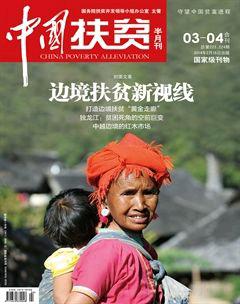苑鹏:现代农民合作社可以管办分离
陈雪
近年来,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农村商业的主渠道,虽然几经变革,但始终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组织商品流通,联结城乡、工农,沟通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农村生产与生活、生产与需要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以及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否发生变异?目前主要有哪些类型?对“三农”带来哪些新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发所研究员苑鹏。
合作社领办人的多样化
《中国扶贫》:现代农民合作组织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苑鹏:近年来,合作社的主流形态呈现所有者和业务相关者同一的特征,成员关系也有了从联合行动的有机体变为非零和博弈的业务相关者联盟。相应地,合作社内部治理也由民主控制走向大股东控制;合作社领办人则由自利的农村精英取代具有合作精神的企业家;合作文化由互助走向互惠。
《中国扶贫》:现阶段农民合作社的类型有哪些?
苑鹏:现阶段,合作社的种类还是比较混乱的。从合作社的成员来讲,成员构成不再局限于具有相同市场地位、从事相同生产经营活动的同业生产者的联合,而是在此基础上,还允许那些处在同一农产品产业链条上具有上游、下游业务关联的相关利益群体共同联合,组成合作社。即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是农产品经营者的同质者的组织,也是服务利用者和服务提供者共同组成的异质者的组织,这些都反映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工商注册登记中。从我这些年对合作社的调研发现,合作社“登记注册类型”一栏涵盖了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个人合伙、私营合伙企业、社团组织以及其他企业(或组织)等多种类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质性特征及变异问题,包括产权制度、内部治理、所有者责任制度,等等。
从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出发,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所有者成员构成的特点,可以划分为以下两大基本类型:作为合作社利用者的农民生产者组成的合作社、农民生产者和作为合作社业务服务提供者的非农产品生产者共同组成的合作社。前者是符合经典合作社理念、与国际接轨的农民合作社;后者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社,因为它与国际主流农业合作社的成员制度安排不同,非农业生产者可以成为正式的成员,从而具有明显的中国印记。
在中国农村,大量存在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是第二类合作社。这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合作社类型,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发起人不是农业生产经营者,而是与之有着紧密的业务联系,为其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多个环节或单环节服务的服务提供者;或者虽然发起人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他们同时也从事农产品经营活动,并且以后者为主,在合作社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农产品生产者的服务供应商。
《中国扶贫》:您所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社有什么特点?
苑鹏:由合作社服务的提供者领办合作社,按照领办人的身份,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组成的合作社。通常是在“公司+农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新模式,通过合作社的产权纽带,不仅可以强化公司与农户的联结机制,而且可以获得更多政府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资源。
这类公司领办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农产品原料对于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并且通过简单的市场交易无法获取或获取成本较高。这类公司领办合作社的基本特征是:公司以合作社的组织方式建立起公司与农户纵向供应的长期合约,实质上,这种模式是“公司+农户”制度的完善,公司和农户的关系本质上是劳务外包关系。农户在合作社中蜕变为可以获得稳定预期收入的公司“打工仔”,而非合作社的所有者。但是,与个人经营相比,农户的经济收益增加,因此,他们愿意加入合作社。
第二类是商人与农户组成的合作社。这类商人以小微企业为主体,经营规模不大,资本实力有限,处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的成长期,在扩大经营的过程中面临激烈的同业竞争,通过带领农民发展合作社,可以培植出一个稳定的客户群体,稳固并扩大自己的经营业务量。
合作社对于商人而言,本质上是其经营业务扩张或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是市场营销战略的应用。而对农户而言,他们也需要这样一个社会化的服务载体,这是因为现代农业的复杂性使得个体农户既无精力、也无能力关注购销活动,作为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户,其购销经验明显少于生产经验,如果让农户自我从事生产经营中的购销活动,他们只能任凭市场宰割、随行就市。如果有服务商在为农户提供农资、技术的同时,还能够帮助他们销售农产品;或者在销售农产品的同时,还能够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农资服务,那么,这种行为不仅能够全面满足农户生产经营的需求,降低农户的生产经营成本,帮助他们规避风险,保障其经营收益,而且也能够为服务商自身带来潜在的市场发展空间,助其实现销售增值和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张。
第三类是投资商与农户组成的合作社。近年来,“投资农业”日益成为金融资本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与其他非农产业相比,农业产业具有天然的弱质性,自然风险不可控制、市场风险变幻莫测,这些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食品安全风险,更加剧了农业的不确定性。投资商为了获取土地资源,获取政府的扶持资金,通过实现农地经营的非农化或非粮化以实现投资利润的最大化。
在产业定位上,他们的瞄准点通常不是农业第一产业,而是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旅游观光、休闲农业等第三产业,这一点在投资者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也反映了出来。于是,他们借助合作社的平台组织农户发展股份合作社,农户以其承包经营的土地入股,投资者以现金等入股,同时承诺入股农户优先获得合作社的就业机会或高于市场价的产品收购权,并保证不低于农户自我经营时的土地租金。通过合作社载体,解决了投资者有资本没资源、农户有资源却无法以市场化的资本定价的问题。
第四类是社区领袖带领农户组建的合作社。社区政治领袖以村书记、村长为代表,他们通过合作社发展,巩固自己在村社中的政治地位,并为自己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发展合作社时,他们更多地是从全村的产业发展出发,从让更大范围的村民受益出发。这类合作社发展有着非常好的制度环境。
可以说不论哪种形式的合作社,都实现了领办人和农户的改进。从农户的角度看,他们解决了家庭经营无法或难以克服的制度缺陷,例如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等等,这也是当前中国各类农民合作社生命力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扶贫》:由非农民生产者领办的合作社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苑鹏:由非农民生产者领办的各类合作社产生的一个共性问题是:他们的出现使得小农发展自我合作社的机会更小。这是因为无论从自身的风险态度、创新精神、资本实力、技术、经营管理才能、捕捉市场机会的嗅觉等方面,还是从外部的社会资本网络资源方面,小农都无法与他们相比,他们具有或掌握了小农缺乏的、市场竞争所必需的各种稀缺性资源。在当今农产品市场竞争白热化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小农成为合作社企业家的可能性日趋渺茫,意味着农民生产者自我组成的同质性的经典合作社的发展前景黯淡。
农民合作社的“中国变异”
《中国扶贫》:您之前一直在著作中提出合作社制度安排变异理论,能解释一下中国农民合作社制度安排变异体现在哪吗?
苑鹏:合作社制度中国之前是没有的,这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自上世纪初引入中国以来,合作社在中国的发展始终面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尴尬局面。而随着成员构成从同质成员转化为农产品供应链上的相关利益群体,合作社制度的安排由此产生了种种变异。
首先,在成员关系上,从联合集体行动的有机体走向非零和博弈的联盟。也就是从过去合作之前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最优结果的你赢我输、你输我赢的竞争关系,通过合作社长期多次重复博弈,走向团体理性,强调效率、公平、公正,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其次,在内部治理上,决策权安排由民主控制走向大股东控制。民主控制一直是合作社最核心的原则,然而,因为中国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基础不是成员共同体而是业务相关者的群体,这就动摇了民主的根基,民主原则不复存在成为必然的结果。由于合作社的大股东承担了合作社的经营风险,相应地,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自然也会落入大股东手中。
第三,在合作社企业家主流群体构成上,自利的精英分子取代具有合作精神的企业家。农户是这些精英分子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帮扶的对象。
中国农民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合作,是个体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非处于个体地位的弱势群体的共同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合作,而非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合作。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不只是建立在互惠制度基础上的,更是经济学意义上通力协作的合作,是相关利益群体联盟,因此呈现出有利则来,无利则走的表现。而不再是合作社制度所特指的建立在超越个人的,一致性的共同理念和信仰基础上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