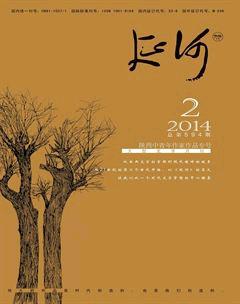目击者
吕虎平
陕西作家协会会员、西安作家协会理事、长安作协副主席、西安市首批签约作家。获首届《手稿》散文奖、《十月》《延安文学》联合征文散文奖、全国散文论坛征文二等奖等十余项散文奖。出版散文集《棉花》《吹进院墙的风》《散碎阳光》《篇十二》,诗集《镜与像》,长篇小说《单面人》等。作品收入《2010年中国散文年选》《稻草人的信仰》《九十九极》《九作家散文选》《中国散文名家散文精选》《我的恋爱》等选本。
一 车祸
“吱嘎”一声,像是天空被撕裂一般,刺破黎明前的黑暗。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准备都没有,这也许是小说的开篇方式,带有悬念性。的确,这“吱嘎”的声音,刺人耳鼓,让人心悸。就在我还未回过神来,那“吱嘎”声扯着旋弧,向来时的方向,啸叫着跑远。我本能的判断,这是肇事逃逸。我正好在拐弯处,茂密的道边榕树遮挡了视线,但我还是凭经验,判断出这样的可能。我加快了骑车速度,看到了一辆黑色宝马,呼啸着继续逃跑。但我还是看到车牌号:川M.BXX38,XX是我没能确定的两个号码,是两个相似的号码,在黎明前的路灯光下,一晃而过。我对数字有着天然的敏感,我瞬间看到的数字,印刻在我的脑海。
我回头看到,道边躺着一个红衣女子,头发蓬乱,电动车被撞得变了形,与躺在地上的她有七八米远的距离。她试图爬起来,但做了多次努力,还是没有爬起来。一片殷虹的血,像一朵盛开的玫瑰,带刺的玫瑰,向四周洇开。周末,我有早起晨练的习惯。穿过这个叫长乐的小区,就到了自行车健康绿道。我再次加快了速度,希望能追上肇事车,看个究竟,但那辆黑色的宝马就像发狂的野马,抛下一路尘烟,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几天后,在拐弯处的电线杆旁,一位憔悴的老妇人,带着一个瘦弱的女孩低头跪在地上,前面铺着一张纸,用极为清秀的正楷写着:寻找目击者。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那么早,除了我,还能有目击者吗?若真的有那么一个,能凑巧记得车牌和车型吗?这是一个城中村改造的小区。小区在郊外,很早的时候叫长乐村,这里是郊外一处繁华地带,因为两所大学带动了这里的人气。商场林立,人头攒动。这个时候商场已经关门了,黑灯瞎火。我从来没碰上过这种事情,我甚至认为这种事情是真的,没准儿是睡梦中的幻想。但我的叙述不得不回到正题上来,车祸是实实在在发生了,肇事车实实在在逃逸了。婆孙俩凄然地跪在地上,希望好心的路人能帮到她们。小区做生意的人很多,两三点还有穿梭走动的年轻人,在酒吧里谋生的小姐,她们花枝招展,浓妆艳抹。而车祸发生的时间,正是小区睡眠的时间,会有人偏巧站在旁边吗?我当时风一般骑过车祸现场,没有看到任何人影,谁还能帮助这对无助的婆孙?
最近,我持续不断地有幻听。听见很遥远的地方传来水滴声,最寂寞的深夜里,有某户人家的水龙头没有关紧,滴滴答答,或许是我家。许多次的经验却告诉我,起身去看,并没有。一个人睡着以后的呼吸声,离我非常近,就像在耳边,或者是火车开来的声响,沉重而浑浊。呼吸声似乎遮蔽住远处墙角耗子咬噬某物发出的咯吱声,窸窸窣窣,怯头怯脑。我本来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这时突然被这无来由的声音惊醒了。开了灯,才知道自己就在家中,岑寂无声的夜,覆盖了整个苍穹。我试图让自己再进入睡梦中,但睡意就像被惊散的鸟雀,倏忽而去,再不回来。我起床冲澡,但不想骑车锻炼,那一幕总是出现在我的梦中,搅扰得我难以入睡。幻听,失眠,臆想,脑海里不能安宁。我怕去长乐小区,惧怕看到那对婆孙凄然而无助的眼神。我打算坐公车去高升桥,那里有一座比较大的书店,在书店消磨时间,也是不错的选择。到了公交站,站上已有许多人。一对年轻男女微笑着,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他们用耳语方式,大声交流着,一看就是甜蜜爱巢中的恋人。一个老太太慢悠悠地对另一个老太太说,听说医院的门诊费又涨了。另一个没接她的话茬儿,只说,前天对面那里发生了车祸,好惨。于是,她们热烈地开始讨论起车祸来,讨论起一个老妇人和小女孩举着牌子,站在马路边,寻找目击证人。幻觉,还是真实,为什么那次车祸总是缠绕着我,阴魂不散。
二 新闻
我很少看报纸和电视新闻,那些胡诌的、加工后的新闻,到底有多少真实。来到成都后,这个城市的大小事情与我无关。市里的报纸和电视台,晚间新闻播报完领导的工作会议行程后,有时也报一些与市民有关的新闻,但我还没有融入这座城市,我还没把自己当作成都的一个市民。近日,我早晨第一个任务就是百度成都肇事新闻;到了单位,翻看报纸,寻找与长乐小区肇事逃逸有关的案子;打开电视看主持人一口嗲嗲的四川话,说一些跑街的鸡毛蒜皮事。我希望哪天打开电视,看到肇事司机被抓,翻开报纸,看到肇事司机被铐的大图片,这样,也许才能让我内心少一些愧疚。
这个社会复杂到人心不古,世事难料。我不愿去报案,总怕与我扯上干系。首先,警察会一脸狐疑地问我:那么早,你到长乐小区干什么?你是看到了肇事车,还是听人说的?天那么黑,你怎么看到的车牌号?你确信你对数字顺序没记错?这些问题,似乎将肇事逃逸直接指向我。现实中,多少好人被冤枉,结果还要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抚慰费。而好人呢?江苏的那个案子,至今在人们心里,还有深深的阴影,那么,他的精神抚慰费由谁承担?我曾坐公交车,有一小偷扒窃了一女士的钱包。一小伙子出手制止,反遭窃贼同伙殴打,满车人没有出拳相助,甚至连那个女士都到了车站迅速下车走了。司机只是大声喊:不要打架,要打架下车去。几个小偷更是气焰嚣张,抓住小伙子,拉下车,一顿狠揍,周边不知情的人,把小伙子误以为小偷,也用脚踹,骂他,吐痰给他。另外,如果我报案了,果真司机被抓,判他三年五年,出来后,他会不会找我事?我一个外地人,客居成都,这些麻烦事我不敢想象。我越想越觉得后怕,还是不要多事,自己给自己找事了。
成都日报:肇事逃逸一年多终自首,看守所里直言“再也不开车” 。X月25日13时30分,彭某开着老板的绿色大货车,在荆竹西路与青冈北路交叉路口下车买完东西后,刚发动油门倒车,惊呼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快停车,你碾到人了!”与长乐小区无关。
成都商报: x月x日晚,宜宾城区雷雨交加。翠屏区与宜宾县交界处的翠柏大道皖宜小区路段发生一起离奇车祸:一辆摩托车将行人撞倒后,紧随其后的一辆轿车碾压倒地的行人和摩托车驾驶员一并逃逸,同向驶来的越野车又撞上摩托车,就在越野车驾驶员准备下车察看时又遭追尾。宜宾警方出动30余警力,全力缉拿肇事逃逸车。还是与长乐小区肇事逃逸案无关……
华西都市报:放寒假了同学聚会,不料换来的却是永别。X月X日凌晨1点过,攀枝花市人民街华府6号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两名在校大学生被一辆皮卡车撞倒,一死一伤,肇事司机驾车逃逸。昨天,记者从攀枝花交警支队获悉,肇事司机朱某已被刑拘。还是与长乐小区肇事逃逸无关。
其实,媒体不是什么都关注。现代媒体已经基本上商业化了,喉舌的功能不断弱化。媒体需要生存,它需要新闻眼,需要噱头,需要能引起受众关注的点。能引起受众关注的方式,一种需要媒体引导,还有一种是幕后推手。当人们的审美疲劳之时,幕后推手看到这一点,于是,芙蓉姐、石榴哥和凤姐这些活宝便应运而生。而真正关注民生,报道民生之痛感的新闻寥寥无几。我有一朋友,他父亲在建筑工地三楼脚手架摔下,正好下面是沙堆,人命保了下来,但却摔断脊柱,瘫在病床上。承包商起初还给送来医药费,后来干脆就不见人影。朋友和家属到处找也找不到,报了案,警察也双手一摊,说是他们也没法找到人啊。是啊,警察事情多着呐,怎么会为你的区区小事,动用大量警力,寻找一个无足轻重的包工头。我曾去医院看望老人,老人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蜡黄的脸没有一点血色。唯有活动的嘴巴和眼睛,告诉我们,他还有生命气息。
朋友的生活极度困苦,父亲的医药费已成最大的负累。朋友是个孝子,到处借债,他不能停止对父亲的治疗。我说,能不能向社会伸出援手。他说,谁能帮我啊。我说,让媒体呼吁呼吁,也许有效果。朋友眼光暗淡,没有一丝激情。他说,找过媒体了,没人愿意写。我说,我也许能帮上忙。我走到医院楼道,给几个媒体的朋友打电话,说明了情况,我对事件本身做了极度渲染,并表示:来吧,我给车马费。朋友骂我,说是什么事情都收车马费吗?后来,几家媒体做了报道,社会上也捐了钱,捐了药,最终也没能挽回朋友父亲的生命。
三 破烂王
那男人围着垃圾场翻拣着,腐败的气息在周身飘荡,风聚风散,那腐败气息却像发酵的酒,挥不去。凌乱的塑料袋,五颜六色,像一堆随处丢弃的残破的衣裳。几个妇人叽叽喳喳地来了,她们手里拿着一个木棍,棍子带两个弯钩的铁丝,像是缺角的鸡爪。她们迅速翻捡着,刨拾着,男人一边刨,一边和女人搭着话,三五不接的话,有一搭没一搭。
一个女人说到了长乐小区的车祸,男人顿了一顿,没再接话。一个女人突然问男人,你看到那天的车祸了吗?男人还是没接话。女人没有注意到男人的反应,继续问,老朱啊,那里不是你的地段吗?你看到了没?男人说没有,收起搭钩仓促走了。几个女人就说老朱这是怎么了?平时话那么多,今儿个蔫驴一样。老朱是个罗锅,还有点瘸。据说,村子有两家为宅基地大打出手,一家强势,一家弱势。老朱替弱势人家说了句公道话,晚上就被强势一家打个半死,去乡政府告,只是得到了一些治疗费,而老朱成了终身残疾。老朱走路时,一瘸一拐,右边肩膀高,像扛了一袋子面,左边肩膀低,左手总像提了重物,压得他抬不起来。从此,老朱总怕事,有事他躲着,有热闹他也不凑。几个女人就说,他肯定看到了车祸,不然,他慌啥子啊。
第二日,警察敲开老朱的门。说是门,其实就是两根木棍,撑着一块废旧的木板。老朱是从乡下来的破烂王,他利用街角的一处废弃的报刊亭作为自己的居所,我时常去长乐小区菜场买菜,经过那里。老朱在活动房内支了一块木板当床,平日捡拾的垃圾堆在角落,差不多了,他就送去回收站,换回几个钱。有人说,老朱有钱,老朱有几张银行卡呢。还有人说,有一次老朱捡到一件旧衣服,里面裹了一万元现金呢。最后越说越多,我最后听到的版本是,老朱捡了十万元钱。
老朱有一个三岁的男孩子,夏天的时候,孩子鼻涕邋遢,光着身子,身上的污垢和着汗水,滴答着,像是灰色的蚯蚓,在男孩的身上滚动,流淌。警察敲开门,屋内的光线昏暗,他只能借助手机照明,看清屋内的一切。老朱正在用一个煤炉煮饭,孩子躺在木板床上,看到来人,有些木呆。警察问,街对面前天早晨的车祸你看到了吗?
没有。
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没有。
不可能嘛!
真的没有。
警察没有办法,他总不能撬开老朱的嘴巴,让老朱承认他看到了一切。警察没有逗留,屋内酸腐的气息,让他憋闷。关于老朱和女人聊天,还有警察敲开他家门所说的一切,都是我合理的推测和虚构,但基本事实存在。如果老朱告诉了警察,他看到的一切,那个孱弱的老妇人和小女孩就不会依然举着牌子,跪在街对面,寻找目击证人了。
责任编辑: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