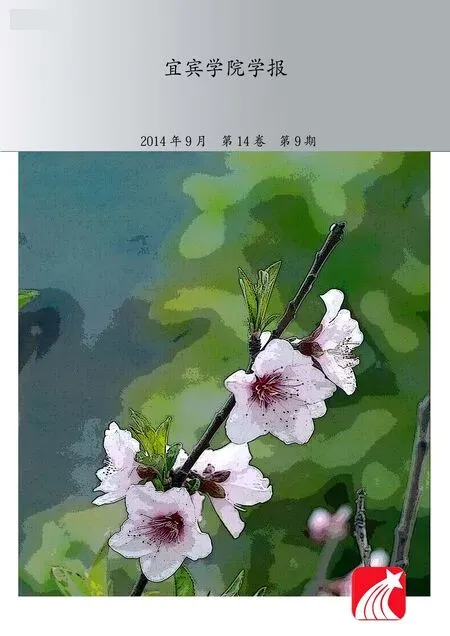一部女性主义元小说
——论《使女的故事》的叙述特质
代 倩
(河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今享有国际声望的加拿大女作家,1985年,阿特伍德出版了她最为知名的小说之一《使女的故事》。这部小说以口述的方式讲述了使女奥芙弗蕾德在极其压抑的集权体制下所遭受的压迫和统治。奥芙弗蕾德处在监管严密,眼目无处不在,随时会被告发的高压政权统治之下,一个随时会威胁到她的肉体与精神的一个陌生环境中,但她始终坚信只有将自己置身于所处的文化之外才可以得以生存,她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把她所经历的、属于她的故事记录并流传下来,让人们知道在这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 语言与叙述
《使女的故事》确立了阿特伍德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阿特伍德先前和之后的小说大多以当代加拿大为背景,而《使女的故事》却截然不同。故事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在一场大清洗后,原美国政府被信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分子多取代,成立了宗教神权统治的基列共和国。女人一方面被美化为人类未来的希望,另一方面却又被分化、统治、角色分工、由生育能力决定命运。宗教化的语言掩盖了真实思想,没有言论自由,思想似乎成了限量配给的东西,人们禁止接触文字。女人们身份地位各有不同,夫人、嬷嬷、使女/生育者、女仆、经济妇等,她们各自穿着和自己身份相匹配的规定服装;她们被要求举止得体、符合身份,她们的自由被限制,所有女人甚至男人的活动都服务于生殖这一中心目标。
故事是由奥芙弗蕾德讲述的,她是一名使女,如同一部毫无感情的生育机器,她的使命就是给一位具有军事权力从而可以统治基列共和国的大主教繁衍子嗣。奥芙弗蕾德本应该保持缄默,保留文字在基列也是绝对禁止的,但讲述的欲望让她设法把自己的故事保存了下来,以录音的方式留给了读者。故事分别在三个主要历史节点,一是第二次女权运动时期,当时奥芙弗蕾德尚年幼,而她的母亲则积极参与其中;第二则是在大清洗后的基列时期,奥芙弗蕾德主要的人生经历就在这一时期,这也是小说的主要部分;第三个在2195年,奥芙弗蕾德的磁带和个人物品被发现,并被皮艾索托教授为首的史学家们进行仔细的学术研究,这一事实也佐证了男性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控制。这部小说生动刻画了原教旨主义政权的毁灭性本质及其对语言的控制。奥芙弗蕾德的叙述可以使我们洞悉她的时代里的各种问题,同时也揭示了叙述和个人自我的力量。[1]95
在使女所处的环境中,她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用一种有限的、具有宗教寓意的话语来进行交流,这种方式很好地体现了语言、权力和性之间的关系。米歇尔·福柯在他的著作《性史》中对类似基列社会中的诸多关系进行了研究。福柯把语言同权力、监管和性联系起来,指出语言和权力既可以使一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的自我和性欲望同时也可以压制它们。而在监狱和惩罚大行其道的基列,有的恐怕就只是压制了。如果有人说了不利于政府的话或者在交谈中作出了错误的语言反应,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被陷害、举报,甚至会面临监禁和死亡。是否拥有话语权完全取决于身份。就像使女的名字不是表明她们是谁,而是她们属于谁,她们所处的地位一样,这些所谓的分类通过把他或者她降格到其所属的类别中而消减个体的作用。奥弗蕾德在思索失去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对自己说这没什么大不了,名字如同电话号码,只对别人有用;但我的想法错了,名字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于是,我把那个名字珍藏起来,像宝贝一般,只待有朝一日有机会将其挖出,使之重见天日”[2]97。在基列,也通过命名来排除异己。对两性关系持不同意见者,如女权主义者被称为“坏女人”,很多有出生缺陷的婴儿被称为“非婴儿”,然后被理所应当地处理掉。通过种族和宗教来给人贴上标签,从而排除异己。因为基列是一个宗教原教旨主义政权,这种贴标签的行为源于圣经,如犹太人被称为“雅各的儿子”,黑人则被称为“含的后人”①。思想是要掩盖起来,不能道于外人的。个人见面或者其他场合下都有标准而教条的具有宗教含义和美好愿望的问好方式,那些不按正确方式问好的人则可能被人怀疑不忠。基列的礼制中有各种迫害方式,称为“大清洗”,并且被冠以不同名目,比如“秘密处决”“挽救仪式”“参与处决”等。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语言变成了代码,思想被监控,所有的性自由也都消失了。
在基列,教育也成为了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嬷嬷们教导女人们如何默默地顺从;哈佛大学则变成了镇压之地,它的建筑变成了基列的秘密警察(眼目)的拘留所。大处决就发生在哈佛校园里,就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大学的围墙上挂着持不同政见者被处决后的尸体”[2] 35。帕伦博指出:哈佛已经成为基列所建立的一个扭曲世界的象征,一个本为追求知识和真理之所变成了压迫、折磨、否认大学所应坚持的任何原则的地方[3]。阿特伍德向我们展示了语言是如何扭曲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揭示出一个政权如何把男人女人们变成一个个具有毁灭性心态的沉默个体。
二 元小说与元历史
《使女的故事》的元小说特征体现在奥芙弗蕾德叙述时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通过对自己构架方式的批评,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所叙述作品的基本结构,而且也探索了文学作品文本之外的世界可能的虚构性”。[4]一方面,故事似乎是真实的,叙述者从不承认故事的虚构性,似乎整个世界都包裹进故事中了。与此同时,奥芙弗蕾德的讲述实际上隐含着对往昔的回忆,这一点从小说的后记可以体现出来。而后记同时又是小说整体框架的一部分,它使读者离开目前奥芙弗蕾德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故事,再次专注于她只是文本的一部分。
后记把奥芙弗蕾德和她的经历都历史化了。当读者觉得基列的方方面面都完全陌生时,它与某一熟悉的时代和文化的接近又让读者警醒。奥芙弗蕾德的叙述是从红色感化中心非常普通的场景开始的:我们的寝室原本是学校体操馆。那里从前曾举行过比赛,为此,光亮可鉴的木板地上到处画着直的和圆的线条[2]3。过去近得几乎可以触摸。“我想我仍可以隐隐约约,如某种残留影像一般,闻到一股刺鼻的汗味、混杂着口香糖的甜味和观看比赛的女生用的香水味。”[1]3接下来是一连串不断变化的中学流行服饰,“先是电影上才能见到的穿呢裙的女生,然后是穿超短裙的,接着是穿裤子的,再后来就是只戴一只耳环、剪刺猬头并染成绿色的”[1]3。这些描述都会使读者想象曾经熟悉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什么样子的,但小说却呈现出了另一个历史走向。因此,读者会尴尬地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自己所处的年代,成了2195年基列研究大会上学术审议和历史争论的焦点,那些专家学者们在解构1985年的历史和文化。
这种从生活体验到文献历史的跳转无疑会产生一种空间,在这段空间中,文本往往试图但是却无法重建事件本身。[5]当奥芙弗蕾德意识到了所留文字与具体事件之间的距离感,她的故事就具有元小说的特征。当躺在床上,回忆白天的事情时,她想:等我逃离这里,假如我有条件把这些事记下来,不管用什么方式,哪怕是用向他人讲述的方式,这也是一种重述,又隔了一层的重述。想准确无误地再现事件的原貌是不可能的,因为经由口中说出来的事永远不可能与事件原样丝毫不差,总难免有所遗漏……[2]154
历史是如何被重述的?《使女的故事》用奥芙弗蕾德所留下的物品为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所看到的故事记录在奥芙弗蕾德留下的“古物”磁带上。在遥远的未来,磁带被挽救、归档并被转述成文字,由另一个男性权威人士皮艾索托教授来解读。而该史学教授只把奥芙弗蕾德视为文献的一部分,认为不仅她的身份成谜,甚至故事中有些人物也完全是空有其名,有待考证。奥芙弗蕾德见证了一个女人在集权统治下经历的一切——噤声、磨难和压迫。人的功能不外乎控制、繁殖和服务,这些功能由嬷嬷和思维警察(眼目)来调控;而人也只因其功能而存在。在一定层面上,《使女的故事》是关于写作过程的。奥芙弗蕾德会在讲叙过程中做出诸如此类的评论,“这期间一部分是我自己想象的”[2]148“这是一种重述。整个故事都是在重述再现过去发生的事件。此刻,当我平躺在单人床上,默默复述着本该说或本不该说,本该做或本不该做,以及本该怎么做的事情时,便是在头脑里重新描述过去发生的一切”。[2]154这样的谈论凸显了构建及表现历史的过程,同时也表明对事件本身的描述可能是被合法化的、被压抑的,因此可能是不可信的。
奥芙弗蕾德的叙述尽力想表达的是尽管她所讲的是对某时某事的阐释,这阐释也同样是真实的,她所讲的就是带有某种深意的真实事件。奥芙弗蕾德对自己的叙述局限性的认识和海登·怀特对元历史的概括不谋而合。怀特认为所有对历史事件的陈述都包含既不可或缺又不可删减的阐释因素。怀特1978年的论著《元历史》中写道: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实质上是一种诗学行为,他预想某一历史领域,并使其成为自己的领地,只有他才能用一些具体理论来解释究竟在此地发生了什么。[6]在怀特对历史作品的分类中,奥芙弗蕾德的叙述介于历史记录和故事之间,因为:“这两类都代表为了让某些未处理的历史记录更易于旁人理解而进行资料选择与整理的过程”[6]。皮艾索托对此甚为沮丧,并且痛惜奥芙弗蕾德的叙述过于关注其个人,这给她的见证留下了许多空白。“假如我们不知名的作者别有禀赋的话,其中一些本来是可以由她来填充的。假如,假如她有记者和间谍的直觉,便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基列王朝的运作情况。要是现在能搞到从沃特弗德私人电脑打印出来的材料,哪怕只有二十来张,我们定将不惜代价”[2]348。
小说的后记充满了对男性占主导的学术界的讽刺。阿特伍德曾做出这样的推论:当所有的白人男性学者不在人世时,他们会被非白人男性学者所取代。女性仍然是被男人审视的对象,不管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还是为他们创造力带来灵感。至于女人,奥芙弗蕾德曾感慨:“我们生活在各种报道之间的空白里”[2]63。
皮艾索托未曾意识到奥芙弗蕾德所做的其实就是在没有听众存在时,去给自己的故事创造一个听众。即使只是想象可能存在这么一个听众,也是对当时僵硬的社会教条的一种反叛。《使女的故事》强调故事的魔力,女主人公奥弗蕾德也尽其所能地去呈现一个聆听故事的人,“只要有故事,就算是在我脑海中,我也是在讲给某个人听。故事不可能只讲给自己听,总会有别的一些听众。即便眼前没有任何人”[2]44。通过想象一个他者,一个外面的人,奥芙弗蕾德在向民主的自我观念迈进。这个自我建立在伦理、公正的体系之上,可以帮她远离当时的各种烦扰,暂时走出这个让人窒息的社会。奥芙弗蕾德只能成为一个逃亡者,因为她无法在那样的社会中生存,而且也不确定她是否还有选择,她只能通过构想一个可以逃避的乌托邦之地,从而得以在幽闭的状态下寻求一丝希望。
结语
基列政权实施对女性从身体到心灵的控制,通过语言这一权力工具来压抑自我,控制性欲望和限制自由;但《使女的故事》证明了女性叙事和书写可以抵抗专制制度并生存下来。[7]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奥弗蕾德有意去审视叙述在创建历史记录中的作用和意义,大量的关于小说本身的叙述使《使女的故事》充满了元小说的特质。叙述的力量是强大的,通过讲述故事,奥芙弗蕾德获得了一种冲破牢笼的自由感,并且为读者指引一条前行的道路。教授对奥芙弗蕾德留下的物品所做的解释很有限,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解读,同时我们也可以对未来有小小的希望,希望可以避免一些正在威胁当代世界的严重问题。同时这部小说也质疑了历史和我们建构历史的方式。奥芙弗雷德给我们提供的“不是父权制度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元历史,揭示男权规则是如何在各种知识方法中被编码,并记录在历史里的”[8]120。奥芙弗蕾德讲述的是发生在过去的故事,这就暗示一个政体和它任何形式的官方语言的消亡可能会掩盖最大的谎言和恐怖。既然在基列这样的恶托邦之后人类仍有未来,这就给了我们希望,最坏的总会被战胜的。
注释:
①《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记载了雅各的故事。雅各是以撒所生孪生子中的弟弟,他是抓住哥哥以扫的脚跟出生的,雅各这一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住”或“欺骗”。雅各用欺骗的手法从以扫那儿得到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和祝福,用计谋夺去了他岳父的牲畜等。含也是《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物,他是挪亚的儿子,他曾与父母、兄弟、妻子和兄弟的妻子共八人进入方舟,避过洪水灭世。含看过了喝醉了的挪亚的下体,而让儿子迦南受挪亚的诅咒,要做兄弟奴隶的奴隶。含相传为非洲人的祖先。
参考文献:
[1] Wisker Gina. Margaret Atwood: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Views of Her Fiction[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2]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羚羊与秧鸡[M]. 陈小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3] Alice Palumbo. On the Border: Margaret Atwood’s novels[J]∥Reingard M. Nischik ed. Margaret Atwood: Works and Impact.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2000.
[4] Patricia Waugh.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5] Tolan Fiona. Margaret Atwood: Feminism and Fiction. [M]. Amsterdam; New York: Rodopi, 2007.
[6]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M].Baltimore;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7] 王苹, 张建颖.《使女的故事》中的权力和抵抗[J] .外国语, 2005(1): 75.
[8] 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C]//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