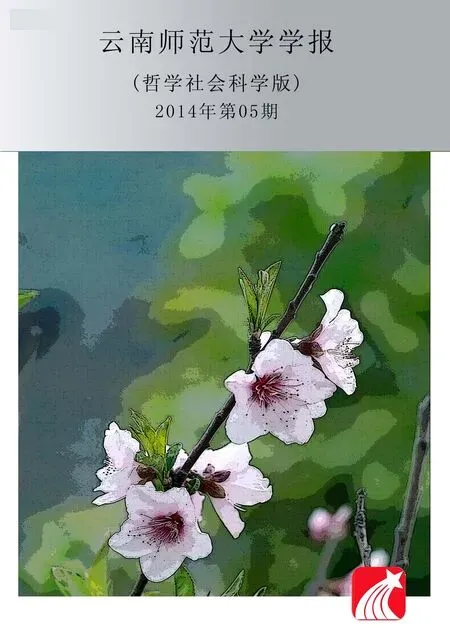南诏时期的和蛮*
段丽波
(云南大学 《思想战线》编辑部,云南 昆明 650091)
南诏国境内的和蛮源于先秦时期的和夷,其时主要分布于大渡河以南。秦汉以降,和夷不见于史载,可能是与当地的其他氐羌系民族一起被记作他称。到了南诏时期,起初与其他乌蛮别种一起被称为“乌蛮”,但到了后来被确切地记为和蛮。因为《蛮书》和《新唐书》所载之和蛮,已然是9世纪中叶时的情形。而在此之前,和蛮早已存在并纳入南诏国的统治范围之内。有唐一代,对和蛮的记载也仅有只言片语。但从其前后的发展历史来推知,前南诏时期的乌蛮主要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南诏立国后渐聚居于境内之银生节度和通海都督,其社会发展仍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阶段,经济不发达,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与其所处的其他乌蛮别种相类似。综合来看,学界对南诏时期和蛮的研究较少,只有尤中在其专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1][p.82-83]、《中国西南民族史》[2][p.264-267]中作过一定探讨,但所论尚不系统和完整。其他大部分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和蛮的流——哈尼族的探讨中,但也都比较简略。本文针对和蛮史料记载之不足的历史状况,欲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对南诏国境内的和蛮从源流、分布、经济、社会、民族关系等作一相对系统的探索,以拓展乌蛮史甚至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阈。
一、和蛮族源考
南诏时期的和蛮源于西北甘青氐羌系民族,其最直接的先民和夷始见于《尚书·禹贡第一》,其载曰:“岷、嶓既蓺,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3][p.219]《水经·桓水》引郑玄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读桓。《地理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尚书》又曰:西倾因桓是来。马融、王肃云:西治倾山,惟因桓水是来,言无他道也……桓水出西倾山,更无别流,所导者惟斯水耳。赵云:《禹贡锥指》曰,古者桓有和音,故郑康成破和为桓。《晋地道记》云,梁州自桓水以南为夷,《书》所谓和夷厎绩。此说是也。[4][p.2940-2941]后《史记·夏本纪》亦载:“华阳黑水惟梁州:汶、嶓既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5][p.63]西倾山所出之桓水,为今白龙江,东南流至甘肃文县东与白水东合,再东南流注嘉陵江。至于岷江称桓,不是指岷江正流,而是指其下游的支流大渡河。大渡河在古代称为“渽水”,据载:“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过郡三,行三千四十里。”[6][p.1598]而《说文》和《水经》作“涐水”,“涐水”即桓水。涐、和、桓音近相通。宋毛晃《禹贡指南》注曰:“和夷,西南夷也。”尤中先生认为,夏朝时之和夷分布在岷山、嶓山及其支脉和蔡山、蒙山地区。和夷的西北部与西戎、氐、羌、渠叟的聚居区相连接。它显然是西戎、氐、羌、渠叟部落群分布向西南的延伸。[7][p.29]而有学者则进一步认为,和夷是先秦时期分布在大渡河以南的族类。[8][p.321]
虽然在先秦文献和《史记》等中有关于和夷的记载,但汉以降,文献中已基本不见对其之记载,可能是与其地其他氐羌系民族杂居错处而被记为他称。从学界来看,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对和夷族属源流的探讨才渐次出现,尤中认为,和夷部落群是西戎、氐、羌的近亲集团。[7][p.29]李宗放认为,“和”是当地民族语言,本义为“山”,与夷相连为“和夷”,与水相连为和水。桓水、涐水是同一水的不同记音,即今大渡河。和夷是指居住在蜀郡桓水以北地区的山区民族,包括这一地区在先秦至汉代的蜀人、氐、羌、徙(叟)、虒、僰、笮,他们都是氐羌系统的民族。[9]段渝则认为,先秦时期大渡河以西、以南的族类以羌族为多,故和夷的族属与羌族有关。[8][p.322]冉光荣、李绍明等从民族神话和历史记载分析后进一步明确认为,和夷可能就是今天哈尼族的先民。[10][p.199]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并没有相互对立,只是关注的角度有异,总体而言,和夷属于羌系民族的观点应大致不误。潘光旦也曾说过,“和夷,疑亦族名,言禹平此部分水土,此种人亦曾出力致功也。此地区为‘彝’族旧地,或当禹时已尔。”[11][p.69]说明先秦时期大渡河以南的族类应包括大量的羌系民族,和夷便是其中之一种。
从史载来看,对和蛮的称呼应是当地乌蛮、白蛮等民族对乌蛮别种之一的专属称谓。在《蛮书》、《新唐书》中均有对“和”字的解释。《云南志》说:“西岩有石和城。乌蛮谓之土山坡陀者,谓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并又明确载说:“川谓之赕,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12][p.75,p.119]这是白蛮、乌蛮等民族语言对“和”之意的阐述。这个民族族称的得名,其中当然也有历史相袭的因素在内,因为白蛮及乌蛮均源于氐羌系民族,关于和蛮先民被记称为和夷至少其应该是知晓的。这一称呼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民族名称。因为在南诏国境内和蛮的分布区到了宋元时期出现了其他民族名称——和泥、窝泥等,即今天哈尼族的先民。
从历史记载来看,大约在唐天宝五年(746年),南诏兼并东方爨部,爨氏在滇东的统治彻底崩溃。在南诏统一东方爨地之后和蛮就少见于记载。事实上,和蛮在其时是东方诸爨三十七部之一。而其后和蛮就统属于南诏治下,并与其他乌蛮杂居,而且从实力来说可能没有其他乌蛮别种的势力强大,只是处于自我发展的民族圈子中,但其部的分化发展仍在继续,因为到了大理国时期,该地出现了多个和蛮后裔的民族名称。
因此,从和蛮的族属源流发展进程来看,还是比较清晰的,先秦时期迁于大渡河以南的羌系民族中的一部分被记为和夷。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南迁,到了南诏时期,被记为乌蛮别种和蛮,宋元以降,在和蛮的分布区域出现了今天哈尼族的先民——窝泥、和泥等的民族名称。当然,在和蛮形成、分化、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杂居民族的融合发展的情形肯定存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和夷、和蛮、和泥和今天的哈尼族直接画等号,这也是民族史研究中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二、和蛮的分布
唐初,部分和蛮的分布地接近于洱海地区,史载:“显庆元年(656年),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显、和蛮大首领王罗祁、郎昆梨盘四州大首领王伽冲率部落四千人归附,入朝贡方物。”[13][p.6322]因为王罗祁统辖下的和蛮分布地近于洱海地区,故才与白蛮首领杨栋附显等一起入朝贡方物。这部分白蛮的分布地在今云南楚雄州南部至普洱地区一带。其东部即与时间稍后的孟谷悮统辖下的和蛮分布区的西部相连。[3][p.265]从和蛮大鬼主孟谷悮与“安南首领岿州刺使爨仁哲、潘州刺使潘明威、獠子首领阿迪”等一道受敕于唐朝的记载[14][p.693]来看,和蛮除一部分南迁至云南西部地区外,尚有一部分迁居于接近安南都护府(今越南北方)之地——今云南红河州、文山州一带,且统属于唐朝。
在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南诏在唐的支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之后南诏不断向东部和南部扩充其势力。渐次把和蛮所居之地纳入了其治下,并设置节度、都督来统之。关于南诏的政区设置,樊绰《云南志》所记为六睑、八节度。而《新唐书》所记为六节度、二都督、十睑。[15][p.6269]其时的和蛮主要聚居于银生节度(开南节度,治于银生城即今云南景东)和通海都督(治于通海镇即今云南通海,相当于今红河州、文山州一带)两个大的区域内,即主要分布聚居于滇南、滇东南地区。据《云南志》记载,在南诏国前期所设的八节度中就包括有和蛮所居之开南、银生节度。其载曰:“云南、柘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贞元十年掠吐蕃铁桥城,今称铁桥节度。其余镇皆分隶焉。”[12][p.77]其间,开南节度并于银生城。又说:“银生城在扑賧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又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12][p.89]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及《中国历史地图集》载“剑南道南部”所定位来看,银生节度辖银生城(今景东)、开南城(今景东文井)、威远城(今景谷威远)、奉逸城(今普洱宁洱)、利润城(今勐腊易武)、柳追和城(今镇沅恩乐)、茫乃道(今景洪)、通蹬川(今墨江)、河普川(今江城)、羌浪川(今越南莱州)、送江川(今临沧凤翔)、邛鹅川(今澜沧勐朗)、林记川(今缅甸孟艮)、大银孔(今泰国景迈),相当于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景栋、泰国景迈、越南莱州及老挝北部丰沙里一带。*关于银生(开南)节度与今天所对应地点的地理位置问题,林超民教授作过专门研究,详见林超民所著《银生与开南》,载《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超民关于景东和巍山相继设立过开南城问题给景东县志办主任的复信(节录)》,可以查阅http://www.jdysh.com/Article/ShowInfo.asp?InfoID=7509;另外,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第67~68页)中也可以看银生(开南)节度部分古今地理位置的对应情况。到了大理国时期,虽然统治和蛮所居之地的政区设置有所改变,但和蛮的分布地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限于当时环境及其写作目的,樊绰在著《蛮书》时,对和蛮所居之地政区设置等的记载较简略。而《元史》作者在搜集其时白蛮等当地民族有关记载的基础上所撰的《元史·地理志》的有关内容,则详细记录了南诏时期和蛮分布情况,南诏蒙氏所立之银生节度即元代之威楚开南等路,[16][p.1460]威楚开南等路开南州(文井)亦载曰:“开南州,州在路西南,其川分十二甸,昔樸、和泥二蛮所居也。……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自南诏至段氏,皆为徼外荒僻之地。”[16][p.1461]而威远州也载曰:“威远州,州在开南州西南,其川有六,昔撲、和泥二蛮所居。至蒙氏兴,开威楚为郡,而州境始通。其后金齿、白夷蛮酋阿只步等夺其地。……至元十二年(1275年),立开南州及威远州,隶威楚路。”[16][p.1462]而元江路又载说:“元江路,古西南夷地。……阿僰诸部蛮自昔据之。宪宗四年(1254)内附,七年(1257年)复叛,率诸部筑城以拒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命云南王讨平之,割罗槃(今元江)、马龙(今新平)、步日(今普洱)、思麽(今思茅)、罗丑、罗陀、步腾、步竭、台威、台阳、设栖、你陀十二部于威远(今景东县境),立元江路。”[16][p.1478]
从以上对和蛮分布地域的记载和梳理来看,前南诏时期,见于史载的和蛮一部分分布在安南都护之北,另一部分近于白蛮洱海地区,并逐渐南迁聚居于滇南、滇东南一带。在南诏立国后,随着南诏国势力向东、向南的不断扩张,和蛮所居之地被纳入南诏治下,并在其地设置了银生节度和通海都督以治之。从南诏中后期始,和蛮的居住地已与近现代哈尼族的基本一致。即主要分布于云南东南部、南部,“六诏山区由晚唐至宋代是包括罗罗、和泥在内的乌蛮住地”,“哀牢山与蒙乐山一带,自隋、唐至今,就是哈尼族的聚居区”,[17][p.17]有部分和蛮则迁徙越过了现代意义的国境线,成为与东南亚国家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跨境而居的民族。
三、和蛮的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
在唐代的文献中,直接记载和蛮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材料微乎其微,但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记载中窥探出和蛮在其时的发展状况。
从和蛮的源流及迁徙的历史进程来看,其先源于甘、青高原的羌系民族,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到了隋唐时期,南迁至滇东南和滇南一带,哀牢山和六诏山从此成为和蛮的传统居地。自此其游牧生活的民族特征由于迁入地环境的改变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和蛮逐渐过上了农牧、定居的生活,一部分继续向南迁徙。学界认为,闻名于世的哈尼族梯田很有可能就是于隋唐时期和蛮开拓并逐渐形成的。《云南志》载曰:“蛮治山田,殊为精好。”[12][p.96]“蛮”是中原汉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蔑称,其意所含较为宽泛,但肯定包括了哈尼族的先民和蛮。到南诏中后期,和蛮营造的梯田就已达到了“精好”的程度。因此,我们说自隋唐以降哈尼族先民已创造出梯田稻作文化,亦当是可信的。红河流域是中国哈尼族的主要聚居区,其文化的核心就是梯田稻作文化。[18]这也是和蛮在南诏时期最突出的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此也可以从哈尼族的迁徙史诗《阿尼阿陪聪坡坡》得到印证。(哈尼)“找着的第一块好地,名字叫作‘策打’,那是清水旺旺的山坡,厚密的树林围着凹塘。挖出大片坡地,梯田开山上梁,支起高高的荡秋,盖起三层的寨房。”[19][p.196]因此,居于红河南岸哀牢山地区的和蛮,在南诏时期已过着山地农业定居的生活,其农业经济较为发达。总体来看,南诏时期的和蛮,其内部各部落的经济文化发展也极不平衡。有的已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有的还不断向南迁徙。此外,聚居于哀牢山、六诏山的和蛮,由于地理环境所限、交通不发达等因素的影响,其商业、交通业也极不发达,虽然已有了梯田的开垦和种植,但其整体经济水平较为低下。
从社会发展来看,隋及初唐时期的和蛮,由于其比较分散居住的状态和实力所限,与其他乌蛮别种类似,其社会发展正处于“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因为在《敕安南首领(岿州刺史)爨仁哲(等)书》中,唐朝皇帝也说和蛮等大鬼主“虽在僻远,各有部落”。唐代文史传家熊飞在为《曲江集》作注时也说:和蛮大鬼主“孟谷悮,部落首领名,唐封其为和蛮大鬼主,史佚其名。大鬼主,南方蛮人部落首领,有大鬼主、小鬼主之分。”[14][p.693,p.695]从史书中仅有的两次对其之明确记载来看,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在其为南诏所统后,特别是自天宝年间南诏东征诸爨之后,和蛮基本上不再见于史册。这虽然是由于汉族史家出于其视野而没有对和蛮进行详细记载,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和蛮在当时确实实力较为弱小,对南诏政权抑或唐朝影响甚微。其时的和蛮或许已与杂居一地的其他民族发生了融合,但其分化发展的进程并没有停止。因为到了唐末至五代时(901~960年),滇东南原和蛮部落所在的六诏山区又出现了维摩、强现、王弄等各部落和泥。[17][p.18]而到了大理国时期,滇东南、南部的和蛮已分化发展为教化山部、铁容甸部、思陀部、伴部、七溪部等,表明其分化发展的进程仍在继续。随着南诏对境内各地统治的加强,原居开南节度内的和蛮内部的自身政治统治关系也被破坏和瓦解,本民族内部“大鬼主”的势力也被逐渐削弱并最终被取消,成为单一的村落,由节度使通过和蛮贵族分子对和蛮人民进行统治。后随着杂居其地的金齿白夷势力的强大,和蛮又受制于金齿白夷。因此,在南诏前期,滇东南、滇南和蛮的社会发展处于部落联盟的发展阶段;而到了南诏中后期,滇东南和蛮的社会发展有了新的特点——正在逐渐形成各自相对封闭的“部”;滇南的和蛮则随着南诏对其统治的加强,特别是由于同区域内金齿白夷的崛起又为其所制,“西部的哈尼族就成了被统治民族的被统治民族。他们就只能生活在保留有更多原始社会痕迹的阶级社会之中”。[2][p.267]
四、和蛮的民族关系
从文献记载来看,东部的和蛮在前南诏时期与唐朝关系密切,为唐朝所统。在南诏发展的过程中,西部的和蛮除了与西洱河杨姓白蛮等一起向唐朝“入朝贡方物”外,后又被南诏所辖而与南诏乌蛮等关系密切。在南诏统一东部诸爨之后,所有的和蛮均处于南诏治下。但由于离南诏的政治中心相对较为偏远,所以南诏与和蛮除了具有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政治关系外,其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不紧密。
前述已知,南诏把和蛮聚居的地区设置为开南节度和通海都督,在这广大的地域内,除了和蛮之外,还有同源于氐羌系的白蛮、乌蛮及其他乌蛮别种,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濮人及百越系的僚人、金齿白夷等,和蛮与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关系。
从《敕安南首领(岿州刺史)爨仁哲(等)书》所记来看,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东部的和蛮与僚人、乌蛮等发生了接触。而从《元史·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开南州所载而言,迁居开南(银生)节度的和蛮,曾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濮人杂居错处,且关系较为密切。因为史载曰:“开南州……昔樸、和泥二蛮所居也。……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16][p.1461]而威远州也载曰:“威远州……昔撲、和泥二蛮所居。至蒙氏兴,开威楚为郡,而州境始通。其后金齿、白夷蛮酋阿只步等夺其地。”[16][p.1462]史料中的“樸”或“撲”即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濮人,而“和泥”即南诏时期的和蛮,“昔”就是指南诏时期或唐代。说明南诏时期的和蛮与濮人杂居于开南(银生)一地,后由于金齿、白夷的强大,其居地被后者所夺,并被其所统。因此,正如前述所言,其地的和蛮实际上是处于南诏与金齿白夷的双重统治之下。所以金齿白夷与和蛮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经济上的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这种统治局面下,和蛮与濮人共同作为被统治民族,共同的杂居地、共同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心理,使其民族间的往来更易于展开。
结 语
南诏时期,源于氐羌系民族的乌蛮由于不断南迁,分布到了更为广阔的地理和地域环境之中,由于迁入的环境各异,不断分化发展为诸多乌蛮别种。作为乌蛮别种之一的和蛮,由于汉族史家对其认识不够,加之其正处于进一步分化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对其之史载少之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天我们对南诏时期和蛮的全面认知。正由于史料的阙如,学界对唐代和蛮的研究不多。在勾联和蛮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我们对南诏时期和蛮的源流、分布及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民族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一研究可以充实和拓展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因为南诏时期的和蛮,经过宋元明清的分化发展,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分化发展为今天的彝语支民族哈尼族。马曜先生曾指出,“到了唐宋时期,云南腹地的白蛮和乌蛮逐步形成今白族和彝语支的彝、纳西、哈尼等族”;“居住于今景东、景谷以至红河地区的乌蛮,唐代称为‘和蛮’,宋代称为‘和泥’,是今哈尼族的先民。”*马曜先生在其主持编写之《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初稿)》(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页、第9页)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后又在其论文《云南二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源和流》(《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及论著《云南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页、第13页。)中也阐述了相同的看法,此观点已成为学界定论。
[1] 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2]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3]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桓水[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5]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第1卷)[M].昆明:晨光出版社,2007.
[8] 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9] 李宗放.“和夷”诸解与我见[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
[10] 冉光荣,李绍明,等.羌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11] 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12] 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1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南蛮下·两爨蛮[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 张九龄撰.熊飞校注.敕安南首领(岿州刺史)爨仁哲(等)书.载《张九龄集校注》(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南蛮上·南诏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 宋濂等.元史·地理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7] 《哈尼族简史》编写组.《哈尼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哈尼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18] 李子贤.红河流域哈尼族神话与梯田稻作文化[J].思想战线,1996,(3).
[19]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哈尼阿培聪坡坡[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