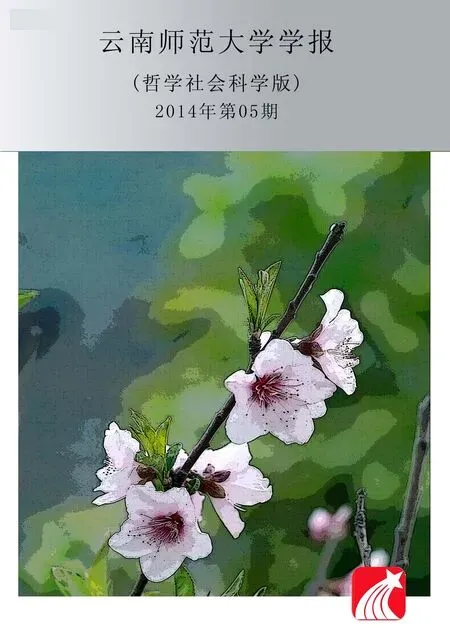人地关系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以上海松江舞草龙为个案*
赵李娜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上海 201418)
一、问题的提出
舞草龙是普遍流传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的一类龙舞形式,它们虽形态各异,然共同特点是植根于南中国独特的稻作文化,内含丰富的民间信仰,在展演时糅合多种民间文艺,现今南方各地的舞草龙大都纳入到各级非遗保护体系中,获得政府和民间重视。在上海市郊区松江叶榭当地,亦有这样的民俗文艺形式,其历史面貌是以草龙舞求雨、祭神、娱人,是稻作农耕浸润下当地民众由生活演绎而成的传统文艺活动,2008年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3年5-6月间,笔者在叶榭当地对舞草龙进行调查,逐渐了解到这一民俗事项的“前世今生”。在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环境下,依靠各种类型的力量支持,叶榭舞草龙的保护和传承已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近30年来由于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草龙求雨仪式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现仅存举行大型活动时的程式化展演。其深层原因是草龙舞属于江南农耕文化的一种形式,在乡村传统生活中,舞龙作为祭祀仪式中娱神的一部分,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认知融为一体。而在当今城市化背景下,舞龙被人们从祭祀仪式中抽离出来,多呈现为面向他者的展演艺术。这样一来其中蕴含的文化语境和个性逐渐被消解,成为一种供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及符号,这是其一。另外,舞草龙在传统社会的展演往往紧紧依托当地的关帝庙会,而现在当地已没有这一固定的大型庙会,草龙求雨仪式生存的空间可以说已岌岌可危。
另外,在具体的传承方式中,舞草龙也存在着一些分离状态。虽然当地学校开设了特色教育项目,形成由初中生组成的舞龙队,每周学习传承这一民间舞蹈,但其实学生只学习舞蹈部分,草龙制作却还是由传承人包办,如今这些老艺人只剩下几位。还有,愿意学习扎草龙这项技艺的传人难找,因为这项以竹编为主的民间传统工艺比较难学,费时费力,这令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据传承人顾顺林先生介绍,草龙形体硕大,用料考究,编法精细,颇费精力与耐力。今年已65岁的竹编艺人、金家村村民俞金仙很无奈地表示:“现在收个徒弟实在太难了,做篾匠这活,累人累腰不说,还挣不到多少钱,现在的小年轻们都不愿意学了。”[1]竹编及草编工艺作为制作草龙过程中的核心技艺,曾在传统经济下的江南日常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普通民众家庭的农业用具和生活用品等皆以竹子编制而成,具有原生态的实用价值和审美意趣。然而,在当今新型材料和工艺的冲击下,寻常百姓家已很难见到有竹编的生活器具,取而代之的是如塑料、不锈钢等有机合成材料制成的生活用品,使原来具有原生态审美情趣的生活变得冰冷与粗糙,这也是大多数古老的传统手艺所面临的问题。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逐渐发现了以上问题,其实这也是现今非遗保护操作与实践中种种不完善的典型缩影。在当今非遗保护研究中,由于实践者大多缺乏对民俗事项的本真内涵与生发根源的根本性理解,造成了保护过程中只取传承而忽略对其文化空间的修复与营造的结果,从而使非遗保护走向“碎片化”的困境。
对于叶榭舞草龙而言,稻作环境、民间信仰、口传故事、仪式程式、文艺表演与手工技能等六项要素构成了这一民俗事项的全部文化空间及表达形式,经过梳理可以解构为环境、信仰和文艺等相互关联的要素,这三类要素存在着根源(生发环境)、内涵(民间信仰)和表征(仪式及文艺展演)之互动关系。一般来说,一定的环境使人在与其互动过程中,形成某些思想观念,在这些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又呈现出一定的艺术形式。大多数民俗形式都是当地民众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人地关系之直接或间接体现,即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研究的最终归结点——“人地互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所关注的一些中心话题,如文化、信仰、艺术等人类文明的几乎所有成果,都可以称作是“人地互动”之产物,在对这些要素的梳理、研究和体味中,皆有可能获得古今人地关系发展与嬗变之真谛。笔者之所以引入这一概念,是想说明在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的调查、研究和保护中,应对民俗事项的生发环境、本真内涵与表征形式有深刻的认识,并厘清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实现对它们的“整体性保护”。基于此,本文拟在田野调查、访谈和资料搜集基础上,对叶榭舞草龙中所蕴含的相关要素及其互动进行梳理,以期对其保护提出策略。
二、舞草龙的表征形式:信仰仪式与文艺展演
舞草龙表面看来只是一种地方性的舞龙活动,实际上其最初的表现形式则是传统农耕社会的求雨仪式,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及访谈,现将仪式程序呈现如下:
舞草龙祭祀仪式选在田间广场,为便于迎请,地点一般选在供奉“神箫”和“青龙王”牌位的庙宇附近。首先布置神坛:三张八仙桌(两大一小),三只木制祭盘供鸡、猪头、鱼,三瓷碗供稻谷、麦、豆,三果盘供西瓜、黄金瓜、浜瓜。参祭人员包括司仪一位,为60岁左右乡民,身着长衫;主祭为一八十岁左右的村中长老。四上供者,二人抬猪头,二人分别托鸡和鱼。六位村姑头扎蓝底白花方头巾,穿粉红斜襟衣衫裤及蓝色绣花彩球鞋,腰系黑绿色镶边围裙,稻谷、瓜、豆等农产品,均来自叶榭本地。祭祀仪式一般在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九月十三当地“关帝庙会”。当天,还会在两张并排的八仙桌前设长条祭桌,上置两盆清水,作为神龙降下的“圣水”,留作泼洒之用。
第一部分 迎神
1. 司仪开祭:放鞭炮6个。
2. 请神:一位男性老年村民,手捧韩湘子神箫*请神时之所以手捧韩湘子神箫,盖因当地流传着以“召龙降雨”传说作为舞草龙活动的由来解释,具体内容下文将详细叙述。在前,另一位手捧青龙王牌位随其后。同时演奏丝竹音乐《请神曲》出庙堂,直到供桌前站立。
《请神曲》主要由丝竹乐器中的箫来演奏,配有吹打乐中的锣鼓,节奏较为简单。
同舞草龙的祭祀音乐一样,其求雨唱词也表现出简单、朴素的特点,这与舞草龙的民间性有着紧密的联系。唱词为:
迎(呀末)迎接圣(啊),
(啊呃候)接圣下云霄。
东请到东天日出扶桑国,
西请到西天佛国老唐僧,
南(呀)请到普陀珞珈山前过,
北请到北海王母歇(呀)马亭。
迎(呀)(末)迎接圣,
接(呀)圣下云霄。[2]
3. 升座:鞭炮五响,五谷丰登;神箫、牌位上供桌,坐北朝南,捧者行礼而退。
第二部分 娱神
1. 上供:猪头、鱼、鸡、稻谷、麦、豆及瓜类分别上供。
2. 敬香:村里长老手持三支清香,行三跪九叩礼。
3. 点眼:由村中长老持毛笔在龙眼上点睛,亦有祈愿之意。
4. 行龙:《请神曲》终,打击乐起。六位村姑持烛台、香炉,三人合掌。出场→祷告→回祭台→吹箫《请神曲》。“韩湘子”上,曲终。九人合舞一条长20米左右大草龙,同时两人合舞两条1米左右小草龙,陪伴周围。舞龙人身着草帽、草衣、草鞋。
5. 接圣水:用“洗帚”(洗锅用的竹制品)向观者泼洒圣水,观者踊跃向前接。
第三部分 送神
1. 敬酒:六村姑捧酒先敬大龙,再洒向小龙。
2. 化龙:最后将两小龙烧掉,寓意小龙带着人间百姓的美好心愿,去祈求玉帝同意降雨,润泽万物。
3. 回宫:大龙返回。整个求雨仪式至此结束。
贯穿于仪式过程中的是当地村民们的文艺表演,使原本庄严的仪式活动充满了欢乐气氛。表演由舞龙和其他文艺组成,舞草龙是表演与仪式的核心,也是其中的最主要环节,充满了浓郁的信仰色彩。其余诸如水族舞和八仙舞等灯舞活动,皆属当地民间歌舞形式。
叶榭草龙舞由源自唐代的求雨仪式演变传承而来,其中具有强烈的民间信仰和祭祀成分,据史料记载,至少在明朝弘治年间当地最大的关帝庙建成之后,叶榭传统关帝庙会一年两次,相沿成习,其间并举办盛大的灯舞活动,草龙舞当然也在其中。在全民狂欢娱乐的庙会情境下,草龙舞中的祭祀仪式成分固然存在,但其中的娱乐成分也渐趋加强,并在娱乐功能上与其他种类繁多的叶榭灯舞并无二致。
一般龙舞都由“龙珠”引导,松江草龙求雨仪式中的龙舞不设“龙珠”,出龙时以箫代珠,有人扮演韩湘子舞箫引龙。草龙舞除序幕、结尾外,基本动作与一般龙舞相似,不同之处多了“求雨”、“取水”等部分。整个表演过程分为“祷告”、“行云”、“求雨”、“滚龙”、“翻尾”、“取水”、“返宫”七个小段。草龙舞表演风格古朴,身段徐缓。锣鼓点子节奏简单,如序幕仅用低微的“笃、笃”之声。“求雨”一段龙身居下,龙首向上,表现向神灵祈求之状;“取水”一段则是龙身紧盘,龙首仰动,凸显吸水之貌。
三、舞草龙的本真内涵:生活需求下的民间信仰
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认为:“我们需要了解的不是唱歌、跳舞本身,而是唱歌跳舞背后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生活需求。”[3]现在所能看到的叶榭舞草龙仅存草龙制作、仪式程序和文艺展演作为表征形式,但若仔细审视展演过程中的若干细节如青龙牌位、韩湘子神箫、关帝神诞日等元素,仍可窥见其本真内涵,即中国传统社会民众在生活中与环境互动产生的心理调适因素即民间神灵信仰。中国民间信仰以神灵崇拜为主要核心,最大特征就是庞杂性、地方性、多元性和功利性,但这些特点都是与我国广阔的地域有紧密关系的,从此意义上来说,中国民间神灵形成机制在于地方民众的自然选择。叶榭位于长江下游的上海西南松江郊区,其地处于江南稻作文化环境中,虽有江河便利,但仍不免有水旱之灾,民众常年辛勤劳作,靠天吃饭,然有时仅得一夕之饱,由于对自然、对社会掌握的无力感使他们将自身的生活及情感需求诉诸民间神灵信仰,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人地互动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从现存我们看到的舞草龙表象如仪式及文艺展演来分析,古代特别是唐宋以降叶榭社会至少存在着龙崇拜(龙王信仰)、关帝信仰和八仙信仰(韩湘子)等民间神灵崇拜。
(一)龙王信仰
早在先秦时期殷商甲骨、《易经》、《管子》等先秦文献中“龙”就被赋予了施云布雨的法力,但龙在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并没有成为专职“水神”。中国龙王信仰自汉晋始,以印度佛教经典中的“龙王传说”为契机,融合杂糅与本土固有的龙蛇崇拜。史籍中龙王与水神结合之形态较早出现于唐初笔记小说《仙传拾遗》及《宣室记》中,体现了当时佛道两教融合互通之态势,显露出唐宋以后龙王信仰多种宗教元素渗入及融合的本质内涵。
从叶榭舞草龙传说来看,其时代背景正是唐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正好是中国龙王信仰在民间生根之分水岭。自此,日益兴盛的龙王信仰遍及各地,取代了原先的湘君、河伯等水神,一跃而成为新一代的水神。宋元以后,有水之处,莫不崇拜龙王,甚至水旱丰歉,悉归龙王执掌。上海地区亦不例外,其地大小龙王庙也建起不少,至明清时期蔚为最盛。学者根据清代方志记载而进行统计,嘉庆年间上海境内就有十多所龙王庙,这一数字尚不包括诸多村镇级的龙王庙在内。[4]基于对自身生存及稻作生产的无限关注与焦虑,沪地民众崇祀龙王的方式主要以进香祈祷和定期举行祀神赛会为主。历史上,每逢大旱,常由地方官员出面,率众前往龙王庙进行祈雨仪式,这一习俗传承久远,直至民国初期仍然存在。1925年《申报》报道过沪上官员齐聚龙王庙祈雨之情景,又据史载1950年6月遭逢大旱,叶榭部分村民还自发舞过草龙。[5]
(二)关帝信仰
宋元以降,关羽信仰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普及,身处东南一隅的上海民众也迅速吸收并接受了这位民间俗神。目前所知,上海境内早在元代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已建有关羽祀庙(庙址在今奉贤柘林),此后境内关帝庙逐渐遍及各村落乡镇,各代皆有增建。明弘治十年(公元1505年),叶榭始于东圩中市(遗址在今叶榭镇叶大公路388号)建关帝庙,至次年竣工。可查考的还有位于镇南(今八字桥村)以及位于今徐姚村的两座小型关帝庙,因历史原因皆被拆除,无稽可考,但以前述弘治年间所建关庙名闻浦南,香火极盛,虽然此庙现亦不存,但在始建时就开始的庙会传统一直延续,世代相传。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与九月十三日,相传是关帝诞辰和忌日(一说为成神日),逢此二日,上海当地居民照例要举行规模盛大、热闹非凡的祀神赛会,叶榭地区亦是如此。方志记载,叶榭关帝庙始建时,举行了热闹的灯舞活动,以后遂为定制,每年都在这两日举行庙会以祭关帝。庙会期间,关帝庙商贩云集,傍晚时分有盛况空前的灯舞活动,队伍首尾相连,声势浩大,连续三日,名闻浦南。自明朝中期起,一年两次,年年举办,代代相传。1958年关帝庙拆除建公社大礼堂,但庙会一年两次仍有延续。至1964年开展“农业学大寨”、农村推广“三熟制”,而农历五月十三正逢农忙时节,于是公社管委会做出决定,庙会改为一年一次,即于农历九月十三日秋闲时节举行。“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受到冲击,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恢复了农历九月十三庙会传统习俗。
五月十三与九月十三在沪人心目中不仅仅是祭祀关帝、赶庙会的日子,同时亦包含了当地人祈求风调雨顺、平安健康的美好诉求。旧时每逢此二日,沪上许多人家还用竹子制成弓箭,用纸制成弓袋,悬挂于关帝庙前,据说还有为避免家中孩童接触厄运之功能。人们还盼望这两个日子下雨,其日之雨名曰“磨刀水”,沪人认为此水可去除年中疾疫,此俗明显有借关帝之力驱祟辟邪之寓意。对此清末上海有竹枝词曰:“瓣香肃拜付儿曹,剪彩悬弧殿宇高;五月十三微雨处,将军灵武润磨刀。”原注曰:“五月十三日为关帝诞。俗以竹为弓矢,系纸作韣,悬之殿庭,谓纳将军箭,孩提易养。是日有雨,为磨刀水,去疫疠。”[6]
颇有意味的是,在一些相关的传说故事及文人作品中,可以发现关帝信仰与民间龙崇拜母题之间,在表征、叙事及文化内涵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至于明末清初时人徐道的《历代神仙通鉴》卷八第九节的“斩龙首”传说,更加直接地阐明了民间在关帝诞辰日祈雨的诉求内涵,其主要情节为:关羽原是一条乌龙,怜悯民间连年大旱民不聊生,违反天帝之命连夜降雨。天帝以法斩之,掷头于地。蒲东解县(即今山西运城)有僧普静,即提龙首至庐中,置合缸内,为诵经咒,九日龙转世为婴,即关羽。[7]这一传说为更深层面探讨关羽崇拜与龙信仰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叶榭舞草龙之所以于关帝庙会时定期举行,也证实了这两位神祇信仰在叶榭当地民众中的融合与杂糅。
可见,在民众心目中,关帝和龙王都被赋予巨大神秘力量,行使行云布雨、解难济困之人生安全职能,两位神明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共同拥有基于安全和生存归属的实用性功能。
(三)八仙信仰
作为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元明以后,全国各地都有八仙故事,但版本却呈五花八门、异彩纷呈之态,这就是八仙在由道教信仰逐渐转向民间信仰时在各个不同文化地域的“在地化”过程,上海松江地区的八仙舞也是当地传统灯舞活动之一,描写的是韩湘子回故里敬花园赏花,其他七位仙人同行的场面。松江八仙故事中以吕洞宾和韩湘子的传说故事最为人熟知,与舞草龙活动也有莫大关系。有关叶榭草龙的传说故事有好几种版本,但其中都少不了韩湘子的参与,这也是草龙前的舞珠人必须手持长箫扮作韩湘子形象的重要传说依据;而有关吕洞宾,在松江地区的民间传说中是与韩湘子故事“捆绑”流传的,这两位八仙人物的传说事迹,为舞草龙活动平添了一份生动与神秘色彩。
关于吕洞宾与韩湘子的故事,在叶榭当地搜集到两个异文,情节基本相同而细节略有差异,现抽取故事梗概叙述如下:
传说吕洞宾云游到苍梧郡湘江岸边,点化一鹤,到人间生鹤童。东江(黄浦江前段古称)边敬花园村一对韩姓夫妇膝下无子,洞宾将鹤童送给他们,夫妇十分高兴,但小孩却日夜啼哭。吕洞宾化名“两口先生”将写有“纯阳子”的渔鼓送给小孩,并给他取名韩湘子。湘子七岁时,父母双亡,靠全村各家吃饭生活,十六岁时他决心求道问药,于是告别村民。在路上湘子又重遇洞宾,跟随洞宾去蓬莱岛学道求药,在岛上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但韩湘子心中还想着敬花园的乡亲。一年后,洞宾与韩湘子游历来到敬花园,此地正遭逢大旱,民不聊生,村民们设坛点香叩拜,求苍天解救。韩湘子立即吹起神箫,召东海蛟龙,顿时大雨如注,终获丰收。村民们用稻禾扎成草龙进行庆祝活动。数年后,韩湘子回故乡探亲,只见禾苗茁壮成长,村民们正在紧张地劳作,但大多数人脸色蜡黄,河边阵阵臭味,水黑而不洁,他马上敲起渔鼓,从东海引来两巨龙,青龙吸走了河中污水,排向东海;另一条黄龙吐出清水,洁净河道,韩湘子从水质中找出了村民病痛之根,兑现了为村民除病的诺言。为感谢韩湘子恩情,村民用稻禾扎黄龙,并用竹叶扎成青龙,打起大渔鼓二龙对舞,拍打小渔鼓与龙伴舞,二龙飞舞戏水。从此以后,扎龙、祭龙、舞龙成为叶榭民间的一祌习俗。*松江文化馆提供。
吕洞宾是八仙中传说故事较多的一位,然从上述叶榭传说来看,吕纯阳显然只是“男二号”,真正的主角乃是韩湘子。其人物原型乃是历史上唐代大文学家和政治家韩愈的侄孙韩湘,《新唐书》有其简略记载,后来逐渐在民间传说与文人小说稗史中累加附会而成后世信仰的八仙之一。元代以降通俗戏曲及小说渐为叙事文学之主流旋律,湘子形象更在这些文学体裁中得到发展完善,作为八仙中的一员,频繁出现在相关的戏曲及小说中,故事主题也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其人之神迹也更加人性化,带上了浓厚的民间文化色彩,在各地的流传都体现着当地民众的愿望与道德观,叶榭的这两则韩湘子召龙降雨故事便是其信仰在地化之明证。仔细查考故事情节,第一则韩湘子出生地是在敬花园,直接成为叶榭人心目中的乡党,而第二则的韩湘子虽然在籍贯上尊重了“史实”,但仍安排他被叶榭韩氏夫妇收养这一段情节,体现了此地民众对这位神仙的认同感。
综上所述,关帝信仰、龙王信仰与八仙韩湘子信仰构成了叶榭舞草龙的信仰基础,在关帝诞辰与成神日举行庙会,舞动稻、竹制成的草龙,前面的舞珠人一副吹箫的韩湘子装扮,这样的仪式与场景,表露了叶榭民众的信仰心理及其世俗诉求。但究其实质,这些信仰基本上可以归结到龙崇拜,是稻作文化语境下人地互动之产物。民众生活的需要是中国民间信仰形成的基础和决定因素。“地方神灵民间信仰既是生活化的信仰,又是信仰化的生活,这种双重特性的形成,主要是由生活决定的。”[8]这里所说的“生活”,即是人所要生存的周围的环境,环境既包括以空气、水、土地、植物、动物等为内容的物质因素,也包括以观念、制度、行为准则等为内容的非物质因素,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即所谓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二者构成了人类生存生产的主体环境。地域性强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大特点,各地信仰与其地人民同自然地理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当地社会人文环境及其景观有莫大关联。民间信仰的产生、传播及其衰落是民众环境感知过程的见证,这是一个渐进的、从朦胧到清晰的过程。
四、保护对策:人地关系语境与文化空间修复
舞草龙作为一种较为古老的原生态舞种,历经上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已为大众广泛参与,同时兼有祭祀和娱乐功能。它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展现着自己所独有的魅力。当地方志记载有乾隆下江南欲观看叶榭龙舞的传说,证明了清代舞草龙的存在。由于传统农耕文化的逐渐消失,舞草龙已渐渐失去其信仰内涵,娱人性大大超过了娱神性,但在20世纪中期其信仰内核仍存余韵。如1950年6月遭逢大旱,叶榭部分村民自发舞过草龙,后因提倡“破除迷信,移风易俗”,草龙舞中断30余年。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认识到草龙舞这一民间活动的重要性和社会历史价值,给予重视与支持。从1986年开始舞草龙作为松江的重要舞种,得到了全社会努力抢救保护传承。1987年中秋期间,舞草龙在方塔公园展演,上海电视台派专人拍摄专题片播放,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2002年举办首届镇运动会上,草龙舞成了主角,组成了全镇的最强表演阵容,邀请最好导演、专业音乐制作人,冒着烈日排练半个月。表演形式新颖别致,两条大龙形体庞大威武无比,由18名男教师出舞;6条小龙精致美观,由18名机关女干部出舞;12只大滚灯,由12名机关男干部出舞;24只小滚灯,由12名幼教女老师出舞。9月15日,舞草龙作为开幕式压轴戏获得观众一致好评。2007年叶榭镇举办第二届运动会,草龙舞再次出演,成为开幕式上的表演节目,魅力依旧不减。自从2008年叶榭舞草龙正式成为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以来,本着“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的原则,松江文化部门和叶榭政府制订了详细周全的保护总体规划,成果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已经初步建立起相关的保护机制。舞草龙求雨仪式源远流长、年代久远,因而文字记录较少,给保存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在这样的现状下,当地政府运用各种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和保存工作,如积极开展田野普查,搜集资料,征集代表性实物等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出版草龙舞专辑丛书及拍摄专题片,运用文字、图像、音像、多媒体等方式对草龙舞进行真实、系统、全面记录,同时建立了草龙舞展示厅,将相关实物陈列其中,以直观、立体的方式将草龙呈现于大众面前,更加深了民众对这项民间艺术的认识,很好地起到了地方文化及非遗保护的宣传效应。
第二,动静态保护结合。
在舞草龙的活态保护上,当地政府十分重视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注意对传承人的保护,这主要表现在支持及其资助传承人自身收徒传承及教育,并为这种传统的传承方式提供一定的传习场所,现已获得政府认证传承人资格的主要有制作草龙的国家级传承人费土根先生和草龙舞活动组织方面的上海市级传承人顾顺林先生。近年来,叶榭当地已经初步建立了以成人传承和校园传承为主的两条路线,现有两支队伍均保持着舞草龙的传习活动,其中成人队伍参加过上海市第七届农运会角逐舞龙大赛。而另外一支学生队伍于2008年春季组建,每学年更新换代,人数长期保持在60人左右,每周授课一节,教学模式已逐渐规范化,编写的教案在市教育系统公开课评比中获一等奖。有了如此完善详细的方案,草龙舞的教学工作可以更好地传授给学生,也为这项活动培养了大量的生力军。
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述,笔者注意到由于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变迁,叶榭舞草龙的传承与保护已经陷入碎片化保护的境地。从本体上来说,由于生存空间的破坏和本真内涵的不存,原汁原味的舞草龙已不存在。近年来,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表述中,“活态保护”与“整体性保护”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两个术语:活态保护倡导力求用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式来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真正落实到保护上,却又难以全面操作。[9]“整体性”就是要保护文化遗存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也包括传承人和生态环境,要从整体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关注并进行多方面的综合保护,这无疑是非遗保护中的理想模式与境界。但现实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难以真正实现“整体”之期许诉求,反而单纯“文化碎片”式的保护比比皆是,使原本颇具整体性的文化结构,沦为支离破碎的状态。以松叶舞草龙求雨仪式来说,这一民俗事项由工艺、舞蹈或仪式等元素混同一体、相互依存,构成完整的文化整体,对舞草龙的保护至少应该包括制作草龙的竹编工艺、祭祀仪式和草龙舞蹈的保护和传承,最重要的当然是恢复舞草龙的文化空间,而并非仅仅重视其中一两个要素而将其中一部分作为一种类型的文化遗产单独或者分开保护,若如此,便只是形式上的保护,文化固有的整体风貌和全面价值势必荡然无存。虽然在叶榭当地乃至松江举行大型运动会、开幕式之时还能目睹到舞草龙之身影,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形式,其中固有的稻作文化风貌已大打折扣。综上,整体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由之路,而想对舞草龙进行整体性保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实行。
第一,积极恢复舞草龙求雨仪式存在的文化生态场,以求从文化记忆方面获得地方民众的认同。
生态学中,将生态系统中各种因素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空间存在,称之为“生态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也可称得上是一种文化生态过程,它的产生、发展、繁荣、衰败与生态场有着密切的关系。[10]也就是说,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的整体性场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产生和传承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智慧、文化人格等诸多因素组合而成的立体空间。它们的合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的首要条件,也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奏。[11]而现实的情况是,现代化及城镇化进程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生态缺失,生态场之整体性不复存在。以舞草龙来说,其产生背景是江南稻作种植业,承载的文化空间是由各种神灵信仰支撑的关帝庙会,现在这些在当地皆面临消失的困境。以前叶榭地区有句古话:“河东(指千步泾东侧邬桥、庄行地区)人一年种几熟,一年四季吃麦粥,河西人一年种一熟,白米饭白粥。”此地历来以产粮棉为主,粮以水稻为主,水稻种植为一年一熟制,十分依赖土地的肥沃和雨水的充足,因而祈求风调雨顺的心理极为迫切,同时,一年一熟的耕作时间表也使得乡民的农闲时间较为充裕,举办庙会祈求神明保佑,娱神、娱人兼及狂欢成为叶榭当地几百年来的生活与信仰传统。从根本上说,作为农耕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庙会从祭祀活动中的诸神、庙会节日时间的选取,早期祭祀的社会功能、庙会中祭祀对象的文化渊源等方面,都可以明显看到农耕文化的影子。自明朝中期起,叶榭传统庙会一年两次,年年举办,代代相传。1958年关帝庙拆除建公社大礼堂,但庙会一年两次的惯例仍延续下来。直至1964年开展“农业学大寨”,农村推广“三熟制”,而农历五月十三正逢农忙时节,于是公社管委会做出决定,庙会节改为一年一次,即在农历九月十三秋闲时节举办。文革时期庙会一度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了九月十三庙会节的习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以传统农耕文明民间信仰诉求为主导的庙会逐渐演变为日常生活用品为主的小型物资交易会,更重要的是庙会的空间承载——庙宇亦逐渐不存。查考当地方志资料,叶榭地区在历史时期至少有三处关帝庙,其中最大的就是建于明朝弘治年间的、位于叶榭镇中市街的武庙(关帝庙),是为乡镇一级的庙宇,自建起之时,叶榭乡民便自发举行庙会,祭祀关帝,同时举办以包括舞草龙为主的灯舞活动,热闹空前,存续达四百年之久,是舞草龙仪式及各种民间信仰展示的绝好空间。现在这座叶榭最大的关帝庙和另外两间较小的关帝庙已经荡然无存,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承载着叶榭世世代代民众情感诉求和文化记忆的庙会也面目全非,难以为继,舞草龙求雨仪式因此也只剩下舞蹈的表征,而无精神与信仰的充盈,这是非遗项目传承中的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一困境,还是应该在相关的文化生态场和空间上下功夫,庙宇等当地文化景观的恢复、庙会的重新热闹,对于舞草龙等一类民间文艺活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当然不仅仅是恢复庙会等的时间、空间景观就可以,还需结合一些生产性的保护来进一步完善舞草龙的传承系统。
第二,对草龙制作、祭祀仪式、草龙舞蹈等实行生产性的活态保护。
舞草龙单纯从表象结构上来说,主要由以竹编工艺为主的草龙制作、舞龙前的祭祀仪式和草龙舞蹈三部分构成,现在除了第三部分娱乐性较强的龙舞以外,都面临着失去生存空间的困境,现在看来,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走出去,进行一定范围和程度的生产性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活态”保护。
制作草龙的技术主要是竹编工艺,这一技术虽然在当今已经失去了大批量的生产价值,但在提倡环保理念和返璞归真原生态审美情趣社会风尚的今日,竹编工艺并非完全失去其市场性和商业价值,因而,如何将这一传统地方民间工艺与市场结合,以生产带动传统,是一个非常值得琢磨的课题。另外,还要结合舞草龙的祭祀仪式与舞蹈部分进行整体性的活态保护,更是舞草龙传承与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诉求在于保持文化的精髓,使其中的生活经验与生存智慧能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更好地被继承、享用并发展完善。因此,“活态性”与“原真性”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指标。“活态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文化自身的规律性有着内在的发生、发展、存在与延续的状态;“原真性”则是指遗产在所属人群共同体的时空中,按照人群共同体的社会法则与文化规则进行的自我展现。[12]舞草龙求雨仪式因具备了地方性、原真性等特点而具有与现代其他大众文化不同的独特异质。在现代人不堪机械化的枯燥生活,渴望逃离城市、回归乡野找寻淳朴与真实的心理需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自身特点,完全可以演变为供给旅游消费的文化资本,从而使得文化保护与民众休闲消费走上协作互惠的良好互动路径。一方面,要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万不能将其封存、圈养和割裂起来静态、碎片化地加以保护,而应在整体性保护的同时提高其适应新的生存时空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旅游开发被视为可促进非遗参与现代社会文化的一种积极手段。作为舞草龙发源地的松江,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旅游产业发展创造了广阔前景,经过多年的经营与宣传,区域旅游文化产业业已成熟,如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功能日益完善,松江新城独具规模,影视制作基地及相关配套服务逐渐成熟,同时浦江源头生态休闲观光资源渐趋丰富。今后松江的旅游规划也将重点围绕其所独具的悠久历史文化资源和独特自然人文景观,进一步发挥本地的旅游资源优势,其中以茂盛山房、张泽老镇和叶榭绿色蔬菜基地为依托的“叶榭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片区”也是当地政府旅游规划的重点项目,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作为我国一线城市标杆的上海,应如何发掘和凸显其传统文化魅力?文化消费视线已逐渐转向对郊区的乡村景观及生活方式的价值的关注与重视之中。在当今,景观作为乡村旅游的基础产品,作为自然的、具有生命意义的景观,作为中国文明的情感故乡,拥有构建休闲旅游文化的先天条件。因此,充分依托松江地区发展休闲旅游的良好态势,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和民俗特质的舞草龙习俗也加入到旅游景观的建设中来,这对于旅游产业本身和非遗项目的发展是一举两得之事,有可能形成双赢局面。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旅游业追逐利益的本性与非遗保护活态性与原真性要求之间存有某种难以回避的冲突,要避免旅游经营者对非遗过度功利化的操作和某些太迎合市场口味的商业包装,这就需要充分理解并尊重非遗民俗项目自身特征而对其进行定位,这一点更需要专家和研究人员更多地参与和指导,各种力量的积极参与,才可能探寻出兼顾保护与开发的有效途径。
第三,传承方式进一步完善,实现舞草龙进高校。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发出了题为“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的宣言,从产、学、研层面上,阐述了高等学校在民族文化建设上的使命。2002年10月,中国第一次非遗教学传承实践与研究的动员大会——“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即为非遗理念进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之良好开端。[1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依靠世代相传的方式进行,各级各地被认定为非遗项目的文化遗产均具有独特地方品质,是各地民众创造与传承的文化精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社会信息。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的精神气质,地方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融合地方历史文化逐渐形成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校园文化特色,其建设基本总是围绕学习的教育思想、教育特色,遵循文化建设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地不断促进高校功能的实现,可以为自身发展争取更大的优势。[14]
随着非遗进高校活动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高校以多种形式将非遗项目引入教学活动中,形成当地历史文化精华的传播与高等教育传承的有机融合。[15]松江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亦十分丰富,区内有位于松江新城西北角占地约八千亩的松江大学城,为现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园区。城内含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东华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七所高校,若将舞草龙作为高校素质文化教育项目引入大学城,那么对于民间文化的传承和高校学生的知识积累与提高,当然大有裨益。在引入这类传统非遗项目的同时,也可以将竹编工艺作为民间工艺项目和草龙舞蹈作为舞蹈和竞技体育项目同时引入高校,再加以文化背景的介绍与学习,以便在大学生心中留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与全貌之整体印象,将优秀地方文化潜移默化地深入学子心中。大专院校青年学子在大学期间接受有关当地非遗知识的教育,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践活动,可增强对我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民俗审美情趣的认识与了解,对他们将来踏上工作岗位以后继续保持关注、热爱、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与理念,起着重要的铺垫和基础作用,当然对于全民文化素养中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的维系,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与帮助,此可谓文化遗产保护之应有之义。
[1] 陈佳欣.松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N].松江报,2010-8-7(3).
[2] 上海松江县民间文学艺术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上海卷·松江县民歌分卷[Z].上海:上海松江县民间文学艺术集成编辑委员会,1993.
[3] 戴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惑[J].瞭望新闻周刊,2005,(30).
[4] 范荧.上海民间信仰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叶榭镇志编纂委员会.叶榭镇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6]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 刘卫英,姜娜.关羽崇拜传说与民间龙信仰[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10).
[8] 陈勤建,尹笑非.地方神灵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的互动联系——以黄道婆、王元暐等地方神灵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11,(1).
[9]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10] 丁永祥.生态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的关键[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11] 陈勤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生态场的恢复、整合和重建[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12] 吴兴帜.文化生态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1,(4).
[13] 陈孟昕,张昕.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讨会综述[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2,(4).
[14] 刘娟.试论地方高校在“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以徐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为例[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15] 彭兆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探索[J].贵州社会科学,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