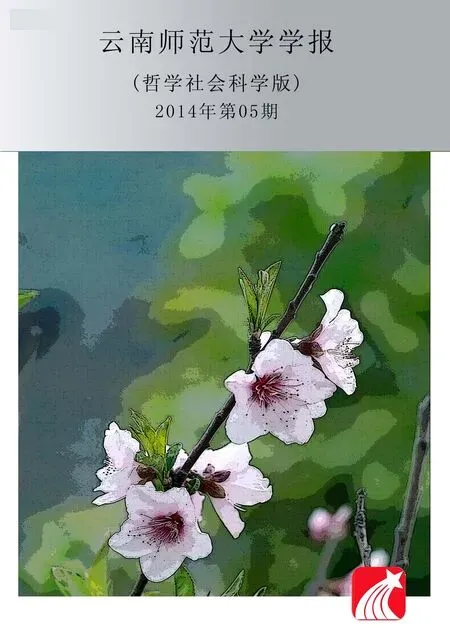论“史识”对汉魏六朝小说叙述的干预*
何 亮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深受史传文学影响的汉魏六朝小说,在叙事体例上遵循史传惯用的“某时某地某人发生了某事”的叙事方式;为满足大众崇尚奇异,追求奇趣的审美文化心理,以史传常用的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方法,打乱正常的时间顺序,制造悬念;为表明故事真实可信,在篇首、文中或文末特意标示故事来源有本可依;在小说观念上也表现出强烈的拟史意识,“史识”成为编撰小说的重要原则和标准。
“史识”是历史家的观察力和史学家尽可能客观公正选择、编撰历史事实的气量和胆识,但历史记叙者并非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赵白生说:“史家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奴婢式的编年史家,他要把‘判断’、‘创造’和‘心灵’融入事实。其结果,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纯粹的事实,而是在历史学家想象里‘重演’过的历史事实。不少史家虽然拒绝承认自己的主观介入,但他们谁也否认不了选择本身就涉及‘判断’,叙述过程多少含有‘创造’的行为,对事件的阐释没有‘心灵’的投入就难以赋予历史以生命。说到底,历史事实是史家的胎儿。”[1][p.28]以这种“史识”编选、著录小说,实际上肯定了主体意识对小说编撰的意义。主体意识逐渐渗透、融入小说,演变成小说家对作品叙述的干预:史传“实录”的叙事原则,使汉魏六朝小说以“求真”为旨归;史家要求对历史事实有独立见解,使小说编撰者以爱憎分明的思想意识,弘扬佛道儒教;“资于政道”的历史使命感,让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补史阙”的汉魏六朝小说,发挥了“广见闻”的社会功能。“史识”对小说编撰者主体意识的肯定,使汉魏六朝小说从“集体编撰”向作家独立创作演进。发展至唐代,小说家自主创作意识的觉醒和加强,小说才真正成为有意识的创作。
一、求 真
前人常用“实录”一词来评价最好的历史著作。班固评司马迁及其《史记》“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p.2738]对于史传的求真,斋藤正谦也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3][p.9902]追求真实、征信被认为是历史叙事的基本原则,也是汉魏六朝小说家叙事的一种追求。
汉魏六朝时期,神仙方术、迷信思想盛行,小说中不乏神奇荒诞、怪异不经的内容,但小说作者都是把它们当成实有其事来记述。《隋志》将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主要归于史部杂传类,其小序说:“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4][p.981-982]所谓“鬼物奇怪之事”,当时人视为实有,以史家“实录”原则予以记载。明胡应麟就认为六朝小说“多传录舛讹”,“未必幻设”。其中的“变异之谈”只是一种“实录”,而非“意识之创造”。[5][p.371]晋郭璞注地理博物体小说《山海经》时,力证书中“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6][p.2153]信而有征。干宝在《搜神记》序言中说明《搜神记》的编写“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访行事于故老”,是对“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的记录。[7][p.2]
小说家往往在开篇、文中或文末,用议论性文字强调故事的真实可信。如《搜神记》“成公智琼”条,文末以干宝、郭璞由卦象论神女身份结束:弦超为神女所降,论者以为神仙,或以为鬼魅,不可得正也。著作郎干宝以《周易》筮之,遇《颐》之《益》。以示寮郎,郭璞曰:“《颐》贞吉,正以养身,雷动山下,气性唯心,变而之《益》,延寿永年,龙乘衔风,乃升于天:此仙人之卦也。”[8][p.286]
干宝、郭璞历史上都实有其人。干宝以著作郎领国史,郭璞是晋代的文学家。文末借干宝、郭璞的论辩性对话,证故事不虚。晋神仙家葛洪《抱朴子·论仙》极力宣扬神仙确实存在,《神仙传》是部纪实之作。无神论者扬雄虽言“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9][p.331]“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9][p.227]谓生死只不过是自然规律,神仙鬼怪之说是无中生有,但他也写了荒诞怪奇的《蜀王本纪》。应劭的情况与他类似。不仅如此,史书的编撰者,亦把小说当成“信史”。在有晋一代,形成了“小说入史”,“史入小说”的潮流。《史通·采撰》云:“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10][p.115-116]在那些“择取不精”的史书修撰中,从小说中选材,也已屡见不鲜。《杂说上·史记》云:“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10][p.456-457]就连“皇家”修史,也多取于小说,可见史学家对其的信奉与推崇。
汉魏六朝的小说观是信史的实录观,认为小说应忠实于历史与社会事实。小说编撰者抱着还原事件真实面貌的理念,对小说作品进行收集、整理、结集。形成于汉魏六朝的所谓“小说”,实际上是小说家将流传于民间里巷的小家之言编撰而成的“小说书”。这些书是一种最广义的“集体创作”。编采者最大的作用,只在于结集及润色,客观呈现事件的真实面貌。[11]不过,这种客观、公正、直书本身就体现了作者的一种立场。
二、弘扬佛道儒教
“刘知几倡史有三长之说,而尤重在识”,[12][p.163]要求史家“具备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德和应有的独立见解”。[13][p.45]这种见解,在汉魏六朝小说中体现为小说编撰者以爱憎分明的思想意识,弘扬佛道儒教,传达自己的人生信仰、理念,体现了作者对作品的干预。
汉魏六朝小说主要以志怪、志人为主,记录神仙道术、巫祝龟策、殊方异物之类的怪异事物,以及人物的言谈举止和逸闻琐事,弘扬佛法、道术、儒教。志怪作者王浮、陶弘景、葛洪、王嘉等本人都是道士,张华、郭璞、萧吉等都是阴阳五行家,昙永、净辩是沙门,王琰、王曼颖、萧子良、梁元帝等为在俗的佛教徒,所以此时期特多《冥祥记》之类“释氏辅教之书”。六朝文人也普遍接受佛道思想,宗教迷信观念极大地支配着他们的写作,自然也会秉笔弘法。
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众说纷纭。近代神话学家袁珂在《山海经全译·前言》开卷即言:“《山海经》是一部由几个部分组合而成的性质非常奇特的古书。它大约成书于从春秋末年到西汉初年这一长时期中,作者非一人,作地是以楚为中心西及巴、东及齐:这便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学者们研讨大致得出的结论。”[14]融合了神仙方术、地理博物和儒家观念。如详述祭祀山神的仪式,“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状皆人面兽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以采衣之”,[15][p.159]云某物出现昭示人间治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15][p.11]“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15][p.10]显然是神仙方士之言。这些在《山海经》中随处可见,还有一些文字意在表露作者以之宣扬儒教。如《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15][p.5-6]“祷过之山”,“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15][p.19]《中山经》“其上有木焉,叶状如棃而赤理,其名曰栯木,服者不妒”,《北山经》“其中多鮆鱼,其状如儵而赤麟,其音如叱,食之不骄”;[15][p.96-97]“有鸟焉,其状如枭而白首,其名曰黄鸟,其明自詨,食之不妒”;《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15][p.301]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不骄”、“不妒”等,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与《山海经》同为地理博物体小说的《神异经》,书中亦掺和着神仙方术和儒家观念。如云食何树果实可以成仙,自是神仙家言,对渴盼成仙之人,无疑有很强的吸引力。此书更为突出的是在异人异物描写中处处表现儒家思想,上引穷奇、饕餮、不孝鸟等。再者如《东荒经》所云:南方有人“恒恭坐面不相犯,相誉而不相毁,见人有患,投死救之,一名敬,一名美,不妄言”;《西荒经》云浑混“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中荒经》云天立不孝鸟,“畀以显忠孝忧”。小说作品“在这些近乎游戏的或正面或反面或赞美或讽喻的形象中,都包含着作者旨在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评价”。[16][p.151]谭献《复堂日记》卷五称其“亦有风议之遗意”。[17][p.110]志怪小说之翘楚的《搜神记》,亦有数量众多的宣扬儒家孝道的故事,如“王祥”、“王延”、“楚僚”、“郭巨”、“衡农”、“东海孝妇”、“犍为孝女”、“刘殷”等。王嘉《拾遗记》也多引儒家教条,卷三善星文者游说宋景公“德之不均,乱将及矣。修德以来人,则天应之祥,人美其化”;[18][p.85]卷三周灵王部分的录语批评他“惟奢纵惑心”;[18][p.84]更说他“溺此仙道,弃彼儒教”,只有“观过才能知仁”,更是堂而皇之地弘扬儒教。
汉魏六朝小说也有不少宣示佛法灵异,弘扬佛教的作品。记载鬼神物魅与人生死祸福之关系的《幽明录》,就有不少佛法果报的怪诞之说。如宣扬奉佛得福的故事,“石长和”“康阿德”“赵泰”等,都借死而复生者的口述,进行说教。赵泰入冥间,冥吏就开始盘问“生时所行事,有何罪故,行何功德,作何善行”。[19][p.180]并告之冥间审判以佛法为准的,“人死有三恶道,杀生祷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布施,生在福舍,安稳无为”。[19][p.180]文末更是赤裸裸地直接要求其返回人间后信奉佛法,昭示世人:“有算三十年,横为恶鬼所取。今遣还家。由是大小发意奉佛,为祖、父母及弟悬幡盖、诵《法华经》作福也。”[19][p.181]张华《博物志》“异闻”、干宝《搜神记》“琴高”、“人死复生”、“桓氏复生”、“王道平”、“河间郡男女”、“李娥”、“戴洋复生”、“柳荣张悌”、“马势妇”、“颜畿”、“冯贵人”、“杜锡婢”、“广陵诸冢”、陶渊明《搜神后记》“徐玄方女”“干宝父妾”“陈良”、刘敬叔《异苑》“徐女复生”、“乐安章沉”、“卢贞”、“琅琊人”等都是以“死而复生”为题材的作品,通过生人亲历冥间之所见、所闻、所感,渲染地域的阴森恐怖,达到使人信佛的目的。
史学家以自己的识见,根据事实本身的是非曲直记载史实,在汉魏六朝小说中,变成了叙述者对故事的一种干预,以“叙述干预”弘扬佛道儒教。
三、广见闻
汉魏六朝时期,小说编撰者主观上希望能“补史”,如张华《博物志》卷八即名“史补”,但其地位卑微,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补史之阙”。此时期特别强调士人博学多闻,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孔子不断勉励、引导弟子勤奋好学,要求门徒“博学于文”,熟悉经典的同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0][p.83]对自然界的事物也要有广博的见识。有才之士也必须熟悉种种掌故和知识,其中就包括“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有关鬼神、变化、术数、方物的知识和传闻。《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疾谬》云:“不才之子也,若问以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庙之大礼,郊祀禘袷之仪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之道度,军国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异同,则恍悸自失,喑呜俛仰,蒙蒙焉,莫莫焉,虽心觉面墙之困,而外护其短乏之病,不肯谧己,强张大谈曰:‘杂碎故事,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识,不足以问吾徒也。’”[21][p.3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华阳博议下》亦云:“两汉以迄六朝所称博洽之士,于术数、方技靡不淹通,如东方、中垒、景纯、崔敏、崔浩、刘焯、刘炫之属,凡三辰七曜、四气五行、九章六律皆穷极奥妙,彼以为学问中一事也。”[5][p.394]博学多识也是荣登显宦的入场券。《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了晋侯厚赏博物知识丰富的子产的史实:“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22][p.1221]赵衰推荐胥臣以为卿,原因就是他“多闻”。王猛向苻坚举荐朱彤,是因为他“博识聪辩”。尤其是六朝时期,清谈盛行。李剑国曾指出:“六朝谈风盛行,知识分子喜作长日剧谈,这是名士风流的一种表现……这里所云谈风,不专指清谈之风,还包括戏谈和讲故事……所谓戏谈,就是‘嘲戏之谈’,或云‘戏语’,这是同讲故事极有关系的一种谈风。”[16][p.226]描述海外神山、异域幻境、神鬼怪物的小说故事,正好满足了人们猎奇、娱乐的心理,增长见识,赢得了人们的青睐。
受此影响,小说编撰者抱着以“广见闻”的目的,搜集、整理流传于民间的小说作品。梁萧绮《拾遗记序》说此书有“殊怪毕举”、“爱广尚奇”的特点。书中多次提到“博识”一词,如卷三周灵王“博识君子,验斯言焉”,[18][p.89]“其爱博多奇才之间,录其广异宏丽之靡矣。”[18][p.27]卷六“后汉”刘向故事,天帝也特派太乙精到人间拜会博学的刘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18][p.153]《洞冥记》作者郭宪在《洞冥记》序中说,此书记载史书所没有录入的汉武帝与道教相关的故事,以广见闻:
宪家世述道书,推求先圣往贤之所撰集,不可穷尽,千室不能藏,万乘不能载,犹有漏逸。或言浮诞,非政教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盖偏国殊方,并不在录。愚谓古曩余事,不可得而弃。况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武帝以欲穷神仙之事,故绝域遐方,贡其珍异奇物,及道术之人,故於汉世盛于群主也。故编次之云尔。[23][p.123]
张华是博学之士,幼年好学不倦,涉猎广泛、驳杂,“图纬方技之书,莫不详览”。他编写《博物志》描述了山川地理、历史人物、奇草异木及飞禽走兽,“出所不见”,望“博物之士,览而鉴焉”,[24][p.7]有采四方风俗异闻,广见识之意。书成后上奏武帝,虽因“记事采言浮妄”招致诘问,但武帝也认为展现了才综万代、无与伦比的博识。刘知几《史通·杂述》也承认小说“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见闻”,[25][p.115]《杂述》篇论杂记类时云“博闻旧事,多识其物”。[25][p.277]
汉魏六朝小说作品内容芜杂,牵涉广泛,多为常人所不知。《搜神记》“斛茗瘕”、“腹瘕病”、“蕨蛇”等记录了奇特、怪异的病症。《神异经》、《山海经》、《海内十洲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等多记异域神物,如入火不燃的“火浣布”、割肉不尽的“无损之兽”、饮之不少的“玉馈之酒”、食之止邪病的“横公鱼”、服其皮可魅惑丈夫的“贡细鸟”、万岁不枯的“声风木”、食之千岁不饥的“五味草”、带之香终年不减的“女香树”、知梦之吉凶的“怀莫草”等。小说中涌现了众多博学多识的人物形象。《海内十洲记》武帝见证神奇的续弦胶,始“益思东方朔之远见”,[26][p.67]亲历月支神香救活长安城内百姓,“益贵方朔之遗语”。《洞冥记》中,东方朔见常人之所不见,知常人所不知,识神驹步景、神草吉云草、使少不老的地日之草、春生之鱼。“斑狐书生”中的孔章,“博物士也”。[7][p.220]听张华言前来拜谒士子的情状后,即知此物为老精。不仅如此,小说中的精魅鬼怪也博学多识。如《搜神记》卷17的“胡博士”条:
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胡博士”,教授诸生。忽不复见。后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但闻讲诵书声。命仆寻之,见空冢中,群狐罗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乃是皓首书生。[7][p.224-225]
老狐幻化成人形,以“博士”自称,“教授诸生”,自是一只学问之狐了。老狐不仅传授知识与世人,也教自己的同类。同卷的“斑狐书生”,文章、历史、经传等无不精通,“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此。比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擿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7][p.219]唐代小说中“学问狐”频频出现,如《广异记》中的《崔昌》,《灵怪录》中的《王生》,《宣室志》中的《尹瑗》等,当是受到《搜神记》之启发。
从以上论述可知,汉魏六朝小说家以“史识”编撰、收集小说作品,逐渐演变成对作品叙述的干预:史传“实录”的叙事原则,使汉魏六朝小说以“求真”为旨归,真实也相应成为衡量其价值的重要尺度。史家要求对历史事实有独立见解,与佛道迷信盛行一时的风潮,使小说编撰者以爱憎分明的思想意识,弘扬佛道儒教。小说本只被视为小道而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编撰者怎样强调“以补史阙”,也无法改变其受人轻视现实的地位。但是,小说内容广泛,举凡天文地理、朝章国典、草木虫鱼、民情风俗、学术考证、笑话奇谈、佛法灵异等,均有关涉。“资于政道”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清谈盛极一时,“博学”为文人雅士所尚的时代风尚,使小说编撰者搜奇猎异,写不寻常之人、之事,让小说发挥了“广见闻”的社会功能。“史识”对主体意识的肯定,使汉魏六朝小说逐渐从“集体创作”向作家独立创作演进。到唐代,小说家自主创作意识的觉醒和加强,使小说才真正成为有意识的创作。
[1] 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日)斋藤正谦.斋藤正谦评《史记》语[A].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0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 [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6]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 [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9] [汉]扬雄撰,韩敬注.法言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采撰(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1] 关诗珮.唐“始有意为小说”——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看现代小说(fiction)观念[J].鲁迅研究月刊,2007,(4).
[12] 柳诒徵.国史要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3] 邓瑞.试论刘知几对史学的贡献[J].学术月刊,1980,(10).
[14] 袁珂.山海经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15]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M].成都:巴蜀书社,1992.
[16]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17] 谭献著,范旭仑整理.复堂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8] [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 [南朝宋]刘义庆撰,郑晚晴辑注.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20]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阳货篇第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1] [晋]葛洪撰,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3] 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序[A].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4] [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5] [唐]刘知几.[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M].
[26] [汉]东方朔撰,王根林校点.海内十洲记[A].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