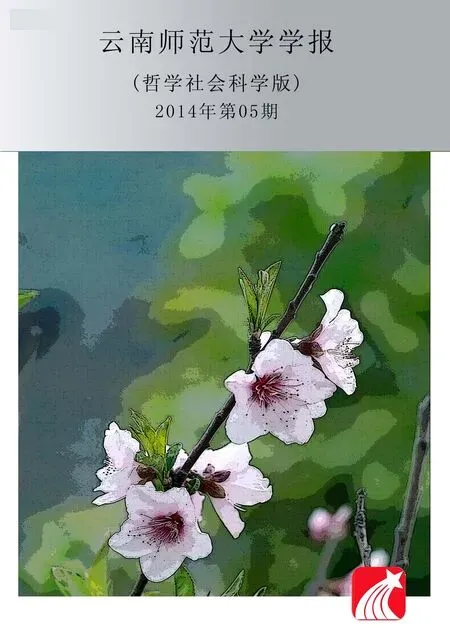生态审美视域下彝族灾难文学资源的创意开发*
肖国荣
(云南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云南 昆明 650092; 楚雄师范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当今世界,生态危机带来的不和谐因素和现象愈来愈突出和频发,生态问题已然成为一个全球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界探讨的热点,于是应运而生了化解生态危机的生态建设。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强调要把生态建设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党的十八大更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立的五位一体观,从中可看出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魄力和决心。但是,现实社会中却出现了部分假借生态建设之名行非生态建设的项目,不仅再生了生态危机,可能还制造了更为深重的生态灾难,究其个中缘由可能有多个,如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项目建设中生态的缺位。为此,各行各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除了深入领会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外,还需做到自觉挖掘各民族文化中的生态资源及其所蕴含的生态审美观,并在生态审美观的引领下开展社会文化经济建设。作为彝族最为重要的生态文化资源的彝族灾难文学在彝族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当发挥其积极作用,寻求以彝族灾难文学为切入点开展研究,不仅是对当下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号召的积极响应,也是加强对生态文化研究热潮的对话。运用哲学、美学、文学、文化产业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开展研究,挖掘彝族灾难文学中蕴含的生态审美意识以开启文化创意,指导如今被世界公认为“朝阳产业”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彝族灾难文学资源合理转化为影视文化产品,积极推动彝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借助影视传媒,把彝族生态审美观念传播给大众的同时,将有利于彝族审美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区域文化经济的繁荣发展及生态文明的建设。研究还着力探索一条把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创意产品的路径。
一、彝族灾难文学蕴含的生态审美意识
《辞海》对“灾难”的解释为灾祸造成的苦难。按照人们惯常的生活常识及经验积累,一般把灾祸分为天灾和人祸,也就是说,导致灾难发生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两方面原因。参照现今通行的文学含义:“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1][p.72]文学是人学,彝族灾难文学不仅源于彝族人民的灾难生活,而且是对彝族人民灾难生活的真实写照,一部彝族灾难文学史便是彝族人民的灾难生活史,从彝族灾难文学作品中可了解到彝族人民的灾难生活及其所形成的对灾难的认识、体验与判断。由此,“彝族灾难文学”便可理解为是使用彝族母语来反映或表现彝族人民因灾祸造成的苦难生活,话语中蕴含着彝族人民面对灾难的生活体验、情感判断、价值取向与思想愿望等的审美意识形态。
“彝族文学按流传方式,可分为民间流传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和文人创作的作家文学(书面文学)两大类。……民间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是彝族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民间文学是彝族文学的主体。……彝族民间文学,按体裁分为: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笑话、歌谣、创世史诗、英雄史诗、抒情长诗、叙事长诗、谚语、谜语、说唱、戏剧等”。[2][p.13-14]作为彝族文学主体的民间文学中的洪水灾难神话又是彝族灾难文学的主体。彝族创世神话被誉为彝族的“根谱”,其中记述彝族先民洪水灾难体验的“洪水灾难神话”,不仅形象地反映了彝族先民遭遇灾难的本真生活面貌与原初体验,还深刻地体现了彝族先民对天、地、神、人和谐境域的向往和对生态价值的审美追求。因其今天在彝族人民重大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仍被讲演和传唱,伴随彝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彝族洪水灾难神话还活态性地吸纳新的社会内容,赋予其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因此,通过彝族洪水灾难神话,我们也能窥探到彝族灾难文学的本质内涵。
彝族洪水灾难神话代表性作品主要有《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洪水泛滥史》、《尼苏夺节》、《门咪间扎节》、《三族起源》、《洪水潮天的故事》、《洪水泛滥》、《洪水滔天》、《阿霹刹、洪水和人的祖先》等。通览彝族洪水灾难神话记叙的内容,究其洪水起因主要是生态出了问题,洪水灾难悲剧的发生引发了彝族先民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活动中萌发并形成了和谐性生态审美意识及其对诗意生存的价值追求。以下便以彝族洪水灾难神话为代表来探讨彝族灾难文学的生态意蕴。
(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审美意识
《阿细的先基》[3][p.46-57]说,“吉罗涅底泼与吉罗涅底摩生了四个好儿子、四个好姑娘,在一块平平的荒地上撬石、掀树、翻土,但到第二天去看时,底下的土却仍然在底下,面上的土仍然在面上。又挖了一天,情况仍然还是一样。晚上兄弟四人就在地的四角一人各把守一角,半夜三更,看见了一个白胡子老倌从天上飞下来,拿着一把铁铲,把翻过来的土又重新翻回去。大儿子喊捆,二儿子喊打,三儿子喊吊,四儿子说让白胡子老倌先说上几句话。白胡子老倌自称是天上的金龙神,说水要淹上天了,你们不能盘庄稼了。随后,大雨下了十三天十三夜,水连着天了。洪水退去后,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小儿子和小姑娘活了下来,在金龙男神和金龙女神的要求下,兄妹俩配成了夫妻。”
《勒俄特依》[4][p.81-83]记载道:“居木家三子,桦槁红树做犁弯,杜鹃花树做枷担,红枣树做赶脚棒,嫩竹做成牵牛绳,黄竹做成赶牛鞭,架起阿卓黑牯牛,来到阿呷地拖犁。前日犁好了,后日又复原,不知为何故?居木家三子,为了知究竟,前去看守地。携带木棍子,长子守上方,次子守中央,幺子守下方。恩体古兹家,派遣阿格叶库臣,身背杉‘乌突’,携带除魔器,手拿套猪绳,赶头黄脸独野猪,来到地上方,将土翻还原,居木长子将他捉。居木长子啊,长子说大话,说要将他杀;居木次子啊,次子说硬话,说要用棍打;居木幺子啊,幺子说话留后路,说要问明白。阿格叶库说:我非可捕人,宇宙的上方,恩体谷兹家,为争格惹阿毕的命案(格惹阿毕是恩体谷兹的使臣。民间故事说,他到下界来催收租谷,被地上的勇士赫体拉巴打死,恩体谷兹便放下九个大海的水淹没大地,以示报复),要放九个海,把地全淹没。”
《彝族洪水故事》说,天神额梯古(即恩梯古兹)派阿碧到地上放牧野兽,因它们常吃地上的庄稼,阿碧被悟悟射死,天神便发洪水惩罚。
另一篇彝文《洪水潮天的故事》[5][p.16-32]则说:天神恩梯古兹派下差人来人间收税,被居布吾午家的黑牛顶死了,于是,天神放九个天湖的水来惩罚地上的人。居布伍午不同意大哥、二哥对天神使者所采取的敌对办法,并保护了天神的使者阿格耶苦白发老人,他才得到天神使者的启示乘木柜免于洪患,成为地上唯一的遗民。居布伍午凭给天神的妻子和女儿治病的办法,娶了天神的三女儿,生了三个儿子,分别成为藏族、汉族、彝族的祖先。
从以上彝族洪水神话故事记叙的内容来看,囿于彝族先民思维认识能力的低下,对导致洪水淹灭人类的原因还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便想象为是因开荒而触怒了天神遂发洪水,虽对天神惩罚人类而发洪水的解释带有想象传奇的色彩,但神话中叙述了导致洪水灾难发生的最初和最直接原因是人类无节制的开荒。神话中的蛇、仙、妖不过是原初自然力的象征,因开荒而影响到整个生物链中的野猪、蛇、熊等的生存和利益,加剧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矛盾,打破了自然整体和谐的局面,最终必然导致洪水悲剧的发生。人在劳动中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人的力量不断得到增长,逐渐与自然分离并掌握了征服自然的本领,甚至还侵占到了代表自然力的天神生活的地盘,于是,人与神之间的一场更为尖锐的冲突便开始了。人神之战通过洪水滔天的方式来重新选择人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已有的文明遂告灭绝,一切又都得重新开始,这大约隐喻了人类只能在某个范围内进行农业垦殖或生存的一定界限,如果越过这个界限,将侵犯到自然整体中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和利益,生态将失去平衡,便会招致自然力狂暴的报复。悲剧的力量是巨大而深远的,如果洪水灾难带给彝族先民的是无限伤痛与自责的话,留给彝族后裔的却是有力的训诫,警示彝族后裔们要自觉地形成尊重生命、爱护自然的和美意识。人与自然的和谐,既是人与物的和谐,也是人与自身的和谐。按阿诺德·伯林特的说法,是一种“参与性”(Engagement)关系,用中国哲学术语是一种交感性的和谐。中国已故哲学家方东美先生说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和谐的双方“非但不敌对,非但不冲突,反倒处处显出和谐的理趣”。[6][p.90]
(二)人与人和谐的生态伦理审美意识
《说文解字》解释“伦”为辈也。伦理,即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准则和秩序。伦理代表社会意志,以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原则为标尺,通过社会与个人的道德良心对不太严重的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行为进行惩罚,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彝族史诗以故事的形式真实地传达了先民们原始的生态伦理意识。
彝族史诗《梅葛》说,格滋天神用雪造的三代人,第一、二代被太阳晒死,第三代“人的两只眼睛朝上生”。这代人懒,糟蹋五谷,心地不好。天帝决定要换一代人。并派使者武姆勒娃下凡寻人种。使者变为熊,把直眼人学博若五个儿子耕的地翻平,“整整犁了三天地,三天都被老熊翻回来。”后五兄弟商议在地里设扣,套住了熊,熊祈求五个儿子帮它解开扣,“四弟兄都喊打,四弟兄都喊杀”,后来熊被小儿子解救,于是武姆勒娃赐小儿子三颗葫芦籽,洪水来时让他和小妹妹搬进葫芦避难,后来兄妹繁衍人类。史诗《查姆》也说洪水之灾的起因,是天神为了换人种,因为独眼睛、直眼睛时代的人心地不好。天神为了换一代人便降下洪水。两部史诗都共同讲述了因人心地不好而受到代表超自然力量的天神的惩罚遂遭遇洪水灾难,天神通过毁灭性的洪水灾难来淘汰良心不好的人种,留下善良的人种生存下来繁衍后代,体现了彝族先民善的道德意志和生态伦理。生态伦理是基于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提出,生态破坏的始因是对生命的不够尊重,为此,生态伦理的要义是:
第一,要尊重和热爱生命。德国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要“敬畏生命”。他所指的“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包括一切自然生命,为此,我们在行动上就要做到不能伤害每一个自然生命,且要力所能及地去保护和救助它们。阿尔贝特·史怀泽认为,生命是不容易的,生命贵在有意志,生命意志支持着生命与种种危害生命的事物顽强斗争。正因为生命如此不容易,我们更要敬重生命,珍惜生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按阿尔贝特·史怀泽的看法,“善就是保护、促进生命,而恶是阻碍和毁坏生命。”[6][p.74]彝族史诗中叙述的人懒、糟蹋五谷、心地不好,既违背了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又违犯了道德的基本准则。人虽然脱胎于自然,但并不能改变他作为有生命的自然的动物特性,这意味着人需要从事维持生命及其个体生存的劳动以获取食物,否则,将危及生命和生存。另一方面,人心地不好是违背了自然道德的原则,如超过了道德的基本底线,将会影响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生活的有效秩序,会招致代表自然道德力量和社会意志的天神的惩罚而发洪水。彝族先民已经萌生了善与恶的原始朦胧的道德标准,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来对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行为的评价,这种道德批判价值已经感性直观地显现在了人的生活实践中,并形象地反映在了作为文学艺术的史诗中,这时它不仅对人们的行为有了规范和约束,而且在生活实践中会自觉地去尊重生命、爱护生命,长此以往,这种生命与生命之间和爱意识便自觉形成和得到人们自由运用,便具有了超越伦理关系的生态审美意义。
第二,要讲求人与人的爱,并把人与人的这种和爱意识扩展到人与自然的爱。人类对自然的爱,源于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是人类的母体,是人类的根,而且也是人类现在生存、发展的力量所在。不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尊重是相互的,体现的爱也是平等的、适度的。每个生命个体既有生存和被爱的权利,同时也要尽到去尊重和爱护其他生命的义务。彝族史诗《梅葛》中叙述的老熊因把“直眼人学博若五个儿子耕的地翻平”而被五兄弟设扣并套住,这一情节说明对于生物的个体生命的权利,人类的尊重是有限的,当其他生物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并影响生活时将受到人类的惩罚。不过,就当今的生态形势而言是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尊重还不够,自从工业社会以来,人类驾驭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并借助高科技手段肆意掠夺大自然的资源,以致不少动物品种因人类的滥捕滥杀以致灭绝。彝族史诗叙述洪水灾难的逻辑前提是因为人心地不好,这揭示了人与人之间需要建立起尊重、关心、爱护的和爱关系的诉求。
彝族洪水神话的生态隐喻无疑又能促使我们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关注与反思。生态问题还将存在,理论的探讨仍要继续。美既是存在的又是变化的,只有在美的体验中才能感受到美的真实存在和把握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及面对未来终极性生存问题的探索与对生存价值的正确判断。彝族洪水神话确凿地蕴含着彝族始终对和谐生态的生存生活环境的向往和追求的主题。如彝族史诗《勒俄特依·兹的住地》中描写了彝族先民居住的环境:“屋后有山能放羊,屋前有坝能栽秧,中间人畜有住处,坝上有坪能赛马,沼泽地带能放猪,寨内又有青年玩耍处,院内又有妇女闲谈处,门前还有待客处,……”[4][p.119-120]反映的语境是彝族先民在频繁的迁徙生活中,苦苦寻找并找到了理想的宜居环境而欣喜的真实情感体验。在这个生存空间里,人与畜都有适宜的生存空间,这可看作是对先民们居住环境的实写,也可理解为是对诗意栖居的追求。
为此,彝族灾难文学中所蕴含的生态审美意识是以和谐为基础,以爱意为旨趣,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态共生共存为价值,并祈望在这种共生性的生命体验中实现生生不息的生命创生。
二、彝族生态审美意识开启文化创意
如今文化创意产业已被世界公认为“朝阳产业”。党中央特别强调:“文化是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在201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新定位、新部署和新要求。[7][p.1]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科学合理地开发彝族文化创意产业正是对党的十八大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号召的积极响应。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能否成为新的经济动力引擎,其关键在于文化创意,因为“文化产业是观念形态的产业化,是将文化、艺术元素融入传统制造业,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除了一些外围行业与制造业或一般文化服务业外,文化产业生产的是精神性的意识形态产品,它在获取丰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提升人的人文素质,影响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塑造丰富而健康的心灵,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这一丰富生产的本质决定了创意在文化产业中的核心地位。”[8][p.48]可以说,文化创意已然成为了一种隐性的文化力和显性的文化生产能力。在当代信息社会里,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命运会取决于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形式的创意能力。接下来,就有必要弄清楚创意的产生、创意的内涵及其与审美意识的关系。
创意首先来自于个人或者是集体的智慧。《辞海》对“创意”的解释为有创造性的想法、构思等。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好点子”、“好主意”或“好想法”,其核心是想法、构思要体现出创造性、创新性和原创性的品格。早在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就曾撰文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文化成长的原动力。因此,创意便定义为:“观念的产生、联结和转化的有价值的实物的过程。”[9][p.25]还有研究认为,“当今世界,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出现,它连接了经济和文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这一新发展范式的核心就是创意——创意、知识与信息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是全球化的世界中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这里的‘创意’是指新想法的提出及其在原创艺术品与文化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运用以及功能创意、科学发明与技术创意。因此,创意的经济效益通过推动企业发展、加速创意、提高生产力并促进经济增长得以实现。”[10][p.3]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创意可认为是人类突破原有或传统的行为模式,以全新的姿态所展现出的新文化形态、创作现象或劳动过程。具体讲,是把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文化资源(文学、音乐、美术、建筑等)、生活用品(如服饰、食具、饮具、饰品等)或传统器具或传统生活方式等不断加以新的元素,跨界延伸并设计出与时代相吻合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新表达方式或形式。在文化创意的开启下将会生产出丰富多样的美的文化产品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与进步。为此,要发展彝族文化创意产业首当其冲的是要有文化创意,用创意打造彝族文化产业品牌。
如果追溯民族文化创意与审美意识的产生,其实二者都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文化创意是与人类劳动所共生的,劳动本身就携带着先天的创意和创造属性,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了实践经验,产生和培养了人的创意意识与创意才能,从而创造出丰富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创意也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一部分,是人类创作或创造的一部分,是人类理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智慧与思想的结晶。彝族审美意识也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欣赏美、创造美的活动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它是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这种能动的反映是彝族在长期的审美实践基础上实现的,并且是在一定的哲学、政治、伦理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如把两者进行对比的话,文化创意和审美意识都是从劳动中产生,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不同的是,文化创意不一定具有美的属性,可能只是理性地来把握世界,而审美意识是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审美地来把握世界。为此,审美意识能够高屋建瓴地来开启并指导文化创意,让创意更美。从学理上讲,审美意识属于美学学科的范畴,但它涉及哲学、美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美术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把审美意识与彝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结合,又是在以上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加进了影视传媒学、经济学等的内容,这种跨界研究,容易开启文化创意。
徐恒醇先生在其著作《生态美学》中说:“生态审美观是对自我生命的和谐状态以及普遍的生命关联和交融的感悟和体认。”[11][p.45]这已是从人与自然的关联中扩展到了社会领域和人的精神世界。其实,代表彝族文化精髓的和谐意识就是生态意识,彝族古代文化中蕴含有如万物和谐共生的“元气论”、“雌雄观”等生态审美意识,以及以“奢香”为代表的和谐生态文化的践行者。根据欧阳黔森同名小说《奢香夫人》改编并联合摄制的28集长篇电视连续剧《奢香夫人》可算是近年来彝族生态审美意识开启文化创意的成功例子。影片以历史人物奢香为对象,成功塑造了一个对彝汉文化交流与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女英雄、女政治家形象——奢香夫人。故事情节围绕主人公奢香而展开叙事,艺术地表现了一个和谐性生态文化的主题。既是彝族生态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又是对彝族古代最具典型的和谐性生态文化记忆的再现,又契合了当今世界和谐性生态文化建设的主题,是历史感与时代感有机结合的文化创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模式。影片对于彝族文化的传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是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文化产品。
可见,彝族生态审美意识能够开启文化创意,有利于文化品牌的树立,指导文化创意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不过,要牢记只有真正把握好彝族生态审美意识的科学内涵,才能更好发挥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引领作用。
三、彝族灾难文学开发为灾难影视产品的路径思考
彝族灾难文学是彝族文化众多资源中的一朵奇葩,具有多方面潜在的产业开发价值,它是大力发展彝族特色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从文化产业学的角度来看,彝族灾难文学作品属于文化资源的范畴,不过,要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创意产品,创意是关键,将具备转化为文化产品条件的文化资源在创意的开启下科学地进行开发。也就是说文化资源仅仅是文化产业实现的重要基础与条件,要实现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的转化,还需要在准确把握彝族生态审美观真实内涵的基础上经过创意的提升。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要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使得相对感性的、粗糙的、零散的文化资源经过深刻化、概括化、典型化与产业化过程。其路径为:
(一)挖掘整理彝族灾难文学资源,创意转化为具有彝族特色的灾难影视产品
彝族灾难文学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对于灾难片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但是,从原始素材到主题形成、故事架构、情节编排、人物造型设计过程等,是艺术家以及影视从业者充分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过程,且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表现往往决定了产品的趣味性、娱乐性以及市场潜力。彝族灾难影视产品应以彝族灾难文学为创作源泉,并以现代生态审美观开启文化创意,指导灾难文学资源变形、加工与科学转化为具有彝族文化特色和体现彝族审美精神的灾难影视产品。
成功利用有限的文化资源创造出价值无限的文化产品的最典型例子当数美国的迪士尼公司。其利用各国的文化资源,各种童话故事、传说和英雄人物形象,创造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动画形象,形成了独特的电影制作产业链,并且将电影业顺利拓展到了多个产业,如旅游、音像出版业、传媒业等。迪士尼动画《功夫熊猫》和《花木兰》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票房成绩可谓深深地触动了国人的神经:当我们在模仿美日韩动漫造型风格时,中国元素却相继被他国挖掘、贴上标签,为什么我们不能挖掘自己的文化符号,创造出承载中华文化内涵的优秀作品?[12][p.313]美国好莱坞电影、日本的动漫游戏、韩国的电影电视剧,它们在出口上都具有统一的鲜明特性。首先是具有极强的想象力与娱乐性。其次是在引人入胜的画面所叙述的故事中,表达了一种普适的价值取向,反映出一部作品的创作群体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和融入了对宇宙人生发人深省的理性哲思。这些美好的文化精神能够超越民族、国家、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与肯定,有利于引导人类对现实社会生活困境的深沉反思,并激发人类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与探索。
彝族灾难文学尤其是灾难神话是转化为灾难影视产品的现实脚本。如前所述的几则洪水灾难神话就具备影视艺术文本的宏大叙事模式、奇特的想象力、非凡的创造力和形象生动的灾难生活写照、深刻的灾难认识与对生态审美理想的追求。而且,其内蕴丰富的生态审美观不仅为文化创意的开启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还契合了当今世界为化解生态危机而产生的生态重建的价值理想。由此,可借鉴他国灾难片的创作模式,将彝族独特的生态审美观同灾难影视产品的创作相结合,彰显彝族特色,整合彝族符号元素,走民族化的创新之路,力求生产出承载彝族审美精神的影视产品。
(二)构建现代生态审美观,以灾难片为载体表达对和谐生态价值的追求
对彝族丰富的文化资源尤其是灾难文学中蕴含的生态审美意识进行专业的挖掘与整理,并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对之进行理论提升,使之活态化、审美化与时代化,以构建现代生态审美观,并以灾难片为载体表达对和谐生态价值的追求。
在当今“媒介化社会”中,影视的视听语言将受众的文化背景差异、民族界限以及地域隔阂缩小到了极限,以影像传播的方式传达出当前全球生态危机和表现了现代人类对和谐生态伦理价值的追求。生态类灾难电影让观众在娱乐的同时获得电影文本传达的生态审美意识,从而着力建构受众的现代生态审美观。灾难电影表现了强烈的现代生态观念和深沉的生态忧患意识,并且还凭借其广大的受众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观众实现着对现实生态环境的优化和改良。灾难片用直观的影像或真切或夸张地呈现了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的生态危机,表达了对生态环境的忧思与关切,传达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生态价值理念。[13]如美国科幻大片《阿凡达》利用数字3D画面、电脑数码特技、巨幕等最新的现代电影特技,以当前人类所面临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试图向外太空拓展生存空间等为切入点,精心设计出了一个虚拟的“类地球”的景观世界——外星族群纳威人的家园潘多拉星球。影片对潘多拉星球的宇宙结构、神灵体系、化身特性、生物多样性等的想象性表达,在为观众提供逼真、唯美、瑰丽的视觉审美和想象空间的同时,还对人类的原始思维与远古神话原型的激活,从根本上成为人与自然关系密切的表征,表达了一个人类和谐生存的共通性主题——地球生态问题。同时,还反思了现代社会中技术主义存在的价值以及工业文明曾带给人类战胜自然的幻想。[14]如前所述,彝族灾难文学突出地反映了彝族人民对生态的关注及其对和谐生态审美理想的追求,[15]如对其进行科学开发,也将会得到受众的欢迎。
(三)扎根彝族本土文化,培养原创影视人才
影视艺术的发展,需要一大批锐意开拓的影视创意产业作家。彝族相对于其他文化发达民族来说,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即使有少数受过高等教育,但专业的影视人才却很少,从而导致高素质、富于创新思维的人才,包括市场运作人才的严重不足。人才问题已经成了制约彝族影视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纵观日本动漫、美国动漫,它们都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背后支撑,而当前我国的动漫作品模仿的较多,反而丧失了我们最宝贵的文化内涵。”[12][p.317]能代表彝族文化的影视作品可谓掐指可数,《阿诗玛》算是彝族文化的一张漂亮名片,由云南撒尼人口头流传的长篇爱情叙事诗《阿诗玛》整理改编为影片,其成功秘诀之一应归功于有一支以著名学者李广田为代表的创意团队——“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为此,培养一批能扎根彝族本土文化,沉下心来从事彝族影视创作的人才是生产精品的基础。
[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 左玉堂.彝族文学史(上册)[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3]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江河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阿细的先基(阿细民间史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
[4] 冯元蔚译.勒俄特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5] 沈伍已口述,邹志诚记录整理.洪水潮天的故事.大凉山彝族民间故事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0.
[6] 陈望衡.环境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7] 谈国新,钟正.民族文化资源数字化与产业化开发[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8] 黄永林.从资源到产业的文化创意——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评述[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9] 李宇红,赵晶媛.文化创意的人文理论和产业研究——人文精神与商业体系: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0.
[10] 埃德娜·多斯桑托斯.张晓明,周建钢等译.2008创意经济报告:创意经济评估的挑战面向科学合理的决策[M].北京: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08.
[11] 徐恒醇.生态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2] 谈国新,钟正.民族文化资源数字化与产业化开发[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3] 王赛凤.从美国灾难大片看美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J].电影文学,2010,(12).
[14] 李简瑷.阿凡达式美学:科技包装与神话原型内核的缝合[J].电影文学,2011,(9).
[15] 管彦波.水文生态视野下的“神山森林”文化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