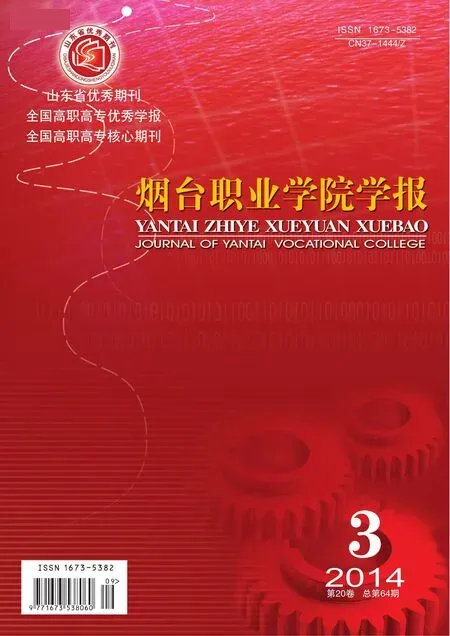海阳秧歌剧的艺术特点与创作*
姜雪芹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烟台264006)
海阳秧歌剧的艺术特点与创作*
姜雪芹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烟台264006)
秧歌剧是海阳大秧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戏剧、歌舞、说唱等艺术形式的共同特点,又在结构、语言、情节等方面具有自身的本质属性,是各种艺术形式的集大成者。
秧歌剧;特点;海阳大秧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秧歌剧与戏剧艺术、说唱艺术、歌舞艺术的亲缘关系,促使它博采众家之长,从剧本到表演以及服饰道具均形成自身艺术特点。这些艺术特点,既有戏剧、歌舞、说唱艺术的影子,又离不开它乡土艺术的本质特性。
1 结构合情
结构是秧歌剧创作的首要问题。在秧歌剧的创作中,词采、音律、科诨、宾白等,只是组成剧作的具体成分,而结构则关系到剧作的整体效果。结构是对剧本主题思想的突出和反映。秧歌剧结构合情合理,主题思想就鲜明。与词采、音律等相比,结构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剧作的成败。如果只有好的词采、音律与宾白,而没有好的结构,就如同守着一大堆材料却盖不出好房子。具体地说,就是在秧歌剧创作中,要坚持主题有谱可循,故事有理有据,人物合情合理。这个情就是民情,这个理就是老百姓的理。抓住这一点安排情节、配备人物、展开矛盾,秧歌剧就会框架结实,主题鲜明。秧歌剧《爱女嫌媳》的创作者,根据乡间普遍存在婆媳间、姑嫂间关系相对微妙的实情,讲述了做婆婆的不要亲闺女嫌媳妇这个持家之理。剧中人物围绕着这个情,这个理,现身说法,不造作僵涩,不装腔作势,深受观众欢迎。
秧歌剧常用的结构方式是“一人一事”。秧歌剧《宝成结缘》就从宝成借粮开始,围绕宝成一个人的遭遇,展开矛盾冲突,其余枝蔓皆由此“事”而生。从这出戏可见,“一人”就是指剧作的中心人物,是主题思想的主要体现者,而其他剧中人物均属陪宾,都围绕着这“一人”发生联系,展开冲突。在《宝成结缘》这出戏中,宝成就是这“一人”,但仅有“一人”还不能确立剧作的结构中心,还必须有“一事”。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围绕“一人”必然有许多事情,而这许多事情,并非都与剧作的主题和作者的创作意图相统一,因此,“一人”还必须与“一事”相结合。那些只有“一人”而无“一事”的剧作,也是不尽人意的。
“一事”,就是指那种能够代表“统一性”,能将全剧情节贯串起来的“一事”,即剧中关键性事件。《宝成结缘》中的宝成,如果不遭遇翦径,不宿王二麻子家,就不会有一系列的事件发生。这样,宝成借粮上路发生的事就是剧中关键性的事情。再是,有的戏中的这一关键性事件,不一定是剧中的中心事件,只是因为它在矛盾冲突中起着枢纽的作用,才成为结构中心之一。例如,《锅腰娶亲》中“洞房”一事,并不是剧中的中心事件,但是,它把整个剧中的矛盾挑了起来。即由这“一事”带起以下的许多情节:新婚夫妇吵架,邻居二大妈劝架,新娘回心转意。一夜的洞房花烛,铺垫了一出夫妻恩爱的好戏,为观众留下了好大的回味空间。显然,“洞房”一事在《锅腰娶亲》的剧情中,具有枢纽作用。
秧歌剧以“一人一事”为结构中心特征的形成,与民间说唱艺术的结构形式有关。说唱艺术敷衍故事是以“一人一事”为主的,从“一人”的“一事”之开头说唱起,一直说到“一事”之结尾。有头有尾,一线到底,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交代得十分清楚。秧歌剧正是吸收了民间说唱艺术的表现方法,形成了“一人一事”的结构方式。
秧歌剧的结构有极为特殊的一点,即在一些反映家庭伦理问题的秧歌剧中,作者往往要安插一个婶子、大妈之类的说事人。当剧中人物矛盾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景况下,说事人及时出现,将做人处世的道理说与矛盾双方听,致使双方悔悟,矛盾化解。《锅腰娶亲》、《妯娌闹》都属于这种形式。也有的在秧歌剧开场或尾声特设一段唱词,以剧中人、事为例,将本剧所要说明的道理总结给观众听,告诉观众生活中应该怎样做或不应该怎样做,这些劝人的话有的由乐大夫演唱,《白云庵》开场就是由乐大夫演唱序言,提纲携领地将所说之理讲与观众听。也有剧中人物直接演唱的,《输钱卖侄》就是这种范例。剧中的吕宝做尽坏事,害人不成反害自己,在兄长吕玉的责问下幡然悔醒,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现身说法,演唱了一段结束语。强化本剧教导世人的“做人千万多行善,作恶必然害自己”的主题思想。吕宝这样唱到:
哎,问得吕宝没话说,众位老少您听着:劝世人多行善少行恶,赌钱场里少摸索,千万的莫学我,好事半点都没做。善恶到头都有报,卖人家最后卖了自己老婆。哥哥合家团圆了,闹得自己没法过。不如闯我关东去,在家没脸见哥哥。拍打腚锤劝世人,千万行事莫学我。谁要跟着我来学,学来学去卖老婆。我哥哥不叫常行善,父子那能常见得?善恶二字人人晓,常行好事莫作恶。
秧歌剧这种剧外人参与剧中说长论短、剧内人游离到剧外现身说法的特殊结构手法,是由它教化人的作用所决定的,也是受民间说唱艺术影响而产生的。
2 情节求奇
秧歌剧作者在攫取素材、编写剧本时,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这是不争的事实。秧歌剧与其它文学艺术体裁一样,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它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必须真实可信,真实性是秧歌剧的艺术生命之所在。如果秧歌剧所描写的情节荒诞不经,没有真实性,那就丧失了秧歌剧的活力,必然为观众所唾弃。当然,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情节看似荒诞的剧作,但有创意,有鲜明的人物个性,也易被观众所接受。秧歌剧《锔大缸》取材于南天门土地神捉拿在凡间作孽的天帝小女儿旱魃的民间传说,作者巧妙地将天神之间的斗法斗智,变成了一个诙谐的锢漏匠与一个风流灵巧的村妇王大娘之间的嬉戏打闹。神走向凡界,走近生活,展现人间的男欢女爱。原本荒诞的情节不显荒诞,《锔大缸》也就成为人们非常喜爱的秧歌轻喜剧。
秧歌剧的真实性既要是生活的,又要是艺术的。现实生活是主要的,但是艺人们在组织秧歌剧情节时,又离不开艺术虚构。如果说,真实性赋予秧歌剧生命力的话,那么艺术虚构则赋予剧作以艺术魅力。现实生活十分复杂,有着本质与现象、真实与虚假之分。秧歌剧作者在选取素材时,不仅要舍去那些与剧作主题无关的素材,剔除那些非本质的、虚假的生活现象,而且还必须根据矛盾冲突的可能性,虚构某些人物与情节,以弥补素材不足。
秧歌剧的欣赏群体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百姓,他们一年年经受着风吹雨栉,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强烈的。他们向往超越自己,超越现实,向往自身以外的世界。秧歌剧作者把握观众这一心理特征,将欣赏者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憧憬和幻想充实到秧歌剧的创作中,使欣赏者生活中遭遇的无法排解的矛盾冲突,在秧歌剧中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就要在秧歌剧情节设置上,大量运用艺术虚构的创作手法。
经过艺术虚构出来的情节,要比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更形象,更妙趣横生。秧歌剧《锅腰娶亲》只是抓住老百姓生活中传言的“赖汉有好妻”之语,采用夸张的手法表述一个貌美端庄的乡间女子错嫁一个丑锅腰的故事。剧本对小两口由打骂到和好的过程描述,既是生活的无奈坦露又隐含着对生活勇敢面对的态度,当二人洞房之中争吵不休乃至打斗时,新媳妇毫不示弱,将丑丈夫打翻在地,这在受封建礼教束缚、女人讲究三从四德的社会环境中纯属罕见,这个情节虚构成分较多。然而,对自己遭遇不平做出激烈反应的这一剧中厉害的女人,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诸多生活中木讷的女人,更耐人寻味,更具传奇色彩。观众在剧中人物真真假假的打骂中,体味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生活的不和谐之处,而当新媳妇在二大妈劝说下回心转意,认可这门婚姻,并对丈夫唱出“你为天来我为地,奴若欺你如欺天”时,观众又不得不这样认为:剧中闹翻了天的小两口尚可和好,生活中还有什么样的夫妻矛盾不可解决呢?可见,生活中不可能发生或很少可能发生的事,经过秧歌艺人的虚构手法的创作,呈现给观众的是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促使观众对自身生活环境进行新的判断和思考。
秧歌剧要有自己的特点,要吸引观众,必须“常中求新、平中求奇”,在生活中抓新奇故事,使所描写的情节具有新奇感,新奇要建立在符合情理的基础上,不能脱离生活的真实,也不能违背现实生活的逻辑,只有建立在情真、理真基础上的新奇,才能奇而不谬,真实可信。秧歌剧《卖绣鞋》中,罗娇容女扮男装上京寻夫,正逢大比之年而中状元,情节虽过于巧合,但还是合人情的,这足见罗娇容的寻夫真情。秧歌剧《宝成结缘》中王二麻子要杀宝成,却错杀了自己的儿子淘气,也可算一奇,但思之合乎人情物理,王二麻子这种心狠手辣之人做出如此荒谬之事,并不突兀。
情节的新奇,是秧歌剧创作的审美要求,求新求奇,是人们对事物的普遍审美要求。新奇必须是自然而然,如为了加强表演效果,吸引观众,秧歌剧中往往要安插一些插科打诨的情节,这些情节一般都是由丑角来演绎的,丑角是秧歌剧经常设置的角色,因为丑角的行为不太受限,可以任意的插科打诨,产生出其不意的现实效果。
3 语言实对
秧歌剧人物主体与客观世界交流,语言起着直接的作用,所以,秧歌剧人物语言的创作,十分注意通过语言与语言环境的契合,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但在更多的场合中,语言及其环境是作为一个整体在感染着观众,只有经过深入分析,才能看出创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语言是非直观的,必须由演员说唱才能完成艺术形象的创作,还需要观众的认可,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中,尽量缩小艺术形象与生活的距离,使观众产生一种逼真的幻觉。
通俗化的语言内容,再加上必要的语言环境的渲染,能使秧歌剧观众产生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幻觉,由此创造出的艺术形象,自然“不与人隔”。语言在秧歌剧里很重要,一出好戏离不开好的语言,秧歌剧语言最主要的是它的“实对”,是它与观众文化心理、文化素质、文化修养相吻合的表达方式。
秧歌剧语言的第一个特点是浅俗。秧歌剧的语言不同于诗文语言,这是由于它与诗文语言的创作者和欣赏者层次不同。诗文是读书人写给读书人看的,秧歌剧则不同,是民间的大众艺术,它的观众大多是缺乏文化修养的下层民众,若是秧歌剧的语言像诗文一样典雅蕴藉,那么大多数下层观众就无法听懂,定会影响欣赏情绪。所以,秧歌剧语言必须是通俗易懂的老百姓语言,要诙谐、幽默、有风趣。这是由它的自身性质决定的。
《百福图》是较普及的秧歌剧。内容是说挑剔的婆婆虐待贤惠的儿媳妇,不懂事的小姑子又从中挑拨帮腔,好心的公公主持正义为媳妇讨理。剧中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所发生的事件也较普通,而人物语言更是通俗易懂,剧中媳妇王春娥唱到:
正月里来是新年,王春娥在房中哭泪不干。自从出嫁到今日,算一算正好是五年。每日里不是推磨就是压碾,使得俺浑身上下筋骨酸,婆婆还骂俺是懒老婆不爱动弹。
唱词中的“哭泪不干”(眼泪不干)、“使得俺”(累得俺)等均是乡村语言,既有亲切感,又略显浅俗。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显浅俗的同时,又要把浅俗与浮浅、粗俗区分开来。能于浅俗之处见道理,方是编剧高手。如果一味地把浮浅、粗俗当做浅俗,则就失去了秧歌剧的艺术魅力,也就失去了大多数的观众。
秧歌剧语言的第二个特点是重“机趣”。一般说来,诗文重典雅端庄,忌讳机趣纤巧。秧歌剧则不然,它是通过秧歌艺人的表演来让大众欣赏的,所用的语言就更应该注重生动有趣,新鲜活泼。秧歌剧要吸引人,就要注重现场效果。秧歌剧最佳的效果就是语言上的生动有趣。因此,对于秧歌剧的语言来说,要有“精神”,有“风致”,就不能缺少“机趣”。否则,就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
秧歌剧语言的重“机趣”,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注重语言的奇巧。所谓奇巧,就是语言要犀利、尖刻,用得恰到好处。如秧歌剧《百福图》李玉花的一段唱:
李玉花忽听得有孩儿哭,急慌慌忙进了俺嫂子的屋。进房门看见俺的侄儿实在是好,漂白的脸富态态,瞪着个小眼真乖乖,真像从俺哥的脸上摘下来。这件事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段夸侄子的语言生动活泼,尤其是“漂白的脸”、“真乖乖”这些尖新的语言,点破了李玉花从恨嫌嫂子到喜欢侄子这样一个心理的转换过程,一个不太懂事又过于天真的小姑娘的性格活灵活现。二是要重视语言的夸张。也就是说,一出戏总不能板着脸孔向观众做抽象的说教,对于秧歌剧作者来说,要寓教于乐,给观众以美的享受,所用语言就应该别出心裁,将观众的胃口吊起来。因为秧歌剧剧中的人物多是由男扮女,有时为了闹场子、出效果,演员常会运用一些自贬打诨的语言。有些丑角人物的语言很极端,嬉笑怒骂,夸张诙谐,还有直接运用乡间粗话形容某人某事的。如秧歌剧《输钱卖侄》中吕宝与其妻杨氏定计时的对唱。吕宝(唱):
有吕宝俺自小游手好闲,又好吃又好赌,捎搭着嫖老婆。这几日运不济倒了血霉,赌子场把宝揭露出白汤输了钱。这一局输了大洋二百多块,俺只得回家去商议俺老婆。进的门见老婆俺脸红了红,未开言俺双膝跪在地溜平,……杨氏(唱):杨氏女人未开口气儿哼哼,骂一声,你这个穷骨头真是能踢蹬。穷贼你整天的什么事也不做,就知道把牌看把钱来耍,不是押宝就是麻将。俺摊上你这样人那赶上没有强,不知道俺哪世杀了老牛丧天良。小奴俺越骂越是有气,你这个贱骨头瞎披张男人皮。输了钱来告诉俺,狠狠心俺加脚踢,老娘不是还账的。你就是下跪俺也没法治。
“漏出了白汤”“穷贼你真是能踢蹬”这一类粗话,夸大其词,也不够文雅,但却透着谐气,为剧情的发展和人物行为做了铺垫。虽显粗俗,却能将整出戏挑活,将现场气氛挑活。
秧歌剧语言第三个特点是直白。秧歌剧是说唱性的歌舞小戏,剧中人物是通过秧歌艺人的语言和行动来体现个性的。由于秧歌剧面对的欣赏群体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表现的又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凡人俗事,在剧中人物的语言上也就不去过多的讲究含蓄、隐晦,不去兜圈子。往往是一针见血,直白显露,几句话就将人物性格体现出来,几段歌词就将事件交代清楚。因此,秧歌剧剧中人物立言时,非常注意语言的个性化,注意语言与剧中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相符。
秧歌剧《跑四川》剧中人物各具性格,围绕着发家致富还是满足生活现状而展开矛盾冲突。故事大意是:主人公陈老喜为给儿子娶媳妇卖了二亩地,心痛不甘,与老伴商定劝说正在学堂读书的儿子到天府之国四川做生意;儿子媳妇新婚燕尔,恩恩爱爱,不愿别离。几多纠缠终明情理,妻子含泪送别丈夫。多年以后,儿子发财归里,荣耀乡间,成就一段民间佳话。剧中老汉、婆婆、儿子、媳妇四个人的身份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心情不一样,他们的语言也不一样。
老汉唱:有老汉(俺)家住在山东海阳地,我的(那个)名字(就)叫陈老喜。所生一子十八岁,三月里把妻娶。娶妻卖上了二亩地,叫一声我的(个)儿你跑趟四川去,商议商议呢的(个)妈(是)乐意不乐意。婆婆唱:有老身俺听此言笑(之又)嘻嘻,叫一声俺的儿呢细听知:人不得外财不发家。看看人家看看咱,看看西屋你二大妈。你二大爷出了趟外,回来把家发,俺的儿你出趟外,回来把家发。俺的儿呢出趟外,也能(以)赶上他。儿子唱:陈公子家住山东海阳地,四口家有爹妈娶妻一房。我的妻胡氏女进门三个月整,二爹妈丧良心叫我去外乡。天降黑来我之在洞房之上,见贤妻独坐在牙床之上。媳妇唱:一更里来掌上银灯,见丈夫到床前面带愁容。莫不是为妻俺惹你生气?莫不是你下学俺没出迎?……
同样是为去四川,四人的身份不同、心境不同,在语言上表露也不同。勤俭持家的陈老喜心疼卖掉的二亩地,欲让新婚不久的儿子到四川经商赚钱;相夫教子的老伴“笑嘻嘻”的响应,又担心新婚的儿子受委屈,便用邻居二大爷出外发家的例子规劝儿子“我的儿出趟外,定能赶上他”;学堂读书的儿子不谙世事,怨恨爹妈“把良心丧”;新婚的妻子贤惠谨慎,丈夫即将离家远走这样的大事并不知晓,看到心境不好的丈夫,最先想到的是自己是否有过错,小心猜疑:“莫不是你下学俺没出迎”?四位人物四种语言,表达的是四种性格,四种心情,一下子就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面临的矛盾冲突展示开来,将观众引入到特定氛围中,随着剧中人物的行为而思索,或喜或悲,或苦或乐。
秧歌剧语言的直白,是指秧歌艺人要进入所描写的角色中,体会每一个剧中人物在某一特定环境中,某一特定事件面前,所具有的心理状态。按照剧中人物的性格逻辑,去思索、去行动。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要与其同甘苦、共命运。
秧歌剧语言的第四个特点是宾白。宾白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串联贯通、承上启下,二是搭桥、调侃。
秧歌剧虽是大众艺术,但宾白也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口头语言。它是经过艺术加工过的口语,文字精练简洁,意涵丰富。念之琅琅上口,声音铿锵,将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秧歌剧《借女吊丧》媒婆的一段宾白就体现了这一点。
媒婆(白):脚大不算美,时兴把脚放。自小爱说媒,东西走四乡。若问俺的名和姓,人称说媒王。
有时为了调剂气氛,增强现场效果,秧歌艺人常临场发挥说些不贴剧情的话,甚至还会用到外来语。东拉西扯,逗笑出哏,像是在说相声,又象是在演双簧,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秧歌剧《借女吊丧》有一段情节是说教书的先生离开学堂,用功的宝全要温习功课,顽劣的淘气却让其与自己玩耍。二人话不投机,淘气一急之下脱口嚷出:“你若不干,俺便挥俄罗斯的巴掌揍你”。“俄罗斯”是乡间艺人发挥的语言,听起来有些离谱,也很荒诞。但将“俄罗斯的”四个字一用,却骤然增添了趣味,也烘托出淘气不学无术、滥用词语的顽劣秉性。这样的宾白秧歌剧中还有很多。这些荒诞的语言非常有助于刻画剧中丑角人物,能活跃现场气氛,老百姓并不去挑剔它是否合乎语言逻辑。
秧歌剧的宾白常用到地方方言,并且不加修饰,显示它的地方性和大众性。在运用方言时,又很注重民间的自然语言,注重它的地域与时间的局限,注重某一时代、某一地方的民间流行方言。这样对该时该地的观众来说,不但是能听得懂,而且听起来有亲切感。这种运用方言“说唱”的风格,虽然保持了秧歌剧的纯朴的乡野味道,但也有它的弊病,那就是对于后世和外地观众来说,听起来就不那么顺耳了。秧歌剧既然是地方民间艺术,就应该固守地方色彩,保持它原始的本色,保留它的文化、它的所长。只有固守了它的地方特色,才会更有生命力,更具民众性,才会具有它的存在意义刻意地要求它往哪一方面靠就失去了它地域文化的特点。
4 曲谱活用
秧歌剧必须遵循曲谱。曲谱是秧歌剧创作填词的准绳,它具体规定了每段唱词的节奏、句格。从遵守曲谱这一点来说,秧歌剧创作在固守主题、故事、情节的基础上,按曲谱填词,似乎是在“依样画葫芦”,容易得很。其实不然。填词不能死守成规。秧歌剧既要遵守曲谱,依谱填词,又不能为曲谱所束缚。曲谱虽然具体规定了每种曲调的样式,但运用起来,却妙在“死中求活”。
同样是依谱填词,由于运用方法不同,就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效果。秧歌剧的曲谱,多用《跑四川调》,也有用《锔大缸调》的,还有用民间花调的。 《跑四川调》是以秧歌剧《陈老喜劝子跑四川》而命名,此曲调富有四川民歌风味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唱词以十字句为基本,第四句与第五句为七言短句,连起来唱时,占用一个长乐句的时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跑四川调》也应属六乐句结构方式。在长期流行中,各地民间艺人,沿用此曲发展、变化,运用到其它秧歌剧中,仍称为《跑四川调》。故也出现五乐句组成的曲谱,其特点基本上与以上七乐句板式相同。
同是运用《跑四川调》,就有许多种唱法。有长音,有短音,有加滑音,也有加颤音的。而且,在一出戏中男角色与女角色,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老者与少者唱法也不相同。这足以说明秧歌艺人无时无刻不在追求“花样无定式”,寻求走出死守成法的路子,力争在秧歌剧的创作上不受曲谱所限制。
(责任编辑 李沛茜)
J825.52
A
1673-5382(2014)03-0005-05
2014-06-29
烟台市社科规划课题“烟台地域特色文化研究——海阳大秧歌”的阶段性成果.
姜雪芹(1963-),女,山东海阳人,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主任护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