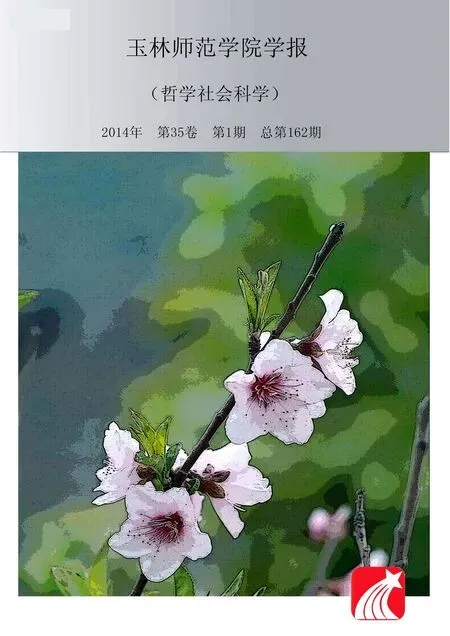广西边疆地区民俗文化翻译
——民族身份认同与翻译策略互补
□杨 琳,刘怀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系,广西 崇左 532200)
广西边疆地区民俗文化翻译
——民族身份认同与翻译策略互补
□杨 琳1,刘怀平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系,广西 崇左 532200)
广西边疆地区民俗文化具有强烈的地域与社会文化色彩,翻译活动有助于传播壮族及其他少数族裔古老历史及璀璨文化,也是增强边疆地区民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途径。然而,民俗文化翻译在边疆民俗文化对外传播中仍是一种派生的语际转换活动,导致标识民族身份的异质性语言文化无法得到较好的彰显与传播,因此采用互补翻译策略既有裨于壮族及其他少数族裔重塑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也可促进边疆民俗文化在东西方跨文化交际语境中与他者的良性互动。
广西边疆; 民俗文化; 翻译;身份认同; 翻译策略互补
一、引言
民俗文化(folk culture)是民间大众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范畴广泛,涉及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岁时节日、民间文学、婚丧嫁娶等物质与精神文化活动。[1]广西边疆地区民俗文化是壮族人民及其他少数族裔与社会生活与交际活动的文化体现,具有强烈的地域与社会文化色彩。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成立以来,北部湾经济区(南宁、北海、钦州与防城港)与崇左地区等已成为广西与东盟各国实现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窗口,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概而言之,学者或将广西边疆文化与旅游联系起来,探讨旅游文化的开发原则以及开发措施;[2]或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壮语词汇的文化色彩,从而引起人们透过不同词性关注壮族情感表达的细腻及思维方式的具体性;[3]也有学者从文化学角度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活动进行实地访查,研究香火球及壮族板鞋舞等运动所体现出的文化意蕴等等。[4]这说明在经济一体化与文化趋同论的浪潮中,人们开始意识到保存边疆民俗文化是壮民族及其他少数族裔彰显其身份标识的重要途径。翻译活动是边疆民俗文化与东盟其他各国乃至全世界进行对话的媒介和桥梁,但是,由于边疆语言文化独特的民族性及地域性,难以甚至不可能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译者关注更多的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活动多为应景式的商用翻译或旅游翻译,从而失落或歪曲了其中所能彰显少数民族身份的文化信息。这是边疆地区风俗文化中译外工作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二、广西边疆地区民俗文化翻译现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作为其中最大的经济实体,其“独特发展道路和巨大文化影响力,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是出于交流的愿望还是抗拒的目的,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越是发展,来自国外的了解欲望和关注程度越强,对中译外的需求也就越大,所涉及领域也迅速扩大”。[5]广西边疆地区尤
其是东兴、上思、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等八县市与越南接壤,处于中国与东盟其他各国交流的最前沿,还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以及苗族、瑶族、水族、侗族、京族、仫佬族、哈尼族、彝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发源地。毋庸置疑,除了能够飞速发展边疆地区经济之外,这是民俗文化向外界焕彩的黄金机遇。但是,边疆民俗文化的翻译现状却不容乐观。一方面,目前可资利用的翻译资料仍散落在旅游指南、商务文化节宣传资料或门户网站的简单介绍当中,没有形成系统的有组织的民俗文化翻译材料,令国外友人欲窥民俗文化之全貌而不得。原因之一是边疆地区翻译人才严重不足,无法组织大规模的民俗文化翻译活动,小语种如越南语、泰语的合格翻译人才缺口更大。翻译材料多限于商贸合作及涉外旅游方面,涉及民俗文化的翻译活动因其语境的复杂及文化独特性等特点而举步维艰;另一原因是“从事翻译工作的主体是不具备任何专业资质的‘业余翻译’或‘兼职翻译’,不是职业翻译”,[5]这就导致了边疆民俗文化对外翻译的质量令人担忧。另一方面,现存可资查阅的翻译资料存在很多问题,有的是译者择词错误或表达不当,有的则是译者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对民俗文化进行了错误的文化假设或朦胧处理,将准确与通顺割裂了开来,形成了严重的翻译腔。上述情况可从北部湾旅游联盟(BGTU)推出的精品旅游线路自助游指南英译本中试取两例进行说明。
原文(1):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独具魅力的渔家风情和古朴瑰丽的山水风光完美融合,让人目不暇接、浮想联翩、身心畅游。①
译文(1):Perfect combination of colorful folk customs, profound religious culture, unique fishing style and charming landscape shall put you in amazing imaginations and refreshing.①
原文(2):崇左最有名的特产要数八角,苦丁茶,指天椒和沙糕,白砂糖,除此之外,宁明的玉桂、砂仁和佛手果等中药材,龙州桄榔粉,枧木菜(砧)板,大新的龙眼,桂圆肉;扶绥天大香糯沙糕、稻杆画等。②
译文(2):The most famous specialty in Chongzuo are the anise, broadleaf holly leaf, conical redpepper fruit and Sha Cake, white granulated sugar, besid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like cinnamon, fructus amomi and bergamot in Ningming, Guanglang Powder in Longzhou, the chopping board made of Jian Tree, longan from Daxin, dried longan; Tianda sweet glutinous rice cake and rice stalk painting in Fusui County, etc.②
无论是对边疆地区风俗文化泛而统之的介绍如译文(1),还是对令人垂涎欲滴的民间饮食之详细罗列如译文(2),均为散落在旅游指南或商务文化节等介绍中的极为有限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缺少越南语或泰语等对应译文,而且因忽略不同民族的语言文体及风格差异导致了对边疆民俗文化翻译的扭曲与变形。民俗文化介绍材料夹杂在旅游文体或广告文体当中,而不同民族的语言文体及风格存在诸多差异。旅游及广告等文体有的突出其“呼唤型”功能,重在增强文本对读者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有的突出其“信息型”功能,文字简洁明了,就事论事,不事雕琢。在汉语当中,“呼唤型”文本“历来深受汉语古典山水诗词及山水游记散文一类作品的影响”,偏爱“文采浓郁”的对偶平行结构和连珠“四字格”的华美行文,[6]如原文(1)中多四字成语及四字成语加“四字格”词语堆砌的偏正词组,辞藻优美,意境融合,符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为了忠实传递文化信息,适当中国化的句式(sinicized patterns)翻译是必要的。分析译文(1),虽然除了最后一个词语“refreshing”词性选择及表达令人困惑外,表达基本无不当之处,但却忽略了英语读者崇尚简洁、信息准确以及直观实用的行文方式,没有清晰地展示出物象,既未迎合译语读者的审美心理,也未达到有效的宣传目的。因此,这种片面注重字面对等的翻译方式忽略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给译语读者造成一种山重水复却无路的感觉。原文(2)突出的是文本的“信息型”功能,此类文本英汉两种语言中基本属于同等结构,重在罗列信息,语言风格以明快为主。原文(2)与译文(2)焦点信息都在民俗文化日常生活特产介绍上,译文符合英语语言由焦点陈述到解释罗列信息的思维之流。但仔细分析,译文(2)既未实现译文的准确与通顺,择词与句式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方面“The most famous specialty in Chongzuo are”就存在严重的翻译腔,另一方面“specialty”在数的形式上既与后面的“are”难以匹配,也与随后出现的种类丰富的特产无法对应,
“沙糕”一词译文前后不一,句中的“besides”也显得突兀不当。译文(2)不仅反应出译者专业资质欠缺,而且译文缺乏严谨的复审校核,既不利于边疆地区民俗文化的传播,也给其参与世界文化的多元对话制造了障碍。因此,只有当译者意识到边疆地区民俗文化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参与世界间对话与互动的重要性,边疆民俗文化的翻译才会真正具有生命力,才能摆脱在旅游文本与经济商业活动宣传资料中的寄生状态。同时,边疆民俗文化翻译活动的从属地位及语言与文化误读不仅消解了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界限,而且因译者所采用的不当翻译策略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紊乱,进而失去了有效传播少数族裔民俗文化的良机。
三、民族身份认同与翻译策略互补
身份认同指“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指一个人对于自我特性的表现,以及与某一群体之间所共有观念(国籍或者文化)的表现”。[7]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可以界定为少数民族在主流文化群体与本族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身份抉择。由于主流文化的不断推进,广西边疆地区壮族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本族文化持续受到冲击而逐渐处于一种亚文化的受制地位,从而导致其民族身份认同的紊乱或向主流文化不断靠近的身份变位。同时,广西边疆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壮族及其他少数族裔历史与文化的强烈地域色彩,主流政治与意识形态外介的首要性及翻译人才欠缺等各种原因,民俗文化翻译活动愈加处于边缘及派生的次要地位,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之独特视角与敏感难以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但是,边疆地区民俗文化翻译是中华民族文化对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本身的多向度色彩,使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了解日趋全面,而且翻译活动对民俗文化的足量及有效介入与少数族裔与亚文化群体身份正位及认同心理关系紧密。Edwin Gentzler在其《美洲的翻译与身份认同:翻译理论的新方向》(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mericas: New Directions in Translation Theory)分析了翻译活动对构建多元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译者通过翻译这种重要的语际转换活动,既可塑造一种文化身份,将其新奇潜在的异质性呈现在其他社会历史文化面前,还可通过这种翻译活动使得该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拥有话语权,从而让他者了解其独特的文化身份。[8]“据《2013-2017年中国民俗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与投资战略分析报告》显示,尽管近年来国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护民俗文化,但仍主要集中于非物质文化保护国家制度的确立与学术界发起的“救亡图存”式的田野调查工作,而对于民俗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及其在整体文化产业结构中的转化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则明显不足”。[1]立足于这个角度,广西边疆地区民俗文化的足量有效翻译首先可使其在汉语文化大环境中获得身份正位,摆脱主流文化对其长期以来的圈束,进而在大环境之外与他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彰显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与意识形态。那么,如何展开边疆地区民俗文化足量有效的翻译活动,进而形成少数族裔对其民俗文化的身份认同,实现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对翻译原材料(source material)的足量滤取。原材料不等同于原本(source text),一定是民俗文化最原始最具有代表性的材料,而非他人所为的改编本。广西边疆地区民俗文化原材料虽不胜繁数,但译者在择取过程中首先要将其从大众熟悉的或冠名为“中国的+世界地名”的旅游景区材料中隔离出来,选择能够反映民俗文化精髓的材料。如防城港地区的饮食与节庆等民俗文化信息夹杂在江山半岛省级旅游度假区旅游指南中,而该度假区被冠以“中国夏威夷”,进而被译为“Hawaii of China”。这种求同去异的作法对民俗文化的推广毫无裨益,不仅使民俗文化中异质性的东西因景区名称的熟悉化与他者化而失去自身的吸引力,剥夺了少数族裔对自身民俗文化心理上由来的骄傲感与自豪感,而认为在文化上没有被代表而退出这种文化体系,从而在无意识或被迫的情况下加剧身份认同的问题,这种危机并非与翻译活动毫不相干。防城港地区十二月份的“金花茶节”与农历六月初十京族的传统节日“哈节”等少数族裔气息浓郁的民俗文化仅以短语的形式出现在旅游小贴士当中,译文也是简而又简;崇左地区骆越文化神韵之精髓宁明县花山(pay laiz,岜莱)岩画,仅用了寥寥数句“……画幅最大,画像最多,分布最密,形象最高大的一幅,是左江原始岩画之王”进行泛述。岩画本身内容的丰富多彩与扑朔迷离,壮族先民的“蛙神”崇拜以及相关的神话传说也可能随着其笼统有限翻译腔严重的介绍材料“…the one whose sizes
are the largest, images are the most, distributions are the densest, and the images are the tallest. They are the kings of the Zuojiang River’s original cliff paintings”③与他者的了解欲与好奇心失之交臂。因此,译者应独辟蹊径,将能够彰显边疆地区民族身份以及塑造民俗身份认同感的民俗文化的材料另立专栏进行翻译,而非进行简单素描或者将其作为旅游小贴士放在不显眼的位置。
其次,如前所述,由于边疆地区民族民俗文化的独特视角与敏感,翻译策略不应固步一格,而应在互补中求取较为满意的译效。德国学者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认为为了彰显民族语言及传承民族文化,应该在翻译中尊重其他民族语言及文化中的异质性。美国学者Lawrence Venuti(韦努蒂)在Schleiermacher的理论基础上首创译学术语“异化翻译法”(foreignization或alination)与“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on),此后关于两种翻译策略的争论与探讨便不绝如缕。有的学者强调语言翻译重在交际,因此归化翻译策略采用译语读者所熟悉的语言习惯与文化价值,尽可能靠近读者的语言场与文化场,最大程度地减轻源语语言及文化中异质性的事物,可以使读者自然流畅地接受译文,实现语言的交际目的;与此相对,有的学者主张只有运用异化策略,疏离译语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场与文化场,在译文中竭力保持其他民族语言与文化陌生的异质性,才能刷新译语读者读者既有的语言认知与文化价值观,给他者世界带去一种新的隐语视角和全新体验。[9]
考虑到边疆地区民俗文化的特质及翻译民俗文化的目的,异化应该是首选的翻译策略。借助此种翻译策略,译者一般通过直译的技巧,对抗性地疏离了主流文化或强势文化的圈束,聚焦于边疆地区少数族裔所特有的语言及文化编码,在用译语读者熟悉的语言解码转换后所呈现的却是截然陌生的主题、意象或意识形态,进而刷新译语读者的常规思维与审美体验,延长译语读者的关注时间以及感受难度。试举民俗文化中节庆为例:
原文(3):“……武鸣三月三歌圩、宾阳炮龙节、马山黑山羊文化旅游节、上林生态旅游养生节、隆安‘那’文化旅游节、邕宁八音、良庆香火龙等。”④
译文(3):“…Wuming March 3 Song Fair, Binyang Gun Drangon Festival, Mashan Black Goat Cultural Tourism Festival, Shanglin Eco-travel Health Festival, Long’an ‘Na’ Cultural Tourism Festival, Yongning Eight Musical Instruments Festival, Liangqing Incense Dragon Cultural Festival.”④
原文(3)罗列了数个壮族及其他少数族裔民俗文化节庆名称,语言表达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将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翻译确实地履行传播信息,促进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交流”,[10]译文(3)中以源语为主体,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翻译节庆名称中标新立异的语言形式,从而使得译语读者通过关注陌生化的译本进而激起他们了解源语民俗文化蕴涵的欲望,这对于传播边疆地区民俗文化及增进民族身份认同的意义尤为重要。如“马山黑山羊文化旅游节””译文中的“black goat”,在英文中除了其动物含义之外,现实当中更多的用法是其贬义延展如“替罪羊、蠢人、色鬼、劣等人或物”等等。这种文化反差会产生一种审美距离美,在译语读者理解了源语内涵之后给他们留下更深的印象,也为民俗文化走向他者创造了更多的契机。当然,译文(3)有值得商榷之处。“歌圩”是壮族古老的风俗习惯,男女老少盛装赴会,聚众数百乃至上万人进行山歌对唱。“歌圩”重在“歌”,此“歌”应重在过程及动作,因此选用“singing fair”或更能体现歌者的参与性与愉悦心情;“炮龙节”、“生态旅游养生节”与“香火龙”等节日的译名的异化译法也值得商榷。
然而,一味强调对抗式的异化策略并非上策。在边疆地区民俗文化外介过程中,由于少数族裔异质的语言文化特色,过度的直译会导致译文与译语读者所熟悉的语言文化的强烈冲突。译者未考虑到源语当中的文化信息并囿于固定的思维模式,忽略了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的可译性限度(limit of translatability),即从时间向度而言语言与文化相对的不可译性,从而为读者设置了过多的阅读、审美与理解障碍,进而导致他们对源语文化的阅读、审美与理解产生气馁放弃之心。因此,译者在适当地采用异化策略的基础上,采用归化策略可以有效地缓解文化冲突,通过意译技巧“对原文进行描述、解释和曲折婉转的陈述传达出原文的所指意义”,以“消除源语和译语之间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11]使读者有效全面地理解译文的内涵。如下例:
原文(4):三娘湾景区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广西十佳景区之一,著名电影《海霞》拍摄基地,更是中华白海豚(五彩海豚)的生态家园。⑤
译文(4):San Niang Bay is a national model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one of the ten excellent scenic spots in Guangxi, the shoot base of famous movie“Haixia”,and the ecological garden of Chinese white Dolphins(Wucai Dolphins).⑤
原文(4)不仅是是旅游信息,其间所蕴含的民俗传说与文化气息非常浓厚。旅游文本的纯粹描述性信息介绍及译文对文化特色词语的过度追求很大程度地降低了译语读者的了解欲望与交流兴趣,遑论有效传递标识边疆地区壮族及其他少数族裔特征的民俗文化信息了。“三娘湾”直译为“San Niang Bay”,虽然遵从了对地名翻译应尽量采取“地从主人”的异化原则,但消解了其背后三位美丽的仙女娘子的动人传说。同时,“San Niang Bay”存在误译现象,“三娘”若按照地名直译是一个整体概念,对应译文为“Sanniang Bay”;但取其民俗传说与文化信息而言,“三娘湾”的译名采用归化策略意译为“Thee Ladies Bay”或者(The Bay of Three Ladies),或许更能激发译语读者进一步了解此旅游信息背后所婉转陈述的文化渊源;“中华白海豚”有其固有的学名“Sousa chinensis”,却被直译为“Chinese white Dolphins”,若是译者有意为之,可在学名后面附加其异化译法表现源语的语言文化视角。但“五彩海豚”被直译为“Wucai Dolphins”不仅无异于保护源语文化,反而暴露出译者将自己限制在狭窄的的词汇储备当中的尴尬处境。同样,译文(3)将“炮龙”中的“炮”译为直译为“gun”,除了译者未详察源语中“炮”(此处对应译词宜为firecracker)的语域要大于与英文中“gun”的含义,而“香火龙”与“熏香龙”的意义也相去甚远。由此看出,归化在许多情况下不仅是一种灵活变通的手段,还是向译语读者自然流畅地传递源语文化信息的重要策略。如果采取更加有效的宣传手段比如在旅游指南后面附上专门的民俗文化译文小专栏,或者形成专门的民俗文化翻译材料,边疆地区壮族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民俗文化在与他民族文化相互碰撞、沟通、理解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身份标识并获得不断成长便值得期盼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元素,广西边疆地区民俗文化对在彰显壮族及其他少数族裔身份特征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有效足量的翻译活动不仅可以向世界文化奉献只有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质的东西和语言现象,而且有助于增强边疆地区民族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但边疆民俗文化翻译中频繁出现的问题也是译者在传播东西方多元文化过程中永远也无法回避的。为了有效传播边疆地区民俗文化信息,译者不宜拘囿于单一的翻译策略,异化与归化、直译与意译的交替互补才可以在准确传达具有强烈中国地域色彩的语言时,确保文化信息的高效传递。译者只有意识到边疆地区民俗文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参与世界多元文化对话与互动的重要性,边疆民俗文化的翻译才会真正具有生命力,才能更好地为壮族与其他少数族裔身份特征代言。 ■
注:
①北部湾旅游联盟(BGTU)精品旅游线路自助游指南:北部湾民俗文化游
②北部湾旅游联盟(BGTU)精品旅游线路自助游指南:崇左特色饮食旅游小贴士
③北部湾旅游联盟(BGTU)精品旅游线路自助游指南:崇左骆越古韵神奇边关景点推荐
④北部湾旅游联盟(BGTU)精品旅游线路自助游指南:南宁地区节庆介绍
⑤北部湾旅游联盟(BGTU)精品旅游线路自助游指南:海豚之乡钦州
[1]民俗文化[D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556712.htm#2.
[2]黄建清等. 广西花山旅游文化开发研究[J].茂名学院学报,2007(4):67.
[3]韦达. 壮族词汇的文化色彩—壮族语言文化系列研究之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81,82.
[4]兰政.广西壮族香火球运动的文化学分析[J].体育学刊,2008(10):100.
[5]黄友义.中国特色中译外及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在第二届中译外高层论坛上的主旨发言[J].中国翻译,2011(6):5-6.
[6]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111.
[7]identity[DB/OL].http://zh.wikipedia.org/wiki/ %E8%BA%AB%E4%BB%BD%E8%AE%A4%E5%90%8C
[8]Edwin Gentzler.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mericas: New Directions in Translation Theory[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
[9]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0]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8.
[11]李正栓等.归化也能高效地传递文化-以乐府英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1(4):51.
【责任编辑 谢文海】
Analysis of Folk Culture Translation of the Border Areas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National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utual Complementation
YANG Lin1, LIU Huai-ping2
(Foreign Languages Dep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ongzuo 532200)
The folk culture of the border areas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possesses very intense local and socio-cultural colors. Translation of the folk culture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splendid ancient cultures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and other minority ethnic groups, but also a very significant approach to the promotion of these people’s identity recognition. However, translation of the border area folk culture is still of a derivative interlingual conversion, which is weak in spreading the exotic lingual and cultural
border areas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folk culture; translation; identity recogni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utual complementation
H172.2
A
1004-4671(2014)01-0017-06
2013-09-01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边疆问题研究”专项课题,项目编号:XWSKYB2010008。
杨琳(1974~),女,甘肃宁县人,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博士生,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
elements of the minority ethnic groups and indicating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sens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erve a good way to remold the uniqu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Zhuang people and other minority ethnic groups promote the benign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border area folk culture and the other world cultures as well .
——基于扩展的增长核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