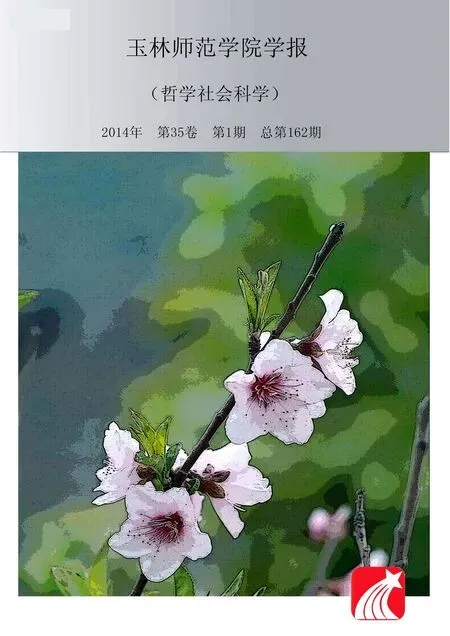当代北海疍民生计变化与选择论——以央视近年来拍摄的三部专题片为例
□吴锡民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一、央视镜头中的北海疍家人生活变化
疍家(即水上人家),让人听起来是个富有诗意而形象的称谓,一说源于他们居以为家的舟楫,外形酷似蛋壳,漂浮于水面;一说因为这些水上人家,长年累月生活在海上,像浮于饱和盐溶液之上的鸡蛋,所以被称为疍民。而疍家人自己则觉得,他们常年与风浪搏斗,生命难以得到保障,如同蛋壳一般脆弱,故称为疍家。据有关文献,北海疍民主要由粤籍、也有少部分闽籍、琼籍疍民等外来群体构成。早在明朝,粤籍疍民就开始陆续流寓北海,眼下聚居银海区侨港镇的归侨,绝大部分是当年从广东前往越南谋生的疍民,也有部分本身就是由北海侨居越南的,还有一部分来自钦州、防城沿海地区的渔民。新世纪以降,这个特殊的群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央电视台近年来播放了几部介绍北海疍家人生活近况的专题片,它们分别是:央视4频道“走遍中国”栏目的《疍家人的海上婚礼》(2010年4月)、央视4频道“远方的家•沿海行”栏目的《北部湾明珠——北海》(2012年5月,该片由五个单元组成,其中的两个单元的题头是,“北海:疍家人水上生活”和“北海:三婆庙里看疍家民俗”)以及央视7频道“乡土”栏目的《寻访采珍珠的疍家人》(2012年11月)。从这些专题片中,我们可以在下列的主要层面觅到问题的答案。
首先,疍家人的民风民俗得以风光重现。北海的疍家人过去是“以舟楫为家”的水上居民,靠海上捕鱼为生。独特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在性格、语言 、服饰、饮食、居住、婚俗等方面都自成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疍家文化。迄今不少疍家人已上岸居住,很多人不再从事海上捕鱼作业,疍家传统风俗也随之经历了变迁。传统的疍家婚礼一般为两天,在水上联舟成排、张灯结彩,举行男女对歌、送礼、取花等活动。现在,疍家的传统婚俗正在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举办传统疍家婚礼的新人可以说少之又少。央视专题片《疍家人的海上婚礼》的拍摄与播出,据北海官方所了解到的情况称,北海的疍家人无不欢欣鼓舞。他们认为,一是可以忠实纪录现阶段的疍家婚俗,定格历史,让疍家人的子孙后代知道他们先人曾经有过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充分肯定疍家人在北海的社会地位,为提升北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疍家文化无疑有着自身独特和应有的贡献。[1]
其次,疍家人的水上生活得到不断改善。目前,生活在北海的疍家人就有几十万,其中大部分疍家人都已改变了以船为家的生活方式,住进了岸上新建的房子里。可是,侨港湾里(广西最大的渔港)的疍家人,却难以割舍祖辈传承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他们身边海域的深厚感情,不论日常劳作,还是吃饭睡觉全都在船上。虽然当地政府给每户疍家人安排一套住房,但是,为了方便每天出海捕鱼,他们继续维持“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的生计。不过,这种选择与过去相比,也有了显著的变化。过去疍家人世世代代与风浪相伴,出海时靠烧香和求神拜佛来祈求平安,倘若遇到天气突变,海上风浪汹涌的时候,来不及返回的疍家人经常被大海吞没。反观现在,疍家人的渔船上一般都安装了卫星导航设备。不仅如此,一日三餐用煤气罐做饭,闲暇之余呆在船上看看影碟等,对疍家人来说,它们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再次,疍家人采珍珠的古珠池——乌坭池重现生机。“乌泥”是个古名,不仅是历史上北部湾天然珍珠出产最多的海域,而且也是至今唯一保留完好的千年古珠池。乌泥村的祖宗是采珍珠的疍家人,后来现代的疍家人把家从海上安到了岸上,建起了乌坭村,已不再过祖祖辈辈在海上四处游弋的生活了,但是都以采珠为主业。乌坭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个体养殖珍珠,发展到后来有组织管理的科学养殖。原先沉寂多年的乌坭古珠池,如今在其中心位置建起了便于养殖与管护为一体的海上大棚。回溯过去,那个年代采集珍珠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俯视现在,时代在进步,疍家人的祖辈们一定没想到当年他们需要在海底煞费苦心寻觅的珍珠,现时竟然可以通过科学的养殖方式来完成。人工养殖的珍珠螺,颗粒圆润,学名叫马氏珠,疍民称其为南珠。古语云: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在历史的记忆中,当年乌坭村的疍家人采集南海珍珠时候,必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如此业内行话的自豪感。
二、变化缘由与疍民量力而行生计选择
央视镜头下的北海疍家人生活发生上述变化的根本原因何在?当中反映出他们怎样的生计选择?通常的答案往往会归结于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我以为,这固然是个不错的“省劲”回答,但终归没有以北海疍家人切身经历为例作答来得更有说服力些。多次亮相于从中央到地方电视荧屏中的、来自北海地角上寮小区的疍家阿婆麦九妹(1930~),在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走进北海》(2004年12月20日)的晚会上,引亢高歌一曲“咸水歌”(“疍家渔民住海边哎,海中渔船把网撒哎,疍家姑娘好风光哎,渔船借水走四方哎——”)之前的一番开场白,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当时,她满怀深情地说道:“解放前,我们渔民过的是苦日子;解放后,苦尽甜来过上了好日子。改革开放后,靠打鱼和做渔货生意又发财致富,感谢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好政策,我们疍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开心,渔歌越唱越响亮了!”[2]与麦九妹有着相同看法的,还有来自北海侨港镇的、将要跨入古稀之年的归侨郭其友。他以自己归国后的切身经历,感受到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更加深信勤劳能够致富。他在广受疍民欢迎的“咸水歌”中唱道:“渔民生活靠做海,自身勤劳是应该,改革开放政策好,幸福生活党带来。”[3]从麦九妹到郭其友,前者在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初,抓住机遇,靠打鱼和做渔货生意,成为北海当时为数不多的“万元户”,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方今,她怀着“渔歌唱出心头爽”的心情,将生意交给儿孙们打理,自己则醉心于享受有感而唱咸水歌的清福。而后者则抓住国家对渔业生产扶持力度不断加强的时机,通过银行贷款的支持,不仅投资建造了42米长的铁壳船,而且购买了两套三室一厅的商品房,后来家里又兴建了一栋三层楼房。现在,他将渔船全部交给儿子管理。不过,他仍在关注侨港的渔业发展。
上述例子,无不有力地表明,作为北海疍家人的代表,麦九妹、郭其友的生活之所以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全靠党的富民政策的深入人心和大力落实。至于在北海疍民当中有多少人能达到麦九妹、郭其友那样的生活水准,在我看来并不重要。因为具体到不同的疍家人的家境,他们当中所发生变化也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这的关注点则偏重在他们当下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事实上。例如,据中新社记者肖欣的《广西北海侨港镇归侨:有没有船都是“疍家渔民”》(2011年10月19日)报道,刚满周岁就来到侨港镇的归侨吴黎雄,现在已经不再打鱼了,将自家小楼一层装修成卖各式手机的店铺,而他家隔壁就是兄嫂的小超市。在吴黎雄看来,经商和捕鱼靠的都是“疍家精神”。疍家渔民常年生活在渔船狭小空间中,养成了勤劳、爱干净、能吃苦的习惯。学过财会、扛过米包、卖过影碟的吴黎雄坚称,虽然不再出海捕鱼,但是自己仍属于有疍家精神的疍家人。另一位归侨卢德华来到侨港时已过而立之年,在越南上学、工作、娶妻、生子的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咸水鱼到了淡水能不能活?祖祖辈辈的打鱼营生能不能继续?”与他一同驾小艇回到中国的胞姐便是出于这种担心,后辗转经香港又去了美国。30年来,亲历了侨港镇从渔业大队到集体承包再到个人承包的变迁,卢德华不仅能继续打鱼,而且来时的小船,慢慢换成了大船,现在还在换。近几年他姐姐回来探亲,停留的时间愈来愈长,她甚至开始“后悔”当年的赴美做法。由此可见,有船的、没有船的疍家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证明,“咸水鱼不仅活了下来,还能游得更远”。[4]
“游得更远”并非拔高夸大之戏言。事实上,不管现在北海哪一场所的“海上游牧民族”——疍家人生活处境如何,我敢说,他们全都大大胜过同样享有“海上吉普赛人”之称的、马来的巴瑶人。终年生活在马来西亚仙本那(Semporna)岛附近海域上的马来原住民——巴瑶人(Bajau),已经有了几百年的海上漂泊历史。他们经常穿梭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水面上,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国籍的海上游牧民族。这里仅就各自与陆地的关系而言,北海的疍家人基于生活质量提升所需(诸如煤气罐、电视、蔬菜等),与陆地的联系较为紧密;而马来的巴瑶人似乎一切皆取之于海洋,就连平常栖居的生活用品,诸如锅碗瓢盆之类的,大都捞自于“文明世界”丢弃在海上的漂浮物。设若他们要下船靠岸,顶多也只是为了取点淡水或弄些柴火或到集市上以物换物。加拿大人莱斯•斯特劳德(Les Stroud,1961~)拍摄的《超越生存:海上吉普赛人》(2011年)纪实片,曾在国内各大电视台“探索”栏目播放。该节目真实记录了马来的巴瑶人生存状态,作者在片尾指出:“目前为止,巴瑶人在海上的生存,是自古以来人类与大自然万物不懈斗争的典型案例。在不远的将来,面对现代化和人类破坏海洋环境的恶果,巴瑶人的聪明才智和自给自足将会经受住考验。又一种文化,又一个世界,要么成为历史,要么超越生存。”[5]相形之下,问题很显然,北海疍家人的境遇比起马来的巴瑶人,则更令人感到“风景这边独好”。
如果说北海的疍家人的生活境况,与“他者”比照,的确宛若一首“咸水歌”所唱道的那样:“疍家渔民乐海天,撒网捕鱼舞翩跹;一网鱼来一片笑,生活是处幸福园”;那么我们在北海不同地点的疍家人之间也来个比较性的粗略提及,又会是怎样的具体情况呢?在上文中我们有过一定的交待,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就拿北海疍家人又一集中生活的地方——地角来说吧,它与侨港的疍家人不同的是,这里的疍家人很早就搬到岸上的房子里居住了。再比如,外沙岛的疍民多半是北海土生土长的海上居民,民风民俗比较传统正宗,传统仪式风俗保存较好;而侨港镇的疍民主要是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战争原因而被迫返回国内的越南华侨,或从广东迁徙而来的疍民,民风民俗与原始北海疍民略有差异。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来自北海哪个处所的疍家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是在岸上还是在海上,都离不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大海。比如,有的疍家人在岸上经营干杂海货生意;有的疍家人在海边从事海产品养殖业;有的疍家人习惯于举家出海打捞“海鲜”等。这也就是说,在北海不同地方的疍家人各自有着量力而行的生计选择,而这些选择又都游离不出“靠海吃海”的疍家人传统的生存之道。不过,相对来说,央视镜头下的、以渔业为主的侨港镇的疍民,坚守疍家人传统的生存之道的意志更突出一些。当然,这对央视影像中的、那些养殖珍珠的乌坭村的疍民来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同样毫不逊色。
三、疍民中依然如故生活背后认识价值
量力而行地进行着各自的生计选择是当代北海疍民生存之道的基本诉求。在这种诉求中,央视镜头下的北海侨港湾里的那些渔疍以及合浦乌坭池大棚里外的那些珠疍,面对新世纪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大潮,却仍然留恋着他们的祖辈们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大海的那种生活。以泊居于侨港湾口上的疍民卢春荣一家(拢共五口人)为例,船老大的儿子卢春荣(小学文化程度,全家唯一能说普通话的人)向央视记者娓娓道来他们家以船为伴的水上生活。日复一日地在海上进行捕鱼作业,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时除了买东西之外,很少到岸上去。陆上的灯红酒绿,他们也目睹过,但是从未想过上岸谋求其它的生计。赚来的钱只求一家人生活基本够用,知足于家人的健康平安。他们在这种平静而简朴的生活中自得其乐。这种自足自乐的简单生活也同样是乌坭村疍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乌坭村的珠疍们虽然把家安在了岸上,但是一天到晚还要不时下到海里,打理乌坭池的珍珠养殖,他们和他们的先辈一样,一生都在仰仗于他们身边的海域生活。珍珠虽然美丽夺目,但是获取它的过程,无论是过去的天然采集,还是现在的海水养殖,不知要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然则,他们却说,日子虽苦,但是很满足。特别是其他疍民忙碌了一天之后,陆续返回到岸上,而继续留守在大海大棚里的那两位渔民,则还要度过枯燥乏味乃至寂寞的夜晚,可是他们却泰然面对这种一成不变的每天轮回。
疍民们(不管是渔疍还是珠疍)“涛声依旧”的生计选择,也许会令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现场采访疍民的央视记者却并不诧异。她认为:“许多习惯了常年海上生活的疍家人,为了方便每天出海捕鱼,他们还是生活在船上。岸上有许多的繁华,他们也见到过,但是那些东西并不能改变他们。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们一辈子都在做着一件事,而且在这件事情当中自得其乐。我们不能够说他们的生活好或不好,因为幸福都是他们自己的。”[6]我觉得,言之虽然有理,但是不够透彻。记得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中说过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在人觉得可爱的东西中最普遍的、也是他在世界上最喜爱的东西——这就是生活。首先是他愿意过的、他最喜爱的生活;然后是随便哪种生活,因为活着总比不活更好:一切活的东西,出于它的自然天性,总是对死亡感到恐惧,总是厌恶死而爱生,由此看来,这个定义就是‘美就是生活’。”[7]以此来寻思疍民们的“迷恋”,很显然,他们的灵魂深处贮存着雷打不动的“喜欢过、愿意过”的生存选项。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它也就衍化为他们的人生常态。对于这种情形的出现,毫无疑问,它要与他们的民风民俗传统的积淀,与他们世代和大海打交道的经风雨抗海浪的历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否则,他们现在这种自足自乐地简单生活着的人生常态的形成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透过这“难以想象”,在价值意义的层面上,我们从中又能更深刻地体悟到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人生途程幸福与否,都不是常态,充其量只是某一时段或某一时刻感受到的一种刺激,无论大小重轻强弱,都是短暂的。而人生往往处在平淡与安宁的常态中,就如同我们追求伟大但实际上我们只能平凡一样。所以当央视镜头中出现那些愿意、喜欢自足自乐地简单生活着的北海疍家人影像并促人思考的时候,作为深化理性认识的参照平台,我们思绪的翅膀禁不住飞到了美国作家、哲学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生活哲学那里。梭罗在其著名散文集《瓦尔登湖》中说:“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8]梭罗先生为了践行他所言说的追寻,放弃优越而富足的城市生活,来到远离尘嚣的瓦尔登湖畔,独自盖房种地,与禽兽为邻,回归到一种最为简朴、充实且极富诗意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中。梭罗弃世于森林而生活两年的生命奇迹,不是通常我们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逃避现实的隐士之举,而是滤净自己思想杂质,使其生命变得更为深邃、纯净和美好的人生真谛的探究(譬如,他入住瓦尔登湖后,经常出门走访,回马萨诸塞州康科德作学术讲演,至始至终将自己置身于社会这个大家庭中)。就此,照我看来,梭罗返璞归真的举动与那些一直习惯于生活如旧的北海疍家人比起来,尽管是一种人生常态的有益探寻,但是,对于自足自乐的、简单生活的谋求,应当说与后者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映射出什么问题来呢?我认为,不论是域外,还是本土,在两者当中,均不乏世上古老真理的蕴含,那就是:活得简单方能活得自在。因为,假如人的许多精力为物质生活所操控,人就失去了快乐的感知和体验。惟有拥有简单的人,才会生活得快活;惟有拥有鲜活和自由心灵的人,才会生活得快乐。[9]央视镜头下那些疍家人的依然如故的生计选择,其实就是对这种如同雾里看花,水中捞月般灼见的最佳诠释。
[1]海城区宣传部.疍家人对《走遍中国》栏目组拍摄疍家婚礼专题片的反响[EB/OL].(北海市人民政府网)http: //www.beihai.gov.cn/11220/2009_11_23/11220_89943_1258967812562.html.
[2]莫玉琼.疍家渔歌唱进《同一首歌》——记七旬渔家阿婆麦九妹[J].北海日报,2004-12-29.
[3]闫祥岭.广西归侨渔民:“咸水歌”声表心迹,盛赞党的好政策[EB/OL].(新华网广西频道)http://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 2011-09/22/content_23756914.htm.
[4]肖欣.广西北海侨港镇归侨:有没有船都是“疍家渔民”[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1/10-19/3400245.shtml.
[5][加拿大]莱斯•斯特劳德.超越生存:海上吉普赛人[EB/OL].(亚太电视网探索频道)http://discovery.baidu.com/program_sch_info.php?id=561.
[6]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沿海行”栏目摄制组.北部湾明珠—北海(第107集)[EB/OL].(中国网络电视台)http://bugu.cntv.cn/documentary/C37137/classpage/video/20120503/100466.shtml.
[7][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论文选[M]. 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9.
[8][美]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84.
[9]覃德清. 试论南岭瑶族的文化智慧[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