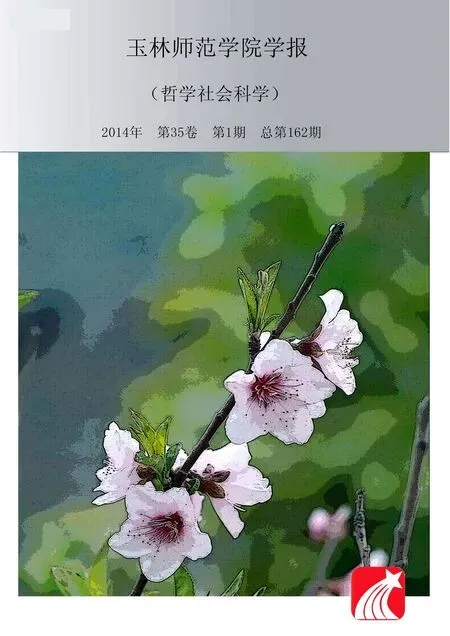伏羲氏与《周易》的“平安”精神考论
□詹石窗
(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四川 成都 610064)
伏羲氏与《周易》的“平安”精神考论
□詹石窗
(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四川 成都 610064)
生活与工作都以“平安”环境为前提。无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现实角度看,“平安”都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保障。由于“平安”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先民非常重视“平安”理论建设。仔细研读《周易》,不仅可以发现先民们对“平安”生活的渴求,而且能够从中汲取智慧,为当代建设“平安社会”服务。
伏羲氏;《周易》;平安
“平安”是人类生活与工作的基本保障。没有平安的环境,不仅生命存在要受到威胁,而且很多工作将无法开展。鉴于“平安”的特别重要,我们的先民很早的时候就在探讨“平安”问题。尽管“平安”这个概念是在《韩非子·解老》首先提出来,但作为先民的基本生存智慧,“平安”的理念却早已有之。无论是上古的神话传说,还是诸子百家的经典文献,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先民们对“平安”的渴求,尤其是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自始至终贯穿着古人追求“平安”的理路。
《周易》分经、传两个部分。“经”包括六十四卦符号系统与卦爻辞。“传”是对“经”的解释,共有七种十篇,所以古人将“传”称作“十翼”。《周易》从卦爻符号产生到最终成书,经历了很长时间。其源头要追溯到新石器中晚期时代的伏羲氏。所以,我们的“平安”理论考察也必须上溯到那个时代。
一、伏羲氏与“安贞吉”
伏羲,又称宓羲、庖牺、包牺、牺皇、皇羲、太昊、苍牙等。相传伏羲是华胥氏踩了天神大脚印之后怀孕而生。宋代罗泌《路史》卷十《太昊纪上》记载:太昊伏羲氏之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尝暨叔嫟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跧之,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孕十有二岁,以十月四日降神。得亥之应,故谓曰岁。生于仇夷,长于起城。”照此看来,伏羲的母亲“华胥”既是人名,也是地名,因其居住于华胥水边,故以地名为其名。她踩了天神大脚印,竟然怀胎十二岁,这当然是一种神话式的象征表现手法;不过,若稽考相关文献,或许会发现上古历法的一些奥秘。罗泌在解释“岁”的时候说:“或曰伏羲即木帝,故曰岁,十有二年而生也。木生于亥,十月在亥,复得亥时,其符皆至。《宝椟记》云: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地而孕,十二年生庖羲,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白髯委地。或曰岁,岁星十二年一周也。《说文》云:古之神圣人,母必感天而生子,故曰
天子。”①这段解释把伏羲看作“木帝”,也就是木星,中国古时候以木星为“岁星”,因岁星运动所形成的历法称作“岁星纪年法”。木星围绕太阳的公转周期为11.8622年。以地球为观测点,以相对不动的恒星为背景来观测岁星在天空的视运动,发现岁星约十二年绕天一周。从这个角度来看华胥氏怀胎十二岁,其实暗示的是岁星的运动周期。作为“木帝”的伏羲氏在娘胎十二年,象征着木星运动周期的圆满,而圆满意味着周期可以预测,也象征天体运动是有序的,彰显给人的印象就是平安。由此,我们可以说,伏羲氏降生神话象征着平安,因为它以圆满的周期为人们展示了大自然的一种秩序。
从名称来看,伏羲氏也蕴藏平安意蕴。“羲”为上下结构,许慎《说文解字》认为“羲”乃从兮,义声。其中,“兮”与“乎”均表示吹号的声响,“乎”是紧急吹号声,而“兮”则是气息微弱的吹号声,说明境况已经不再紧急。“义”的繁体作“義”,上“羊”下“我”。在甲骨文中,“羊”通祥,系祭祀占卜所显示的吉祥之兆;“我”像一种有许多利齿的武器,是“戌”的变形,表示护卫。占卜既得祥兆,又有武器护卫,也就预示平安。
对于“羲”字,许多学者从天文学角度予以解释,认为那是古代观察天象的写照。“羲”字上面的“羊”表示天文观察台悬挂着羊头,是图腾崇拜的符号表征;下面的“禾”与“兮”组合,既表示祭坛,也表示观察台,右侧的“戈”是武器,表示用武器护卫天文观察台。根据这样的描述,则伏羲氏当是一个天文观察专家。他在哪里观察呢?种种迹象表明是在东方,因为他是“木帝”,木在五行中居于东方,所以伏羲氏又表征日出东方。“羲”通“曦”,表示早上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发出光芒,谓之“晨曦”。先民们在晨曦照耀下,热情高涨,载歌载舞,表现出对太阳的无比崇拜,这种崇拜表达了先民们祈求平安的愿望,所以代表太阳崇拜的“羲”便蕴含了“平安”精神。
文献记载,伏羲姓风。《路史》卷十《太昊纪上》有一条注释:“孔演《明道经》云:燧皇在伏羲前,风姓,始王天下。是伏羲因燧皇之姓矣。三坟书言:因风之帝,木能生风,故为姓。”所云“燧皇”就是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他姓风,伏羲氏也姓风,可见伏羲氏是燧人氏的后裔。作为燧人氏后裔,伏羲氏的“风”姓也与平安意识关系密切。邓氏《姓书》云:“东方之帝木,能生风,故为姓。”②由此可见,“风”姓是因“木”而起,“木”于五行方位在东方,表征太阳升起,在深层次里寄托着太阳崇拜的观念,其崇拜初衷也出于平安渴求。
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伏羲氏代表着远古先民一系列的发明创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创造了八卦。《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伏羲氏为什么要作《易》八卦?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作《易》八卦的?对此,宋代经学家李杞认为是为了平安。他在《用易详解》卷十五《系辞下传》中说:“《易》之兴也,岂非有忧患而然哉!惟其有忧患,故其辞危。危惧者,则使之平安;慢易者,则使之倾侧。”李杞的意思是:《易》之兴起出于忧患。因为忧患,所以言辞险危,让人感到畏惧。营造危惧言辞的目的是要让读《易》用《易》者能够警戒小心,避免伤害,获得平安;如果没有危惧之心,对《易经》抱着轻慢态度,其结果就是自我垮台。可见,引领“平安”就是作《易》的初衷。李杞虽然是泛论作《易》宗旨,但也包括了创作“八卦”的目的,因为整部《周易》就是以八卦为基础,所以“作《易》是为了平安”这个判断可以合理推出“创作八卦也是为了平安”的逻辑结论。
在最初,八卦只是八个象征符号,并没有文字说明,我们难于确证其平安的意涵,但从后来的卦爻辞里,我们依然能够捕捉到远古先民追求平安的强烈渴望。《周易·坤》卦辞谓:
坤,元,亨……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这条卦辞的结尾明确使用了“安”字,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平安”;而“贞”就是正,“吉”即吉祥。以“安”为先,“贞吉”随之,说明“平安”具有决定性意义。
“安贞吉”三个字是《周易》卦爻辞对事物运动、发展结果的评判,具体而言就是对“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这个现象的一种预示,它具有什么启示价值呢?这牵涉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理解,所以我们必须从这句话的解读说起。
历史上,《易经》专家对于“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这句神秘的卦辞相当关注,进行了种种解释。魏晋玄学大家王弼在《周易注》卷一中说:
西南致养之地,与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东北反西南者也,故曰丧朋。阴之为物,必离其党,之于反类,而后获安贞吉。
王弼认为,西南方是养育万物的好地方,其功德与坤卦相同,所以说“得朋”;东北方与西南方相反,所以说“丧朋”。从性质上看,西南方是阴方,坤卦属于阴性之卦,阴与阴相遇就是“得朋”;阴与阴相离就是“丧朋”。在王弼看来,阴性的事物必须离开阴性的同党,而去寻求与之相反的阳性事物,最后才能获得平安、中正、吉祥。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王弼的注释进行发挥,他说:
西南得朋者,此假象以明人事。西南坤位,是阴也。今以阴诣阴,是得朋,俱是阴类,不获吉也。犹人既怀阴柔之行,又向阴柔之所,是纯阴柔弱,故非吉也。东北丧朋安贞吉者,西南既为阴,东北反西南,即为阳也。以柔顺之道往诣于阳,是丧失阴朋,故得安静贞正之吉,以阴而兼有阳故也。③
照孔颖达的看法,“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是假借卦象来指明人事。西南方向是坤卦之位,西南与坤卦都属阴,阴与阴相遇,这就是“得朋”;东北与西南相反,西南既然是阴,那么东北便属阳。以柔顺的“阴”去拜访刚强的“阳”,其结果虽然是丧失阴性朋友,却能够平安吉祥,因为这时的阴遇上了阳,彼此相兼而感通。
孔颖达的解释与王弼的解释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把阴与阴相遇称作“得朋”,把阴与阴相离称作“丧朋”,基于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思路,王弼与孔颖达都主张,阴应该求阳才能平安吉祥。
王弼与孔颖达的解释影响了易学界千余年。唐宋以来,关于“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这句话基本上都是遵循这样的思路进行解释的。直到民国时期,尚秉和先生作《周易尚氏学》④,一反以往的说法,他把阴求阳看作“得朋”,把阴求阴看作“丧朋”,即异性相遇为“得朋”,同性相遇为“丧朋”,其理论根据是《周易》的“十二辟卦”,指出“坤”在“十二辟卦”里居于西北亥位,阴气逆行,沿着西南方向前进,遇阳渐盛;若由东南向东北前进,则阳气渐失。这个说法可谓独辟蹊径,在理解“得朋”与“丧朋”问题上有根本性的不同;不过,在吉凶判断上则与此前的解释一致,这就是主张阴阳相偶才能平安吉祥。
追溯易学史上关于《坤》卦“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1)在八卦学说中,“平安”的判断乃是基于阴阳相偶、和合感通。(2)事物必须相辅相成,惟有相辅相成才构筑了平安条件。(3)追求平安生活必须寻求或者创造阴阳和合感通的环境。
二、从卦象图式看“平安”理趣
《周易》中的平安智慧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那么,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伏羲氏冥思苦想出来的吗?也不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周易》平安智慧是建立在卦爻符号的理解基础上的。所以,认识八卦起源和符号内涵,这是我们揭开《周易》平安理论奥秘的关键一环。
八卦是如何产生的?古人对此探讨已多。最为经典的论述要算《周易·系辞下》的一段话: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包羲”又称作“包牺”,即指“伏羲氏”。“包”通于“庖”,有庖厨的意涵,从这个角度看,伏羲氏本来是一个高级厨师,善于做可口饭菜,所以被尊为“王”。这个“王”字,既有领导者的意义,又有使天下兴旺的旨趣。在成为天下王以后,伏羲氏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文化建设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作八卦。按照《系辞下》的描述,八卦是在“三观”与“两取”前提下创作的。“三观”即观天象、观地法、观鸟兽纹理与适宜于地上生长的诸种物类;“两取”就是以近处的人体及远处的事物为象征。
伏羲氏通过观察,援取事物具体形象,升华为抽象表征符号,称作“观物取象”。这里的“物”就是宇宙间客观存在的万物,“象”就是万物的形象。伏羲氏通过仰观俯察,最终演绎出爻象与卦象。其中,根本的爻象是一阴(- -)一阳(—);基本的卦象就是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兌,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凡八类事物。
伏羲氏“观物取象”的工作对于当时民众的平安生活来说非常重要。只有通过观察,对自身以及周边环境深入了解,形成一定的表征符号,才能便于交流,避免危险,维护平安。伏羲氏正是在充分了解事物情况下才创作八卦的,因此八卦也就体现了先民们认知世界、洞察事物的基本思路与平安智慧。
八卦是怎样体现平安智慧的呢?《系辞下》“以通神明之德”提供了基本答案。“德”字,早期甲骨文写作“”。其外围是“行”,表示十字路口;中间是个大眼睛,表示洞察事物的穿透力。后来,“德”的意义有了扩展、引申,如《韩非子》称:“德者,道之功也。”这是把“德”看作“道”的功用能量。以此类推,“神明之德”就是神明的功用、能量。“神明”就是神灵,祂们具有佑助正道的功能。《孝经·感应》:“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唐玄宗注:“事天地能明察,则神感至诚而降福佑,故曰彰也。”⑤在先民心目中,以诚感神,意味着神明能够保佑平安。《系辞下》把八卦看作可以“通神明之德”,实际上等于认定了八卦可以通神,保佑平安。直到今天,许多人把“太极八卦图”悬挂在门上或其他重要处所,也具有辟邪安镇的用意。
《系辞下》在讲述八卦功能的时候,还用了“以类万物之情”一句,这是平安智慧的进一步体现。所云“情”,有欲望感情之“情”,也有事物情状之“情”,这两种“情”是不同的。根据上下文,可知《系辞下》讲的“情”指的是情状,“万物之情”就是万物的存在、发展状态。“以类万物之情”是说八卦具有表征万物情状的功能。换一句话来讲,八卦可以看作万物的映像。通过八卦,我们可以认识万物的本质特征,了解其基本状态,因此有助平安生活。
八卦是如何“类万物之情”的呢?这种“类”又是如何“运载”平安智慧的呢?《周易·说卦传》关于“先天八卦方位”与“后天八卦方位”的论述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
《周易·说卦传》称: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这里的“天地”指乾、坤,“山泽”指艮、兌,“雷风”指震、巽,“水火”指坎、离。此八卦中,乾、震、坎、艮,为阳;坤、巽、离、兌,为阴。皆两两相对,系平安秩序的基本符号表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坤》卦的“安贞吉”正是以阴遇阳为平安、吉祥。
对于《说卦传》这段话,前人概括为“先天八卦方位”。如朱熹在《周易本义》卷首即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方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兌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谓‘先天之学’也。”(其图式如下)
“伏羲先天八卦方位”既是“万物之情”的符号演示,也是先民们维护平安的思想表征。因为“先天八卦方位”既遵循了“观物取象”的感知路向,也体现了创制者逻辑推演过程中的“安贞吉”精神。《周易·系辞上》在论及八卦形成与功能时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谓“太极”就是“道”,这个“道”的本义就是“安”。在上古金文中,“道”写作“”,像一个十字路口埋着一个人头。为什么把人头埋在十字路口呢?原来古人打仗,甲乙双方有一方打败了,敌方首脑就被埋在十字路口。先民们相信,人是有灵魂的,死了就必须埋入地中,所谓“入土为安”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春秋时期,老子作《道德经》,对“道”
的意义进行哲理升华。该书第三十五章谓:“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所谓“大象”即“道”,而“执大象”就是信仰大道、奉行大道、固守大道。“天下往”是说圣人奉行大道,天下万物都归向大道。按照《道德经》的说法,天下万物归向大道,这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道是“安平泰”的。“安”当然是安全,而“平”就是太平,安全与太平合起来就是平安,可见老子讲“道”的要义还是平安。追溯一下“道”意涵的历史发展,就不难明白《周易》讲的“太极”所具有的平安精神旨趣,因为“太极”即“道”,反过来说“道”即“太极”,“道”具有“平安”理趣,“太极”便续存了“平安”意涵了。至于由太极化生的两仪、四象、八卦便无一例外地继承了“太极大道”的平安基因了。
先天八卦方位的功能,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天地定位”。在甲骨文中,定写作“”,宝盖头“”代表房屋,“”表示征战归邑,其造字本义是:结束征战,安居度日。《说文解字》称:“定,安也。”可见,“定”字本有“安”的意涵,而“安”同样也有“定”的意义,后来有“安定”或者“定安”的合成词,表明“安”与“定”的意义融通。既然“安”可以“定”,而“定”能够“安”,那么大《易》“先天八卦”的“乾坤”位置一确定,就意味着天下秩序有了符号表征的基本坐标。乾坤定南北,坎离界东西,而震巽、艮兌也两两相对有应,这就叫做“对待”,因对待而阴阳感通,正如夫妻彼此和合而能生子,安居乐业。
有“对待”就有“流行”。由“先天八卦”向“后天八卦”的演化就是“流行”。关于“后天八卦”,《周易·说卦传》也有一段话说明: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所谓“帝”即天帝,代表天地元气。这段话阐述“帝”的行进历程,也就是元气的流行情况。它出于“震”,生长于“巽”,彰显于“离”,致力用事于坤,成熟欣悦于“兌”,交配结合于“乾”,勤勉劳倦于“坎”,重萌于“艮”。由此可见,一元之气不断流行,通过八卦显示出来。
一元之气流行,所经八卦的具体位置如何呢?根据《说卦传》的解释可知:坎离定南北,震兌界东西,巽在东南,坤在西南,乾在西北,艮在东北。按照前人的解说,这个方位据说是由周文王确立的,故而称作“文王八卦方位”,因属后天行为,故而又称作“后天八卦方位”。(其图式如下)
后天八卦方位是因为先天八卦流行交感而成。
四正卦:乾阳之气动,坤卦中爻交于乾卦,则成离卦;乾中爻交于坤卦,则成坎卦;坎卦内爻与离卦外爻相交,则成震卦;离卦外爻与坎卦内爻相交,则成兌卦。
四维卦:艮阳之气动,艮卦之初爻、三爻与兌卦之初爻、三爻相交,则成巽卦;兑卦之初爻、二爻与艮卦之初爻、二爻相交,则成乾卦;震阳之气动,震卦之二爻、三爻与巽卦之二爻、三爻相交,则成坤卦;巽卦之初爻、三爻与震卦之初爻、三爻相交,则成艮卦。至此,“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变为“文王后天八卦”方位。这就是“流行”的大旨所在。
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向文王后天八卦方位转变过程乃是一个“交感”过程;而“交感”便意味着状态平安。因为“感”出于“咸”,这个“咸”本有“安”的旨趣。《周易·咸》之《彖》称: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这一条《彖》辞指出:咸的意思就是交感;阴柔之气往上,阳刚之气往下,二气交感有应,不分彼此,亲密无间。交感的时候,如艮山之稳重,似兌泽之灵动,就像男子以礼下求女子,所以能够得正欣悦,亨通吉祥。天地交感,形成了万物化育生长;圣人感化人心,造就了天下和平昌盛。⑥《彖》辞由“取女吉”进而论述天地之感,所言“吉”以及“天下和平”都包含着平安意涵。
由上述分析可知,伏羲氏先天八卦向文王后天
八卦方位演变,是八卦阴阳之气在交感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伏羲先天八卦方位侧重于表征万物的对待有序,而文王后天八卦方位侧重于表征万物的流行变化。不论是“对待”还是“流行”,八卦都指示了平安的合理状态。从这个意义来讲,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都是最好的平安吉祥物。
当八卦两两相重而成为六十四卦的时候,平安智慧便随着六十四卦的布列与周转而得到传递与能量补充,所以我们看到卦爻辞以及“十翼”里,作者通过爻象与卦象,展示事物的曲折运动、发展变化过程,告知人们什么状态下有危险、如何避免危险,如何走出困境,最终获得平安。《周易》以辩证思维方式和“中道”精神,分析判断各种情境,为人们提供了合理行动的方向,故而是一部切实可用的平安生活指导的大智慧宝典,身边备此一书,时时翻阅,当可化险为夷,“保和太和”,提升生活之境界。 ■
注:
①罗泌《路史》卷十《太昊纪上》,《四库全书》本。
②罗泌《路史》卷十《太昊纪上》,《四库全书》本。
③孔颖达:《周易注疏》卷二,《四库全书》本。
④详见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唐明皇:《孝经注疏》卷八,《四库全书》本。
⑥参看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新一版,第239页。
[1][宋]罗泌. 路史(卷十)[M]. 四库全书.史部.
[2][唐]孔颖达. 周易注疏(卷二),[M].四库全书.经部.
[3][民国]尚秉和. 周易尚氏学(卷二)[M]. 中华书局,1980.
[4][唐]李隆基. 孝经注疏(卷八)[M] . 四库全书.经部.
[5][当代]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卷五)[M].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吴庆丰】
On Fu Xi and Safety Spirit in "Book of Changes"
ZHAN Shi-chuang
(Religion · Philosophy and Social Research Innovative Base,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610064)
Life and work both look on “safe environment” as precondition. Whether it i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r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safety would be seen as the first guarantee of human existence. Due to this great significance, Chinese ancestor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building of “safety” theory. Through reading the "Book of Changes" carefully, we not only can find out ancestors’ desire for safety, but also can learn wisdom from it and take advantage of it to help build a contemporary “safe society”.
Fu Xi; "Book of Changes"; safeness
B221
A
1004-4671(2014)01-0002-06
2013-08-26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百年道教研究与创新工程”(批准号:09@ZH011)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道学精华集成”(批准号:09JZD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詹石窗(1954~),男,福建省厦门市人,哲学博士,现为国家“九八五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