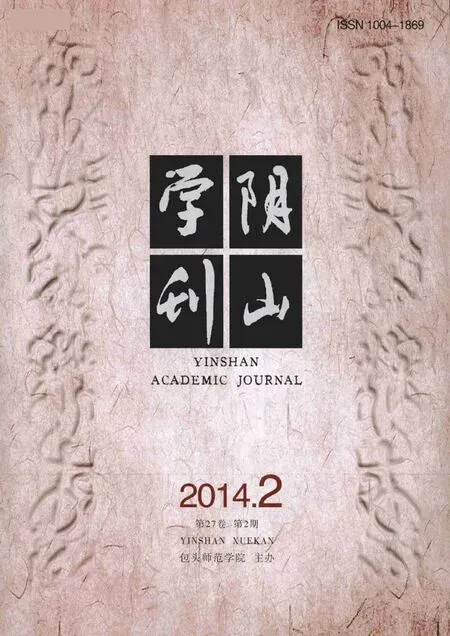传播力与媒介使用者的关系变迁
——新媒体语境下对传播学经典问题的再思考
马 宁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一、引 言
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不断催生出丰富多样、具有变革意义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模式,而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实践,也在伴随着这些新形态、新模式不断发生着变化。除了关注新鲜事务本身,对传播学经典要素间关系变迁的观察思考,也是我们在推介新的传播技术、发现新的传播形态、解构新的传播模式之外,研究新媒体、新规律和新现象的一种有效视角。
在传播学研究中,对于效果和受众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对“传播现象对传播对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类经典问题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探讨,问题所涉及的传播学要素、理论、方法和案例及其组合方式也非常丰富多样。本文选取“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这两个要素进行组合,通过探讨两者的关系变迁,尝试对新媒体的发展进行解读,同时也是对传播学经典问题在新语境下的再思考。
二、非主流的“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
“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这两个要素,在大众传播主导下的传播学经典研究体系中并非主流。一方面,传统媒体在强调传播效果和影响力的同时,却有意回避其商业性、目的性和政治性,而力求用新闻专业主义、组织管理和媒介伦理等规范其内容生产和传播,因此源于政治学范畴Power的“传播力”并未在传播学发展初期成为主流,然而在传播实践中,这种通过传播影响别人的能力,却一直是传播主体所追求和向往的;另一方面,源于广播听众的“受众”Audience一词,长期代表着大众传播的主要对象,其被动和单一的词意形象地反映了传播学经典研究中客体的特点,但是在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推动下,受众的行为和习惯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信息消费中对于媒介的选择和使用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并且,从“受众”到“媒介使用者”的变化不只发生在互联网时代,早在电视媒体高度发达的20世纪后期,“受众”就已经开始分化,但凸显主体性的要素符号“媒介使用者”,并未在大众传播的主导下成为主流。
因此,选择“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这两个要素进行组合,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变迁不会只是在外力作用下的被动反应,也包含两者在自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的主动结果。为了规避要素本身的超前性和变革性,我们首先需要将大众传播语境作为起点,对“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进行阶段性的界定。
(一)被“传播力”单向作用的“媒介使用者”
“传播力”是个典型的具有大众传播特色的概念,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对于“传播力”的使用,多指涉的是媒体、企业、政府、组织等主体在大众传播模式下影响受众个体认知和行为的能力。曼纽尔·卡斯特在2009年的《Communication Power》一书中,对于Power一词做了政治学的溯源,指出Power是在政治语境下影响和改变他人的能力;因此他基于“网络三部曲”中对网络社会的宏大叙事,探讨了如何利用网络社会中的传播来影响人们对政治的认知、判断和选择,这种能力便是他所定义和理解的“传播力”,然而受众个体与这种“传播力”依然是单一、单向的被作用关系。
不过,曼纽尔·卡斯特在新作中也留下了贴近现实的观察和思考:个体与传播力的关系在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带来的变革中必将发生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将不仅分布在政治领域。要想正确认识这种关系的变化,必须对于“受众”有新的认识。在大众传播时代,平面媒体和广播电影电视沿商业轨迹的发展逐步唤醒和培养了受众个体对媒介选择、内容质量、个性化定制化的诉求,被动的“受众”已经逐渐转变为主动的“媒介使用者”。
然而,符号要素的语义变迁,始终无法逾越其语境所处的阶段。“媒介使用者”与“传播力”的初始关系,反映了大众传播主导下的传播学经典研究体系的特点:传播力的拥有者集中于强势的大众传播媒介,媒介使用者与传播力之间是单一、单向的被作用关系。在布尔迪厄对媒介场域与其他场域相互作用的批判中,他曾期望媒介使用者中的知识分子能够与掌握传播力的大众媒介对立起来,以催生媒介的变革和场域发展的希望。发生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事实证明,最终改变“媒介使用者”与“传播力”关系的,是中性的技术;而布尔迪厄寄予希望的、具有潜在影响力和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在与大众媒介的合作和对立中,欣然接受了大众媒介赋予和分享的传播力,之后与大众媒介完成了多方共赢、相安无事的合谋——布尔迪厄着重阐述的“知识分子记者”和现实中与传统媒介唇齿相依的意见领袖,正是其中的代表。在大众传播的语境下,泛化的“媒介使用者”仍然被传统媒介强势的“传播力”单一、单向地作用着。
马略卡岛(Mallorca)位于地中海,面积3640平方公里(南北75公里、东西100公里),马略卡岛首府帕尔马。马略卡岛上到处是砂质的海滩、陡峭的悬崖、种植着橄榄或是杏树的田野等自然风光。
(二)被中性技术唤醒的“媒介使用者”
被布尔迪厄们寄予厚望的“媒介使用者”中的知识分子,并非全部选择与传统大众媒介合谋。这个群体对于“传播力”的觉醒和诉求,也许始终存在,或者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如大众传播语境下受时空、资源限制的群体传播里,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变革。这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媒介使用者”,属于从受众中分化出来的群体,在“传播力”与“媒介使用者”的关系变迁中,他们或者选择了阶段性的妥协、或者选择了持续性的融合,或者在静候与争取变革的到来:中性的技术对媒介形态和传播模式的影响,便是他们所等待的。然而,在信息技术革命到来前的漫长阶段,大众传播主导的资源配置和话语权体系牢牢把控着“传播力”,知识分子们寻求的变革在与传统媒介的博弈中常常异化为布尔迪厄所描述的场景:“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1](P41)
文化资源、社会结构、商业资本同传播主客体的复杂关系及相互作用,必然会对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的关系变迁产生影响,然而讨论其过程和结果需要宏大漫长的社会学叙事,并且这些影响对于变迁的作用,不如信息技术更具革命性和中立性。从事务发展的自然规律来看,“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理应从单一、单向的被作用关系,进入多元、多向的相互作用关系;从“媒介使用者”中最早觉醒的知识分子,扩大到逐渐被唤醒的普罗大众——这些曾经的客体对于自身“传播力”和平等对话权的认知和诉求,是关系变迁的主观动力。“传播力”从理所当然地被占据绝对优势的大众媒介所拥有,进入到了“媒介使用者”从失衡弱势转为追求自身的“传播力”、并与大众媒介对话和相互作用的新阶段。这种关系变化,在大众传播模式覆盖广、受众量级多、媒介资源高度集中、信息传播严重不对称的区域尤为凸显。而中性的技术,扮演了变革中最为关键的角色。
在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的关系变迁中,结果似乎已经显而易见,而过程也因此更加值得关注:在要素选取时我们已经讨论过,“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自身具有超前性和变革性,但是通过对其在大众传播语境中的界定,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组合无法通过在特定语境下的自发展带来根本质变。那么,扮演关键角色的中性的技术,究竟为媒介变革带来了怎样场域级别的影响?
三、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的关系变迁动因
关于信息技术革命和新媒体发展,学界和业界的研究实践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在此我们主要基于大众媒介、信息网络和传播场域三个维度的变化,勾勒出“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关系变迁的过程环境,包括大众媒介的数字化和关系化、信息网络的社交化和媒介化、多场域复合扩张与连续在场。
(一)大众媒介的数字化和关系化
数字化使媒介的内容生产、存储和传输打破了以往的时间和地域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降低了媒介场域的准入门槛和大众媒介的资源垄断程度。短期内,大众媒介的传播力因数字化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多媒体呈现、非线性制播、跨区域覆盖、全媒体整合和运营效率提升让传统大众媒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数字化同时催生了新媒体和媒介平台的出现,技术突破使长期被传统大众媒介垄断的媒介资源和商业资本得到了新的迁移空间,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的关系也开始产生实质性变革,新浪微博在中国的成功以及微信当前的炙手可热就是最好的实例。
媒介使用者对传播力的觉醒和诉求,让传统大众媒介长期习惯和赖以生存的中心化、广播式传播遭遇巨大挑战,大众传播主导的资源配给和资本流通开始受到新媒体和媒介平台的持续冲击。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趋势,让大众媒介逐渐意识到传播力已经开始向媒介使用者和其他要素迁移,传统大众媒介已无法全面把控内容生产、存储、传输、增值的各个环节——即使是大众媒介最为核心的内容生产环节,以中国为例,根据互联网数据中心DCCI发布的数据:在2010年6月,用户产生的内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在互联网的流量达到50.7%,首次超越专业制作内容(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的流量。[2](P25)
伴随数字化应运而生的交互性,为媒介形态和传播模式带来了技术、内容、关系等多个层面的互动可能:技术层面的互动,是在底层对传统广电技术单向传输特点的革新,下行通道与上行通道的实时共存让交互成为必然,不过这种技术革新对最终用户而言依然是不可见的;内容层面的互动,让媒介的核心资源内容,在生产、存储、传输、增值、监测等各个环节实现了非线、实时、延时、精准、跨区域和多平台的革新,最终用户在信息消费的过程中体验得到大幅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新技术让媒介使用者可以更加便利、更为有效地实现从消费信息到生产信息的扩展;关系层面的互动,从早期主要集中于受众对传播效果的反馈,逐步扩展到用户制作内容UGC、个性化定制信息消费需求、媒介使用者信息抓取与分析等细分领域,在媒介使用者传播力不断提升和社会化网络的社交媒体趋势下,大众媒介的中心化、广播式的信息传播特点需要面对媒介使用者去中心化、碎片化的信息消费趋势,大众媒介不得不重视关系层面的互动,来重塑与媒介使用者的关系,以保持其传播力以及对商业资本的吸引力。
大众媒介的关系化,是顺应新媒体研究者和互联网从业者热衷的媒介产品化运营趋势的一种表现:媒介不再只关心产品开发与生产层面的问题,更需要关注用户体验和用户关系管理。在信息技术的助推下,媒介使用者的传播力增长,与新媒体和媒介平台的发展迅速结合,形成了打破传统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全新传播单元。并且,传统大众媒介在议题设置和内容供给上强势的垄断性,已经被具有自主性和网络性、以媒介使用者为中心的传播单元所打破,当微信朋友圈在以关系构建的封闭环境中实现各具传播力的信息流通时,传统大众媒介不仅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关系化的转变来让这些传播单元帮助其传播媒介生产的内容,还需要琢磨如何让这些传播单元反哺其内容生产。
(二)信息网络的社交化和媒介化
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让信息网络中的信息总量和信息流通速率不断发生几何量级的跳跃。进入2013年,全球每分钟IP数据传输量达639800GB,每分钟有2.04亿封电子邮件寄出、每分钟Twitter上新增10万条新信息而Facebook有600万人做点击阅读动作。[2](P11)
信息总量的扩张,仍未对信息网络的整体结构产生本质层面的冲击,但是其运行趋势和复杂程度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在本质层面,信息流通仍然是信息网络运行的基本特征,而信息单元之间的社会交往,是信息网络运行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动力。
然而,信息单元间的信息流通并非对等和顺畅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节点作用。布尔迪厄在讨论媒介场域与其他场域的辩证关系时曾指出,在媒介场域与其他场域的相互作用中,媒介场域既表现出其独立性和斗争性,又表现出中介性和低自主性。媒介场域在信息网络里中心化、广播式的节点作用,一方面让传播单元之间的连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控了单元间的信息流通——媒介使用者与传播力的关系孱弱和大众媒介对传播资源及商业资本的垄断更加剧了这种状况。
信息网络的社交化,一直是媒介场域之外的传播主体所追求的,然而受到地域、资源、时间和资本的限制,尤其是媒介使用者与传播力的关系孱弱,使这种追求的效果甚微。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首先使信息网络中的信息总量和个体的传播力及连接的便利性都得到大幅提升。媒介场域之外的传播主体,比如企业、政府、社会组织和团体等,其结构化的传播单元也在丰富与发展之中。如新媒体研究者和互联网从业者所热衷的,他们除了对媒介场域给出了媒介产品化运营的建议,同时也对其他场域的传播主体提出了信息产品媒介化发展的期望。这些信息产品具备了主体性、信息流、通道、使用者的特征之后,一个结构化的传播单元就已经初具雏形,在进入媒介场域与具备或正在形成传播力的媒介使用者建立社交关系后,信息网络中必将出现更多媒介化的传播主体。微信公众平台的火热,正是这一趋势的最好例证。
媒介使用者并非单独存在于媒介场域,然而在这个场域里,其消费和生产信息的意识和认同是最为强烈的。这也是其他场域的传播主体必须以媒介化的方式进入媒介场域的重要原因:在这里它们可以通过媒介化的方式实现其社交化的扩张,与合适的媒介使用者建立关系,使其消费、生产和传播信息。这种策略的成功实施,与媒介使用者和传播力的关系变迁是相辅相成的,中性的技术和随之而来的具有社交性质的媒介平台,如Facebook、微博和微信,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在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中,企业、政府、社会组织和团体,甚至是大众媒介的年轻从业者、媒介使用者中伺机而动的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关系决裂的意见领袖等个体,都开始借助新兴的信息传播技术和具有社交性质的媒介平台,完成自身传播单元的媒介化,并在发掘更多媒介使用者、不断集聚传播力的过程中,推进媒介使用者和传播力的关系变迁,一个良性的有机循环在信息网络的媒介场域开始了持续不断的运转。
(三)多场域复合扩张与连续在场
在大众媒介的数字化和关系化、信息网络的社交化和媒介化的共同作用下,媒介场域和其他场域出现了多场域复合扩张的情况:信息网络中的传播主体不断增多、传播力持续集聚和增长。尤其是一部分媒介使用者借助与传播力多元、多向的相互作用,发展成为跨区域、跨行业、跨组织的传播主体,这种示范效应进一步激化了媒介使用者的传播力意识和诉求,加速了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的关系变迁。国内近年来的自媒体热潮,引发了媒介从业者、意见领袖、知识分子的积极讨论和参与,也形成了更为丰富的信息网络覆盖和信息流通方式。
然而,泛化的传播主体并非是新兴信息传播技术的直接产物,拉扎斯菲尔德早在1944年的《人民的选择》中,就运用二级传播理论强调了“意见领袖”的作用,罗杰斯则用升级的多级传播理论把“意见领袖”扩展为大大小小的传播中介,并用“影响流”来进行概括。比较于大众传播语境中的“意见领袖”和“影响流”,中性的技术在新媒体语境里,降低了媒介使用者成为“意见领袖”的门槛、消解了新兴传播主体对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依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时间和空间对个体传播力的严重限制。由此,每个媒介使用者都可能成为传播力的真正拥有者,并在媒介场域和媒介场域之外的其他场域进行平等、多向的对话和传播的生成及延续。覆盖多场域的信息流和泛化的传播单元,让媒介使用者持续的信息消费和生产成为可能。在由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社会化网络、基于位置的服务等新兴传播技术革新的信息网络中,无处不在的媒介(Media Anywhere)和持续不断的信息流(Information of flows)已经成为技术现实,而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的关系变迁,将让这种技术现实升级为社会现实。
曼纽尔·卡斯特在描绘全球化的网络社会图谱时,引入了“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永恒的时间”(timeless time),而让时空发生如此压缩的(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是信息的流动(information flows)。因信息的流动成为当今社会组织的中心,世界各地能够“整合在连接了它们最有活力部分的国际网络之中”。[3](P136)但是,在传统大众媒介仍然把控信息网络关键节点的情况下,媒介使用者只能习惯被大众媒介的传播力单一、单向的作用,“受众”的身份难以真正变为对信息产品和信息流动具有自主性和选择性的“媒介使用者”。如果更为广泛的个体未能分享全球化信息网络的革新红利,全球化和网络化难免陷入虚无和马太效应的迷思之中。
在技术现实的层面,云计算让信息网络跨越时空的限制,电信网、广电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让信息网络跨越网关的阻隔,PC、手机、平板和电视的多屏融合让信息网络跨越终端的屏障。这种“一云三网多屏”的技术现实,让信息流可以更加顺畅地在多个场域持续传播,传统大众媒介的中心化、广播式的节点作用被多场域复合扩张的信息网络进一步消解,相应的媒介资源和商业资本也开始发生迁移。媒介使用者对传统大众媒介的惯性依赖,开始受到更为丰富的信息消费和生产模式的持续影响;曾经的受众不再被客厅中的电视、轿车上的广播、餐桌旁的报纸和影院里的电影以固定时空和垄断信源的模式所牵制,媒介使用者面对的是有着丰富选择和多样交互的连续在场体验。
率先由技术现实构建的无处不在的媒介(Media Anywhere)和持续不断的信息流(Information of flows),提供的正是这种连续在场的新媒体语境。媒介使用者和传播力的关系因此不断发生微妙的变化,媒介使用者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力开始产生质疑,并对自身的传播力逐渐产生诉求:这个过程,不仅发生在意见领袖和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具有社交媒体性质的媒介平台和移动终端让每个媒介使用者都具备了拥有传播力的可能。这种可能,不同于大众传播语境下的群体传播,实现了跨越时空、摆脱资源限制的蜕变。由技术现实构建的连续在场,终将演化为由媒介使用者的传播力构建的无处不在的媒介和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中心的信息网络,将升级为以媒介使用者为中心的信息网络——这是一次从大众传播到社会化传播的剧变,也是一场媒介使用者和传播力关系变迁的革新。从单一、单向的被作用,到多元、多向的相互作用,媒介使用者与传播力新的关系让我们对无处不在的媒介和持续不断的信息流有了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
五、“媒介使用者”的“传播力”想象
媒介使用者和传播力多元、多向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单体现在媒介使用者从大众传播语境中被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力单一、单向的作用,转化为新媒体语境下对自身传播力的觉醒和诉求;对应于大众媒介的数字化和关系化、信息网络的社交化和媒介化、多场域复合扩张与连续在场,媒介使用者通过自身和多元的传播力相互作用,逐步在应证媒介使用者全程介入传播、自身媒介化以及成为信息网络中传播单元的可能性。
在信息传播发展和媒介变革的过程中,新媒体语境下信息消费的个体被赋予了生产消费者(Prosumer)的身份符号:生产消费者是一个由“生产”和“消费”和“者”组成的合成词[4](P27)。这个身份符号是媒介使用者和传播力多元、多向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形象表征,一方面媒介使用者需要在消费信息的过程中被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各类传播单元的传播力所作用,另一方面媒介使用者也要通过不断生产信息实现自身传播力的价值持续传递。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使用者和传播力的角色和作用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借助这种多元、多向的相互作用,由媒介使用者的传播力构建的无处不在的媒介和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将让连续在场的技术现实变为社会现实。
信息网络的传播现象,从以大众媒介为中心、以技术产品为中心,终将发展为以人为中心——《连线》杂志在上世纪末关于“从人到人的传播”的预言,已经在技术领域成为现实,“媒介使用者”与“传播力”的关系变迁,将让这个预言在更多领域得到验证。
六、反思与展望
回归“传播现象对传播对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个经典问题,在媒介使用者成长为传播主体的语境下,传播力与主体已经发生了多元、多向的相互作用。我们对于“影响”的判断,也可以从收视率和发行量等大众传播模式的统计数据,扩充为对各类传播主体所在单元的传播效果进行大数据汇总。传播力与媒介使用者的关系变迁,是信息技术、新媒体和传播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借助“媒介使用者”的“传播力”想象,对于“传播现象对传播对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尝试一种更为关注质量而非数量的反思。在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中我们会发现,媒介使用者的成长伴随着大众媒介对传播力的强势诠释和媒介使用者逐渐丧失自主意识的受众化趋势。对于伴随着“一云三网多屏”长大的新一代年轻群体,无处不在的媒介和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形成的连续在场效应,是否会让分化的媒介使用者对集体无意识和娱乐行为更加沉迷?
在社会诚信缺失、身份认同混杂、虚拟与现实背离等现象凸显的地区,我们对于传播现象对传播对象的影响价值不得不持理智的批判态度。“媒介使用者”与“传播力”的关系变迁,是否会加剧大众传播语境下的“娱乐至死”和“消逝的童年”在新媒体语境中的蔓延?“相比权威不容置疑、个人选择匮乏、信息更为同质、交互成本更高的时代,难道一个有着纷繁信息、更多选择,并提供了挑战权威、人际交互、信息过滤的有力工具的时代,反而让个人变得更加无所适从、更加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5](P107)
媒介使用者和传播力的关系变迁,同时意味着媒介伦理和责任感的迁移。无处不在的媒介和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完成了信息网络中量的跃变,也有可能带来质的退变。对于媒介使用者和传播力的关系变迁而言,取代大众媒介成为更多传播单元中心的媒介使用者,会因为传播力的权重而影响不同的媒介使用者;传播力集聚效应强并对传播力的可持续发展重视的媒介使用者,会逐渐成为更多媒介使用者的代理人——信息总量的爆炸和信息来源的多样,让信任而非信息成为维系媒介使用者与传播力关系更为重要的因素。这是大众传播语境下的把关人,转化为新媒体语境下的代理人的一种表现,这种转化与传播力和媒介使用者的关系变迁密切联系。
传播力和信任代理,将成为未来更加复杂的信息网络中,媒介使用者进一步分化的重要表征;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资源配置变迁,也将与不断发展的信息传播技术,共同决定传播力与媒介使用者关系变迁的新方向。
[1]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腾讯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研究所.中国网络媒体的未来[EB/OL].http://tech.qq.com/a/20131122/015404.htm#p=1.
[3]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王亚炜.生产消费者对品牌塑造的价值分析[J].商业时代,2012,(23).
[5]何威.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